【摘 要】该文利用实物版本学的方法,通过对十八部《咫进斋丛书》复本的考察,推翻了此前对该丛书“初刻与重刻”两个版本的认定,证明此前所谓“初刻”实际上是“盗版”翻刻,而所谓“重刻”才是“原版”初刻。这两个本子又都可以区分出多个不同的印次。
《咫进斋丛书》(以下或简称《丛书》),是清末藏书家姚觐元(1824-1890)[1]所刻书,陈澧(1810-1882)认为它“别择精而校雠善”[2]。该丛书已印行者共三集,另有第四集朱、墨印校样本存世[3]。
2008年,王曦发表《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一文,首次公开指出《咫进斋丛书》有两种版本。文中并以所校《四声等子》为例,认为错讹较多的当是“初刻本”,错讹较少的是校勘后的“重刻本”。[4]2021年,马珂发表《〈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一文,对王曦的观点表示认可,并以《丛书》中所收之《小尔雅疏证》和《中州金石目》二书为证,总结“初刻本与重刻本”的两点不同分别是“序跋的增入”和“内容的校改并重刻”。[5]然而,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仅以文字错讹的多少来判定两个版本何者为初刻、何者为重刻,根本无法成立。
王、马二人简单的认为,错讹多即“初刻”,错讹少即“重刻”,其实是默认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这两个版本都是咫进斋所刻,只有这样,重刻之时才会去对初刻进行优化。但仍不能绝对保证重刻就必然较初刻错讹更少。
退一步讲,假令重刻确实是错讹更少,又何以认定这两个版本都是出于咫进斋所刻呢?从常理上来说,实在是没有这种必要。从版刻史的实际来看,也鲜见此类案例。马珂根据陈澧所作序,解读说:“从清光绪七年陈澧序也可以看出《咫进斋丛书》是如何汇刻成书的,即是单种刻印再汇成一集,再以’集’汇成丛书的成书模式,所以会出现在丛书汇印之前,其单种也有印刷出版的情况,结集而成的《咫进斋丛书》也就存在着初刻本与重刻本之分。”前几句言《丛书》的“成书模式”基本能够成立,但末一句却显得突兀。从所述《丛书》的汇印过程来看,顶多能推论出《丛书》所收书有单印本与汇印本之分,而不是“初刻与重刻”的区别。
总而言之,我们对《咫进斋丛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实有很大的疑问。因为相关记载的付诸阙如,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恐怕只能藉助实物版本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复本的比较分析,来获得一点蛛丝马迹。
一、《咫进斋丛书》复本十八部之调查
《咫进斋丛书》既有两个版本,且刻印时间又在光绪以后,所以刷印数量当较一般丛书为多。检索今日各地所存,其复本当在二百部以上(包含残本)。[6]限于时间与条件,我们仅以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十八部以“咫进斋丛书”之名著录者为考察对象,[7]其零种以本书书名著录者则不在此内。
此次所考察之十八部《丛书》,八部藏国图,十部藏北大。先述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复本八部
1.索书号:8197
此部两函九册,收书十六种五十一卷。书根题写册号,首册且书丛书名。
所收书依次是:第一册,《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第二册,《说文引经考》二卷坿补遗;第三册,《说文答问疏证》六卷;第四册,《小尔雅疏证》五卷;第五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二卷、《大云山房杂记》二卷、《销毁抽毁书目》二卷;第六册,《凤墅残帖释文》八卷;第七册,《中州金石目》四卷坿补遗;第八册,《务民义斋算学》十一卷;第九册,《咽喉脉证通论》一卷、《瘗鹤铭图考》一卷、《苏斋唐碑选》一卷、《三十五举》一卷《续》一卷《再续》一卷。
书前有总目一纸,首行题“初印咫进斋丛书总目”,钤“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长方。内钤“国子/监印”满汉文朱方,又有“国子监南学书/光绪九年二月/查过准部齐全”朱文戳记。首册有“京师图书馆藏”朱印牙签,题作“清光绪初年刻”本、“五十一”卷“九”册、“清监书”。
其版式为:左右双边,上黑口,双对鱼尾。版心下镌“咫进斋丛书/归安姚氏刊”。半叶十三行,行廿二字。
2.索书号:8196
此部四函三十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为三集。书根题写册次,首册又题有丛书名。
第一集十三种四十一卷:《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孝经疑问》一卷、《说文答问疏证》六卷、《瘗鹤铭图考》一卷、《苏斋唐碑选》一卷、《姚氏药言》一卷、《咽喉脉证通论》一卷、《务民义斋算学》十一卷、《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二卷、《大云山房杂记》二卷、《棠湖诗稿》一卷、《春草堂遗稿》一卷。
第二集十一种二十七卷:《小尔雅疏证》五卷、《说文引经考》二卷坿补遗、《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古今韵考》四卷、《前徽录》一卷、《中州金石目》四卷坿补遗、《三十五举》一卷《续》一卷《再续》一卷、《安吴论书》一卷、《寒秀草堂笔记》四卷。
第三集十三种二十二卷。《礼记天算释》一卷、《孝经郑注》一卷、《尔雅补郭》二卷、《说文新坿考》六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说文校定本》二卷、《四声等子》一卷、《销毁抽毁书目》一卷、《禁书总目》一卷、《违碍书目》一卷、《慎疾刍言》一卷、《阳宅辟谬》一卷、《清闻斋诗存》三卷。
第一册冠以“丛书”书名页,楷书题“咫进斋/丛书”,下有“咫进/斋印”木印,背面题字两行“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次为《丛书》“序”一叶,无题名,版心镌“序”字,落款署“光绪七年番禺陈澧序”。次为“总目”二叶,题“咫进斋丛书总目”,分三集依次罗列所收书之书名及卷数。
其后为第一集书名页,A面楷书题“咫进斋丛/书弟一集/归安姚氏校刊”,B面题字两行“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次为“弟一集目”,首行题“咫进斋丛书弟一集”,下列该集所收书之书名及卷数。后即为该集所收书。
第十一册《小尔雅疏证》,前为第二集书名页,A面楷书大字题“咫进斋丛书/弟二集”,又小字署“彦侍方伯/雅命/弟龚易图/署签”,下有“易图”木印。B面题字两行“归安姚/氏校刊”。次为“弟二集目”,首行题“咫进斋丛书弟二集”。其后即该集所收书。
第二十一册《礼记天算释》,前为第三集书名页,A面楷书大字题“咫进斋丛/书弟三集”,又小字署“彦侍方伯命翕题”。B面题字两行“归安姚/氏校刊”。次为“弟三集目”,首行题“咫进斋丛书弟三集”。其后即该集所收书,惟将《禁书总目》置于《慎疾刍言》后与目录次序不同。
第七册《瘗鹤铭图考》之后,有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文共四叶,本应在第六册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后,而误置于此。第十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中有“十二章图”两组,一组为“十二章分图”六叶(对应卷一),一组为“历代十二章图”(对应卷二),第一组首叶首行镌“十二章图”,此部误置第二组第三叶于第一组第三叶之后。
所收各书前,除《安吴论书》外,均有书名页,半数以小篆题写,皆无署名。
内钤“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3.索书号:38185
此部二十四册,收书三十六种八十七卷,亦分三集,较上一部缺第二集《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书根题写册次及当册书名,首册又题丛书名。据知,此部原为二十六册,今缺第十三、十四两册,当即《说文检字》部分。
此部无第一集书名页及“弟一集目”,误置“弟二集目”于《〈小尔雅疏证〉序》后,又误置《礼记天算释》书名页于第三集书名页前。
此部又无《孝经疑问》书名页,误置《销毁抽毁书目》书名页于《瘗鹤铭图考》书前,误置《〈棠湖诗稿〉跋》于正文前,误置《说文引经考》书名页于卷下之首,误置《孝经郑注》、《尔雅补郭》二书书名页于《〈礼记天算释〉序》前,缺《〈说文新坿考〉序》,《书目总跋》二叶本应在《违碍书目》之后而误置《销毁抽毁书目》部分第二叶后。
第八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一种,其次序本应为:书名页、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序、十二章图、卷一、卷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跋。此部误订上一种《务民义斋算学》之《造各表简法》于《图说》册前,又误置下一种《大云山房杂记》书名页及《刻〈大云山房杂记〉序》于《〈图说〉序》之前,且误置《图说》书名页于《十二章图》之后,误置《〈图说〉跋》于《十二章图》之前。此部该种之次序即错乱为:《造各表简法》、《杂记》书名页、《刻〈杂记〉序》、《〈图说〉序》、《〈图说〉跋》、十二章图、《图说》书名页、卷一、卷二。
内钤“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4.索书号:39205
此部二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无字。
此部缺“第三集目”一叶。
朱士端《〈说文校定本〉后叙》两叶,本当在第二十册《说文校定本》之末,此部误置第五册《说文答问疏证》卷六后。第十七册《孝经郑注》本应有《〈孝经郑注〉叙》、《传》各两叶,此部重复《叙》之第二叶,脱《传》之第一叶。
内钤“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5.索书号:40449
此部四函三十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集次及当册书名。
第十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两组“十二章图”,误置“历代十二章图”第三叶于“十二章分图”第三叶、四叶之间。
内钤“饮/冰室”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6.索书号:41966
此部三函三十二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集次及当册书名。
第十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两组“十二章图”,误以第二组“历代十二章图”在前,而以第一组“十二章分图”在后。第二十册《三十五举校勘记》两叶,本应在《三十五举》正文后,而误置《续三十五举》正文后。第三十一册《慎疾刍言》之书名页,本应在同册《违碍书目》之《书目总跋》之后,而误置《书目总跋》之前。
内钤“国立北京图/书馆珍藏”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8]
7.索书号:XD282
此部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无题字。书衣右上角有藏馆所编册号。
第八册“第二集目”一叶,本应在《小尔雅疏证》书名页之前,此部误置《〈小尔雅疏证〉序》之后。
第七册所收《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大云山房杂记》二种,其次序本应为:《图说》书名页、《图说》序、《十二章图》、《图说》卷一、《图说》卷二、《图说》跋、《杂记》书名页、《刻〈杂记〉》序、《杂记》卷一、《杂记》卷二,此部误置《杂记》书名页、《刻〈杂记〉》序于册首,后接《图说》跋、《十二章图》,其后始为《图说》书名页等其他部分。
第十六册《孝经郑注》一书,本应有《叙》二叶、《后叙》三叶、《传》二叶,此部重复《叙》之第二叶,又脱《后叙》前两叶及《传》之第一叶。第十七册《说文新坿考》中,缺姚觐元《〈说文新坿考〉序》两叶。第二十一册所收《瘗鹤铭图考》、《苏斋唐碑选》、《姚氏药言》三种,本应在第一集《说文答问疏证》之后,因此部书根无册次,藏馆误标作“21”册而处第三集《销毁抽毁书目》后。第二十三册《违碍书目》之末,缺《书目总跋》二叶。
此部无《孝经疑问》之书名页。《说文引经考》书名页本应在第九册卷上之首,而误置第十册卷下之前。第十六册中,误置《礼记天算释》之书名页于第三集书名页之前,又误置《孝经郑注》、《尔雅补郭》之书名页于“第三集目”之后。《销毁抽毁书目》书名页本应在第二十册中,此部误置第二十一册《瘗鹤铭图考》之前。
内钤“吴兴/汤氏/珍藏”朱方、“长乐郑/振铎西/谛藏本”朱方、“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8.索书号:XD493
此部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8196同。书根无题字。书衣右上角有藏馆所编册号。
因此部书根无册次,藏馆所标册号与诸书应有次序多有错乱。第一至八册所收书为第一集,次序无误。然第九册即为第二集末一种《寒秀草堂笔记》,其后即为第三集。查第十九册至二十三册所收之《小尔雅疏证》、《说文引经考》、《说文检字》、《古今均考》、《前徽录》五种,本当在第一集(即第八册)后。第十七册、十八册所收之《中州金石目》、《三十五举》《续》《再续》、《安吴论书》五种,当接《前徽录》之下。
此部“丛书”书名页仅有A面题字(楷书题“咫进斋/丛书”,下有“咫进/斋印”木印),B面无字,即无“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两行。
第四册《说文答问疏证》后,当有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叶,此部误置第五册《瘗鹤铭图考》中。第七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十二章图”,一组图六叶对应卷一,一组图三叶对应卷二,此部误倒三叶一组在前。第十册中,《孝经郑注》缺书名页及《传》两叶。第十三册《说文校定本》,本应有《后叙》两叶,此部缺第二叶即刘恭冕《后叙》一叶。第十八册中,《三十五举校勘记》本应在《三十五举》正文后,此部误置《再续三十五举》之后。
内钤“长乐郑/振铎西/谛藏本”朱方、“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复本十部
1.索书号:Y/9100/7830
此部五函二十八册,前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末一函装帧(函套)与前四函不同,书品偏小,所收为姚晏、姚衡《凤墅残帖释文》八卷及钱大昕《凤墅残帖释文》二卷,故总计收书三十九种一百卷。惟《凤墅残帖释文》二种,不见于《总目》中。书根题写册次。
第二函《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两组“十二章图”,误置“历代十二章图”第三叶于“十二章分图”第二叶、三叶之间。第三函《续三十五举》书内,误将本应在正文之前的《续三十五举题辞》两叶,置于正文前两叶之后。
此部无《安吴论书》、《礼记天算释》、《阳宅辟谬》之书名页。
其版式为:左右双边,上黑口,双对鱼尾。版心下镌“咫进斋丛书/归安姚氏刊”。半叶十三行,行廿二字。
2.索书号:X/081.17/4241.1
此部二函十六册,存二十四种五十四卷,缺第一集之《务民义斋算学》十一卷、《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二卷、《大云山房杂记》二卷、《棠湖诗稿》一卷、《春草堂遗稿》一卷,第二集之《小尔雅疏证》五卷、《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三十五举》一卷《续》一卷《再续》一卷、《安吴论书》一卷,第三集《说文新附考》六卷、《禁书总目》一卷。书根题写当册书名。
因此部缺《小尔雅疏证》,故无第二集书名页及“第二集目”。
内钤“马/裕藻”白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3.索书号:X/081.17/4241
此部四函三十二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及丛书名。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
第六册《瘗鹤铭图考》正文前,有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文共四叶,本应在第五册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中,而误置于此。第九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之“十二章图”,一组图六叶对应卷一,一组图三叶对应卷二,此部误倒三叶一组在前。第二十三册内《孝经郑注》一种无书名页,较全本缺《传》二叶。第二十九册内《销毁抽毁书目》末附《书目总跋》二叶,本应在第三十一册《违碍书目》之末,而误置于此。
第十一册《小尔雅疏证》正文前,有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一叶,此前诸部均无。
内钤“非宇馆/萧氏珍/藏图书”朱方、“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朱方、“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图书馆”椭圆朱、“北京/大学/藏书”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4.索书号:X/081.17/4241/C2
此部三函二十三册,存书三十五种八十七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缺第三集之《说文校定本》二卷、《四声等子》一卷。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及当册书名,知所缺为第二十一册。
此部无“丛书”书名页及各书书名页,仅有各集“集名页”。
第九册《小尔雅疏证》一书中,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一文。第十册《说文引经考》书前,冠以包世臣《文学薛君碑》、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两文共四叶,本应在第五册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中,而误置于此。第十五册中,本应在《三十五举》正文之后的《三十五举校勘记》两叶,误置于《三十五举序》之前。第十七册内《孝经郑注》一种,较全本缺《传》二叶。第二十二册、二十三册所收书,依次为《违碍书目》、《销毁抽毁书目》、《慎疾刍言》、《禁书总目》,据全书《总目》及“第三集目”,知其次序当为《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慎疾刍言》,而该部《禁书总目》后附《书目总跋》二叶,本应在《违碍书目》后,亦属误置。
内钤“铁仙/家藏”朱方、“铁仙图画/经籍藏印”朱长方、“抱经楼/藏善本”白长方、“四明沈氏/双泉草堂/珍赏印”朱方、“北京大学/图书馆/考藏记”白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5.索书号:X/081.17/4241/C3
此部三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及当册书名。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但有“苏州振新书社经印”朱戳。此部又无《棠湖诗稿》之书名页。
第九册《小尔雅疏证》,末有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一叶。第十七册内《孝经郑注》一种,较全本缺《传》二叶。
内钤“北平中/法大学/藏书”朱方、“北平中/法大学/图书馆/藏书章”朱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粉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6.索书号:X/081.17/4241/C4
此部四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题写册号、丛书名及当册书名。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
首册“第一集目”,本应在《公羊礼疏》之书名页前,此部二者误倒。第九册“第二集目”,本应在《小尔雅疏证》书名页前,此部误置《〈小尔雅疏证〉序》之后。第十七册“第三集目”,本应在《礼记天算释》书名页前,此部误置《〈礼记天算释〉序》之后。
此部第九册《小尔雅疏证》中,亦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第十五册《三十五举校勘记》当在《三十五举》正文后,此部误置在前。第二十一册《说文校定本》中,缺《后叙》两叶。
内钤“梓廑/图籍”朱方、“北京古学/院藏书”朱长方、“北京大学图书”狭长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7.索书号:X/081.17/4241/C5
此部二函二十四册,收书三十七种九十卷,分三集(与国图8196同)。书根无题字。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又无各书书名页。
第六册《〈瘗鹤铭图考〉序》前,有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两叶,《瘗鹤铭图考》正文前又有包世臣《文学薛君碑》两叶,此二文均应在第五册《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中,误置于此。第八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两组“十二章图”,误以第二组“历代十二章图”在前,而以第一组“十二章分图”在后。第九册《小尔雅疏证》亦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第十七册《孝经郑注》书后,本应有《〈孝经郑注〉后叙》三叶,此部误置前两叶于《〈孝经郑注〉叙》之前。第二十一册《说文校定本》,缺《叙》、《后叙》各两叶。
内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粉方。有“通学”价签,标为“十六元”。 版式与上一部同。
8.索书号:X/081.17/4241/C6
此部一函八册,收书十三种四十一卷,仅为第一集。有夹板。书品宽大,印制书签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标册。书根无题字。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其后无陈澧序、无《咫进斋丛书总目》,亦无“第一集”书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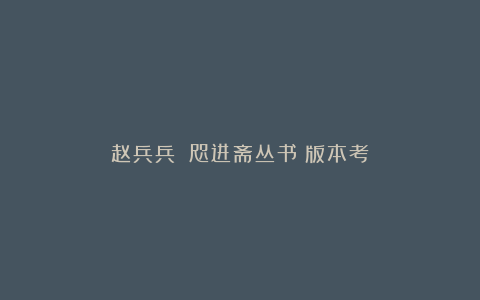
第八册中,误置《〈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跋》于《大云山房杂记》书名页之后。
内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粉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9.索书号:LX/7594
此部二函二十册,收书二十四种七十二卷,不分集。书根所题册号为阿拉伯数字,非原书所有。
此部“丛书”书名页,与国图藏XD493同,B面无字。其后无陈澧序、无《咫进斋丛书总目》,亦无各集书名页及各集“目录”。
据现存次序,所收书依次为:第一册,《孝经疑问》、《公羊问答》;第二至四册,《公羊礼疏》;第五、六册,《说文引经考》;第七册,《说文答问疏证》;第八册,《说文检字》;第九、十册,《小尔雅疏证》;第十一册,《三十五举》《续》《再续》、《古今韵考》;第十二、十三册,《中州金石目》;第十四册,《瘗鹤铭图考》、《苏斋唐碑选》、《销毁抽毁书目》;第十五、十六册,《务民义斋算学》;第十七册,《凤墅残帖释文》;第十八册,《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大云山房杂记》;第十九册,《姚氏药言》、《前徽录》;第二十册,《棠湖诗稿》、《春草堂遗稿》、《咽喉脉证通论》。
此部与前述分三集者相比,不仅次序大异,又无第二集之《安吴论书》、《寒秀草堂笔记》及第三集中除《销毁抽毁书目》之外的其馀各书,共少十四种二十六卷,而多《凤墅残帖释文》八卷。
此部《小尔雅疏证》中,亦无葛起鹏《〈小尔雅疏证〉后序》。
内钤“北京大/学藏”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10.索书号:LX/443
此部仅存一册,书根题册号“五”,又题写该册所收书之书名——《瘗鹤铭图考》、《苏斋唐碑选》、《销毁抽毁书目》。
此部以上述三种书为一册,与上一部不分集者(LX/7594)同。
内钤“北京大/学藏”朱方。版式与上一部同。
纵观以上各部《丛书》,可以明显看到,“副文本”部分(书名页、目录、序跋、传记之类)常出现此有彼无、此前彼后或张冠李戴的现象,这说明装订之时,出错概率颇高,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不同刻本之间的差异。
二、《咫进斋丛书》之版本与印次
不同的两个版本,不管其间是何种关系,两相比对,都不难确定其为“二”而非“一”。因为雕版为手工操作,无论刻工技术如何纯熟,都不能保证所刻与其底本毫无二致。但要区分两个内容基本一致而无明显刻书时间特征的版本孰先孰后,却非易事。如果二者时代相差较远,则可据纸张、墨色来判断“刻板”之先后,但考虑到或许存在“先刻板而后印刷”的情况,此时实际只能区别出“印刷”之先后。至于两个版本时代相近的情况,则非但难以定其“印刷”先后,更难以判断其“刻板”先后了。因此,要区分两个版本孰先孰后,应当综合考证,而不能简单地依据其文字错讹的多少来作为唯一证据。
雕版印刷,需要一叶叶印,从理论上说,所有印本都存在先后之分。但同一次刷墨印制,往往印成多部,此同一批次所印常难分辨先后。而不同批次所印,其板框磨损程度不同,有时又有抽换、修补版片的情况,这就为区分不同印次及其先后提供了线索。
基于此一认识,可以区分出上述十八部《咫进斋丛书》的“版本与印次”,只是北大第10号藏本,残缺过多,考察价值不大,故讨论印次时剔除在外。
(一)两个版本的差异
将上述各部《丛书》进行比对,不难发现,《丛书》确有两套版片。即以郑振铎旧藏两部之第一集第一种《公羊礼疏》卷一叶1A为例,乍一看,两本似乎并无不同。但仔细比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些则差异显著,譬如首行题名中的“羊”字,左侧的本子并无异样,而右侧的本子却将竖画的末端刻成了向左的弯钩,近似“于”字的末端。整体上看,二者虽同为匠体字,但左侧的本子刻工较精,字体大小较为匀称,而右侧的本子明显逊色,其字体忽大忽小,刻工技术难称纯熟。
左:XD493 右:XD282
与左侧本子相同的有北大藏第3号至第10号本,与右侧本子相同的有国图藏第2号至第7号本以及北大藏第1号、第2号本。国图藏第1号本虽无《公羊礼疏》,但以其所有者与其他各部比对,亦可知它与上述左侧本子同属一套版片。这样,我们便可将上述十八部《丛书》分为两组:一组包含国图藏8197、XD493,北大藏X/081.17/4241以及同号C2-C6、LX/7594、LX/443,共十部,可称为“X本”;一组包含国图藏8196、38185、39205、40449、41966、XD282,北大藏Y/9100/7830、X/081.17/4241.1,共八部,可称为“Y本”。
此二本相校,Y本讹误字明显多于X本,可知王曦、马珂所言之“初刻”即指Y本,“重刻”则指X本。但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X本为“原版”初刻,Y本则为“盗版”翻刻。Y本之所以讹误更多,是因为该本属于“盗版”,为谋利之产物,并非姚氏咫进斋所刻。
首先,觐元无重刻的必要。陈澧为《丛书》所作序中说:
归安姚彦侍方伯,承其祖文僖公家学,好传古籍,尤精于声音训诂,故搜采独多,皆世间不传之本。而又虚怀博访,往往从故家藏本,暨通人写本,辗转录出。好古之士,有终身求之而不得者。每刻一书,必期尽善而后止。得之若是其艰,刻之更若是其慎,而求书之志,固未有艾也。十年来,刻成三十馀种,汇为《咫进斋丛书》。举以示澧,澧受而读之,见其别择精而校雠善,足补从前丛书所未备。爰属及门陶春海孝廉,略以刻书年月之先后,编为三集,集以四部为次。
可见,觐元刻此《丛书》,历时十馀年之久。假令汇印时,在初刻版片尚存的情况下,确有重刻之举,则其理由不外如下两种可能:一是此前十馀年间所刻三十馀种书,版式非一,既汇为《丛书》,则当划一,故为重刻;二是此前所刻版片因累年刷印,已多有磨损,以致部分抽换亦不能解决问题,故全部重刻。但这两种假设都不能成立。
第一种情形若存在,则如今所见两本当有一本是版式参差的情况,但上述两本内部版式均同,其版片即各为一套完整《丛书》,并没有一套版式参差的《丛书》存在。也就是说,觐元从刻书之始,即已确定版式,便已计划将来要汇印出版。所以,不管是独立刷印,抑或是汇集印行,其版式并无二致。觐元在同治癸酉“冬十有一月朔”(1873.12.20)所作《〈药言〉后记》中说:“原书页前后各九行,行十八字,通三十页。今刊入’丛书’,页前后各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此所谓“丛书”,当即指《咫进斋丛书》,故所记行款与《丛书》各印本同。而陈澧《〈丛书〉序》作于光绪七年(1881),则所谓“十年来,刻成三十馀种”云云者,即包含此同治十二年(1873)所刻之《药言》,故知觐元历年所刻《丛书》中各书均为同一版式。
第二种情形若存在,则今日所见两本中之“初刻”,在汇集印行时,已是面目模糊之邋遢本。但如今所见两本,均无此类现象。更何况,若说早年所刻书因刷印较多而有磨损尚属可信,但汇印之前的一段时间新刻之书,何来因磨损而重刻的理由呢?并且,若一套版片因刷印过多而磨损,则其印本必多,《丛书》时代既近,则存世者当不难见此类邋遢本,此又与实际情况不符。
其次,觐元无重刻的机缘。《丛书》三集虽仅有九十卷,但叶数在一千六百叶以上,双面刻板亦超出八百片,数量可观。耗资不菲之外,存储亦属难题。而觐元于此三集外,拟印之书尚夥,既有已刻而未印行的《丛书》第四集,亦有他投入多年心血而终未刻版之《说文解字考异》。未竟之业尚且来不及一一实现,何有先耗时间、精力重复已成之业者?
第三,说“X本为原版初刻”,有重要证据。前述两个版本的十七部印本(已剔除北大藏LX/443),除国图藏第1号(8197)印行于光绪九年二月之前,北大藏第8号(X/081.17/4241/C6)、第9号(LX/7594)印行时间难定外,其馀十四部均印行于光绪十年之后。因为这十四部印本,在觐元《书目总跋》之末均有附记两行,文云:“浙本末叶后半,凡残阙’应’下三字,又尾七行书目五种,于甲申三月在苏州觅得全编,校补讫。觐再记。”甲申,即光绪十年(1884)。[9]此十五部印本中,《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之末又均有阴刻“甲申校补”四字,知所言“浙本末叶残阙”云云,即是指《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末尾数行初刻时本有残缺,至光绪十年始得全本为之校补。如觐元所说,则当有“未校补”之本,且为该书之初刻。幸运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确藏一部“未校补”之印本,其《书目总跋》之末并无觐元附记两行,而其《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末尾数行确有残阙如觐元所言者。[10]
左:X本(XD493) 中:初刻本(中山大学藏)
右:Y本(8196)
将前述X本、Y本与中山大学藏此部初刻印本比对,可以发现就《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而言,三本均非同版(见上图)。但比对其他叶面,可知X本与此部初刻印本实出同版。《禁书总目》末叶之不同,为校补时换版所致。也就是说,X本即是咫进斋原刻本,其各印本与中山大学所藏此部印本之不同,只是印次有别而已。Y本则是后出之翻刻本,且其底本为“已校补”之本。
中山大学所藏此部初刻印本,既属“未校补”之本,则其印行时间当在光绪九年三月(李文田题字)至光绪十年三月(觐元校补)之间。又该书钤有“番禺王国瑞所藏”白长方、“学荫轩”朱长方之印,考王国瑞在广东书局中任分校,或为陈澧之弟子。[11]而觐元汇印《丛书》,则由陈澧作《序》,并由陈澧之弟子陶春海为之分集。光绪九年,觐元由广东布政使任上罢官,当年三月二十日离开广州。[12]则此部印本当即为李文田题字后之汇印初印本,时间即在该年三月也。
X本诸印本,既多印行于光绪十年三月后,则可知觐元寓苏之时,初刻版片尚保存无虞。北大藏本第5号(X/081.17/4241/C3)为振新书社所经印者,亦属X本。查民国十九年(1930)《苏州振新书社精刻木版书目》,列有归安姚氏刻本《咫进斋丛书》一种,其提要云:“今由本社印行。”[13]此目所著录者当即X本。也就是说,直至民国时,初刻版片依然存世。既如此,则觐元在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何以会重刻一部错误增多的Y本呢?
第四,说“Y本为盗版翻刻”,亦有版本依据。通过前文对《丛书》两个版本诸印本基本情况的描述,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区别,即凡Y本均有“丛书”书名页,且该叶两面均有字(A面楷书题“咫进斋/丛书”,下有“咫进/斋印”木印,B面题字两行“光绪九年春三月/顺德李文田书题”)。而X本除8197、X/081.17/4241/C2两部外,其馀七部之“丛书”书名页均只有A面镌字。何以说此点不同,便可成为“Y本为盗版翻刻”的证据呢?
因为A面所题楷书“咫进斋丛书”五字,察其笔迹,当出觐元之手,故其下有“咫进斋印”木印(翻刻自手书题字之钤印)。B面之镌字,则是翻刻Y本时,依照各集书名页均两面有字的例子,将第一集书名页B面题字同样镌刻于“丛书”书名页之后。殊不知,“丛书”书名页之题字并非李文田手笔,它和第一集书名页李文田所题字有显著不同(见下图)。此可谓弄巧成拙。
以XD493为例:“丛书”书名页A面、第一集书名页A面、第一集书名页B面
总而言之,《咫进斋丛书》确有两个版本,其中“原版”初刻(即X本)错讹少、刻工精,“盗版”翻刻(即Y本)错讹多、刻工拙。
(二)不同印次的区别
通常情况下,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印本,可以根据相同叶面的磨损程度的不同来定其前后,这种磨损包括板框、界栏的断裂以及文字笔画的缺坏。但有时印刷时间较近的印本,因版片完整程度相近,而刷印质量不一,往往出现难以分别先后的情况。所以,有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1.原版初刻本:X本的不同印次
此本共十部,分别为:国图藏第1号(8197)、8号(XD493),北大藏第3号(X/081.17/4241)、4-8号(C2-C6)、9号(LX/7594)、10号(LX/443)。末一部残缺过多,不予讨论。
(1)该组印本有抽换版片的情况,可以据此将诸部印本进行如下分类。
分类一:《公羊礼疏》卷六第十一叶、十二叶,一类上黑口有苏州码字(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4号、6-9号),一类上黑口无苏州码字(北大藏第3号、5号)。中山大学藏汇印初印本与前一类同。以叶12B为例:
左:北大藏第4号 中:北大藏第5号 右:中大藏本
分类二:《中州金石目·补遗》前两叶,一类上黑口有苏州码字(北大藏第6号、9号),一类上黑口无苏州码字(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5号、7号)。中山大学藏汇印初印本与后一类同。以叶2B为例:
左:北大藏第6号 中:北大藏第4号 右:中大藏本
(2)该组印本有文字残损、改换的情况,故可据以进行如下分类。
分类三:《〈公羊礼疏〉序》第一叶A面第一行有一“蹈”字,一类印本此字完整(北大藏第8-9号),一类印本缺右旁“舀”字上一撇(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5号、7号),一类印本“舀”字上一撇略有残存(北大藏第6号)。中山大学藏汇印初印本与第一类同。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9号 中:北大藏第7号 右:北大藏第6号
分类四:同样是《〈公羊礼疏〉序》第一叶A面第一行,末一字“者”,除了北大藏第9号印本完整外,其馀各印本(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8号)均缺末笔。中大藏本亦缺。见上图。
分类五:《说文引经考·补遗》第五十叶首行题名及版心题名,北大藏第3号印本均误作“补遣”,其馀各印本(国图藏第1号、8号,北大藏第4-7号、9号)皆不误。中大藏本亦无误。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3号 右:国图藏第1号
分类六:《中州金石目》卷一第一叶A面第三行有一“铜”字,除国图藏第1号、北大藏第9号印本完整无缺外,其馀各印本(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7号)右旁“同”字均残坏不成字。中大藏本与前者同。见下图:
左:国图藏第1号 中:国图藏第8号 右:中大藏本
分类七:《中州金石目》卷三第一叶B面第十三行应有“刘洛真造释迦象”七字,一类“象”字残缺头部两笔(北大藏第4号),一类缺前六字(国图藏第8号,北大藏第3号、5号、7号),一类“象”字仅缺第二笔(北大藏第6号、9号)。中大藏本与末一类同。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4号 中:北大藏第7号 右:中大藏本
为便直观,可将上述七组分类结果列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无论如何分类,国图藏第1号印本都和北大藏第3号印本不同,也就是说,以上诸印本中,此二部之间差别最多。所以此二者即当为最早与最晚的印本。我们已经知道,国图藏第1号印本印成于光绪九年二月之前,而北大藏第3号则印成于光绪十年三月之后,所以前者为诸印本中最早的印本,后者为诸印本中最晚的印本。
再以北大藏第3号印本为中心,将上表重新调整如下:
既已知道“国图1”为最早印本,“北大3”为最晚印本,结合此表,可初步排出各印本次序:国图1/北大9,北大6/北大8/中大,北大4,国图8/北大7,北大5,北大3。如此一来,只需对前三组印本内部进行排次,便可得诸印本之次序。
第一组:国图1与北大9
这两个印本收书数量均少于其他印本,且不分集,然其印刷时间却又最早,可知此二部均为分集汇印之前所印行者。也就是说,北大第9号印本同样印行于光绪九年三月之前,该印本内各书次序并非原为分集排次而流传颠倒,实则原本即是如此。查此二部印本同有之《凤墅残帖释文》虽属同版,但也有换版叶面。而北大藏第1号印本虽属Y本,但其中配入之第五函《凤墅残帖释文》却与上述二部为同版。此三部《凤墅残帖释文》亦可根据换版与文字残损进行分类。
首先,卷四前八叶,国图1与北大1为同版,北大9独异。以叶8B为例:
左:国图藏第1号 中:北大藏第1号 右:北大藏第9号
其次,卷四第九叶A面第九行有一“狭”字,北大1此字完整,国图1与北大9则已残坏。见下图:
左:北大藏第1号 中:国图藏第1号 右:北大藏第9号
由此可知,此三部《凤墅残帖释文》印刷先后为:北大1、国图1、北大9。
第二组:北大6、8与中大藏本
先看北大6与中大藏本。虽然前述七种分类未能分出此二部印本之先后(由分类二则北大6早于中大本,由分类三、六则中大本早于北大6),但根据前文所述,中大本印行于光绪九年三月,而北大藏第6号本属于印行于光绪十年三月之后的本子。因此,中大藏本要早于北大6。之所以出现分类二的情形,则当是印行“北大6”时,采用了换版之前的早期版片,其原因则无从揣想。
再看北大8与中大藏本。此二部印本叶面状态基本相同,其间界栏断续常出现彼此互胜的情况,难以判断先后。不妨视之为同批次印本。又因北大藏第8号本装帧特殊,且其书签为专门印制,或为分集汇印之试印本,似较中大本更早。
第三组:国图8与北大7
在以上七组分类中,此二部始终相同,故难以分别先后。抽检多处二部相同的叶面,其状态亦无明显差别,无优劣之分。亦当视为同批次印本。
至此,我们可以将上述原版初刻(即X本)诸印本的印行次序排列如下:国图1>北大9>(北大8≈中大)>北大6>北大4>(国图8≈北大7)>北大5>北大3。
同时,根据这些印本的次序,我们可以推断《咫进斋丛书》的印行模式为:光绪七年(陈澧作序时间)之前,先是单种印行(如Y本之《凤墅残帖释文》),然后以若干种汇集印行(如国图1、北大9);光绪七年后,始有分集汇印本(如北大8、中大本)。只是上述印本数量较少,直至光绪十年三月校补后,分集汇印全本才多有印行(北大6以下诸本)。
2.盗版翻刻本:Y本的不同印次
此本共八部,分别为:国图藏第2号(8196)、3号(38185)、4号(39205)、5号(40449)、6号(41966)、7号(XD282),北大藏第1号(Y/9100/7830)、2号(X/081.17/4241.1)。
如前文所证,Y本是以X本光绪十年三月校补后之印本为底本进行翻刻的,所以此八部印本均印行于光绪十年三月之后。
该系列印本亦有换版现象,即《公羊礼疏》之“凡例”一叶。该叶A面第十行有一“羊”字,可作为二者异版之代表点位。一类“羊”字如常镌刻(国图藏第5号、6号,北大藏第2号),一类刻“羊”字竖画末端为左弯钩作“”形(国图藏第2-4号、7号,北大藏第1号)。见下图:
左:国图藏第5号 中:国图藏第2号 右:国图藏第3号
第一类三部印本,所呈现的版面状况无明显不同,只能从更细微处着眼。以《公羊礼疏》卷一首叶A面为例(见下图),可以发现右边栏中部稍偏下有一处断板,国图藏第6号印本较国图藏第5号与北大藏第2号印本裂口稍宽,则印次当较后。从叶面整体状况来看,国图藏第5号印本似早于北大藏第2号印本。因此,该三部印本次序当为:国图5早于北大2,北大2早于国图6。
左:国图藏第5号 中:国图藏第6号 右:北大藏第2号
第二类五部印本,可以根据《公羊礼疏》之“凡例”叶(见下图及前页例图)对其印次进行区分。首先,第二行末之“正”字,国图藏第2号及北大藏第1号本均完整无缺,而国图藏第3号、4号、7号三本该字第一笔横画均已残坏,故前二者印刷较早。其次,根据叶面的整体状况,大体可以判断,国图藏第2号印本早于北大藏第1号印本,国图藏第4号印本早于第7号印本、第7号印本早于第3号印本。
左:北大藏第1号 中:国图藏第4号 右:国图藏第7号
再将以上两类印本之相同叶面比对,不难确定,第一类印本印刷时间要早于第二类印本。仍以《公羊礼疏》卷一首叶A面为例,可以发现:第一类印本中国图藏第5号、北大藏第2号印本仅波及第六行“沈”字、第七行“年”字,国图藏第6号印本又延及第九行“元”字;后一类印本中国图藏第2号、北大藏第1号印本之断板状况尚与国图藏第6号印本大致相当,此后便明显变宽,至国图藏第4号印本,已延及第十行“若”字、第十一行“自”字、第十二行“则”字,而国图藏第7号、3号印本断裂程度进一步加大。见下图及上页图:
左:国图藏第2号 中:国图藏第4号 右:国图藏第7号
至此,我们可以将上述盗版翻刻(即Y本)诸印本的印行次序排列如下:国图5>北大2>国图6>国图2>北大1>国图4>国图7>国图3。
2022年4月完稿
2025年2月修订
[1]案:觐元生平,详参清姚慰祖《彦侍府君行状》,见(清)姚学邃纂修:《〔浙江湖州〕吴兴姚氏家乘》,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上图藏(JP712),卷十六叶1-12(影像本第8册第269-291页)。
[2]陈澧:《〈咫进斋丛书〉序》,载《咫进斋丛书》,清光绪间姚觐元刻本,卷前。
[3]案:《丛书》第四集的相关情况,笔者将另文探讨,本文暂不涉及。
[4]王曦:《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207-209页。
[5]马珂:《〈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兼谈〈咫进斋丛书〉第四集》,《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1期,第105-107页。
[6]案:以“咫进斋丛书”作为题名限定符,于“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检索(2022-04-16),可得169条著录信息。而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十部尚未列入该数据库,加上未公布的其他古籍存藏单位的数据,总数当在二百部以上。
[7]案:国图与北大另有《丛书》第四集各一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不计入。
[8]案:另有一部(索书号:42964),见《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7册第116页),但国图官网无该条数据,赴古籍馆填单提书,工作人员告以查无此书。未知何故。
[9]案:王曦已注意到此处“附记”,渠所见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三部《咫进斋丛书》均有之,所以认为“此三部丛书合集成书的时间最早也只能是1884年,而不是1883年。”(《咫进斋丛书〈四声等子〉版本研究》,第209页注释[2])而马珂则径以为“丛书合集成书的时间最早也是光绪十年(1884)”(《〈咫进斋丛书〉版本研究》,第105页)其实,南大所藏三部丛书有此“附记”,只能说明其印刷时间在光绪十年以后,而不能作为判定《咫进斋丛书》合集成书时间的证据。
[10]案:《广州大典》“丛部”第69册第七辑所影印《咫进斋丛书》(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即据中山大学此部藏本,以下或称中大本。《禁书总目》第六十四叶见第803页,《书目总跋》见第820页。
[11]李绪柏编著:《清代岭南大儒:陈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12]姚觐元:《弓斋日记》,上图藏稿本(线善792100-11),影像本,第206页。
[13]《苏州振新书社精刻木板书目》,苏州:振新书社,1930年,叶6B。案:国图藏本著录作“板”,书中卷端实作“版”。书衣署“振新书社书目”,落款署“庚午三月/陆镛题”。
赵兵兵,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