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之際郡縣變動與地方統治關係
──以司州為例(A.D. 189-300)
張正田
一、研究動機
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州郡析置頻仍[1]。然在曹操秉政至晉初八王之亂前這段期間,正承兩漢地方郡國較穩定狀態而啟十六國南北朝時大量析置州郡,其間郡縣析置、改置狀況,可能關乎漢晉之際,國家為在行政區劃空間布局上,找尋更有效、或更符合國家與區域勢力間合理範圍。《晉書》載:
咸上言:『然泰始開元以暨於今,十有五年矣。……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晉書,47/1324,傅咸附傳)。
說明晉初郡國數目膨脹之情況。表面上看傅咸所言,晉初郡國數與兩漢相較,頗不合理,然國家作此安排用意何在?本文擬以司州為討論對象,因該州位天子腳下,為中央控制力最佳之核心區。且為曹魏至西晉中葉八王之亂以前,中央控制力較能統馭全國,故時間斷限定於此。冀能藉分析晉司州區的郡縣析、改置,觀察中央對此地空間安排之理由。
嚴耕望曾指出漢晉間所增置約七十郡國,其中有二十五者個係漢世都尉所改設(嚴耕望,1990: 175-186),唐長孺則指出曹操政權所創屯田農官,至西晉時悉改為郡縣(唐長孺,1957: 41-42),嚴、唐所論,或為此時代析置郡國兩大主因。然在西晉政治核心區之司州境內,新析置郡國中由都尉、或屯田農官改制者各佔多少?其對西晉統治是否有利害關係?或另有因其他途徑析置者?新析置郡國與中央權力作用上是否有某程度關係?以上為董卓之亂起至八王之亂前的漢晉之際,值得探討之問題。
魏司州與西晉司州轄區最大不同處,在於魏司州只轄「三河地區」[2]及弘農郡,晉卻將司州卻擴大轄及鄴城附近地區,使晉司州同時轄洛陽與鄴兩大區域,為何西晉要做如此安排?西晉中央是否打算藉如此區劃,對當時華北兩大繁華區域——洛陽與鄴,作更有效的監督控制?。
前文所述,殆對漢晉之際晉司州區郡級政區變動作考察,本文擬更進一步探討此際本區縣級政區置廢、改隸他郡等變動,以更細步觀察魏、晉二朝,國家在調整京師所在「政治核心區」之控制力。關於對特定區域之縣級政區變動、以觀察中央與地方關係之研究。學界歷來成果並不多,是為本文研究中較困難處。
學界以往對漢晉之際至八王之亂前之魏晉中央政府,多少存有「控制方式錯誤、導致動亂不斷」印象。然本文之假設為:魏、晉官僚決策群並未料到帝國後來會崩壞如此快速,故在政區安排上,可能會考量其空間合理性,以圖長治。故本文冀望能透過考察此際國家對中央政府政治核心區「晉司州區」郡、縣級行政區劃變動,觀察國家對此區政治控制之企圖心。又鑒於以往對中古前期史多只重視政治、經濟、人事、組織史之研究,對中古前期之空間、地域史研究成果累積則較少,即過去研究傾向略是「重組織、輕空間」,希望本文之研究,能為學界略盡棉薄貢獻。尤其歷史上行政區治所的選擇,往往代表政府基於統治需要與現實環境選擇之結果,若能發現魏、晉政府對政治核心區之地方政府層級安排也如此,則很可能證明筆者之問題假設。
二、晉司州區郡國析置概況
本文雖以探討西晉政治核心區司州為主,但為求整體了解此時期郡國演變概況,仍先依《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略估漢至西晉間天下郡國增加數概況,製成〈表1〉,其中「州」以西晉轄區為準:
按上表,可算出漢晉之際全國郡增加率約為63.81%,其中荊、揚、交、廣等州增加數偏高,概多為孫吳、蜀漢二政權析置。又嚴耕望指出,魏晉間新增郡國約七十郡中,其中二十五郡皆為漢世都尉駐處所改制,嚴氏稱之為:
必然之途徑,亦為增置郡國之一最常見之方式也。(嚴耕望,1990: 175-186)[8]
故「都尉改郡」制為就全中國觀點、考證詳實之論點,亦為此時增置郡國方式之一。
然西晉司州郡國析置情形,若依《晉書.地理志》與《後漢書.郡國志》並參照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3冊[9],漢晉之際之晉司州[10]所增郡國,有平陽、上洛、汲、頓丘、廣平、陽平、滎陽。晉司州範圍之漢舊郡國,依《後漢書.郡國志》,司隸校尉有河東、河內、河南、弘農;冀州之魏郡,其中合於嚴氏所考二十五由「都尉改郡」者,至少有晉司州之滎陽、廣平、陽平三郡(嚴耕望,1990: 185-186)。而晉司州之郡國增加率為140.00%﹙含漢冀州魏郡﹚,增加數為七,為之最高。
然除前述郡國外,漢晉之際增設之郡國也有曹魏時代所設之民屯農官典農校尉、典農中郎將等所改制者(唐長孺,1957: 41-42;王仲犖,1979: 123-141;黃耀能,1978: 266-294[11])。《三國志》載:
﹙咸熙元年﹚﹙264年A.D﹚……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為令長。(三國志.魏志,4/153,陳留王奐紀)
由此可知,當時凡魏境所有農官悉改為郡守、縣令。又《晉書》載:
﹙泰始二年﹚﹙266年A.D﹚十二月,罷農官為郡縣。(晉書,3/55,武帝紀)
可見由民屯農官改制為郡縣,亦為此期地方行政演變之一途[12]。以此途改為郡國者,本文稱之為「罷農(官)為郡」。
雖根據學者研究成果,多認為魏晉時代隱戶情形頗嚴重,《晉書.地理志》所載資料往往不符現實[13]。但因《晉書.地理志》是記載西晉戶口唯一史料,故仍需參用,然亦只載戶數而無口數,故暫將後漢及西晉司州郡國戶數作
由上表可知,漢晉間全國總戶數減少率約74.63%,相對地,晉司州地區卻只降低26.66%,故晉司州戶數相對變化率實是增加的,戶數相對增加率達2.8倍;而晉司州之郡增加率達140.00%,也跟戶數相對增加率成正比。由此也可反應出晉司州因戶數相對增加率高,顯示出此州除政治核心區之重要性外,在經濟重要性也不可小估,西晉中央對藉由司州行政區劃之空間安排,以利國家對此區域之控制,當有所重視之必要。
若依《晉書.地理志》,本州在漢晉之際所新增郡國中,有四個是西晉立國第二年之泰始二年﹙266年A.D.﹚新置或復置,分別是司州之滎陽[15]、上洛、汲、頓丘。此外,晉司州由民屯農官改制郡者,還有雖改制俄復廢之郡國,如《晉書》即載魏舒曾任「宜陽、滎陽二郡太守」(晉書,41/1886,魏舒傳)[16],然宜陽郡就不見於《晉書.地理志》,可見非晉時常置郡。此類置而復廢郡國,將於後文提及,也可見漢晉之際司州曾新置郡國數不只四個。這反應出在漢晉之際,國家為在司州地區找尋合理的行政區空間安排,最後才去蕪存菁留下四個新置常置郡國。這些新置常置郡國中,由「罷農為郡」改制者至少有汲郡,汲郡屯田事見《晉書》:
魏明帝初為平原侯,(何)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晉書,33/994,何曾傳)。
賈充……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晉書,41/1165,賈充傳)
而司州亦為曹魏屯田重心區之一(王仲犖,1979: 123-141)。下文將討論晉司州地區「罷農為郡」過程及置廢情形。
三、「罷農為郡」過程及置廢情形
因曹魏缺乏軍糧,而用棗祇、韓浩等議,於東漢建安元年﹙196A.D.﹚開始持續大量屯田政策[17]。依西嶋定生、黃耀能等研究,其據史書,歸納出有三十四條有關民屯地名之史事,並刪其重複者,得許、潁川、蘄春、沛、魏郡、洛陽、襄城、河東、野王、河內、睢陽、汲郡、宜陽、列人、原武、弘農、鄴、滎陽、長安諸處為當時屯田要地(西嶋定生,1956: 1-84;黃耀能,1978: 271-273)。本文據此,首先排除非晉司州之地:許、許昌乃同一地,是為西晉豫州潁川郡治;襄城郡亦屬豫州、睢陽為梁國治,亦屬豫州;蘄春位於長江,西晉時亦屬豫州弋陽郡管轄[18];沛國亦屬豫州,以上皆屬豫州地[19],長安則在魏晉時之雍州,皆非本文所討論司州範圍之地。剩餘地點都在司州,若以「罷農(官)改郡」之角度觀察上述地點,可見司州為魏時主要施行屯田政策地區之一。
其次分論司州屯田地點如後:鄴即晉魏郡之治,與河東、河內,皆屬漢舊郡,不太可能因「罷農改郡」而使一城分二郡。汲郡如前言為「罷農改郡」政策下之所改之常置郡(晉書,14/417,地理志上),滎陽亦已設都尉,符合嚴耕望論述「都尉改郡」之例,《晉書》亦載:
滎陽郡,泰始二年﹙266年A.D.﹚置。[20] (晉書,卷14/416,地理志上)
而東漢並無設滎陽郡,至少可知滎陽是魏晉時期才設郡。其餘只剩野王、原武、宜陽、列人四者,試分析其歷史演變如下:
(一) 野王
野王:按《晉書.地理志》無載野王郡,但又載: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晉書,37/1090,安平孚王子輔附傳)
則野王曾一度在魏末設郡,很可能就是於曹魏咸熙元年(264A.D.﹚第一次「罷農為郡」時所改制,然在魏末晉初時廢之,合併入河內郡。野王縣則為晉河內郡治,而魏之河內郡治卻在懷縣[21],推估野王郡是割河內郡西部數縣所設郡。
廢野王郡也可能與設汲郡有關。前已述汲郡依《晉書》所載,係設於泰始二年﹙266年A.D.﹚,其轄區範圍為汲縣、朝歌、共縣、林慮、獲嘉、脩武等六縣(晉書,14/417,地理志上),此正當魏河內郡東境,故汲郡之設其實正是割魏河內郡東境而設。若《晉書》所載設汲郡之年份266年是正確的,則汲郡必是依266年之「罷農改郡」令而設,而依264年第一次「罷農改郡」令,所割魏河內郡西境之野王郡,勢必遭裁廢,否則一個魏河內郡境勢必三分,於空間架構上,郡治距離太過緊密、郡轄區也會相對縮小而至不合理。故推估266年設汲郡後,可能即廢野王郡、再將野王併入河內郡,晉廷並決定將河內郡治自懷縣改徙至野王縣。
為何晉廷要作此安排?不妨以空間結構角度觀之。依《譚圖.西晉司州圖》(譚其驤,1992,3冊: 35-36),筆者實際量懷縣至野王縣之距,所得公分數約為2.33公分,再乘以比例尺(二百一十萬分之一),約估野王至懷縣之距為24.78公里;再以此法量懷縣至汲縣距離,約估得68.88公里,故知野王至懷縣較近,懷縣至汲縣較遠,兩者距離比為1:2.78,由此可知西晉政府為何要廢野王郡而保留汲郡,係為尋求更合理之空間安排。
(二) 原武
原武:《晉書》載:
﹙洪﹚仕魏,歷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晉書, 37/1087,安平孚王孫洪附傳)
可知魏末時原武亦曾因「罷農為郡」而改制為郡,而《晉書.地理志上》亦無載此郡,可知原武郡置後又廢。同前推論,原武可能因地過近於滎陽、汲郡、陳留諸郡間,若設此郡轄區亦難廣,郡治距離過於緊密,由是被廢,併入滎陽郡[22]。
再談滎陽何時設郡。依《晉書.地理志上》載,滎陽郡乃泰始二年﹙266年A.D.﹚置,此史料可能有誤,請容考辯於後:按《三國志.魏書》載傅嘏:
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三國志.魏書卷21/624,傅嘏傳)
及《三國志.魏書》注引《魏略》:
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李)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三國志.魏書,21/290,何、鄧、丁、畢、李、桓附傳注引《魏略》)
皆可知滎陽早在曹魏時已由「都尉改郡」,非遲至晉泰始二年才置,故《晉書.地理志上》滎陽郡條所載此郡設置年有誤。按《水經注疏》載:
魏正始三年(242 A.D.),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水經注疏》,7/668,〈濟水一〉)[23]
則滎陽早於242年已設郡,且其係裂原漢代河內郡東境之滎陽、京縣、密縣、卷縣、陽武、苑陵、中牟、開封[24]、原武[25]等諸縣而新置,則無論原武郡係在264或266年之「罷農為官」令下改制為郡,勢必是裂方置二十餘年之滎陽郡、再置新郡,如此原魏河南境東境九縣勢必再割裂,造成郡距過小、政區空間安排趨不合理,故原武郡遂置後又廢。
(三) 宜陽
宜陽:見《晉書》載:
文帝﹙司馬昭﹚……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舒﹚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晉書,41/1886,魏舒傳)
可知西晉魏舒曾任宜陽太守一職,可見宜陽亦曾置郡。然《晉書.地理志上》亦無載此郡,可見此郡亦一度由「罷農為官」政策置郡後又被廢,或因地近弘農、或因人口較少而被併入弘農[26]。
宜陽故郡前身,據《三國志》載為「宜陽典農」(三國志.魏書,24/686,高柔傳),然依《水經注疏》所載:
洛水又東……而東南流,逕宜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農治此,後改為郡。(水經注疏,卷15/1300,洛水)
因《晉書》編纂時間是唐朝,遠晚於《水經注》成書時間之北魏,有理由相信《水經注》此條史料較可靠。即宜陽故郡之前身,實即是「洛陽典農」,「洛陽典農」其實並不在洛陽,而在司州弘農郡宜陽縣,關於此點,《三國志.魏書》注引《魏略》有一條史料可為旁證:
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三國志.魏書,卷9/291,曹、何、鄧、丁、畢、李、桓傳注引《魏略》)
此史料明言洛陽典農之治,不在洛陽城內、而在城外,至於在城外何處,即是《水經注》所載之弘農郡宜陽縣。也許因此縣離洛陽頗遠,又非洛陽所在之河南尹所轄,魏、晉時人可能常將「洛陽典農」別稱為「宜陽典農」,然兩者其實是指同一地、同一農官職。而《晉書》常將「宜陽典農」、「洛陽典農」[27]混書,可能乃唐人已經搞不清兩者其實同一地,而誤將兩者當成兩地,故混書之。
(四) 列人
列人:列人屯田事見《三國志.魏書》載:
﹙管﹚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三國志.魏書,卷29/816,方伎.管輅傳)
但尋諸史料,似皆無「列人太守」或「列人郡」等相關記載,似或因其地極迫近廣平、魏郡間而未設新郡?亦或同前述推理曾一時設置後廢而史書不及見載?
前述宜陽、原武、野王等諸廢置郡[28],或曾因魏咸熙元年﹙284A.D.﹚及晉泰始二年﹙286A.D.﹚三年間二度「罷農為郡」,而一時改制為正常地方行政體系之郡國,但《晉書.地理志》不書,可見非晉武帝時常態設郡,隨設而銷。亦即因漢末三國以來戎馬兵禍,全國戶口因兵亂而大量減少,社會及居民結構因流亡避亂而大為改變[29],故西晉政府在新興一統、較為安定後,仍需一定之州郡地方官以鎮撫百姓,故於司州境內尋找其合適的設郡地點。也因之在因襲「罷農為郡」政策下改置新郡之歷史過程中,仍不斷在尋覓合理的治所地點。
這種現象,其實早在曹魏時代即已有之,《三國志.魏書》載:
自帝即位至于是歲(嘉平五年)﹙253A.D.﹚,郡國縣道多有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三國志.魏書,4/127,齊王芳紀)
即可證此。同理又見《三國志.魏書》:
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豫州諸郡,唯陽安郡不動。(三國志.魏書,23/668-669,趙儼傳)
而《補三國疆域志補注》考為:
陽安郡……蓋魏武破張繡時所立。……魏受禪後,陽安郡不見國志,蓋魏置郡不久即廢。(洪亮吉,1955: 16)
此史料亦可見魏晉間兵戎亂禍之際郡國設定之不穩定性。
筆者將上述有關晉司州屯田處演變情形,略製〈表3〉,以供參考:
嚴耕望曾考證諸史料後,論及「都尉改郡」演變結果曰:
當建安時代,都尉既已領民比郡,即被視郡……實與某郡行政上已毫無關係。此在政區分割上已完成手續……改都尉官名為太守,不過正名而已。(嚴耕望,1990: 184)
而農官是否可能同於前論,亦領實土實民?
《三國志.魏書》載:
﹙魏﹚明帝即位……﹙司馬芝﹚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利要入。芝奏曰:「……武皇帝特開典農之官,專以農桑為業……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益一畝之收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諸典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三國志.魏書,卷12/388-389,司馬芝傳)
由引文知典農官權力早在魏明帝時即已變質膨脹,可讓諸典農官「治生,各為部下之計」,甚至連商旅過往之事似亦可聽聞,隨日後之演變,典農官權力可能實質化。日後入晉,罷農為郡,也很可能為典農官權力日漸擴大、成為實質性之地方官的「正名」。雖前述傅咸批評西晉時天下戶口大減而郡縣徒增,然晉廷可能因襲世勢,為政局、或官僚系統之穩定,仍不得順勢將農官正名為地方郡守。但即令如此,晉廷仍需兼顧實質上郡國置點之空間合理性,若干新郡,如前述野王、宜陽等,遂見廢;而獲存者如汲郡。
四、其他郡國析置之探討
除上述郡國之外,魏晉間析置常置郡尚未解者,仍有司州之頓丘、平陽、上洛,茲一一討論之:
(一) 頓丘
頓丘:頓丘設郡依《晉書.地理志》亦為西晉泰始二年[30],且戶數僅六千三百,相較於司州其他郡國戶數動輒萬餘至十餘萬戶,似太稀少,晉廷會將戶數如此少之地獨立設郡,略不合理。詳見下表:
又《晉書.束皙傳》載:
皙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飢窮,欲大興廣農……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狹逼,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晉書,51/1431-1432,束皙傳)
由引文知晉司州之頓丘、陽平兩郡交界一帶,有頗多自曹魏時期由官方遷徙來之外來移民於此屯田,久而繁盛,兩郡交界處之外來移民,到西晉時合計已至五六千戶。而這僅是頓丘郡邊界之戶數,郡本部四縣[31]之人可能不少於此,由此推論《晉書.地理志上》所載頓丘郡戶數不甚詳實,很可能不僅只6,300戶,但此也不能推論頓丘之民已夠多到可獨立設郡之境。推估西晉可能為鎮撫監督這群來自「西州」[32]之外來移民,特立頓丘為郡。惜史料未明言於曹魏時,是否亦在頓丘替這些外來移民設有典農官,遂難證頓丘是「罷農為郡」所改置之新郡。但頓丘位於鄴、洛陽兩司州大城間,雜居新置外來移民,若處理不當,反會造成內政上治安隱憂,遂可能使西晉政府考慮於頓丘置郡以鎮撫此輩,似為較合理之推論。
(二) 上洛
《晉書.地理志上》載:
上洛郡,泰始二年﹙286A.D.﹚分京兆南部置。(晉書,14/416,地理志上)
又見《三國志.魏書》載:
建安十一年(206A.D.)春正月,﹙曹﹚公征﹙高﹚幹……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三國志.魏書,1/28,武帝紀)
由引文可知,曹魏建安十一年時,上洛一帶已設都尉,故此郡亦合嚴耕望所謂「都尉部改制為郡」之例,但嚴氏文中並未提及此郡,於此補之。
(三) 平陽
《晉書.地理志上》載: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晉書,14/416,地理志上)
又見《三國志.魏書》:
(正始)八年﹙247A.D.﹚……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三國志.魏書,4/122,齊王芳紀)
《晉志》作河東為十二縣、《魏書》作十縣,究竟其縣數為何,暫非本節討論範圍(詳後)。然尋諸史料,暫無見平陽見載設有「都尉」或「農官」,則此郡並非由「都尉改郡」或「罷農為郡」二途析置之郡,其因何得置郡?參考《資治通鑑》載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6A.D.﹚: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之為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而同條胡注:「五部分居并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陽。」(資治通鑑,67/2146-2147,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條),由此條可推論,平陽設郡之因,可能係因為防禦南匈奴南侵洛陽京師而置。故在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之31年後,將原先由匈奴右賢王監視匈奴族五部、並以漢人為五部司馬監護之政策,改成設置為郡以威壓防禦,故可視平陽郡為司州之「邊郡」,為軍事型之郡國。
五、晉司州擴轄及鄴城諸郡探研
兩漢之司隸校尉,有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者謂之三輔﹚、河東、河內、河南﹙三者謂之三河﹚、弘農諸郡。至曹魏,將三輔及其西別立雍州[33],魏司州,僅存弘農以及其東之三河與平陽等郡。入晉,司州轄區卻東轄至鄴區四郡,即魏郡、廣平、陽平、頓丘。鄴區四郡,後漢時僅約當魏郡一郡耳,因曹魏致力開發此區而成為大邑,茲舉以下《三國志.魏書》數史料:
﹙建安﹚十七年﹙212A.D.﹚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三國志.魏書,1/36,武帝紀)
由此史料可知,時曹操鎮鄴,魏郡之鄴城為曹氏之政治核心區,操割鄴城附近鄰郡共十四個縣,皆劃入魏郡,以擴張魏郡腹地,這是曹氏致力開發魏郡重要之舉。
﹙建安﹚十八年,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三國志.魏書,1/42,武帝紀)
至第二年之建安十八年,概因魏郡轄區太大,操又分魏郡為東西兩部、各置都尉以分轄之。
﹙黃初﹚二年﹙221 A.D.﹚……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三國志.魏書,2/76,文帝紀)
至文帝曹丕時,以「都尉改郡」例,將東部都尉置陽平郡、西部都尉置廣平郡。比照前第二引文,可知操當時分魏郡為東西兩部,實則應該還有魏郡本部,共計三部,至文帝時,才將東西兩部都尉轄區各置新郡,本部仍存魏郡,原魏郡一郡至此分為三郡,亦可見當時魏郡戶口之巨[34]。
并土新附,習……領并州刺史……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三國志.魏書,15/469,梁習傳)
這是移并州民數萬口以實鄴區戶口之史例。
文帝即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三國志.魏書,15/482,賈逵傳)
由此條史料可知,不單魏郡已分為三郡,單以魏郡下轄之鄴縣,一縣竟達數萬戶,以三國時華北人口不過西漢一大郡[35]以觀之,此時鄴城已擁數萬戶,實為當時之大邑。
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三國志.魏書,15/479,溫恢傳)
魏文帝以內廷侍中之信臣,出鎮於鄴為太守,亦可見魏文帝十分重視此處。
由上引諸史料來看,鄴區於魏晉間已經營為繁榮大邑,至魏文帝黃初二年﹙221 A.D.﹚時尚切割出陽平、廣平二郡;入晉,再切割出頓丘,是為鄴區四郡。又見〈表4〉可知,晉鄴區四郡之戶數總數至少有133,200戶,約與京師河南尹相等,亦佔晉司州全戶數[36]之28.00%,故西晉朝廷刻意將此區納入司州,使司州同時掌控當時華北二大邑──洛陽與鄴,以直接控制之。
此外,亦可能另有政治性考量。因曹氏父子已居鄴數十年,是為漢末曹氏魏國封國所在,有其政治性象徵,曹氏宗族勢力於此盤根錯節,至曹魏末司馬昭專權時,司馬昭仍對之不放心而欲嚴密監控,如曹魏末司馬昭專權時,在鍾會作亂於蜀、司馬昭西征之際,仍不放心鄴城尚有許多曹氏宗族勢力可能會趁機為亂,令山濤帥親兵五百入鎮[37],可見鄴城政治重要性,連司馬氏亦不敢掉以輕心。西晉以司州同時掌控洛陽與鄴這二個政治都市,可見其政治目的。
六、略論三河、弘農地區縣改隸他郡原因
曹魏時致力開發鄴區,同時也大規模調整魏鄴區三郡之轄區範圍,轄地、轄縣皆擴增許多,其改變原因多為政治力介入、致力開發當地之結果,概如前述,茲不累敘[38]。本段則討論魏晉時期三河、弘農地區縣改隸他郡之情況,並略論改隸之各縣其可能原因為何,就本區郡級政區邊界之變動、及縣級政區改隸他郡,作更細部之研究。
(一) 河內郡蕩陰縣改隸魏郡
前述《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在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春正月史料載曹操專政時︰「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三縣以擴大鄴郡轄區。但參考《譚圖》研究成果,此後至魏代,原河內郡割鄴三縣只剩下蕩陰縣仍隸魏郡,於朝歌、林慮二縣仍還隸魏河內郡。若以空間距離角度觀之,筆者比照前述方法,量《譚圖》中蕩陰、朝歌、林慮三縣距魏郡治鄴縣距離,分別約得42.0、78.6、59.2公里,以蕩陰縣距魏郡治最近。故可能在為文帝黃初二年新置鄴區三郡前後之際,魏廷為考量鄴區三郡空間分佈合理性,不使距鄴縣過遠之朝歌、林慮仍隸魏郡,考量將之還隸魏河內郡,晉汲郡亦因之。
(二) 弘農郡盧氏縣改隸上洛郡
上洛郡為按「都尉改郡」慣例,由「上洛都尉」所改制之新置郡。此新郡僅轄三縣,分別為原魏雍州京兆郡之上洛、商兩縣;及弘農郡盧氏縣。推知原「上洛都尉」僅轄京兆上洛、商兩縣,後改制為郡時,轄縣太少,故割弘農郡距此二縣最近之盧氏縣以益之。
(三) 豫州潁川郡陽翟縣、陽城縣改隸河南尹
潁川郡陽翟縣、陽城縣皆位潁水上游段,陽翟縣則較陽城縣接近潁川中游;陽城縣則位較上流段、接近嵩山南麓。在漢代,河南、潁川兩郡以嵩山為界,以南為潁川郡境,陽翟縣尚為潁川郡治。入魏,卻將潁川郡治移至許昌,陽翟、陽城兩縣俱入魏河南尹。此處需問兩個問題,一︰為何潁川郡治會在魏時移治許昌?二:為何陽翟等兩縣會割入河南尹?首先第一個問題,應該與曹操迎漢獻帝入許昌、並改許昌為許都有關。《後漢書》載: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後漢書,80下/2653,文苑.禰衡傳)
又《三國志.魏書》載:
因為屯田,積穀于許都以制四方。(三國志.魏書,28/775,鄧艾傳)
可見曹操迎獻帝居許都時,因戰事需要、致力開發許都,積穀於此,人物薈萃,許都也成為潁川郡大邑,故日後中央將潁川郡治移至此。
潁川郡雖治移許昌,為何陽翟等兩縣卻又割入河南?推估可能為魏文帝丕時,雖都河南卻仍欲繼續加強對許昌之控制有關。加強對許昌之控制,有於利用兵孫吳之軍事目的。《三國志.魏書》載:
孫權復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三國志.魏書,2/82,文帝丕紀)
又載:
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三國志.魏書,13/399-400,鍾繇子毓附傳)
皆可見魏對孫吳用兵,需藉重許昌戰略要地。魏廷可能為加強控制許昌,不惜用「犬牙交錯」手法,將嵩山南麓之陽翟、陽城二縣改隸河南尹。
「犬牙相入」之行政區劃法為周振鶴所提出(周振鶴,1990: 106-136),其認為傳統中國行政區劃邊界劃分概有兩大原則,一是按「山川形便」原則,即以天然山川作為行政區劃邊界,使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劃相一致。漢河南尹與潁川郡邊界按嵩山為界劃分,即是符合此原則。另一原則即「犬牙相入」,即是與前述原則相反,係為政者刻意將行政區邊界與自然山川形勢不相重和,也刻意將一政區邊界拉到另一自然地理區域範圍內,對自然地理區外的另行政區加強控制[39]。故由魏廷將嵩山南麓潁水流域、原屬潁川郡地之陽翟、陽城二縣改隸河南尹之事上,可見其欲將強控制潁水流域、乃至潁川郡許昌要地、甚至整個豫州之企圖,以利南下對用兵孫吳之戰略控制。
(四) 弘農郡新安縣改隸河南尹
弘農郡與河南尹,以函谷關為界,新安縣在關之西,在漢、魏兩世皆屬弘農郡轄,關之東則隸河南尹轄,這本屬符合「山川形便」原則之合理行政空間區劃。晉廷將新安改隸京師河南,很可能同於前述陽翟、陽城兩縣般,是朝廷利用「犬牙相入」原則刻意重劃政區邊界之結果,將函谷關西側之新安縣,直隸京師河南尹,使京師更能直接控制函谷關以西之地。由新安、陽翟、陽城三縣之區劃安排,可看出晉廷欲加強河南尹控制京師附近、與鄰近不同自然地理區之企圖,不使山勢自然阻隔,削弱河南尹對不同自然地理區之鄰近縣份的控制力,使河南尹能越山、越關而治郊縣[40]。
(五) 弘農郡陸渾縣改隸河南尹
漢陸渾縣屬弘農郡,與河南尹新城縣同屬伊水中游段,依《譚圖》所繪,筆者按前述方法量得兩城直線距離相距僅約20公里,實頗為相近之兩縣。然在兩漢,兩縣卻分屬不同郡所轄,陸渾隸弘農;新城隸河南。陸渾縣在漢世隸屬弘農郡,實不合理,因伊水與洛水同為西南往東北流、再會合於洛陽城之兩水,洛水在北、伊水在南,兩水中尚夾有熊耳山區,若要由陸渾縣往弘農郡治,必須橫越熊耳山與洛水峽谷,且北過洛水後,尚需翻越崤山山區,才能抵黃河沿岸之弘農郡治。故陸渾隸弘農,兩地交通來往不便,不若陸渾至洛陽只需順伊水而下即可。且陸渾縣順伊水而下,即是新城縣,新城在漢世即屬河南,陸渾縣卻遙屬弘農,甚不合理。故魏世改將陸渾隸河南,很可能是為更正以往不合理之行政空間安排,利用「山川形便」原則,使河南尹西南界線合理化。
(六) 河東郡端氏、濩澤兩縣改隸平陽郡
《晉書》載: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晉書,14/416,地理志上)
又見《三國志.魏書》:
﹙正始﹚八年﹙247 A.D.﹚……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 (三國志.魏書,4/122,齊王芳紀)
由前引史料可知平陽郡在247年割河東郡北部置此郡,《魏書》作平陽郡轄十縣、《晉志》作轄十二縣,也可知魏初設河東郡時,本轄十縣,日後又增領二縣,即端氏、濩澤兩縣。但何時增領之?目前暫不詳,但可知是魏末晉初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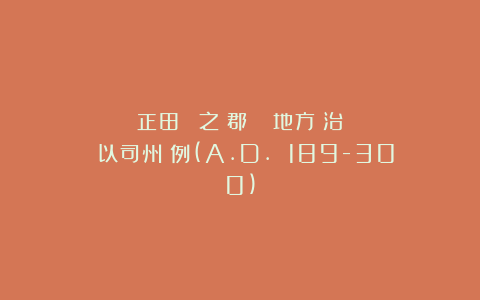
為何247年新設河東郡時只轄十縣,日後又要增領端氏、濩澤兩縣?首先比較〈附圖2〉、〈附圖3〉,可知端氏、濩澤兩縣區,皆在晉河東郡東北、平陽郡東境之地。此區地形狀況究竟有何特色?是否兩縣改隸與當時交通線分佈有關?本文計畫考察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嚴耕望,1985,第5卷)對此區交通線分布狀況研究成果,或可知兩縣為何要改隸之因。
首先要說明,嚴氏此書雖為研究唐代交通道之成果,唐道也不一定完全等於魏晉時道,然嚴氏此書多根據中古以來各種史料考證之研究成果,其大致仍可反應中古前期交通道概況,故本文斟酌參用之。首先必須了解端氏、濩澤二縣在唐代之地名,才可能參用嚴氏前引書。依《新唐書.地理志三》可知,端氏縣在唐代仍襲用舊名;而濩澤縣則改名陽城縣(新唐書,39/1008)。據《唐代交通圖考.河北河東區》中之〈唐代河東太行區交通圖(南幅)〉一圖可知,唐端氏、陽城二縣在沁水流域中游段,沁水流域為南北向之河流,為狹長峽谷地形,東、西兩側皆有山地。沁水中游區段,東隔刁黃嶺與唐潞、澤地區[41]相鄰;西隔烏嶺山地與汾水、涑水二流域相鄰[42];西南則隔王屋山脈。參考本文〈附圖2〉、〈附圖3〉,則可知魏時河東、平陽二郡,在端氏、濩澤二縣區,是以烏嶺山脈為郡界,端氏、濩澤二縣區是橫越王屋山區隸於魏河東郡;晉時則改以王屋山為郡界,二縣區改以越過烏嶺山脈隸於晉平陽郡,可知魏晉之際,二郡界的調整,關鍵在此。但為何晉廷要將郡界由原先烏嶺山脈改為王屋山區?參考前引嚴氏〈唐代河東太行區交通圖(南幅)〉所繪交通路線即知矣。唐代烏嶺山地,有兩條東西向烏嶺道可通汾水流域下游區、與沁水流域中游區[43],若中古前期這兩道也存在、或至少存一條道路的話,這條烏嶺道即是聯絡晉平陽郡治與端氏、濩澤二縣區之重要交通道。而王屋山區,據嚴氏《唐代交通圖考.河北河東區》考證,在唐代尚沒有任何官道可連絡涑水流域、亦即魏晉之河東郡本部,何況中古前期之魏晉時代,王屋山區很可能也沒有官道可連絡「河東郡本部」與「端氏、濩澤二縣」兩地。故知端氏、濩澤二縣改隸晉平陽郡之因,是在交通路線上便隸於平陽郡而不便於河東郡,故晉廷改隸之,也可見晉廷對河東、平陽兩郡行政區劃空間分配合理性之重視[44]。
七、晉司州區增、廢縣情形略探
歷史上郡、縣治所的選擇,往往代表政府基於統治需要與現實環境選擇之結果。本文前數節已討論漢晉之際郡級政區置廢、郡界變更情形,並探究此際中央政府對司州區郡治與轄縣、邊界之選擇,觀察當時中央政府對司州地區郡級政區的重新安排。本節則希望更進一步,略探漢晉之際對晉司州區移、增、廢縣情形,一窺漢晉之際中央對晉司州區縣級政區重新調整的情形。
要略論縣治之移、增、廢,首先當了解「縣」在傳統中國地方政區的空間性質,才能了解傳統中國在縣級政區作重整時之用意。由《漢書》載:
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 (漢書,19上/742,百官公卿表第7上)
可知古代中國縣級政區概以方百里為合理空間範圍,人口密度大則減少之,密度稀少則增加之,視該地方實際狀況予以合理調整。周振鶴也指出,中國歷史上「百里之縣」,幅員一直相當穩定(周振鶴,1990: 65-71)。故本文定義「移治縣」為約百里範圍內某一縣廢,但另一新縣又同時在此範圍內設置,雖縣名不一定完全繼承,但仍是為「移治縣」。「新增縣」、「廢置縣」則顧名思義,在一地區鄰近縣份都未變動情況下[45],國家應實質需要增、廢某縣。
筆者分別觀察本區漢縣、魏縣、晉縣三時期縣級之置廢情形,發現一移治縣、二新增縣、五廢置縣,茲分介紹如後:
(一) 臨水移治縣
本區唯一一個移治縣,即漢冀州梁期縣。漢梁期縣之廢,據楊守敬考證,是在後漢末年廢(水經注疏,10/944-945,清漳水、濁漳水),《晉書》即載有臨水縣(晉書,14/415,地理志上.司州廣平郡條);《晉書.竇允傳》亦載:
泰始中……拜臨水令。(晉書,90/2332,良吏.竇允傳)
則確知至晉武帝泰始年間已設臨水縣,推估此縣是魏至晉初置。據筆者按按前述方法量測《譚圖》結果,在魏時曾南移約14.7公里,尚在古代「百里之地」範圍內,並改名為臨水縣,合於本文「移治縣」之定義,可視為漢梁期廢縣之移治縣。據譚其驤研究成果之《譚圖》,其在魏代地圖即繪出此縣(譚其驤,1992,3冊: 11-12),若依其研究,則魏時已置此縣。
若依譚其驤研究成果,為何魏廷會選擇在漢梁期廢縣「百里之境」重置新縣?是否可藉由其移動路線,看出國家考慮此縣設廢因素之端倪?據筆者按前述方法量《譚圖》,恰得漢梁期縣移往臨水縣是偏向鄴城方向移動約14.7公里;又得臨水縣只距鄴城約7.35公里[46],距鄴城極近,乍看之下反是個空間安排不恰當之縣。然恰巧在漢魏之際,曹氏政權曾大力開發鄴區,推知本縣可能因應鄴區之開發,鄴城附近人口激增,故此縣移治極靠近鄴城之地,重置新縣。
(二) 長樂新增縣
長樂縣是本期晉司州區新增縣,乃魏新增縣,同時此縣也是位於鄴區附近,很可能是位因應此際鄴城附近人口增加而設。由〈附圖4〉可看出,長樂縣是位魏郡之鄴、魏、安陽、蕩陰、內黃等諸縣略中心位置,與諸縣略城等距狀況、為約20-40公里之等距中心點,在此際鄴區人口增加狀況下,符合前述「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原則而設置之新縣。
(三) 安陽新增縣
安陽縣亦是本期晉司州區新增縣,乃魏新增縣,此縣也是位於鄴區附近,也很可能是位因應此際鄴城附近人口增加而設。安陽縣是位魏郡之鄴、長樂、蕩陰等諸縣略中心位置,與諸縣略城等距狀況、為約20-40公里之等距中心點,在此際鄴區人口增加狀況下,符合前述「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原則而置之新縣。
(四) 原武廢縣
本期本區廢縣數達五,分別為原武、新鄭、榖城、波、輪氏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廢縣,悉在魏司州區,亦即在晉司州新轄之鄴區四郡,因曹魏致力開發人口大增,無廢縣之需;而魏司州區因處四戰之地人口銳少,故廢縣多。但原武是其中唯一一個由郡級政區被廢後又旋即被廢縣者,故特此獨立小一節述論。前已述原武本曾因為「罷農為郡」政策下一度設郡,但晉初旋即被廢郡。然原武在廢郡後仍被廢縣,推估可能係因原武地望過近於其南向之陽武縣,因而被廢縣。筆者按前述方法實際量測《譚圖》,發現原武距陽武縣不過約9.45公里,若因應本時期天下人口大減,「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三國志.魏書,14/453,蔣濟傳)之歷史背景下,這種縣距過短之縣,很可能陷入被廢命運。以下新鄭等四廢縣可能也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或加上因縣距過短,遂一一被廢,略述於後小節。
(五) 新鄭等其他廢縣
其餘新鄭、榖城、波、輪氏等四廢縣,分別述論如下:新鄭廢縣,漢、魏縣,晉廢。位於滎陽郡南方洧水上流段,鄰縣為苑陵、密兩縣,可能因人口銳減、縣距過短因而被廢。
榖城廢縣,漢、魏縣,晉廢。位洛陽西側榖水流域,概與南方洛水流域之河南縣過近,距筆者量《譚圖》,得此兩縣距僅約8.4公里,很可能係縣距太短而被廢、併入河南縣。
波廢縣,漢縣,魏、晉廢。位河內郡野王縣之西,距東向野王、北向沁水、西南向河陽、西向軹等臨縣皆過近,在人口大量銳減的歷史背景下,這種縣距過小之縣也淪入被廢命運。
輪氏廢縣,又作綸氏,漢縣,魏、晉廢。本縣本為漢豫州潁川郡轄縣,隨同前述潁水流域上游段之陽翟、陽城兩縣地區被併入魏司州河南尹,但本縣可能在前述兩縣被併入河南尹過程左右時被廢。不過本縣被廢之因可能與縣距過小因素無關,而是在其自然地理環境本就在嵩山南方之陽乾山附近,也是潁水發源地[47]。這種城鎮可能是先秦時,因山高地勢險要而設之軍防型城鎮[48],人口可能本就不多,故在魏晉之際人口銳減歷史背景下被廢[49]。
(六) 小結
根據本節研究,發現魏、晉時期,對晉司州區縣級政區更動者有七,其中廢縣高達五,佔總更動數七縣之71.43%。故知本期本區,魏、晉朝廷對縣級政區施政趨勢,決然不同於郡級政區因應既有農官、都尉等行政組織之「增設」,反對縣級有所裁撤。這顯然是反映出當時人口減少,不需要太多縣級政區統治人民,至少本文可在本期本區縣級政區之變動上,看到此趨勢。
至於本期本區唯一一移治縣、與二增置縣,皆是在鄴區附近,這也很可能是因應本期鄴區附近大量開發,戶口增加,出現百姓甚或豪族「多不法」之情況(三國志.魏書,15/482,賈逵傳),中古前期強宗豪族崛起之歷史背景,也很可能已在鄴區萌芽。故國家對鄴區之行政控制,除了郡級政區從一調整為四郡外,對縣級政區也增治二新縣、並向鄴城附近移動一縣。這種調整,在本區已達五廢縣下,更顯示出國家對鄴區人口增加之重視程度。這也象徵在鄴區之外的魏司州、也就是以洛陽為中心之政治最核心區,漢晉之際,全都採廢縣之施政傾向,全無一增縣,這更可反映出本期國家對實際上人口大量減少狀況下的現實施政取向。
八、結論
前言雖有提及傅咸感慨而上言西晉人口遽少,卻而徒增郡國。但漢晉之際,州郡縣膨脹積習已久,如前言嚴耕望所舉二十五例由都尉改制為郡者,至少有九者為孫吳所設,五者為蜀漢所設,四者為曹魏所改,一者為劉璋所改。亦即晉武於太康元年﹙280 A.D.﹚一統天下時,至少依嚴氏所考之例中,已見有十九個,晉廷概必順勢因襲。若觀晉廷對司州政區之安排的「鄴區納於司州」及「改農官為郡後、仍有數者被廢」之二施政,可見朝廷決策群頗明智。至少對司州區而言,晉廷將空間規劃不合理之原武、宜陽、野王等郡裁撤,不能直說晉廷對此只是「空張郡國」數目。但若要大廢漢魏以來各地新設之郡國,尤其對政治核心區之司州而言,恐亦會直接危及政局穩定。若以晉武個人常因循陋風之性觀之[50],很可能亦無力做大廢郡國之改革,對於已成實質官僚體系化之部尉、農官之流,亦予以正名化,以收籠其對晉廷之支持與效忠,以維持晉廷統治之穩定。且,兩度的罷農為郡令,分別於曹魏咸熙元年﹙284 A.D.﹚及西晉泰始二年﹙286 A.D.﹚年間頒布,此時正是晉武欲奪曹魏政權之際,此種推論合理性甚大。至少對晉司州之觀察,可看出這個現象。
然都尉及民屯農官之實質化,亦是使西晉朝廷會採取將之「正名」之另一因,在領實土實民之情況下,與其名義上原先屬郡很可能已無實質上從屬關係,亦是魏晉間郡國數膨脹之本質原因之一。
西晉官僚決策群並沒有料到帝國後來會崩壞如此快速,故在政區安排上,亦當會考量其空間合理性,以圖長治。依嚴氏研究,晉廷對天下新增郡國的政策,是因襲本來郡國膨脹之政治慣例而不多作裁廢改革。而本文則針對中央政府所在的政治核心區司州做研究,亦發現晉廷沿襲「都尉改郡」、「罷農為郡」兩政策,除少數極不合空間合理性之郡國外,盡量對新增郡國不多加裁撤。此外,晉廷對曹魏為防禦南匈奴而設之平陽郡,也仍予保留。
此外本文發現,在晉司州轄境的東移上,可見晉廷欲利用司州行政區劃,控制華北新生精華區——鄴區四郡之企圖。鄴城之開發始於曹氏,曹氏宗族勢力在此亦盤根錯節,利用司州管轄此境正可加強對鄴區之控制。故鄴城﹙魏郡﹚於兩漢數百年本皆隸於冀州,晉廷將司州轄境橫跨至此,可說明晉廷欲鞏固政治核心區穩定性之企圖。
州、縣治的選擇往往代表政府基於統治需要與現實環境選擇治所之結果。對於漢晉之際朝廷對勁司州區縣級政區之調整,卻不同於郡級政區,而傾向採取廢縣趨勢,反應本期人口大量減少,「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之歷史背景下,國家雖仍欲保留縣級政區統治殘存人民,仍採適當廢縣措施。除鄴區附近有一移治縣、二新增縣外,在鄴區之外的魏司州區、也就是以洛陽為中心之政治最核心區,漢晉之際,全都採廢縣之施政傾向,全無一增縣。這是本期國家對郡、縣兩級政區施政傾向決然不同之處。而由魏司州區與鄴區二區域相比較來看,前者悉採廢縣趨勢,廢縣數達五;後者仍有二增置縣、一移治縣,鄉對也反映出漢末魏朝時鄴區人口增加,使國家將鄴區納入司州控制範圍之現象。
再論晉司州區郡級政區之變動方面,本區畢竟有少數農官改郡又見廢者,如野王、宜陽、原武等,這些本是因空間不合理而廢之新郡,然晉廷對這些郡下之官僚群,是否有做若干人事安排,以安撫這些喪失既得利益之人?目前似不見史料載其詳細過程,故尚不得知其中詳細。又,筆者曾推思一個疑點,亦似找不到相關史料而苦無從推論,即是當時因晉廷實行九品中正法,是否亦會造成一種情形,即晉廷利用膨脹郡國可增加「郡中正」之名額[51],使士人階層就宦途管道更多,故因此使晉廷對新增郡國數目亦難大加裁廢,或多因襲由「都尉改郡」、「罷農為郡」所新增郡國,增加郡中正數目以收攬人心?此或許可供學界更作進一步研究。然或許從本期縣級政區為因應實際上人口大量減少、而多加裁撤之施政傾向,反映到本區郡級政區之卻以增加為施政傾向上,可反證此疑問之可能性。
本文原載《中華人文社會學報》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