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狄震
游记小说:关中“冷汉”闯关东
七月的日头毒得能烙饼,渭河边的土路裂成碎块,跟老树皮褪的鳞甲一样翘着边。董安里老槐树下围了半村人,眼窝子全黏在那辆墨绿硬派越野上——车胎比碾场的滚子还粗,车标亮得能照见人影,引擎盖上的新车蜡在日头下闪着贼光,连苍蝇落上去都得打滑。四个影子挤在车旁,看着不像是一路人,却都是关中地面上长起来的“冷”性子。
陕西人说的“冷”,原不是指天寒。年轻娃叫“冷娃”,汉子就叫“冷汉”,说的是那性子——看着硬邦邦跟秦岭的顽石一样,心里头却藏着一团火,不声不响就把事办了,认死理的劲儿,九头牛都拉不回。喜子哥、华丛荣、大官人,再加上我这个揣着牛皮攻略本的,凑在一块儿倒真应了这“冷”字,就是没出门前,谁都没觉出自己那点性子,原跟黄土高坡的沟壑一样,深得很呢。
我抱着三本画满红圈的攻略,牛皮本封皮上“环东北大冒险”五个字用红笔描得发亮,边角都被我摸得起了毛。心里头念着老师的话:“东北的雪比关中的麦垛厚,风光比渭河里的浪花多。”旁边的华丛荣,单手撑着车门,牛仔裤卷到膝盖,露着沾土的帆布鞋,鞋头还破了个小洞——她是华阴独一份的“冷姑娘”,说话脆生生的:“这铁疙瘩,我改了仨月,避震器换了越野款,油箱加了副油箱,出门靠谱得很,撒野也跑得欢!”
“丛荣!你得是疯了?把自己攒了三年的旧越野改得这么野?”二嫂子拍车顶的嗓门,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掉了我一脑袋槐树叶。喜子哥揣着鼓囊囊的行李包,黄铜皮带扣闪着光,嘴贫得没个正形:“路线咋走嘛?别绕远路,我昨儿个激动得没睡好,腿都软咧。”大官人背着洗白的帆布包,攥着本卷边的《地理风物志》,裤兜里藏着写满打卡点的烟盒纸,字是用铅笔写的,密密麻麻:“秦岭长,渭水长,关东路远得很,咱去闯一闯!”
“走咧!”华丛荣踩下油门,引擎吼得跟出栏的豹子一样,震得地面都发颤。“沿G331绕东北那‘大鸡头’,先去阿尔山、满洲里,再到根河、漠河,最后顺着滨海公路回屋!”
刚拐出村口,车猛地颠了一下——准是压着路上的石坷垃了。我在后座没坐稳,攻略“哗啦”一声掉在脚垫上,捡的时候手忙脚乱。喜子哥正歪着身子啃牛肉,“哧溜”一下就滑下去,后脑勺磕在中控台上,疼得他直骂:“你个碎怂!咋毛手毛脚的?”大官人坐在副驾后排,笑着弹掉烟蒂:“没事嘛,路上的小插曲,反倒有意思。你蜷着腿,正好减肥。”出门前大伙就商量好,遇事拿不定主意就问大官人,他比咱稳当。
车过黄河大桥,河泥的腥气顺着车窗缝钻进来。浪头拍着桥墩,跟敲闷鼓一样,浑黄的河水卷着泥沙,宽得望不见边,比西河宽了足足十倍。我扒着车窗挥手,学课本里写的“告别故乡的河”,手刚伸出去,就被风灌了一袖子土。喜子哥突然拍大腿,嗓门比浪声还大:“哎呀!我买好的清真牛肉,忘在书桌上咧!”大官人慢悠悠掏出个油纸包,递到他跟前:“早给你塞包里了,怕你路上馋。到服务区再吃,我还能忘你那点馋嘴毛病?”喜子哥接过来,凑鼻子底下闻了闻,嘿嘿笑了。
一天跑了千里路,进了内蒙国道就成了土路,车颠得骨头缝都疼,我手里的攻略本都跟着“哒哒”响。偏巧,手里的攻略,夹撕的是标着左云县、金沙滩的那页——那是我特意标红的“杨家将古战场”,急得我直跳脚,眼泪都快出来了。华丛荣停下车,点开手机导航,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划:“过了海子山往前二十里就到呼和浩特了,先逛趟塞上老街,正好找家打印店补份攻略”
清早的呼和浩特,青石板路被阳光照得发亮,路边的奶茶店飘着奶香味。从大召出来,直奔草原,清风裹着青草香扑进车窗,比关中的麦香还清爽。咱时不时就停车,拍那跟绿绸子一样的草原,牛羊跟撒在上面的珍珠似的,还有骑马的牧民,鞭子一甩,“驾”的一声,马儿就跑远了。华从荣举着手机拍个不停,嘴里念叨:“得发个朋友圈,配文就写‘关中冷汉闯草原’,馋哭华阴的伙计们!”穿大阴山的时候,喜子哥指着窗外的山路:“这是白道,古时候当兵的走的路,咱现在走,也算是踏了回古路,沾沾英雄气。”过了武川,走四子王旗,路边戍边战士的塑像衣角翻飞,二连浩特的国门在雨里红得扎眼。远处的额仁达布散淖尔盐湖泛着银光,跟撒了把碎银子;恐龙地质公园的驿路博物馆里,石林和野外的石头奇形怪状,有的像展翅的雄鹰,有的像卧着的恐龙。我蹲在旁边画个不停,铅笔都快断了,大官人对着岩石纹路研究半天,突然拍了下我肩膀:“这是地球的年轮嘛,你看这纹路,一圈就是几百万年。”
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越来越绿,深绿的草长到齐腰深,牛羊散在里头,只露个脑袋,蒙古包飘着奶白的炊烟。岔路边的临时摊点上,呼市农大草业专业的学生阿古拉守着沙果、蓝莓摊,黑红的脸上挂着笑。他家里有万亩草场,说起草原眼里闪着光:“我学草业,就是想让草原一直绿着,草绿了,牛羊就肥,日子才能甜。”当晚咱在东乌小镇吃大饺和烤肉米饭,就着咸奶茶,香得人舒坦。喜子哥吃得满嘴流油,还不忘跟老板夸:“比屋里的臊子面还顶饱!”
暮色里,车开进了阿尔山,先扎进地质公园——黑色的火山岩铺在地上,气泡痕迹清楚得能数见,我蹲在上面摸,硌得手疼;天池蓝得跟宝石一样,映着深绿的山,听说这池子里没有鱼,因为水太凉;柴源峡谷的水清亮得能看见底,地质裂变过的石头泛着青白色,水流过石头,哗哗地响,跟唱歌似的。林间一堆忙忙碌碌的蚂蚁,让大官人想起课本里的兴安岭红蚂蚁,我凑过去看:“跟咱关中的蚂蚁不一样,壮实得多,黑得发亮!”林区深处,松针的清香扑鼻子,路边“抗联老木屋遗址”的木牌漆皮都掉了,门框上“保家卫国”四个字虽说模糊,却透着硬气。我画松树的时候,跟喜子哥吵了起来——我说“画里加些极光才好看,咱说不定能看着”,他拍着桌子:“这山里埋着先烈的骨头,瞎画是糟践历史!极光哪是这儿能看着的?”大官人赶紧递烟劝和,结果慌里慌张,给我递了他抽的粗烟,给喜子哥递了细烟。我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喜子哥抽着细烟,也咳得直摆手,我俩对视一眼,倒先笑了。
呼伦贝尔大草原天高云阔,新巴尔虎右旗的那达慕正好开着,鼓点声老远就撞进耳朵,震得人心慌。喜子哥眼尖,隔着人群就瞅见“正宗锅包肉”的摊子,拉着我就跑,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最后一盘锅包肉,被个穿红裙子的姑娘买走了。他急得直跺脚,赶紧追上去:“妹子,等一下!我兄弟头一回来东北,就想尝口锅包肉,你能不能分咱一半?我给你钱!”拉扯间,姑娘手一滑,盘子“哐当”一声摔在地上,金黄的锅包肉撒了一地。姑娘慌着要赔钱:“对不起对不起,要不……去俺家吃?俺妈今天刚炸了锅包肉,放了野山杏酱,比这还香!”
这姑娘叫其其格,蒙古包里她妈正围着灶台炸锅包肉,油花四溅,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喜子哥凑在灶台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刚炸好的锅包肉,他捏起一块就往嘴里塞,烫得直哈气,还含糊着说:“比华阴的肉夹馍还香!阿姨,您这手艺,能开馆子了!”华丛荣跟着其其格学煮奶茶,先放砖茶,再放牛奶,煮得咕嘟咕嘟响,学得有模有样,就是最后放糖的时候,放多了,甜得发齁。
离开蒙古包的时候,其其格骑着马追来,马跑得飞快,马尾辫在风里飘着。她塞给华从荣一袋野山杏酱:“去满洲里吃锅包肉,蘸着这个香!”又红着脸对喜子哥说:“下次来,俺还带你吃俺妈做的锅包肉,再带你去看草原的日出。”喜子哥耳根子都红了,挠着头说:“下次给你带华阴的肉夹馍,正宗得很,皮酥肉香!”
车里大伙戏语喜子哥,其其格如此有意思,喜子哥说:那天夜晚在阿尔山街上看篝火,那个唱歌的蒙古姑娘穿着红裙子,当时觉得很漂亮,多留意了几眼。原来她第二天就回到呼伦贝尔,参加草原上的那达慕活动,因而就熟识些罢了。
满洲里的俄式建筑蓝黄相间,跟童话里的房子一样,列巴的麦香混着格瓦斯的甜气,飘得满街都是。套娃广场上,十几米高的套娃蓝眼金发,裙摆上绣满花纹,我蹲在旁边画画,画得正入神,突然被个俄罗斯老太太拽住胳膊。她头发花白,戴着花头巾,手里攥着个小套娃和巧克力,硬是塞给我,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俄语。我赶紧掏出刚画好的套娃速写,递给她,她竖着大拇指说“хорошо”(好),我也学着说“спасибо”(谢谢),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眯了。
往根河走的路,草色越来越淡,松林越来越密,天也越来越凉。半路上车爆胎了,华丛荣蹲在路边换备胎,从工具箱里摸出个旧指南针——是她二十八岁攒钱买的头一样户外装备,边缘都磨得发亮。她一边拧螺丝,一边说:“当年我就想着,以后要开着车,带着这指南针,去最远的地方。”我抱着攻略本蹲在旁边翻,突然指着“敖鲁古雅”的红圈喊:“到根河必须去这儿!咱去看驯鹿!攻略上说,驯鹿挂着彩绳,可有意思了!”
沿着额尔古纳河走进根河,根河原名额尔古纳后旗,根河的敖鲁古雅,是最后的驯鹿部落。七月的雨中根河还存着残雪,驯鹿挂着彩绳,踩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梅花印。我蹲在鄂温克姑娘旁边看喂驯鹿,手里拿着冻奶豆腐,没留神脚下一滑,摔了个屁股墩,手里的冻奶豆腐飞了出去,正好砸在一只小驯鹿的头上。小驯鹿受了惊,撒腿就跑,我急得直喊,最后还是鄂温克小伙骑着马,慢悠悠牵着驯鹿领了回来。我给小驯鹿喂了块冻奶豆腐,它舔了舔我的手,痒痒的。那天晚上,我终于把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听完了,鄂温克人的故事,像根河的水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临走在街边尝了支根河老冰棍,冰得我牙都快掉了,却越吃越上瘾。
从根河往漠河走要绕进林区小道——夏日的林子早变了色,樟子松的深绿、白桦的米黄、山杨的火红,一层层叠着,风一吹,叶子“哗哗”响,跟打翻了关中染坊的颜料缸一样。“层林尽染”四个字,以前只在课本里见过,这下才算真见着了。车开得慢,喜子哥把窗玻璃摇到底,伸手接飘下来的枫叶,枫叶红得像火,他喊着:“比华阴的五角枫叶红得烈!俺要摘几片带回去,给其其格当书签!”我趴在车窗上画秋林,笔尖沾了风,连线条都带着夏的脆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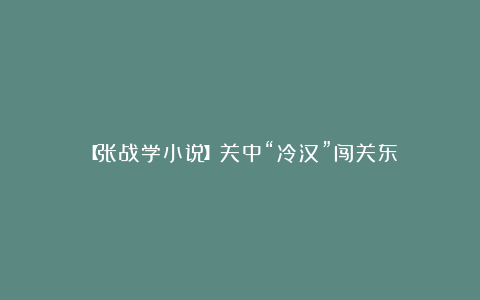
走着走着,我瞅着喜子哥那憨样,忍不住逗他:“喜子,你说其其格要是知道你连个玉米都串不利索,上次烤串把玉米烤成黑炭,还会不会给你做锅包肉?”喜子哥斜我一眼,嘴硬得很:“你个碎怂懂个啥?俺那是让着老太太,真要比,你串仨俺能串五个!再说了,俺烤的炭烤玉米,那是特色!”大官人在旁边笑:“你俩别瞎谝了”喜子哥不服气:“陷了咋咧?俺们关中汉子有的是力气,大不了抬着走!”我接话:“就你那怂样,上次搬行李,抬两步就得喊累,还不如大官人稳当。”大官人弹了弹烟灰:“你俩少吵两句,前面就到冷极村了,进去喝碗热汤。”
根河深处藏着神州最冷的“冷极村”,华丛荣笑着打方向盘:“都到这儿了,去沾沾‘中国冷极’的气!说不定以后跟人吹牛逼,还能说咱去过中国最冷的地方!”村里木栅栏围着矮房,房檐下挂着金灿灿的玉米串,跟灯笼似的,门口堆着半人高的柴火垛。一个穿花袄的老太太正蹲在门口晒蘑菇,见人来,赶紧站起来,往屋里喊:“柱子,来客人咧!”出来个黑壮的小伙,是老太太的孙子,胳膊上的肌肉块子鼓鼓的。听说咱从陕西来,非要拉着喝杯热茶。老太太端上冻梨,黑黢黢的,咱啃着带冰碴子的梨,听柱子讲冬天的冷极村:“零下五十度,撒泡尿都能冻成冰棍,出门得裹着棉被走!钢笔水都能冻住,写不了字!”喜子哥听得咋舌,掏出包里剩下的清真牛肉干递过去:“尝尝咱关中的肉,跟你们的冻肉不一样,有嚼劲!”柱子接过去掰了块,塞给老太太一块,又抓了把刚晒好的榛蘑塞进我包里:“路上炖肉香得很,比你们的香菇鲜,俺妈说这是山珍!”
林区的路越来越窄,路边的落叶铺了厚厚的一层,车开过去“沙沙”响。没留神,车轮陷进了落叶下的泥坑,轰油门的时候,泥水溅了华丛荣一裤腿,黑一块黄一块的。正愁着,林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一个扛着斧头的老伐木工走了过来——头发花白,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跟我攻略本里画的林区老人一模一样。老伐木工没说话,放下斧头,从车上卸下来根粗木杠,帮咱垫在车轮下,又喊着号子:“一、二、推!”咱四个跟着一起使劲,车“呜”地一声就冲了出来。华丛荣要给钱,他摆手说不要,指着我怀里的攻略本问:“要去漠河看极光?”我点头,他从口袋里摸出个桦树皮做的小盒子,递给我:“里头是松脂,点着了能驱蚊,漠河晚上蚊子凶得很,能把人叮成包子。”后来才知道,没了林木可伐的伐木工人,都摇身变成了护林员,守着这片兴安岭森林,跟守着自家孩子一样。
到北极村那晚,豪气的兴安老妹带我们住进民宿,又送大伙到黑龙江边——看神州北极石碑、哨所、邮局,找北字广场上的各种“北”字,脚都走酸了,最终却没见到极光,只因没完没了的雨。大官人蹲在江边,掏出本子纸,用铅笔写:“根河雪,驯鹿苔,冷极秋,
到北极村那晚,豪气的兴安老妹带我们住进民宿,又送大伙到黑龙江边——看神州北极石碑、哨所、邮局,找北字广场上的各种“北”字,脚都走酸了,最终却没见到极光,只因没完没了的雨。大官人蹲在江边,在手册上用铅笔写下:“根河雪,驯鹿苔,冷极秋,榛蘑香,漠河夜,极光来,关中客,乐开怀。”写完自己先笑了:“虽没见着极光,倒把一路的念想都写全了。”我抢过烟盒纸,在末尾添了句“雨也甜”,喜子哥凑过来,非要加上“锅包肉香”,华丛荣没动笔,却把手机里拍的其其格送的杏酱照片设成了屏保。
第二天从北极村往回走,刚出村就吵了起来——喜子哥嫌攻略上的路线绕,盯着导航上一条虚线小道直嚷嚷:“俺看导航上有条近路,俩小时就能到塔河,按攻略走得绕半天!说不定还能抄着近路看个不一样的林子!”大官人翻着《地理风物志》,眉头皱成个疙瘩:“这小道连个名字都没有,没标在正经地图上,雨天泥多,万一陷车咋办?”我抱着攻略本帮腔:“试试嘛,说不定能省时间,还能捡着野蓝莓!”
华丛荣没说话,盯着导航琢磨半天,突然猛打方向盘,却不是往小道走,而是拐回了正路:“听大官人的。林区小道雨天容易滑坡,咱按攻略走正规路——再说了,绕点路怕啥?路上的风景,多瞅一眼是一眼。”喜子哥急了,嗓门拔高:“你就是怂!咱关中冷汉啥时候怕过这点泥?”大官人也来了气:“不是怂,是稳当!昨天陷车是谁喊着胳膊酸,推完车蹲在路边揉胳膊?”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我赶紧递烟,华丛荣猛踩了脚油门,引擎“呜”地一声:“别吵了!按攻略走,到塔河我请你们吃锅包肉,蘸着其其格的杏酱,管够!”喜子哥哼了一声,却悄悄把副驾的安全带系得紧了些——他心里头,其实比谁都认大官人的稳当。
没走多久,天就阴得跟墨染似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车玻璃上,越下越大,雨刮器开到最大档,刮得“咯吱”响,还是赶不上雨下的速度。到塔河的时候,雨已经成了瓢泼的,路边的林区市场积水没过脚踝,喜子哥原想给其其格买蓝莓干,这下也没法下车,只能隔着车窗跟摊主喊价,喊了半天,嗓门都哑了,才以“比关中贵两毛”的价格买了两袋,小心翼翼揣进怀里,跟护着宝贝似的。
过小兴安岭的时候,雾气裹着雨,国道旁的林海蒙着层白纱,连路牌都看得模糊。大官人盯着前方,眼睛都不敢眨:“慢点开!前面有急转弯,路边就是沟!”华丛荣紧握着方向盘,额头上渗了汗,手心都湿了,却还笑着说:“放心,这铁疙瘩我改了避震,经得住!”话音刚落,车就滑了一下,吓得我手里的攻略本差点掉地上,喜子哥也不吵了,攥着扶手,大气不敢出。
好不容易到了五大连池,雨才算小了点。火山口的堰塞湖蒙着层雾气,跟披了层纱似的,湖边的火山石被雨水浇得发黑,坑坑洼洼的。我撑着伞蹲在旁边歇脚,喜子哥凑过来,踢了踢脚下的石头:“这石头湿了倒比煤渣子好看些,就是硌脚。”大官人敲了敲石头,突然叫我摸:“你摸摸,还热乎着——这是火山岩,里头藏着地下的火气,雨天也凉不透。”我伸手一摸,果然暖烘烘的,跟揣着个小暖炉似的。
雨又下了起来,一路伴着进了北大荒。金黄的稻穗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垂着,跟弯腰鞠躬似的,收割机停在田边,老乡们站在屋檐下跟咱挥手,手里还挥着刚摘的黄瓜。一路冒雨赶,天擦黑才到哈尔滨,俄式建筑上的霓虹灯在雨雾里闪着光,跟撒了把星星,晚上住的民宿就在道里大街旁,推开窗户能看见雨中的街景,夜光飘进屋里,暖得人心安。
一早喜子哥就拉着去中央大街,石板路被雨水冲得发亮,他踩着石板,学着东北人的样子“哐哐”走,嘴里念叨:“这路比咱村的土路扎实!”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在阳光下闪着光,喜子哥举着手机拍个不停,说要发给其其格看。回来的时候,喜子哥买了四根马迭尔冰棍,“快吃!这冰棍跟咱关中的冰酪不一样,冰得很,甜得正!”大官人逛了俄货店,买了两盒巧克力,说要带回去给家里的娃;华丛荣则在列巴店排了半小时队,买了个比洗脸盆还大的列巴,说要带回去给二嫂子尝尝,“让她知道东北的面包有多实在”。
喜子哥趴在窗台上给其其格发消息,手指头戳着屏幕,笑得憨:“俺到哈尔滨了,淋了一路雨,不过冰棍好吃得很,列巴也大,下次带你带你看索菲亚大教堂!”太阳岛上的极地世界,用新科技模拟出了极光,绿的、紫的光在头顶飘着,跟做梦似的,我盯着极光,突然想起在阿尔山跟大官人吵的架——原来极光这么美,却不该画在埋着先烈的林子里,大官人说得对,有些地方的风景,得带着敬畏看。
长春僻巷里的百姓食堂,扒肉炖得烂乎,筷子一夹就碎,浇在米饭上,香得能多吃一碗;扒肉干饭店的锅包肉外酥里嫩,蘸着其其格给的野山杏酱,酸中带甜,再就着柱子给的榛蘑炖的肉,香得直跺脚,喜子哥连吃两盘,说“比其其格妈做的还香,就是少点草原的味儿”。沈阳故宫红墙黄瓦,阳光照在墙上,金闪闪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东北的雨,关中的晴,都是咱中国的景;东北的热乎,关中的冷硬,都是咱中国人的性子。”
锦州的晚霞把海水染成金红,跟泼了桶熔金似的。葫芦岛滨海公路旁的海水浑黄,浪头拍着礁石,“哗哗”响。喜子哥站在礁石上,对着大海喊:“其其格!俺到海边了!下次带你来看海!”喊完自己先红了脸,大官人笑着拍他肩膀:“咋不喊大点声?让大海帮你传传话,说不定其其格能听见。”大伙站在龙港区的龙背山龙湾浴场海边,海风裹着咸气吹过来,喜子哥突然轻声说:“该回了。”四个人都没说话,就站在海边,看着太阳一点点沉下去,把海水染成橘红、玫红,最后变成墨蓝。
归途千里,从锦州到京津冀晋,雨又断断续续下了起来,时而淅淅沥沥,时而瓢泼大雨,却没再让人心慌——因为知道,往前开,就是家。我开着车,喜子哥靠在副驾上,抱着给其其格买的蓝莓干,睡得打呼;大官人翻着《地理风物志》,时不时指给我看:“你看,咱走的这条路,就是当年闯关东的人走的,只不过他们靠脚,咱靠车。”华从荣说:“在上面添一句,从关中到东北,走了万里路,见了万样景,最暖的还是人心。”
车拐进董安村,晚风拂过老槐树,华丛荣摸着口袋里的一摞川资,喜子哥拽着我们凑在一起:“咱四个,才算真正的关中冷汉,闯了关东!”原来陕西人的“冷”,是心里藏着火,不声不响把路走了,把愿圆了,把故事记了。像秦岭的顽石,看着冷,心里的火,能暖透岁月,能把远方走成故乡。
作者简介:张战学,笔名狄震,网名华岳青晨,法官,诗人,作者,行者,渭南作协会员,《作家前线》签约作家,曾用华山长涧客等作文学追梦人,创作散文、诗歌、小说等,行迹遍布九州,有《法悟》,《途说》、《行走的歌》结集。
投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