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生活打卡季#“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本土民族学理论之一,不但为先秦史研究所重视,也深刻影响了范文澜、费孝通等人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学生何兹全所说,“夷夏东西说”原本是傅斯年计划写作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英文书名为From Tribes to Empire)的一部分,但该书并未出版。何兹全推测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陆续发表的《论所谓五等爵》(1930年),《姜嫄》(1930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1930年),《夷夏东西说》(1933年)及《周东封与殷移民》(1934年)等文章都是该书的组成部分。
欧阳哲生认为,傅斯年的《周颂说》《东北史纲》第一卷及为答董作宾而作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等篇亦莫不与此有关。关于傅斯年的生平,上述与民族有关之著述的学术脉络和背景,以及史学界的后续发展与批评,都已经有方家备述,本文不再赘言。唯有一点需要说明,史学家多以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一书为哲学作品,实则该书的中卷“释义”部分与其民族学思想有莫大干系,故而本文将之一并纳入关于“夷夏东西说”的总体框架当中来处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0月
前人多认为傅斯年先秦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东西两大族别更替取代了以往基于虞夏商周的朝代更替,进而为先秦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框架。比如张光直说:“这篇文章(指《夷夏东西说》一文——引者)之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都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现在华北古史被他的系统预料到了,而是表现在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王汎森亦认为:“傅斯年以’民族代兴’的观点来理解殷周之间剧烈的变化,深化了他原有的周人在西、殷人在东的观点,成为他后来在古史方面的几篇杰作。”凡此说固然不错,但在本文看来,傅斯年的总体目标显然并不只是先秦的民族史问题,而是接受了当时西学中的普遍判断,进而想解决中国的国家形成机制及其早期变迁问题,傅斯年的民族学从来都是跟他对中国国家的发生学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需要说明的是,傅斯年在这一系列研究中所谈及到的“部落”,并非人类学在前文明社会中所见到的以内婚制和胞族制度为基础的那种部落,而应该指涉的是英雄及其家族已经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家父长制的国家,因此他一方面认为秦以前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于秦汉之后,另一方面也仍旧沿用了虞夏商周的朝代说。本文为行文故,下文不再说明。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1935年春视察安阳殷墟发掘
由左而右依次为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
一、傅斯年论先秦的多民族政治结构
王汎森已经指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的关系:“文化上如此剧烈的变化,显然与’民族’代兴有关。这不是王氏原有的观点。因为在这方面,王国维仍持守传统的看法,主张’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所以王国维将直线的切开平铺,傅斯年又以种族观点将它们划分成两个集团。”实际上,在写作《夷夏东西说》之前两年,傅斯年在写给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就已经指出:“虞夏商周四代的观念,只可说是周代人的观念,或可说西土(包括河南西部、山西之河东及陕西)人的观念。若东土人则如《左传》所记各东夷之传说,并不如此,当是大皞,少皞,殷,一个系统。”这里所谓的“东夷”,是秦汉前持续存在的一个大族团,文化极为发达,曾经建立起不少邦国,亦长期被殷商统治,“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内,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皞、少皞、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这两种不同的史统观念不仅涉及对两个集团各自的文化特征、空间范围和政治属性的界定,还涉及两个集团的整合方式——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间的此起彼伏,并非单纯的征服关系,如果不能由此实现某种稳固的政治架构,那么“夷夏东西说”便不成为一种国家理论了。更为关键的是,傅斯年还直接挑战了王国维以截断众流之猛劲建立的道德天下框架,力陈周之人道的建立是借用和发展商代宗教的结果。但傅斯年并不是要强调殷周之间的连续性,而是要在殷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一种结构性关系,这一关系是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根本机制所在。傅斯年认为,周在客观上固然受殷人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在宗教上,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一影响,原本属于殷人的部落神帝喾才成为一个超越部落和宗族范围的神。除此之外,傅斯年还详细论证了社神崇拜在三代的连续演变:“殷之宗教……除去若干自然现象崇拜以外,完全是一个祖先教……由宗神的帝喾,变为全民的上帝,在殷商时代当已有相当的发展,而这上帝失去宗神性最好的机会,是在民族变迁中。乙民族□用了甲民族的上帝,必不承认这上帝只是甲民族的上帝。”“盖夏商周同祀土(即今所谓’土地庙’)而各以其祖配之。夏以句龙,殷以相土,周以弃稷。”所以殷周之间共享相同的天神和地祇。但到周代崛起之后,一方面天神失去了宗神的特质,另一方面周人则将自己的祖先稷配祀于社,构成了宗教上的总体格局;而在主观上,周更愿意认同于夏:“周人伐殷时,说是以商待夏之道还之于商,或至竟去说是为夏人报仇,且承诸夏正统……周人对于夏的称呼,不是戎商一样的。《周颂》中两称时夏……时夏之时如何解,虽不可确知,然称周亦曰时周……则时夏之称,必甚美甚亲近者。”在补记中,傅斯年进一步说:“时夏时周与戎殷戎商似为相对名词……有内诸夏而外殷商之意。”至于殷人,则其公室为戎族,而其统治的土地和人民则最初属于东夷,“盖殷末东方之国,曾泛称夷,此诸夷者,其中实有太皞、少皞、有济之后而为负荷古代文化之民族,故殷亡而箕子往归之,周衰而孔子思居之”。这里提到的戎和夷的政治与文化关联,在两年后成为“夷夏东西说”的核心问题。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帝俈(喾)画像石
东汉《武梁祠堂画像题字》
早在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凡列中国之民族类别有八种,其中第四种“徐淮族”即是东夷。但他并不认为东夷足以成为早期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根本来源,而只是强调其武力发达:“其遗俗之强武,数千年来犹烂然有声于国史。刘汉之兴以淮泗,朱明之兴以凤颖,其他各时代,每天下有事,此族必岿然为重于一方,或且动全国。”可见早在清末学界就已经能够以更加科学和细致的民族学知识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更加清晰的分类。而傅斯年将东夷提到政治与文化格局的根本地位上来分析,其用意自然并不是分析民族集团构成的多样性,而是要具体阐明夷夏二族文化之结构性关系。傅斯年并非没有注意到南方荆楚集团即祝融八姓,但却没有像同时代的蒙文通和后来的徐旭生一样将其与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并列为三个族团,而是将之看作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族团,在先秦中国完成国家结构性整合的过程中已经只有文化的意义而没有政治意义了。在夷夏对峙之前,“祝融之本土,即所谓’祝融之虚’者……照地望说,正在中央,似乎可信。陶唐氏既在有虞之先,而祝融八姓之内许多是古国。所谓昆吾为夏伯者,无异说,在夏时昆吾曾为一个强大国,与夏为敌。所谓大彭豕韦为商伯者,无异说,在商时大彭豕韦为强大国,与商为敌……凡此种种皆证明西土之夏,东土之殷,皆继祝融诸姓而强大,在夏殷未作之前,据东土西土者,必以祝融诸姓为最强大。”这样强大的一个集团,在夏商两代逐渐被新兴大国驱逐,周兴之后再次被驱逐一次,先是成为殷人宗盟中的异姓盟友,其熊姓一支的政治制度逐渐同化于殷,后周室以召伯虎大定江汉。周庄王末年,楚国开始强大,“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此后荆楚集团便再无窥伺周室的能力了。傅斯年之所以将荆楚集团悬置起来,而单讨论东夷和华夏两个集团,并非因为前者没有历史影响,而是在早期中国的国家建构中,荆楚集团并没有以自身的政治、宗教或者文化力量而获得结构性的位置。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1959年陕西蓝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訇簋(又称询簋)
或许正是由于虞夏商周四代的观念主导了周以后的历史书写,而甲骨文材料并不足以提供完善的东土材料和观念史证据,傅斯年在《东北史纲》第一卷和《夷夏东西说》一文中重复引用了大量的神话学材料来证明东夷作为一个神话和历史主体的地位。他说:“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例如犹太民族,方言尚有差异,其齐一处反在其创世神话;又如希腊罗马同为印度欧罗巴民族西南支派,其关系之密切可以其全神系统证之。中国东北历代各部落之’人降论’,见于《朱蒙天女》等传说者,分析之虽成数种传说,比较之却是一个神话。”这种神话民族论无疑与德国民族学当中关于英雄和民族关系的分析有直接的关系。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Herder)曾经说道:“一个民族的神话,展现给我们它幼年时期的整个形而上学和其思维方式的所有精微之处。神话的表述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族最古老的符号学及它们动情和运思的方式。”而深受赫尔德思想影响的德国心理学家和民族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沿着意大利修辞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的思路,将人类精神的历史分成图腾时代、英雄和诸神的时代以及人性的时代三个基本模式。不论对赫尔德还是冯特来说,英雄神话都是民族得以形成的源头和研究民族问题的重要依据。傅斯年的意图在于,通过将朱蒙天女神话、满族的布库里雍顺神话和商代始祖神话联结成一个神话整体,一方面解决满族及东北与中国整体的关系,另一方面解决早期东夷文化的整体性和精神内涵问题。
《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傅斯年将玄鸟等同于甲骨文材料中频繁出现的“妣乙”,并且认为《吕氏春秋·音初篇》的材料证明了这一判断: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礼记·月令·仲春》载: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而《毛诗正义》则直接将玄鸟等同于鳦鸟:
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祖先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父乙觥腹部凤鸟纹
图源: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
傅斯年认为这则神话在后世的东夷系统民族中多有反映,其中《论衡·吉验篇》载: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魏书·高句丽传》中亦载有朱蒙的出生神话: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度,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通过对以上神话叙事的分析,傅斯年认为,东北各部族神话至少有共同的来源,并且能够证明殷商之源头与东北有密切的关联。而实际上,加上后续几则本文没有引述的神话,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首先,《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作为东夷后裔的郯国国君仍旧能够清晰指出,玄鸟氏是司春分秋分的官职,伯赵氏是司夏至冬至的官职,青鸟氏主立春和立夏,丹鸟氏主立秋和立冬。四个官职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间均分成八份。而玄鸟北飞则无疑是指春分日。那么,这显然并不是简单的物候问题,而是说商弃、朱蒙(即东明)及布库里雍顺的英雄位格之构成与春分时节有根本性的关联。燕鸟之卵、“有气大如鸡子”都与春分后太阳的形象有关,此亦为朱蒙之母“为日所照”证明。英雄之母在这里都变成“太阳的妻子”,而英雄则是一次天地神婚的产物,所以朱蒙才会宣称自己是“日之子”。其次,朱蒙神话中,英雄最初都是一个未孵化的卵,而这个卵与苯教的卵生神话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静止孵化的,卵只是用来标志等级的边界;而前者则先后被置于猪、马、鸟跟前,也就是家中的牲畜、路上和野外三个空间中。而在《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中,野外之鸟被替换成深山百兽。显然,“卵的冒险”是一个单独的情节,也是英雄的第一个功绩即开辟空间,而英雄本身就是时间的表征,因此在卵被孵化之前,英雄的主要功能在于确立时间和空间秩序。再次,朱蒙很明显是一个武士性格的英雄,以善于养马和射猎闻名,而这一点与《三国史记·高句骊传》所言其养父是一只丰产性格的金蛙大异其趣,也可由《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中朱蒙的生父和养父的性格差异看出来,后者是在打鱼的时候将朱蒙的母亲即河伯的女儿打捞上来的。朱蒙见嫉于父兄,在外逃时为大河所阻,“以弓打水,龟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朱蒙是天神太阳和河伯之女的儿子,这与同样作为政治英雄的“陌生人-王”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同时继承父系的法权和母系的宗教与财产权结合而成的政治英雄,而朱蒙则是通过生父继承了控制时间和战争的权力,通过养父继承了空间的权力,通过母亲成为河流(即边界)及地下世界的主人,因此其政治权力是基于时空制度而构建起来的,这也呼应了郯国国君对少皞以时间划分官职的政治形态。与此同时,在逃难成功后,朱蒙遇到三位贤人,分别着麻衣、衲衣和水藻衣,名字依次为再思、武骨和默居,衣衫的完整程度正与他们各自承担的宗教、战争和生产三个等级相对应。值得一提的是,朱蒙在成功跨过河流之后,忘记了母亲给他的麦种,她母亲派两只鸠来送麦种。而五种鸠在少皞国中是管理百姓的官,其中鳲鸠主管水土,而鹘鸠主管农事。朱蒙一箭射中双鸠,开喉得麦种,又用水喷鸠,使之复活飞去。这些情况在在表明朱蒙拒绝直接成为丰产的英雄,而是以武力控制水土农业。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吉安高句丽四神墓中的凤鸟壁画
不论朱蒙在社会学上与养父的等级分化、开辟空间时的严整秩序,还是他所遇三贤的等级结构来说,都应该将这一神话看作是更根本和更加完备的版本。相比之下,《论衡·吉验篇》的记载则相对残缺,而姜嫄履巨人迹生弃的神话,虽然也涉及将初生之弃弃于隘巷、山林和渠中冰上的情节,但明显次序散乱,应是后来模仿之神话。何况弃是彻头彻尾的农业英雄,其母履神之迹而孕固然是相宜的,弃也从未宣称自己是天神或者太阳之子。在将东夷系统神话和周代始祖神话的对比中,傅斯年已经注意到两种性格鲜明的英雄的巨大差异,而这一差异引发的持续的东西部战争才是先秦时代诸国争雄的核心问题,这显然不是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能够解释的。
商起源于东北,在相土时代,东部势力范围已经位于泰山下,西部或者到达了济水的西岸。在汤王时,商已取东夷之国,占领了原来属于少皞的土地和人口,并且向北压迫韦,向西与夏遭遇,向南挺进到淮水流域。到盘庚时,势力越过太行,一路达到渭水。而夏则起于山西省南部的汾水流域和河南的伊洛嵩高一带,东部最多到达济水上游,西部则以渭水下游为限。傅斯年认为,有夏一代的所谓大事,几乎全部都是与东夷集团的斗争。程憬亦曾说:“当商人没有兴起之时,有夏是大河南北一带的霸主。夷羿能乘’有夏之方衰’’因夏民以代夏政’,则夷方必为当时一强大的部落。其后,夏之霸权复转入新兴的商之手。我们借依甲骨文金文的指示,夷方已复兴起,活跃,而商人常以兵戎相见,其势似不甚弱。”夷夏争胜最重要的材料来自《左传·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
《左传》所论已经高度伦理化,但我们仍旧不难从中看出,后羿、寒浞和浇(亦作“奡”)都是武士型的英雄。《淮南子·本经训》载: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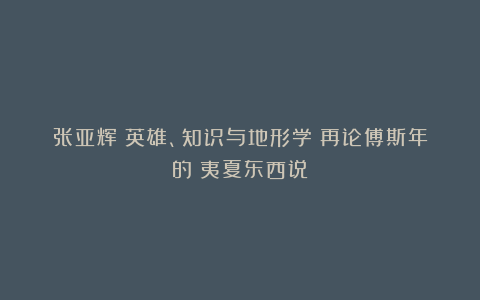
程憬据此列举了后羿的七大功绩,并将其与赫克利斯(即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作了对比分析。从后羿和寒浞的关系上,我们不难识别出这一神话与朱蒙神话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后羿即朱蒙的生父。《楚辞·天问》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这里后羿娶的是河伯的妻子而非女儿。如果朱蒙作为卵的形态的主要功绩在于确立时空秩序,那么我们理应从后羿的七大功绩中看到同样的结论:猰貐居于弱水,前世为二十八星宿的危所杀;凿齿因牙齿过长而混淆了进食与战争,但又保持着人的形体;九婴是水火之怪,大风则就是不受节制的风,封豨本身就是生活在桑林中的大猪,射杀九日则是为了调整天地之间的距离。人们最为熟悉的嫦娥奔月,则是为了回应英雄的短暂人生及月亮的周期性问题。详细分析这些神话不是本文的目的,只是要指出,程憬对东夷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比较没有注意到东夷神话自身的时空制度基础。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彩漆后羿弋射图衣箱·局部
湖北省博物馆藏
至于东夷和西土两种英雄的区别,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论语·宪问》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在这里,南宫适清晰地将东夷的两位英雄界定为武士型,而将夏周两代的始祖全部等同于生产型。傅斯年亦曾引述《史记·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甚至包括鲧,傅斯年亦据《楚辞·天问》认为与农业有关:“自鲧永遏于羽山后,禹平水土,秬、黍、雚皆茂长,巫乃将鲧化为黄熊。”顾颉刚认为,禹的神职为主领名山川的社神,但也不得不承认“禹也是一个’俾民稼穑’的国王”;而程憬则指出,好些学者认为禹成为主名山川的神很可能是作为主稼穑之人王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在后羿、寒浞与少康的争斗之前,还有一段中国历史的著名公案,即伯益与启争统的问题。传统所论或者持禅让说,或者如《竹书纪年》所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而傅斯年认为,这原本就是一次夷夏之争,伯益即伯翳,乃是秦赵两国公认的祖先,也就是嬴姓之祖,因此是东夷人,益启争统无疑是另外一次夷夏之争。有夏一代最后一次夷夏之争是汤放桀,傅斯年认为:“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
南宫适的英雄类型学似乎故意遗漏了殷商,孔子似乎也没什么兴趣去修正这一说法。而恰恰是殷商成为东土和西土两个史统唯一的交会点。换句话说,在夷夏争胜的结构分析之外,还需要考虑历史本身带来的影响。汤放桀之后,历史取代了结构,成为主导模式,但结构本身并未完全失去效力。傅斯年在一系列与“夷夏东西说”相关的讨论中,更多讨论的是从殷商的宗教性向周的人文性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文明的二重性问题,而不再诉诸夷夏交胜的结构变迁。换句话说,殷商变革在傅斯年看来更多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而不是东西两种文明碰撞形成的外部制度,而形成于殷周之际的二重性在有清一代有清晰的体现:“满洲的祭天,本是跳神。然……承袭了儒家的祀正统之天,在天坛,并承袭了嘉靖帝的道士之天,在高大殿,而同时继续其跳神之天,于坤宁宫中杀猪!因为接受前一代的土地人民文化,不得不接受前一代的宗教。”将殷周辩证法与清代传统的多元性相互等同,当然在学术上是巨大的冒险,也同时指出中国历史中隐藏的另外一种包含复杂民族学意味的层累说,但如何将这种层累的机制与推翻帝制之后的中国结合成一个连贯的叙事,是傅斯年没能彻底解决的。不过在与王国维的对话中,傅斯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以殷商为枢纽、以殷周辩证法为核心的综合宗教与人文的史学格局。他在1931年写作的《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一文中说:“大概与儒家相隔愈远、与乎未如何理想化之史料,其真确性愈大,如《孟子》不如《楚辞》,《楚辞》不如《山海经》。禹鲧故事,求之《孟子》,不如求之《楚辞》,求之《楚辞》,不如求之《山海经》。”从历史研究的目标来说,这段话的意味不但能从神话、宗教与历史三者的关系来理解,同时也表明,越是诉诸一种多元民族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策略才越是有效的。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甲骨文记载了军事进攻前五百头牛的祭祀活动
出土于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
在傅斯年看来,最后一次夷夏争胜应是秦的崛起:“嬴姓国今可考者有商末之奄,淮夷之徐,西方之秦、赵、梁……东南之江、黄……伯翳为秦赵之祖,嬴姓之所宗……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这一点在神话上亦有明证,《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按颛顼在古帝系统中应属东系,说别详)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东夷之传说,辩详上文)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按,此皋陶谟之伯益故事)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
伯翳之子继承了东土的武士传统,在费昌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仍旧保持着与鸟的密切联系,“太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与神话中的朱蒙一样,嬴姓后裔同样呈现出善于养马的天赋。
然而,神话的结构并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进程,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的结论部分没有继续分析东夷和华夏的文化差异,而是专注于中国先秦历史的东西格局:“在由部落进为帝国的过程达到相当高阶段时,这样的东西二元局势,自非混合不可,于是起于东者,逆流压迫西方。起于西者,顺流压迫东方。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实际上,尽管东夷诸族在神话上呈现出明显的武士英雄性格,而华夏则更多体现为丰产性格,但在三代历史中仍旧是西胜东更多,且相争与相成根本就是一体两面。傅斯年认为,这是由中国地理格局中固有的高地和低地关系造成的。东部平原湖泽众多,便于发展农业而弱于军事防守;西部高地的经济固然逊于东部平原,但“攻人易而受攻难。山中虽不便农业,但天然的林木是在早年社会发展上很有帮助的,陵谷的水草是便于畜牧的。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但东西两方在秦崛起之前,似乎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支配关系:“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神话与地形学的解释在这里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傅斯年似乎意在说明,军事上的胜负并不被神话学或者文化的性格所主导,反而主要是地形学造成的,但如何解释“禹稷”的农业性格与所谓“强悍的部落”之养成的矛盾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意识到,傅斯年最终诉诸地形学同样是不够的,因为商人集团本身来自东方,却具有强悍的军事性格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我们今天仍旧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说明商究竟如何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李济认为商朝的出现可能与整个种族的狩猎习俗有关,而张光直则认为:“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商人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族,许多学者将之看作是一个军事单位。在一个既具有防御功能又是居住生活区的小型城邑中,对居住其中的’族’来说,军事职能是其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族的首领则是该族的军事统帅;而王都与小型城邑相比,这种军事特色就更为浓厚,层次也更为高级。商王则是都邑(也就是国家)的军事统帅,这一位置就要求他必须具有强健的体魄……所有这些族既是商王朝的军事组织,又是社会政治单位。在和平年代,由常备军维持社会秩序。”而其战争技术和武器装备在当时也是最为先进的。商人南下统治东夷并最终灭夏之后,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而周代崛起时已经深受商文明的影响,神话的结构在这里就已经让位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关联和辩证法了。所以商不能如傅斯年所说的,被单纯看作是继承了东夷文化的东方集团,更应该被看作是东西两个集团间真正的整合力量。关于这一点,似乎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中被论述得更加清晰。傅斯年所谓西部高地上的强悍部落,其实已经被明确指出与西部游牧部落有关,后来顾颉刚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中则进一步说明古羌人诸国加入了武王伐商的战争当中。所以“夷夏东西说”从战争和政治整合的意义上来说,到了商代夏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了。而秦人崛起于西陲,仍旧带着东夷好战的古风最终完成政治统合,可能是早期神话学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而东夷文化的另外一个关键遗产则是先秦的知识结构。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商代兽面纹铜钺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二、知识与民族
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先秦时代器物形制的历史、制度的发展以至不同民族间的关系,都有可靠的材料作为证据。虽然对这些证据的解读仍旧会引起学术上的争论,然而关于宗教和思想的变迁过程,则不容易有明确的证据。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力陈“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他仍旧依赖将制度史变迁与《尚书·召诰》的文字表述结合起来方能定论,但没有详细分析《召诰》中的“命”“天”等文字的具体含义。至少在葛兰言(Marcel Granet)看来,先秦的“德”字并不是王国维所言的道德,而是包含更为鲜明的宗教意涵:“王朝的’德’是通过顺从天意才获得的”,因此和一个王朝的气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非一种内在自觉的道德力量。相比之下,葛兰言的立场更接近傅斯年而不是王国维。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的写作出版比《夷夏东西说》的发表要早,其核心是分析先秦时代宗教、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傅斯年统计了各种载体的先秦遗文中“性”“命”两个字的字义,意在指出儒家道德化的性命之说在《孟子》时代才成熟,在此之前,这两个字的含义更多地与宗教而非道德有关:“生字之含义,在金文及《诗》《书》中,并无后人所谓’性’之一义,而皆属于生之本义……命之一字……其’天命’一义虽肇端甚早,然天命之命与王命之命在字义上亦无分别。”这一分析将先秦道德世界的自觉之发生确定在了孔孟时代,并以语言学证据为基础证明了商周间的思想连续性。
傅斯年统计的文献包括周代金文、《周诰》《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等,这些当然不是先秦文献的全部。其选择文献的用意很明显是只要处理周代的典章制度和儒家的先秦经典,至于和“生”“命”两字本义更为接近的道家经典则完全没有出现在傅斯年的统计材料当中。经过大量的语言学材料分析,傅斯年认为,“生”与“性”两个字在东周之前完全是混用的:“荀子所谓性恶者,即谓生来本恶也。孟子所谓性善者,亦谓生来本善也。”如果将生命本身的存在看作是一宗教现象,则彼时所谓“性”,完全不能被看作是抽象的品德。而“生”与“性”两字的关系即为“令”与“命”两字的关系。“令、命二字之本义为发号施令之动词,而所发之号、所出之令(或命)亦为令(或命)。凡在上位者均可以发号施令”,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天命和王命。傅斯年同样分析了《召诰》中的材料,指出:“殷世及周初人心中之天令(或作天命)固’谆谆然命之’也,凡人之哲,吉凶,历年,皆天命之也。”“天命”一词在晚周之前有明确的宗教意义,“天命一词既省作命,后来又加以前定及超越于善恶之意,而亡其本为口语,此即后来孔子所言之命,墨子所非之命”,因此也就转变成道德哲学的概念,但其宗教的概念并没有因此消失,五德始终说和汉代的谶纬之说中都保留了其原本的宗教意涵。至于“性”字,则本为“生”,“古初以为万物之生皆由于天,凡人与物生来之所赋,皆天生之也”,而到了晚周则发展成一种人内在的道德品性之含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西周利簋及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傅斯年对“生”“性”“令”“命”四个字的分析本意是要说明,中国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有一个从宗教世界走向人文世界的过程,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都区分神法和人为法一样,中国古人亦区分天道与人道,在“生”“令”二字用其本义时,天道即为人道,而当“性”“命”二字取其道德意涵时,人道挺立而有别于天道。先秦不同民族传统对天道与人道关系的不同看法即形成不同流派。结合《夷夏东西说》一文的神话与历史分析,实可说《性命古训辩证》要探讨的真正问题其实在于先秦的思想史与民族史之内在关联。
傅斯年已经发现,在已经出土的大部分殷商文献中,对至上神的称谓是“帝”或者“上帝”,而天是到了殷晚期才出现在文献当中的。郭沫若亦说,“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绝不曾称之为天”,而“天”字虽字形从人,但主要是指高处。关于这个上帝,不论傅斯年、郭沫若还是徐旭生,都认为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帝俊。因为帝是一个人格神,所以傅斯年多次将之与犹太教的耶和华作比较,郭沫若也曾经说:“由卜辞看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这和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但显然,帝俊最重要的特征还是一个时空型的神灵,《山海经》载: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不论天干地支观念的具体起源为何,帝俊都明显和天文气象有关。《左传·昭公元年》载: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郭沫若认为,参商分别为黄道十二宫中的第一、第六两宫,故高辛氏二子之神话仍旧是关乎天文学和季节循环的。所以帝俊不能被看作是以色列的意志与盟约之神,而是时空制度之神。而这则神话表明最初殷商始祖的活动是发生在天上的,这也就解释了上文提到的有娀氏二女为什么处于高台之上。“天”的概念在殷商晚期开始出现,最初大概指的就是帝俊在天上的居所,或者说是一种提喻的修辞,并最终逐步取代了本喻。天取代了帝之后,所谓“宾于帝”就成为一个开放结构,从而使周得以在继承殷商传统的同时安置自己的宗教位置。但是如此以提喻替代本喻,宗教之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傅斯年在这里直接批评了王国维的看法:“殷周之际大变化,未必在宗法制度也。既不在物质文明,又不在宗法制度,其转变之特征究何在?曰,在人道主义之黎明。”因为是黎明,故而在“生”“命”二字的考察中仍旧可见明晰的宗教特征和殷周间的连续性,也因为是黎明,故商代的人殉、苛刑峻法和军国主义性格都得到克制:“恤民而用之,慎刑以服之,其作用固为乎自己。此中是否有良心的发展,抑仅是政治的手腕,今亦不可考知,然既走此一方向……则已启人道主义之路,已至良心之黎明,已将百僚庶民之地位增高。”但由此认为周族已经完全走向道德世界而忽略宗教,仍旧言之过早;不如说,周代真正开启的是一个由殷商继承而来的“宗教-人格之天”和周人自己的“理性-人文之天”的复合结构,这一复合性此后成为中国政治传统和知识传统的根本特征。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董作宾题拓殷墟“大龟七版”之一
1934年史语所第九次殷墟发掘出土
殷周制度之连续和变革只是理解先秦知识传统的一个维度,其中涉及的是殷族、东夷和周族关于宗教与人文黎明的总体知识格局。而各个民族遗留的文化遗产在上述复合性基础上的发展,则构成另外一个维度。首先,儒起于殷遗民聚集的鲁国,本为殷人的教士集团,“故在早期儒教中,殷遗色彩甚浓厚,尤以三年之丧一事为明显。所谓三年之丧,乃儒家宗教仪式中之最要义,而此制是殷俗,非周制也”。在《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中,傅斯年说:“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胡适后来据此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支持三年之丧为东国礼,而所谓东国之俗究竟来自殷商还是东夷则并无定论。《礼记·杂记》:“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明言三年丧乃是东夷之俗。总括起来,则“早期儒教实以二代文政遗训之调和为立场,其为鲁国产品”。其次,墨家起源于宋国。“东周列国中,宋人最富于宗教性,亦最富于民族思想……东周诸子学说中,亦以墨家最富于宗教性。”但墨子非乐、尚贤似都与宋人文化相互矛盾。傅斯年则认为,墨子并非承袭之教徒,而是宗教变革家,“故墨子一面发挥其极浓厚之宗教信仰,不悖宋人传统,一面尽反其当世之靡俗,不作任何调和”。其次,名法之学起于晋,而晋的历史和文化又远承于夏。“法家多以为天道不必谈,其人性观则以为可畏以威,而不可怀以德……此一派思想之发展,固有待于晋国新政新社会之环境者焉。”其次,道家思想起于齐,与《管子》之书一脉相承。“盖齐地之上层思想集合成一自然论,其下层信念混融成一天运说,此两派人入汉朝皆极有势力,溶化一切方术家言者也。”傅斯年并未有意穷尽诸子学说,就以上四家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诸国在结构与历史中所处之地位和政治策略与诸子流派的共变关系至为明显,傅斯年最早系统地梳理了诸子学理与诸国政治之关系,并为先秦诸子思想史提供了明确的民族学解释;另一方面,傅斯年反对民国时以南北方文化区分诸子的看法,“以东西分,虽不中,犹差近”。在《战国子家叙论》一文中,傅斯年就已经意识到,以齐、鲁、宋为一方,以晋为另外一方,其思想格局仍旧与夷夏东西对张相对应。比如论及齐与宗教之关系:“且所谓东夷者,很多是些有长久传说的古国,或者济河岱宗以东,竟是一个很大的文明区域……齐国自能发达他的特殊文化”,对后世思想影响深远者凡五:宗教、五行论、托于管晏的政论、齐儒学、齐文辞。到了汉代,这种由早期的神话和地形学塑造的思想格局终于被一种全新的二元论所取代,汉儒“分性情为二元,以善归之于性,以恶归之于情,简言之虽可以性包情,故亦谓性有善恶犹天之有阴阳”。由此,中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彻底完成了新国家形态的整合。
三、结论:一个民族学的教益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面对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格局和世界思想状况,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起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截断众流自然可解燃眉之急,但终非了局。由于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的快速发展,不论是从学术本身来说,还是从当时的世界革命局势来说,中国学术界都需要基于现代科学方法解决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转变的机制与过程。当时西方的国家起源理论,不论是基于自然法假设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基于民族学成果的“从氏族到城邦”之转变,抑或基于印欧人经验更加为人推崇的“家父长制到国家制度”之成长,似乎对于解释中国的历史与考古材料都有凿枘不入之憾,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则在于中国早期国家中没有发展出城邦制度,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中国国家之文化与道德性的根本特征如何形成。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张帆译:《自由与文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0月
傅斯年以“夷夏东西说”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之意义,不只是如后世史家所说的打破西土史统的一元叙事,主张民族代兴之论,从民族学视角观之,更加重要的是提出一个从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动态政治格局逐步形成国家的社会学机制,进而触及国家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国家历史表述的策略问题。夷夏东西格局不是一个历史偶然形成的地形学或者文化学的框架,而是一个具有高度普遍意义的政治起源学说。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1944年出版的《自由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与傅斯年非常类似的国家起源理论,他说:“大量的侵略者从高地和草原入侵肥沃地区,占领并控制富饶的农耕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有目的、有组织并具有建设性的侵略战争进入历史舞台。”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有创造性的战争类型:“军事侵略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促进了文化间的互动并建立起一个更加充分的执法、行政、立法体系……这个新形成的联邦拥有比组成双方任何一方都更为发达的文明……我们能够推断,正是通过侵略,才形成了早期的正式法典、官方法庭以及警察体系……同时,不同群体之间交换并相互促进宗教和科学思想。”尽管夷夏关系不能被完全等同于马林诺夫斯基在前文明社会所见到的战争类型——夷夏两端的社会与政治的互补性整合意味无疑更加鲜明,且上文已经指出傅斯年由于忽视了夷夏英雄类型的分化而没有看到的商周间的辩证关系,而马林诺夫斯基的战争理论完全忽视了在战争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与英雄类型的分化,并由此导致他所说的战争理论过于依赖暴力本身,但是两位前辈学人基于完全不同的经验和写作背景,相隔11年提出的政治、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仍旧体现出了思想上的强烈共鸣,而且这个理论直到今天仍旧在增强其解释力。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就发现,高地和低地关系中武力充沛的一端可以用海洋上来的力量来替代——这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东夷在神话中为何诉诸一种武士型英雄——他甚至将这种从神话和历史中都可以清晰看到的二元关系之整合称作“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如此形成的国家并不能确保其道德性,中国经验的根本价值在于呈现出曾经作为被统治者的农业群体对国王或统治者之政治与道德的反思性,从而完成从天道向人道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傅斯年过于急切地想证明先秦中国的多民族争胜之局面,反而没能在更高的视野中看到自己的理论与王国维的理论本质上是互补的,一如他主张的夷夏东西格局其实是以历史上夷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互补的整体为前提的,而不是夷夏偶然遭遇的结果。
中国在先秦时代实现国家整合的方式,一方面与东夷和华夏两种英雄的类型学有关系,另一方面则与东西两方的时空制度的整合有关。前者作为一种自然等级制度,与全世界的经验都有明确的关联;而后者则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学,与希腊斯多亚学派兴起之后强烈的一元论色彩的哲学和闪米特-阿拉伯的宗教传统有本质的差别。自然等级和时空制度的结合点则在于类似于商汤这样的“低度发展的英雄”如何通过神圣山川的仪式同时控制时空制度与政治秩序,并由此构成道德哲学的基础。中国民族学的教益在于,不论任何时期的政治制度抑或思想传统,都需要在一种多民族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获得其道德性,而这种道德性对于任何一个文明都是最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