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张仁初搬进青岛八大关一栋德式小楼,此处原为德国驻青岛领事馆职员宿舍,红瓦黄墙的砖木结构里还留着铜制门牌号。
二楼书房挂着朝鲜带回的铜勺,勺柄刻着“26军”三个字,每天早饭前要用绒布擦两遍,擦到第三遍时总会停顿。
客厅沙发套是军用帆布改的,坐垫里填着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军鸭绒睡袋,每逢阴雨天就泛潮气,老伴刘浩总说该晒晒,他却摆摆手:“霉味比香水味实在。”
离休头三个月,他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出现在济南军区档案室。
管理员记得清楚,老将军借阅的抗美援朝作战记录摞起来齐腰高,钢笔水渗透蓝格稿纸,在第二页洇出淡蓝印痕。
有次抄到长津湖战役冻伤统计表,笔尖突然折断,墨水溅在“冻伤两千”几个字上,晕成团黑斑 。
1963年麦收时节,两个山东农民找上门来。
警卫员查介绍信时,张仁初在二楼听见胶东口音,趿着布鞋就往外跑。
这两人是抗战时期的警卫员吕德胜、吕庆超,复员后在家务农遇上饥荒。
饭桌上摆着白菜炖粉条,刘浩把特供猪肉罐头全开了。
临走时老将军掏出工资袋,又让司机开车送他们到长途车站,吉普车开出院门时,他站在老槐树下挥手,呢子大衣肩章褪了色的将星闪着微光 。
书房五斗柜最下层锁着铁盒,装着淮海战役时的作战地图,黄百韬兵团覆灭处用红铅笔打了三个圈。
每月第三个周日,他要把地图铺在地板上比对,有回小孙子踩出脚印,橡皮擦到“永城”二字时喃喃道:“杜聿明就是在这儿被围的。”
1965年取消军衔制,他把55式将官服叠进樟木箱,箱底压着朝鲜国旗勋章,绶带褪成淡黄色。
济南军区派人征求换装意见,他说:“中山装挺好,就是口袋要多两个,能装烟盒火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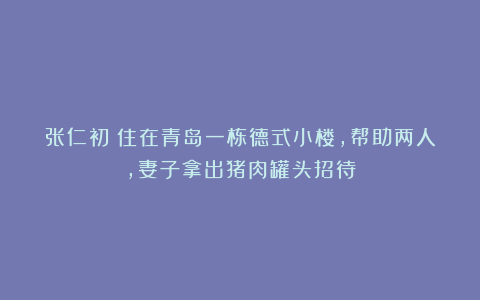
其实他朝鲜战场就戒了烟——战士民主会上批评军长抽公家烟,他当场摔了烟斗:“从今天起不再吸!”
夏天傍晚常坐藤椅乘凉,芭蕉扇柄缠着医用胶布。
有次听见隔壁小孩唱“雄赳赳气昂昂”,突然站起来打拍子,藤椅晃悠吓得警卫员赶紧扶住。
邻居都知道他耳背,但谁要说起“腊子口”,他准接茬:“当年我带六连冲了六次……”
窗台钢盔改的花盆里,陆房突围时老乡送的仙人掌每月11号浇次水,1967年开花那天,他盯着小白花对秘书说:“该给鲁中老区学校捐点图书。”
1968年深秋住院检查护士量血压时,他总指着照片里穿呢大衣的干部:“这是报务员老李,上甘岭挨了七发炮弹没挪窝。”
铜碗反光在天花板映出裂纹,他说像长津湖的弹道轨迹 。
原8纵参谋长老李来看他,两人蘸酒在床单画睢杞战役战线,护士换床单时抱怨酒味大,他笑着摸出两块钱:“算我赔的。”
最后半年常盯着院里的槐树发呆,树上铁皮罐头盒风一吹当啷响,他说像夜行军时炊事班的锅碗声。
1969年10月捐出淮海战役地图时,特意嘱咐军事博物馆要放在黄百韬兵团覆灭处 。
捐完第二天忽然要穿将校呢大衣,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对镜子敬礼时呢料空荡荡挂在肩上。
11月4日晨,昏迷两天的他忽然清醒,叫着小儿子乳名说要吃地瓜面窝头。
炊事班现磨面粉蒸好送来时,人已没了呼吸。
窝头在床头柜凉成硬坨,老槐树叶正落在盛过景芝白干的铜碗里 。
追悼会在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举行,最醒目的花圈挽联别着晒干的高粱穗,玻璃罩里封着鲁中南黄土。
哀乐放完,不知谁起了头唱《八路军进行曲》,满屋子拐杖点地打拍子,跑调的歌声震得挽联哗哗响 。
骨灰盒送往山东福寿园“红星园”时,胶州湾飘着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