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之行
一、可可托海
天突然就变冷了,在阿勒泰地区的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额尔齐斯大峡谷,气温骤降,我穿上了厚实的秋衣。冷风中的峡谷令我感到了秋的肃杀,溪流湍急,铁灰色的山峰硬冷,青绿的松树、秋黄的桦木、杨树,绵延着盘入大山深处。这该是大自然调色板涂抹的色彩,高冷、热烈。天空纯静的蓝,这样的底色,心也变得无瑕。
这里是富蕴县吐尔洪乡,当地的村民正在修筑通往溪边的栈道。有人牵着毛驴,驮送着建筑所用的物资,有人在溪边劳作,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地游客,在奇山异水间踏着欢快的脚步,驴行着。
山色坚硬,内心柔软。此刻,我的耳畔萦绕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在异域现场,雪山、戈壁,驼铃声响起,再来听听这首令人心碎的歌曲,一定会令无数人为这凄美的爱情感到忧伤。而我身处的可可托海,山谷里的风吹拂着,秋黄的桦树叶发出瑟瑟的声响。
当我站在桥头,望着凝碧的溪流远去,便陷入了忧思,陷入了某种尘世的伤感。脱离人群,独自行走,有个好处是不受人为的干扰,大山为我提供了这种可能。这里的阳光温暖,有着尘世未有的超凡脱俗。陌生的环境,令我的身心变得无拘无束,触觉又变得灵敏。
沿着石阶和山坡的泥土路往上,抵达山腰,我的视野变得开阔。大山在我脚下,险峻的溪谷一览无遗。在一处面向神钟山的山坡,我驻足观望,这座海拔1359米的山峰,又名阿米尔萨拉峰,它拔地而起,孤傲独立,如钟似锥。这座花岗岩的奇峰,被赋予了“钟生平安”“情定钟生”“钟爱一生”等各种含义。极目四周,我发现了日月辉映的场景,对面的阳光笼罩着神钟山,发出神圣而迷人的光环,又在近处的草叶间流动。一只鹰在溪谷之上飞翔,变成黑点,渐入空阔而寂寥的天际。月亮在我身后的巨石之上,散发出淡淡的光晕。此刻,我的躯体不知疲惫,深陷于山林、草木之中。
神钟山又名“佛龛”,大概是因山形相似。当然,这里也有神话传说,《山海经》第八卷海外北经曰:“钟山之神,名曰烛明,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晵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之下。”这里的山谷阴冷,白色的溪流激荡着,响着碎银般的歌声,越过无数黑色的溪石,卷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扬长而去。
在靠近溪边的平坦处,两匹健硕的黄马正悠闲地在桦树下踱步。一只被蒙上眼睛的雄鹰用锋利的爪子勾在一段木桩上,它灵敏地晃动着头颅,眼罩之下,它那凌厉的目光一定瞪着试图靠近的人们。它的主人,一名维吾尔族小伙正安静地坐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与它合影的顾客。
二、白哈巴
汽车在哈巴河县境内山间公路盘旋,这里多弯道和险峻的山谷。这里的山峦起伏,植被以灌丛草甸、高山植被、石山植被为主。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70%,生长着白桦、新疆针叶林、落叶松、云杉、冷杉、山杨等。
山体坚硬,风越吹越冷,我在中哈边境大峡谷的观景台眺望。远处,一条蜿蜒的长河在冷寂的河谷流淌,使我仿佛置身于旷远的水墨画里,山野寂然,静默无声。金黄的桦树叶涂抹着近处的山峦,秋风舞,秋叶落,斑澜的图景。极目更远处的河对岸,那里植被稀少,铁灰色的山峦坦胸露腹,呈现出萧瑟的景象。
我们事先在县城办了边境通行证,故能够顺利抵达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这里也是西北第一哨所的所在地。这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境内,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距哈萨克斯坦东锡勒克仅1.5公里,有国防公路相通。
白哈巴村所处的位置是阿尔泰山山脉的山谷地带,与哈萨克斯坦的大山遥遥相望,阿尔泰山上绵密金黄的松树林一直延伸至此。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蒙古族的支系图瓦人居住最集中的一个村子,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图瓦人村落。村子以蒙古人及哈萨克人为主,分为白哈巴一村和白哈巴二村。村民们在临近沟谷的台地上,搭建了木楞屋,每家每户围着圈养牲畜的栅栏,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松林和桦林之中。这里的气氛宁静、祥和,数百年来,图瓦人在临近沟谷的平坦地带放牧牛羊,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
远山的尖顶长年积雪,雪山之下,青草摇曳,牛羊肥美,溪水欢快地流淌。我们沿着宽阔的马路前行,与一排排整齐的木楞屋擦肩而过。这里的木楞屋有的看上去有些年头,有的正在新建,工人们将整根原木用来搭建墙体和顶棚,下部呈正方形,上部呈等腰三角形,顶部呈“人”字形,顶尖坡陡,可防雨防雪。墙体原木之间的缝隙以苔藓填充,顶棚和屋顶之间形成两头通风的尖阁,用于储藏饲料和风干肉品。一般屋内炕上铺着花毡,墙上挂着刺绣的帐幔壁毯,中央为精制的火炉。
白哈巴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八个小镇之一。因为是景区,为便于游客观光,这里的公交上下相当方便,相距不远的每一处都设置了站点。当然,这些新建的木楞屋有一部分是用于接待游客住宿和开办餐厅。“林中小屋”“山野里餐厅”“夜雨餐厅”“西北第一村邮局”,这样的命名散发出偏远地区的山野风情。披着羊毛头巾的图瓦妇女在晾晒衣物,洁白的床单在风中飘扬,几匹马儿在栅栏里悠闲地吃草。马路上开着红色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的中年图瓦人、骑着骏马扬长而去的帅小伙,以及站在门口闲聊的脸上遍布皱纹的老人,我看清了他们古铜色皮肤的样貌,也加深了我对白哈巴村图瓦人的印象。
我们在乡间的土路上漫游,金黄的杨树叶、桦树叶点燃了火一样的热情,迎接着深入异乡的游客。这里是姑娘们的最爱,她们在村口竖有“白哈巴”村名的白石边,在桦树林,在木楞屋旁四处转悠,就是为了拍几张迷人的照片。当然,也有人静坐在写着“我在白哈巴一直等你”的厅馆门口,尽情地呼吸着乡野的气息,并享受着迷人的山色。正午时分,选一家当地特色的餐厅,吃烤全羊、手抓肉、各色烧烤、各种大盘系列、野菜、冷水鱼、喝图瓦人酿造的奶酒,是贪恋美食的人所喜爱的。
图瓦人的生活习性正在逐渐改变,他们已开始适应陆续到来的游客。这些年,从原始封闭的边陲村庄到网红打卡地,图瓦人正接受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商业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元素正融入他们曾经单调的游牧生活。
三、喀纳斯
很早以前就知道新疆有个喀纳斯,那是因为传说喀纳斯湖里有湖怪出没。那时候年纪尚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各种武侠、科幻、飞碟、气功、伪科学等等,我沉溺于这样的猎奇。此刻,喀纳斯离我咫尺之遥,从白哈巴村到喀纳斯湖也就三十一公里路程。
喀纳斯湖坐落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脉的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泰山西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北邻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东连蒙古国,位于边境小县布尔津境内,是一个很深的山间大湖,也是我国惟一属北冰洋水系的内陆湖。在蒙古语中,喀纳斯的意思是“美丽而神秘的湖”。这里有秀丽的高山、河流、森林、湖泊、草原等奇异的自然景观。集成吉思汗西征军点将台、古代岩画等历史文化遗迹与蒙古族图瓦人独特的民俗风情于一体,被誉为“世外桃源”。
天空湛蓝,四野空旷,飘逸的云朵一掠而过。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嗅着草木的芬芳,我在林间漫步着。杨树、松树、桦树、杉树,各种低矮的灌木、草甸,马匹膘肥体壮,牛羊们悠闲地吃着草,这一切刺激着我神经,也舒缓着我的身体。两只皮毛乌黑的小松鼠在路旁的松树下相互追逐,金黄的秋叶被踩得“沙沙”作响,它们飞速蹿上了树干,绕了一圈之后隐入深林。在林密的更深入,那里一定有着更多的飞禽和野生动物,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独自脱离队伍,沿着指向湖边的林深处走,游人渐已稀少,但我听到了“哗哗”的水声,那是喀纳斯湖在召唤着我。我的行走仿佛在冥冥之中得到暗示,就像我的朋友嘎玛丹增在一篇散文《在暗夜里穿行》里写的那样:“阿尔泰高山耸峙,沟深林密,河流纵横,满坡草绿。”“我突然决定沿着河边便道继续前行,穿过前方深度不明的原始森林,在寂静无人的黑暗里,走近喀纳斯湖。”此刻,我同样穿行在晦暗不明的森林,朝着闪着银光的湖边走去。未知的地方总能给人带来惊喜。
阿尔泰群山连绵,澄蓝的湖水拍打着湖岸,黑色的石头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湖岸边的桦树、山杨、云杉高耸挺拔,墨绿和金黄交相辉映。神秘的喀纳斯湖崭露头角,将我的视线带往更加辽阔的远方。2024年9月26日的这个下午,我就像一只落单的飞鸟,沿着喀纳斯湖的滩边,独自轻盈地漫步。这里清亮的湖水洗刷着我的双眼,洗刷着来自尘世的蒙尘与污垢。天光掠过,如饮甘露,我因这美丽的邂逅陷入了空灵的冥想。于是,我为这奇异的遇见写下了如下诗行:
《喀纳斯湖》
秋黄,云朵飘逸
枫木,桦木,云杉
落叶松的色彩缤纷
阳光在万千细密的枝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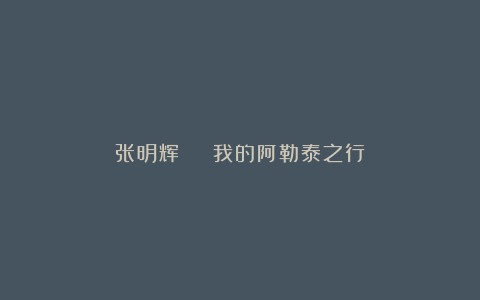
摇曳
喀纳斯的湖水
在激荡中苏醒
碧波荡漾
一次次汹涌的撞击
退却,循环往复
如同生与死的激辩
喀纳斯湖如同人的眼睛
仰望苍穹
谁在风中瞭望
这寂静的旷野
这辽阔的森林
图瓦人的苏尔响起
悠扬,激樾
苍劲如雄鹰展翅
那是无数个祖先的亡魂
在风中哭泣
四、禾木村
河流宽阔,浪花飞溅,湍急的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流淌,桥下的河水如脱僵的野马浩荡奔流。图瓦人的木楞屋散落在山谷的草原地带,靠近森林与河流,便于放牧和居住。
禾木乡是中国西部最靠近北边的一个乡,乡里的禾木村是仅有的三个图瓦人聚居地之一,其余两个分别是白哈巴村和喀纳斯村。禾木乡是图瓦人村落中最大的一个村,现有村民1800余人,以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为主,其中蒙古族图瓦人有1400多人。
穿行在木楞屋间的乡村公路,我所看到的禾木村依旧是保存着原始的风貌。在路的两侧,丰硕、修长的桦木,身姿笔挺,灰白树干,高入云天。金黄的树叶细密,如帘般低垂,被风吹动,发出簌簌的声响。墨绿的松树上挂着松针,巨大的树冠如塔影笼罩。一路上,这样的青黄的景象令人百看不厌。
路的一侧,马蹄声响起,一位当地牧民骑着黑马急驰而去,隐入树林。白桦树下,一位包着印花头帕的阿姨正拿着手机用当地方言与人通话。身侧的一排木楞屋被用作售卖商品的店铺,木杆上挂满毡帽、头巾、羊毛披肩等各种物品。至今我仍分不清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人,只能从他们的打扮和样貌猜测。更多的马匹正列队在林子深处出没,它们在马鞭的驱驰下,在泥泞的黑土地上一路小跑。这是牵引游客的马队,在当地牧民的率领下,朝着对面陡峭的山坡移动。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三三两两上下山的游客擦肩,独自朝着山顶观景台的木栈道方向走去。山陡林密,沿着盘旋的木栈道台阶上山,我亦步亦趋。在半山腰,几乎已经能够看到禾木村的全貌了,在金黄山谷的平原地带,一堆堆白色的木楞屋散落其间。跟随着攀登者的脚步,越往上走,海拔越高,视野越开阔。午后的太阳躲在云层里,仿佛在作片刻的休憩。
当我登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这里有个诗意的名字——云端部落,位于两山这间的平坦地带,同样有着成片青翠的草场。一群骏马嘶鸣着,在山顶的青草地上尽情撒野。山峦拔高了我的视线,在天的尽头,绵延起伏的山峦尽收眼底。金黄的桦树林在尽情燃烧着,木楞屋如一堆散落的白色石头坦露着。
一只雄鹰在远处天际翱翔,巡视着它的领地。栅栏边,一个敦厚的中年男人正眯着眼,接过我递给他的纸烟,并用生硬的普通话与我交流。后来,我才知晓他的名字——阿力腾加甫,一个土生土长的图瓦人。得知我要骑马下山,在谈好价格之后,他领我走向不远处的一匹黄马。他娴熟地教我踏上马蹬,坐上马鞍,随后翻身上马,夹紧马肚,甩动缰绳。坚实的蹄声叩响山冈,也加速了我的心跳。马儿踏着碎步在山间崎岖的羊肠小道上穿行,一路颠簸,朝着山脚下的林子走去。
配图:张明辉 / 编辑:闺门多暇
说明:本平台打赏即稿酬。投稿信息关注公众号后获取。
订阅《向度》:点击上方小程序或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