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简所见“施刑”探微
张俊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代有一种刑徒的身份史书称“弛刑”,按照传统史书记录的解释是“谓若今徒解钳釱赭衣,置任输作也。”颜师古同意这种说法后又加上其生活中存在的类似现象,谓“若今徒囚但不枷锁而责保散役之耳。”[1]至于“施刑”劳作的具体方式尚不得而知。汉简出土之后,有关汉代“弛刑”与“施刑”的问题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限于当时的材料有限对于它的认识仍是存留些不清楚的地方。《肩水金关汉简(叁)》之中有几条与之关联比较密切的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汉代的“施刑”提供了可能。与之关联的资料汉简中或作“弛刑”,或作“施刑”、“施刑士”,考虑到汉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词本文使用“施刑”一词。 现试在前贤的基础上,对西北汉简所见的“施刑”资料进一步阐述。
一.缘起
“施刑”一词,传统史书作“弛刑”,凡三见。其中一见于《史记》,即“郑吉,家在会稽。以卒伍起从军为郎,使护将弛刑士田渠梨。”[2]本条史料出自《史记·建元以来侯者表》,而郑吉屯田西域是在汉宣帝之时,其年代比《史记》的成书年代要晚上近50年。之所以在《史记》中出现有郑吉事,当为褚少孙所补文字部分。[3]
在《汉书》中虽为二见,实为一事,见于赵充国平羌之乱,文字记录稍有差异。分别是:
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4]
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5]
“弛刑”一词再度出现是在二十世纪初发现的西北汉简中,斯坦因发现的简牍中有一条资料。这条资料因为残断严重,文义不是太清楚。罗振玉、王国维编撰的《流沙坠简》未见收录,始见于张凤编辑的《汉简西陲木简汇编》[6]。从AB两面书写的文字和“叩头”来看似乎是书信用语。简文为:
“弛刑”二字在居延旧简中也是仅有一见,且也是目前所有三万枚居延汉简中仅有的。简文是:
本简,属于“邮书课”,其中的“十六年”为永元十六年(104年),记录了当时文书传递过程中施刑徒参与了邮书传递。且从现有文字来看,简牍原本文字残泐,释文有点难度。《合校》已经详列了各家释文差异,这里不再列举。只是橐他后面的“隧长”二字不应该是“隧长”,其写法类似下面的“弛刑”,应该释为“弛刑”。
除了上述二简外,西北简牍资料中更多的是以“施刑”或“施刑士”出现的。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以史语所简牍金石资料库检索所得信息来看,“施刑”凡出现31例。伴随着资料的丰富也就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9]从已有的检讨来看,因为有史书的旁证,史书所言以诏书“施刑”的观点得到了印证。“施刑”就是以“诏书”脱去镣枷之后的刑徒被派往某地从事专门的劳作。至于劳作的方式和劳作后的具体归宿问题,在原来资料的基础上还得不到比较完整的认识。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与发表,特别是金关汉简与悬泉汉简的出土,与“施刑”相关的资料得到大大丰富,已有的认识也将得到补充。有现代技术带来的检索方便,现将所有能见到的“施刑”资料归拢在一起,再根据他们分属的文书性质及其所揭示的“施刑”问题略加检讨。
二.囚徒因诏书方能“施刑”
《汉书》卷八关于“复作”的解释时孟康成将“复”字与“弛刑”联系起来,原文是“复,音服,谓弛刑徒也,有赦令诏书去其钳釱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律名为复作也。”颜师古注文称“孟说是也。”[10]这一点也就是目前认为“弛刑”必源于诏书的依据。[11]居延旧简中有一条明确记录“以诏书施刑”的简文,并且得到已有研究者的注意。简文是:
这条简文的解释比较多,其中以张建刚的说法比较合理。[12]从简牍的形制来看,本简比较宽属于木牍,下与左上部分残缺;从文字来看,现存文字有四行,左上侧一行文字残缺严重,即“·凡”以上未释读的文字部分;“□延吏□□簿”可释为“塞延袤道里簿”。按照甲渠候官塞延袤道里簿的文字,本简木牍存在的四行文字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解。前两行是分别说明施刑徒的身份状况,后两行文字反映的是甲渠候官汉塞的总长度状况。
其中“以诏书施刑”的两个人,一个人姓孙氏,初元五年七月因为“贼伤人”被判处“髡钳城旦”;另一人钱万世因为“兰渡塞”(偷越边境),在初元四年十一月被判处“完城旦”。“髡钳城旦”按照现有的认识是五年刑,“完城旦”比前者差一等属四年刑。居延新简的赎罪钱数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13]
孙氏与钱万世二人均在甲渠候官辖区服役,正好赶上史书未曾记录的初元五年八月戊申诏书,按照诏书二人的身份均可以改为“施刑”,即“以诏书施刑”。按照汉代诏书从长安传达到居延地区的时间不应少于30天,[14]七月庚寅到八月戊寅的10多天时间,与诏书传递无关,而居延都尉或甲渠候官收到诏书的具体执行时间应该要晚得多。按照后面的初元五年甲渠候官“塞延袤道里簿”,可以看作是甲渠候官初元五年的年终岁末文书。
本简出土在肩水金关,上下残,文义当与某人的出行有关。“以县次续食,给法所当得”类似传文书的用语。我们关注的是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其中提到某人施刑的原因不是一般的诏书,而是“以请诏”。“请诏”作为诏书的一种形式,是对某人或某事请求文书经皇上恩准、批复的诏书。类似的请诏文书如:
前简的“请诏”指的是皇帝对河西诸郡包括敦煌太守府请求调派传马文书的批复,皇帝同意让天水郡给这几个郡调派传马进行补充;后简意思更加明确,龟兹王生病后请求汉元帝派医术高明者替其治病,医者偃、博二人在龟兹住了5年之后回来,回来的时间是建昭元年(前38年),则二人以请诏出使龟兹为龟兹王绛宾治病的时间当在永光元年(前43年)。
三.施刑士的派发调遣
不仅囚徒的施刑离不开诏书,从悬泉置出土的传文书记录来看“施刑士”的远距离派发调遣也是有诏书背景的。悬泉汉简中有几条送施刑徒经过悬泉置的传文书抄件,虽然有点出入,但大致都是“以诏书送施刑”出现的。此类文书有:
以上五简是悬泉汉简中送施刑人员经过悬泉置的传文书,其中前四简都是有“以诏书送施刑士”等词出现的,只有末简是例外。多数简文出现“以诏书送施刑士”可见不仅囚徒施刑需要诏书,而且施刑士的征发同样也是有诏书背景的。即当时根据某一诏书将囚徒施刑后,再征派到某一需要的地点。从目前保存的文字来看,前四简与后一简差异最大的地方是后一简是持传人经过悬泉置返回的时间,前四简则不明确。也许正是因为有“闰月甲申过东”的记录,本简的传文书抄录时才省缺了“以诏书”三字。
首简送施刑士到伊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有史书记载的伊循屯田事约与之有关系;后面的送施刑士到玉门关和阳关则有点费解。如果不考虑玉门关和阳关的地理属性还比较容易理解,不就是两个地名吗?但若细究玉门关和阳关属性则较费些事。史书记汉王朝据两关界西域,阳关与玉门关是汉与西域的分界点,可以理解为二关所在的关卡。此等意义上的两关是个比较小的地方,为什么要将传文书反映的施刑士送到两关呢?两关也可以理解为阳关都尉和玉门关都尉,是汉代敦煌郡的两个部都尉,将施刑士送到两个部都尉辖区服役。而两个部都尉又实际上是敦煌郡的郡属都尉,直接受敦煌郡太守府管辖,他们所用的施刑士应该由敦煌郡太守府分派方妥,与后面悬泉置接收的施刑士类似,即施刑士不应该直接送到两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送至两关的施刑士应该只是临时的举措,其最终目的地应该是与西域有关的某一地方。
而另外一种记录送施刑士的文书,因为具体的文书性质属于粮食出入簿而不是传文书,其中的文字并没有记录与反映其所送的施刑徒是不是有诏书背景。如:
此三简重点记录的是悬泉置为送施刑徒的三人提供了多少粮食,三人都是因为送施刑士经过悬泉置而在悬泉置停留吃了几顿饭或多少升粟米。其与传文书的内容从文字要求上来看具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考虑文书的功能性质就可以将传文书与粮食出入簿因为“施刑”问题而混在一起。屋兰亭长封益寿与其随从在悬泉置的食宿是从东向西经过的,每人吃了一顿饭每顿是粟三升;武威使者“乃移置”(“乃移置”,人名可能释文有问题)由东向西送施刑士赵昌在悬泉置吃了一顿饭,悬泉置提供的不是粟而是米,且都是三升,可见赵昌的待遇要好一些。
西北汉简中除了征发、派遣的施刑士之外,还可以看到随使者、将军出使西域的“施刑士“。如:
前简属于居延旧简,元康四年二月“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等人的文书中追记元康二年派遣施刑士50人事,郑吉派尉丞赦将施刑士50人送到某处;后二简属于著名的“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中的文字,长罗侯出使西域随行的施刑士在悬泉置被接待,其中施刑士的数量有300人之多。
四.施刑士的使用
在西北汉简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施刑士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文书,这里面包括有施刑出入簿、名籍简、禀名籍和劳作簿等。如:
施刑出入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是使用“施刑”基层单位的档案文书,其中的部分文书为我们考察这些“施刑”的来源提供了资料。如:
以上六简文字略有差异,根据已知出入簿文书格式可以归为“出入簿”类文书。简18和简19出土在甲渠候官所在的破城子,可以看作是甲渠候官有关“施刑”的出入簿类文书,其中的“毋出入”即是明证,承上月(十一月)剩1人,人数之少可能不是候官所用的文书,而是其下属机构使用“施刑”的情况;简20出土在A10瓦因托尼,属于殄北候官所在地,“■右”也是出入簿类文书的典型文书用简;简21出土在悬泉置,“■右受府”说明悬泉置一次从太守府接收“施刑”人员11人;简23属于削衣,文书性质不明,可以看作是悬泉置汇报“施刑”使用状况的文书,其中的2人因赦而免,赦免的结果直接导致悬泉置“施刑”出入簿中的“出”。会赦而免是施刑“出”的一个因素,后面提到服役期满的“施刑”也会归入出入簿类的“出”类。
名籍简:名籍简是简牍文书常见的一种文书形式,一般包括人员的籍贯、姓名、身高和年龄等。考虑到简牍的残断,我们可以将下面有关施刑登记的文书看作是“名籍简”。如:
以上六简或残或完整,与一般戍卒名籍简格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区别这些文字记录我们暂时归为“名籍简”。可见施刑的名籍简一般会有籍贯、姓名和施刑前的身份(刑徒名)。为了说明它与戍卒名籍简的差异,我们不妨再举数例简文加以旁证。如:
前二简是一般所言的戍卒名籍简格式,后一简属于因为在悬泉置劳作而由悬泉置制作的名籍。[16]可见在名籍简中籍贯、姓名、爵位和年龄是必不可少的(悬泉简除外)。用在一般戍卒名籍简中的身份爵位可能就是标志施刑身份原本的囚徒名。考虑到这一点,下面的记录囚徒信息的简文估计也应该属于名籍简。即:
我们之所以将本简的文字全部迻录,主要是因为本木牍的A、B面有互相照应的文字,A面记录的前三个囚徒属于施刑,应该指的就是B面“其三人犯法外给事中,以诏书(施刑)”。前三人之中目前可以看到的有两人,即北地大要阴利里的“公孙合”与大常阳陵北武都里的“石骏”,二人原来的罪名都是“盗亡乏兴”,另一人的罪名是“盗出财物边关”,唯人名不存。
禀名籍:在简牍文书中除了看到前面为施刑人员提供饮食之外,如“过长罗侯费用簿”,还有具体使用施刑的单位为施刑人员提供月供口粮的记录文书。
从简25和简26的口粮标准与物品来看,在居延地区戍卒与施刑士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悬泉汉简中尚看不到。
以上三简,分别出土在不同地方,可比性不高。简28出土在P9博罗松治,汉代卅井候官所在地;简29为悬泉汉简,简30出土在马圈湾遗址。只有简30的施刑可与另一简为同一册书,且从定量标准上看不出“卒”与“施刑”的差异。[17]
劳作簿:这里的“劳作簿”只能算是借用,与真正的“劳作簿”尚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只是为了区分这些与施刑相关的简牍文书而已。通过这些残断的文书我们可以发现“施刑”的具体劳作岗位。从这些文书所示的岗位来看,施刑士被分在了边塞最基层的防御单位“隧”之中。如:
以上四简属于居延汉简,施刑士被分配在“隧”中,日常工作或劳作内容应该类似普通的戍卒。隧卒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候望、巡视天田、传递烽火信号,有时还会参加除沙、制墼、伐茭和运茭等劳作。
在前面我们谈到过施刑从事邮书传递任务的情况,即简552·3记录的橐他施刑与破胡施刑二人之间进行的邮书交接,且时间是永元十六年(104年)事,属于东汉之时。记录有施刑士与鄣卒在一起的简文26·21,也可以看作是施刑士在候官驻地劳作的情形。
悬泉汉简中我们见到的施刑士,除了属于经过此地的外,还有悬泉置从太守府接收的施刑士,他们到悬泉置从事干什么工作,这一点简牍文书并没有反映。不过可以知道,类似悬泉置的邮驿机构也是施刑士劳作的场所之一。
施刑士在《汉书》记录的有从事讨羌战争者,有随军屯田伊循者,至于具体劳作方式并没有交代,简牍文书使我们看到了施刑士不同劳作岗位或分工。在边塞可以作为普通守边人员戍卒使用,也可以在候官所在地的鄣中从事劳作,也可以在类似悬泉置的邮驿机构中从事邮书传递工作;时间跨度从西汉始,经王莽一直到东汉都有使用。如果说史书的记载有点类似“敢死队”成员的性质,那么后者则将他们作为了一种人员的补充。从更广的角度可以看作是汉代囚徒的又一种管理方式和手段。
五.施刑士的管理
前面所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管理,在此我们想利用肩水金关汉简的资料谈一谈以前尚不知道的管理方式。相关简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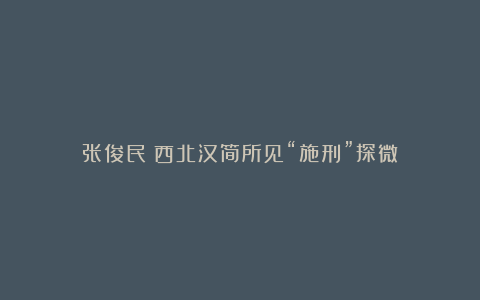
这是金关汉简中出现的与施刑相关的简文,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的“作一日当二”和“作一日□”。施刑者在居延屯作应该如何对待呢?按照文书格式应该是“作一日当二(日)”。即施刑士在居延劳作一天可以算作二天计。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仅有的资料,其价值之高是不能忽视的。
按照此等记录施刑士在居延地区劳作一天算作两天,而普通的小吏(候长、候史和隧长)日迹两天才算三天,[19]两者相较,可见对施刑士的“一日当二日”规定应该是特殊优待了。
由这条简文出发,再检索《肩水金关汉简(三)》,我们发现还有一条对于认识与研究施刑士至关重要的简文。原文是:
细审图版,其中的省略号“……”应该释作“屯作一日当二日□□□□□”,“前”字可能是“备”字(也可能是“满”字,两字差异不大,悬泉汉简中就存在混用状况),最后的两个“□□”应是左侧一行文字的余笔(可省略)。按照我们的释读方式原来的简文应该是:
本简左右残,左行仅存最后的余笔,右行文字残存半个字或少半个字,一些字仍无法释读。不过,根据现有文书格式,本简应该属于施刑士归故郡的传文书,与我们以前曾注意到的囚徒归故郡文书类似。[20] 其中明确记录施刑士归故郡的原因是其服役期满,亦即简文的“作日备”。
何为“作日备”?如何计算才算“备”?
首先对“作日”与“备”的理解可以在秦简中找到相应的文字记录,并用来作为参考。秦简记:
有罪以赀赎及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四。……其日未备而柀入钱者,许之。以日当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衣食而令居之。官作居赀赎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而毕到其官;官相近者,尽九月而告其计所官,计之其作年。[21]
这是秦律中关于如何“居赀赎债”的有关规定和具体方法,其中的“作日”和“备”,用在汉代与之相应的劳役刑中应该就是“劳作”与劳作期满。以前曾经看到过囚徒服役期满申请减罪的文书,服役期满与“作日备”估计就是一个意思。如:
我们只是根据简73EJT30:16的传文书文字特征推测可能是施刑士归故郡的文书,实际上尚看不到“归故郡”与施刑士减罪的文字。施刑士“作日备”的时间计算方式按照已知的状况估计应该是施刑前的本刑,如髡钳城旦、完城旦。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施刑者在居延“作一日当二日”,单看“一日当二日”是对施刑的劳作时间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将施刑者劳 “作一日当二日”与“北边絜令第四”规定的“北边候长、候史迹二日当三日”比较就会发现施刑的待遇明显要比候长、候史还要高[22]。在汉塞防御系统中参与日迹工作的候长、候史无论如何也是小吏,尚不如因诏书而施刑的囚徒享受的待遇好,两者的差异说明了什么呢?这一点很值得探讨与研究。
金关汉简中也有一条资料,其中的“诏书发”与“作日”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施刑”,且其中的文字还可以补释较多。原释文作:
有了上述“作日备”的检讨,本条简文可释读为:
本简为“削衣”,按照一般所言的削衣形成原因是书写错误后为了改正削下来的部分,这种意义上的削衣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而实际上为了将简牍削成别的物品再利用,也会将简牍上的文字削下来。如与汉简伴出的物品中常见的一种木匙,无疑就是由简牍刮削而来的。“施刑会赦免”,这是目前所见的最直接证据,就是施刑士可以与其它类型的囚徒一样,也会因为皇帝的恩赐而被赦免,且赦免后的囚徒还可以归故郡。如:
“归故郡”是施刑士的一种出路或结局,也是当时的一种管理方法,而实际上施刑士还有一种选择,他可以选择不着急回家。与之相关的管理文书如:
惜本简下残,具体的安排方式不明。不过从本简文字开头的“·”格式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一种制度文书,是对施刑士服役期满后不归故郡当如何处置的规定。居延旧简中的简262·19就可以看作是实际处置这类状况的文书,简文记施刑孙田没有直接归故郡,而是留在了原来劳作的地方做了别的事情[23]。
六.施刑的又一种生活方式
简牍文书中还有许多与施刑相关的资料,除了因为残缺仅见施刑人名之外所示信息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两种反映施刑生活状况的文书。为了全面观察西北汉简中存在的“施刑”,我们不妨将他们引出来。
施刑的逃亡:边塞地区存在人员逃亡的现象应该说是一种普遍行为,并不仅仅是施刑人员才会逃亡,简牍文书中我们可以看与捕亡相关的文书。
前三简之中的首简是上报亡人的文书,其中提到了逃亡的施刑士张广等人原本就是“行为巧诈”;后二简为具体地追捕逃亡施刑士的文书,且施刑士“金利等”竟然也属于“诏所名捕”人员。
本简通过孙根之口,反映了施刑宋后参与了边塞地区的债务纠纷,士吏孙根是受候官派遣协调宋后与徐乐的债务。这种情况与普通戍卒在边地存在的债务纠纷也是一致,表明施刑士与一般人员一样,也是深深地融进了边塞的社会生活之中。
七.“弛刑”与“施刑”
从前面例举的实例来看,“弛刑”出现的情况比较少,多数是以“施刑”出现的,即简牍文书中出现的更多情况是“施刑”,怀疑“弛刑”释读可能是受到了史书记载的影响。在简牍发现之初,受资料数量的限制才将这两个字释读为“弛刑”,而实际上应作“施刑”。另一方面在编辑的字书中就没有收录“弛刑”之“弛”字[24]。
小结
从史书中出现的“弛刑”,到西北汉简中大量出现的“施刑”,使我们有可能对“弛刑”是“施刑”之误产生了怀疑。这点怀疑,因为尚缺乏能直接推翻最早释文“弛刑”的证据而存在,但是作为“施刑”大量存在的资料则是不争的事实。汉简中“施刑”的产生不仅是“囚徒”因为诏书方能施刑,而且施刑的远途征调也是有诏书的背景。这一点同史书记载因诏书施刑是对应的。之外,汉简中还有一条是因为“请诏”而施刑的资料。
在西北汉简中施刑,除了用于远征西域的人员之外,更多的则是在西北边塞地区直接参与劳作的施刑人员。他们或在边塞的最基层单位“隧”中,或与候官所在地的鄣卒一起劳作,有的还可以在邮驿机构中干活甚至参加邮书传递。可见,他们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泛,深深地融入了边塞的社会生活之中。
施刑人员不仅可以通过赦令而免除劳作,甚至可以从遥远的边塞回归故里,而且也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继续在边地从事劳作。这些状况在西北汉简都可以找到证据。在居延地区从事“屯作”的“施刑”在完成一定期限的服役劳作之后,也是可以免罪的。劳役的期限似乎有一种优待,即劳作一天可以按两天计算。这种方式虽然目前只是在居延汉简中出现了,估计用在其它地区也是可以的。这种优待又体现出施刑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身份,之所以独特又与因诏书施刑有关。而施刑具体的劳役期限可能是由原来的本刑决定的。
注释
[1]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260页。
[2] 司马迁:《史记》,1963年,中华书局第1068页。
[3] 司马迁:《史记》之出版说明第3页。
[4] 班固:《汉书》,第1068页。
[5] 班固:《汉书》,第2977页。
[6] 张凤:《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参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2007年第625页。
[7] 此类简号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下同)。释文又见劳干:《汉晋西陲木简新考》,释文作“□□番弛刑具身远客未晓习俗不使(45.5)史赵众叩头(46.5)”,(台北)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七,1985年第6页。
[8] 此类简号见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同。
[9] 张鹤泉:《略论汉代的弛刑徒》《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薛英群:《说弛刑简》,《西北史地》,1992年第2期(可能是因为编校问题“弛”误作“驰”);张建刚:《汉代的罚作、复作与弛刑》,《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陈玲 寇凤梅:《汉代弛刑徒略论》,《河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0] 班固:《汉书》,第236页。
[11] 张建刚:《汉代的罚作、复作与弛刑》,《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
[12] 张建刚:《汉代的罚作、复作与弛刑》,《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
[13] 居延新简E.P.T56: 37、36记“髡钳城旦舂九百石,直钱六万;赎完城旦舂六百石,直钱四万”。此类简号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下同。
[14] 综合已有诏书传递时间,我们认为从长安到张掖郡大概需要30天,从长安到敦煌的时间是40天。参见张俊民:《简牍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21页。
[15] 张俊民:《肩水金关汉简(壹)释文补例续》,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12年5月8日。此类简号见肩水金关汉简,下同。
[16] 本简与ⅠT0309③:54为一册书,自名“县泉置神爵二年正月戍卒名籍”。
[17] 敦·337释文作:“卒王星亖斗,十月食”。
[18] “百”字原作“□”,为作者补释。
[19] 张俊民:《汉代边境防御制度初探》,《简帛研究(200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 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文书格式简》,《简帛研究(200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22] 居延汉简562·19
[23] 简文“施刑孙田 今留不 ”。
[24] 陈建贡、徐敏编:《简牍帛书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
本文原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9卷第2期,第3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