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城
/ BOOK TOWN
念及《新青年》鼎盛时的人才济济,并与后来的历史进行对比之后,孙郁说:“他们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坛再未有过如此灿烂的群星,想到这里,不禁为后人黯然神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在人类的衍生史中,美丽有时就这么短暂。”此话正道出孙郁此番写作之缘由。《寻路者》(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的写作正是孙郁的向前追寻。孙郁在寻找民国那些人走过的足迹,并借聆听他们的心跳,进一步描绘他们在依旧勃勃的文字中留下的影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闻一多等人是早先于孙郁的寻路者。他们在历史的暗道里寻民与国的出路,孙郁在他们身后寻与他们有关的点滴。他们的“寻”决定了孙郁的“寻”,孙郁的“寻”则是对他们的“寻”之呼应。给后世留下不绝念想的历史人物,实则需要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的寻路者。孙郁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否则历史的迷雾如何拨开,历史的谜底如何揭示?
一
《寻路者》是关于民国人物的书写。有单个的显影,更有群体的勾勒。有先后、主次之分,无高下之别。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梁实秋、闻一多均被请进书中,留下独特的音容笑貌。与鲁迅或亲或疏的学生,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等人,以及老舍、巴金、张爱玲、张中行等人也参与并壮大着寻路的队伍。《寻路者》与好奇于他们的秘辛、计较于日常琐事的著作不同,它既讲述他们的人生履历与个性举止,更一次次深入旧日文本最深处,提炼如此作为背后的精神源头。人之活着,最本质之要素在于精神,更何况是倚靠文字凭借思想安身立命的文化人。
《寻路者》
孙郁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鲁迅是整本书中分量最重的人物。在《夜枭声》这篇中,孙郁如此说道:“但鲁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撕碎了常人式的认知之网,将触角延伸到理性无法解析的精神黑洞里。确切、已然、逻辑、秩序,通通被颠覆了。他看到了一个未被描述的另一类的世界,思想必须重新组合,格律已失去意义,唯有在那片混沌的世界里,才隐含着别样的可能。鲁迅诅咒了世界,也诅咒了自己,而他被人诅咒和亵渎,那也是自然的了。”这是无处可去的选择,这是无人可以诉说的悲哀,宁愿把自己置身所有人不去的异地,来显示自己是最非凡最独特的存在。鲁迅并不想当先知的,他也自知不够格,但愿意作为警示般的存在,愤怒于自个儿的愤怒、悲哀于自我的悲哀、孤独于自己的孤独里。那么,周遭的人如何看待他,他是无所谓的。他的孤独,终究是无法亦无须挣脱的处境。
与鲁迅关系既不近也不远的同道中,胡适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从《新青年》四卷四号上刊登的,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孙郁看出他文字里对旧学颠覆性很强的背后,是隐隐的热热的光,是一种亲和力的自然涌动。与此同时,在写给汪懋祖的信中,他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在孙郁看来“则是难得的雅量”。这样的人,放在当今时代里,也是罕见的,是自有一种魅力的。如果不是身处那样的时代,这样的才华与品质,应该能够惠及更多青年学子。
《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916年9月出版
《未名社旧影》是孙郁对鲁迅学生的整体勾勒。他们都有共同的、相仿的文学梦,鲁迅愿意帮助他们做些事,于是就有了未名社。其中,最可以说道、最让人怀念的当属英年早逝的韦素园。他忠厚、纯情,鉴赏目光锐利,有殉道的激情。按照孙郁的话来讲,“他身体柔弱,却有着坚毅的一面,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而且“他和朋友相处,总要付出更多的一些,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他是未名社的中坚力量与灵魂。偏是这样的人,早早撒手于人间,与心爱的文学事业久别了。孙郁曾走近过其墓地,心中的悲叹可想而知。
作为先行者,他们或如先知般的存在,他们果敢勇毅,走着自己的路。他们在学术或文学作品中留下的声音,组合成不那么令人欢欣的氛围。有些暗淡,有些阴霾,有些杂乱,有些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是时代带给的困境,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摆脱。
民国历史不长,却复杂、浩繁,学者们研究著作迭出,各有视角与心得,可谓众声喧哗。孙郁目光所聚焦的是民国史的一小段,甚至只是某几个角落而已。孙郁的写作不为美化人物或遮蔽美好之外的许多面,而是把他已知的一面写出。如果说在书中多有展示他们美好一面的话,那是作者的向善、爱美之心起的作用,亦是作者并未求全责备的温柔之心在明显跳动。借钱穆先生的话来讲便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务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历史人物一味挑剔者,是无知的,是虚无的,是贫乏的,当然也是不足取的。
深邃、苍茫的历史里,若无可以留恋的人物在,那便不值得回望。孙郁笔下的“寻路者”们,无疑当得起如今的人们频频回首。民国乃乱世,乱世中的众声喧哗,各种话语交错而生,精彩与美好也就在其中了。
二
在我看来,孙郁《寻路者》不失为一席文化盛宴。虽为盛宴,却不张扬,不仅不张扬,甚至显得低调。这是孙郁的文风决定的,在故纸堆里埋首久了,抬起头来,提笔写出自我感受,至于旁人看不看得懂、理解得是否透彻,是他无暇顾及的。短暂的民国史幽深得很,人性之幽深比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探寻,不是一次可以到位、能够完成的。借先贤留下的文字,孙郁一次次深入其中。
遣词造句时,他常带着商量的语气,倾诉着合乎情理的可能,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又在时移世易之后,生发出新的可能也未可知。我想说的是,这正是孙郁讲述历史的魅力,因娓娓道来而产生的亲和,给人如在目前之感。写作如谈话,其内心之诚可想而知。我以为,这是读者绝不能错过的一种福利。许多人写作,总是天然地摆起架子、板起面孔,装出先知的模样,让人读着如听训示,内心之压抑与不快可想而知。在《月下诗魂》中,他说:“生命乃一个过程,人很可能成为自己选择的对象的奴隶。”同样在这篇文章,他还说道:“人只有不断摆脱外套束缚且质疑着这个世界时,大约才能免遭苦役。”写出困惑,亦写出解惑之道。给人以淡淡的愁绪乃至哀伤,转而又照进一缕阳光,让人欣喜。
徐志摩等人创办的
《新月》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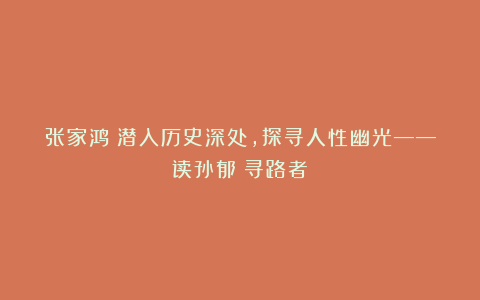
1928—1933年间出版
《月下诗魂》这篇,谈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人士与鲁迅的不同,孙郁认为:“我读胡适诸人的文字,常常觉得他们美好的态度对现实是无力的,少的恰是自我的痛感,也未能予人以深深的痛感。打不中对手的内脏。新月派的批判意识是梦的游走,几乎不能搬动眼前的冰山。”那么鲁迅呢?“单如果看看鲁迅的冷峻与热力,却可以融化些什么,将阴冷的氛围驱走了。鲁迅之不同于自由主义文人在于,不相信一个确切的要领可以涵盖一切。”胡适的缺点是有的,相形之下,鲁迅有优点,却也不是胜过所有人的存在。他也是有缺点的。
孙郁的表达固然呈现出自家观点,却又让人时常觉得,历史或人性常常存在别的可能。孙郁的看,是他的姿态与模样,并非限制他人的看,并不束缚别人自由地看与想象。唯其如此,此盛宴才是丰盛的,丰厚的。
盛宴的背后,是孙郁的静气。守静之人,才不会焦躁,不想毕其功于一役,不会急于得出振聋发聩的结论以赢得当代人的交口称赞。讲述历史,是他的不断挖掘,也是他的内心皈依。诚如他在《〈语丝〉内外》中所言:“在鲁迅的文字里,学问和本我的体验是交织在一起的。”孙郁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之深受鲁迅影响,此乃其中之一。学问固然是学问,然而,学问若少了体验的支撑,很难说是真正的认知。
鲁迅(1881—1936)
陈独秀(1879—1942)
《在路上》一文从鲁迅与陈独秀两人的关系出发,梳理他们在可能相遇的时空里各自的行迹与心境。在文章的末尾,孙郁写道:“大家都在行进的路上,前面是茫茫的夜,身后也是茫茫的夜,就那么走着。相互依偎着前行是一种走,独自跋涉也是一种走,在通往明天的路上,有更好的方式吗?鲁迅是悲观的,他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如何,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自己还能做一点什么。”这是颇有情感的一句话,尽管孙郁的表达是内敛的。他并不跳出来,可是却寄托着很深的慨叹,以及更多莫可名状的心绪。也许,陈独秀与鲁迅若能相互依偎着行走,是胜于他们各自行走的。《新青年》的存在,竟未能把二者拉近,实在是可惜可叹的。个人直接的、温热的感受被历史的意识贯穿着,成为一条清晰的脉络,在孙郁心中是早已扎根的。那是沉浸于民国史后又悠然走出的自然而然,那是让自我生命融入民国学人学识与性情之后的清醒认知。
《徐旭生西游日记》
徐炳昶 徐旭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想念徐炳昶其为人,孙郁表达出忍不住的赞许、止不住的敬意。与同时期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徐氏并非固守书斋的学者。加入考古团队深入大漠之后,他一次次被斯文·赫定等人的科学精神打动,并把详情写进日记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高贵、荣誉、世俗,甘心沉入到远古,沉入到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不独日记里流淌出的真知灼见,单是这般远离与深入,已然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能为之。更不必说,彼时有多少同行会鄙夷于他加入考古队之后的西北之行?
1927年,徐炳昶(右)担任中外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中)为外方团长,袁复礼(左)曾为中方代理团长
《故都寒士》中,遥想张中行于北大学习时的情形,孙郁写道:“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张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师者倘若传道授业解惑时,又自然流淌出真性情,学生自然是受益匪浅的。仅此一点,张中行已然足够孙郁羡慕的,当然,孙郁传递出的还有对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敬意。敬意之后还有如在耳畔的叹息。同一篇文章里,孙郁继续写道:“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与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对他是一种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张中行的孤独是自然的,其文字的孤独也是定然的。其文字有那样师承,起自那样的校园,是张中行的存在,让孙郁瞬间触碰着历史。
文字若有温度与情怀,袒露心迹是必然的。孙郁的文字常有这样的特质,唯其如此,才能打动许多其实对民国文学并不熟悉、对民国文人只知其名的人。饱含温度与情怀的文字勾勒,方能让文化盛宴处于热气腾腾的状态。鲁迅、胡适、闻一多、周作人等人,前人不知说过几回,甚至已被大众认定为标签式的确凿存在。可是在孙郁笔下,依然是音容笑貌如在昨日,呼吸欢笑如在目前,这并不追求独特的呈现,却是充满个性的存在。
孙郁写民国文化人,是从自我内心出发的观察。脚步与心跳合拍者,乃守静收心之人。在如此浮躁的当下,静气是作家最难得的修养,静气亦是作家文字最难得的特质。静气,不是守在某个角落的不言语,默守自我,而是在外力逼迫与时代骤变之时保持定力,继续深入早先确立的领域。如此则文字自然不会有焦灼之感,鲜有浮躁之气。如此则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己就是当仁不让的王者。沉潜于历史深处,找寻自我的一片天地,孙郁是孤独的,也是快意的。正如那些执着行走在择定之路上的历史人物。这是自信,亦是自足。不与他人争,并非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的自大与自负,而是让自我生命之火自然而然地燃烧。
遇见有静气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与福利。读到他的一本书,只是被静气散发出的光芒几缕照见而已。他更多值得品鉴的文字,在下一个时间或某个路口,静候读者有缘遇见。多年来,我读孙郁便是如此。多年前读他的《鲁迅藏画录》《张中行别传》《写作的叛徒》,前阵子细读《聆听者》《民国文学课》《闲话汪曾祺》,直至如今细读《寻路者》,我在他温润、优雅且充满真实自我的世界里流连忘返。
三
固然,孙郁的文字是写他们的,因鲁迅、周作人、闻一多、老舍等人而来。对他们作品和人生的解读,是孙郁的倾听与审视,当然也是共鸣产生之后的对话。倾听与审视有所本源,对话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它虽源于他者却也是心声的抒发,他的文字自成一个世界。经常地,我可以暂时忘却他笔下人物的存在,把那些句段放在当下生活中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审视与解读。我以为,这正标志着评论文字日臻化境。文字里有他们,文字里有孙郁自我的显影,文字脱离背景人物仍具有的勃发生命力。
我在《寻路者》的字里行间寻找这般独立的、高耸的、显赫的存在,如高山上的青松,即便失去倚靠的高山,它们的高大、卓绝、肃然亦不减分毫。我并不以深刻许之,只是它们确乎于遇见的那一瞬间即撞击了我,并且在全本读完后的温习时令我舍不得远离,且能引起我深一层、进一步地思索。
《夜枭声》中,他说:“光明是诞生于黑暗之中的;唯有久久沉浸在黑暗之中的人,才会给人提供丰沛的亮色。”人在乱世中的抗争,人在现实中的前行,莫不如此。久在黑暗,了然于黑暗的源头与面相,足以让他给人提供可供借鉴的建议。在《古道西风》中,他说:“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这何尝不是他的自省乃至自警?若能真正洗刷自我,那么大的哀痛亦意味着大的突围与进境。这岂是人人可为的?非智勇双全者不能为也。以哀痛为准绳,借以观察古往今来之圣贤,不也可乎?在《同人们》中,他说道:“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人类永无法摆脱之困境。历史本就是困境,更何况打量呢?时光流逝,距离凸显,迷雾阵阵,焉得轻易窥探真相。更何况,经过代代言说的历史,愈发扑朔迷离。既如此,打量到的历史,往往只是个人眼中的历史。在《月下诗魂》的末尾,孙郁写道:“海市蜃楼固然美,那却是缥缈的存在。人毕竟生活在人间世中。有梦是好的,如能睁着眼睛看到梦之外的风风雨雨,知道还是可怜世间的匆匆过客,那么庶几不为幻觉所扰,一边幻想着,一边实干着,大约就不会沦为清议的虚妄。”人可以想象,却不应活在幻想中,或者说被幻想罩住了现实。海市蜃楼,观赏倒是可以的,却不可视作全部,否则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踩在虚无。《帝都之影》中,他如此诠释文学与写作——“文学是寂寞人的事。”随后,他又说:“因为写作,便感到了一个真的自我的存在。”拥抱文学,意味着选择寂寞与孤独。否则如何在日日与文学的耳鬓厮磨中,窥见文学之奥秘?因为寂寞或孤独,而认清自我、丰富自我、升华自我,正是文学带来的终极意义。
没错,它们虽然涌动于孙郁的笔端,是当下新近出版之作品的一部分,我却愿意把它们视作名言警句的存在,不必挂在墙上制作成正式的版式,以广而告之于众人,而是放在心中久久回味、咀嚼,并在往后日子里时时接受其润泽。基于此,我大概是可以把《寻路者》视作一本厚重的集文散的,它不仅以描摹刻画鲁迅、胡适、巴金等人的形影为目的,还给人以长久的鞭策与激励,赐予人温热的感动与指点,令人借此奋进再奋进。人生如此短暂,奋进是征途,也是目的。人生如此短暂,转瞬即为过去。既如此,命运就是没有止境的征途。
掩卷深思,我深以为经由《寻路者》的探寻与挖掘,孙郁创造出带着个人深刻烙印的民国。大家都在茫然的路上走着,有的人志趣变更,变轨之后走向别的路,那就目光遥送便是;有的人走得太急,摔倒在地磕破膝盖渗出血丝,同道们搀扶起他,一道继续前行;有的人稳稳地走着,竟遇见许多人、见过无数风景,心中的共鸣的言语至今给人带来久久感动。探寻是他们的道路,也是他们的归宿。至于最后是否看到希望的曙光,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路上勇敢走着,就够了。
「END」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