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到夏天,我就会变成水生动物,白天不在溪里就在河里,吃好晚饭,村妇们呼朋引伴去水库洗澡,我(和我姐)又抓起衣服赶紧跟上。欢快的大姑大婶们聚在临岸的浅水区搓澡、闲聊,我抓紧时间展示泳技愉悦自己。我最爱“潜泳”,整个身子埋进水里往前游,常常一口气就能游过半个水库(水库不大,或许应该叫山塘)。有一回,我从水下钻出,发现已经游到水库尽头。山风吹拂,说话声、欢笑声那么远,水面黑魆魆的很安静。在水一芳,无比满足。
今年暑假,我也是以潜泳的方式度过的,醉心于工作,抬头一看,假期余额已经不多。
过去两个多月,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六月下旬,课程结束,我先给译著《约翰·济慈的颂歌》写了篇后记,四五千字。七月,译著通过印前质检、即将进厂印刷,我觉得不放心,把它喊回来重新校阅了一遍。这本书有三四十万字,旁征博引,上天入地,学术性很强,复杂句很多,中英文对照着读一遍需要不少时间。我在两周内逐字逐句校读、修改完毕,按约定时间寄还给出版社,这效率超乎我自己的想象。
(此书已正式出版,各网站书店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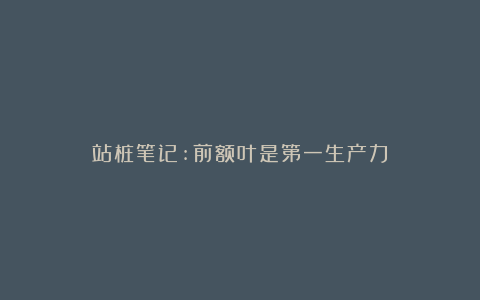
更令我不敢想的是,七月我还完成了另两件事。一是对“译后记”进行修改、扩写,发展成一篇学术论文(将在九月刊出)。二是完成了另一本书稿的整理、完善工作(当然,这本书十年前就已经干了个大概),预计将在今年或明年出版。
八月,我回了趟老家,出门云游了一番。然后查阅了一堆文献,用两周时间为同事主编的教材撰写了一章,一万七千字,昨天刚发走。
闲散如我,竟能在两个月内完成这么多事,挺意外的。我常对董老师感叹:“原来一个月可以做这么多事啊,前面五十年我都干什么去了?”他便说:“悠着点,一个人是没法按这种强度长久工作的。”
校对书稿的那两周,我每天四点多起床(自然醒),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半。一般来说,每两个小时就需要充一次电,我的充电方式自然是站桩或打坐。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气感主要集中在头部,只要一进入功态,气流就往脑袋里涌。百会穴感受到两股力量,一股力量使劲往上提,好像要把脑袋和脖颈一并拽出去,另一股力量沉甸甸的往下压,好像要把整个身体种进地里。在这上下两股强力的作用下,百会穴有节奏地呼吸着,一起一伏,如同婴儿熟睡,如同胎动。脑袋的其他区域也随之起伏,甚至胸口,小腹和腿脚也会有相同的频率。每次练功二十分钟,疲累感便会缓解,头脑重又清明,于是,一个满血复活的我又坐到了电脑前。以前看拳击比赛,常觉得不可思议,运动员被打得血肉模糊,眼看着要就地倒下,断送职业生涯了,没想到教练给他喝了口水,在他肩上拍了两拍,他又斗志昂扬地重返擂台,跟对手死磕了起来,最后还能来个振臂高呼的告别。七月的我,差不多也是如此。
暑假里的站桩新进展之一是,前额叶的气感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力(虽然只限于右侧一小片区域)。有时候甚至比百会穴的律动更清晰,仿佛南宋朝廷南渡,将中枢从汴京迁到了临安。前两天,我忽发奇想,觉得我之所以突然变得善于规划、敢于决断,能够心无旁骛有条不紊且轻松愉快地推进各项工作,可能是因为我的前额叶在觉醒。
查了些资料,发现前额叶果然脱不了干系。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简称PFC)是人类大脑中最晚进化出来的区域,是高级认知功能的指挥中枢。它掌管着我们最富“人性”的能力,如目标设定、计划执行、注意力集中、情绪管理、延迟满足等。它能协调各个脑区,统合记忆、情感与动机,将混沌化为秩序,将愿望化为行动。另有资料表明,正念冥想(站桩打坐也在其中)能增加前额叶脑皮层和右前脑岛等脑皮层区域的厚度,并能使前额叶的α波增强,形成最佳决策脑波。
在我蠢蠢欲动张罗退休的年纪,前额叶略施小功,让我领受到了工作的乐趣,并让我产生一种虚拟语气的谵妄式幻想——我是不是原本也蛮可以做个”卷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