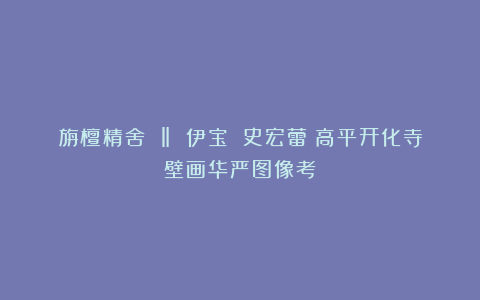|
图说:开化寺大殿
正文|
开化寺位于山西省晋城高平市东北舍利山山麓,从院内碑刻《泽州舍利山开化寺修功德记》可知,寺院大雄宝殿东壁所绘壁画取材自《华严经》:“凡人游乎寺也,望殿宇巍峨,灿以丹青……其东序曰华严。”其中的东序即是指大雄宝殿内的东壁。从空间布局来看,壁画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柴泽俊解读其由南至北分别为《兜率天宫会》《普光法堂会》《重会普光法堂》《三重会普光法堂》;谷东方认为由北至南依次为第五会、第一会、第九会、毗卢遮那佛,扆壁东侧为《弥勒说法图》;李璐珂则认为其华严图像不仅有东壁四幅,还包括扆壁东侧(北壁稍间)的《弥勒上生经变图》,由南至北第一幅为《入法界品经变图》,第二幅第九会之《大庄严重阁——狮子三昧图》,第三幅第一会之《摩竭提国兰若菩提场》,第四幅第五会之《兜率天宫图》,转扆壁第五幅《兜率天宫图》,这一图像辨析是以图像建筑内容为主要依据,重点提取了城垣与宫殿的结构,她认为东壁第二幅、第三幅、第四幅与扆壁第五幅皆为局部表达,而第一幅中佛之法身内须弥山图像则完整表现了《兜率天宫图》的内容。从图像结构表达来看,这五幅图采用了三类构图法,扆壁为“中堂三联”构图,《入法界品经变图》采用了“天圆”构图,其他三组则是“地方”构图。图像内容的表现与西壁相比似乎并不统一,三类构图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虽然都具有“曼陀罗”的放射状结构,但在每一会壁画中主尊卢舍那佛图像大小不一,而这与一般壁画讲求空间对称的描绘手法完全不同。从目前建筑结构来看,大雄宝殿俯视图接近正方形,并且按照中央毗卢遮那佛为圆心可作内切圆的结构,这种方圆恰恰是《营造法式》在总例图样中所绘“圆方方圆图”(图1),其结构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世界的理解。而唐密曼陀罗同样利用方圆来表现宇宙世界的方位,这种图像在敦煌西夏壁画中仍有表现(图2)。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建筑或壁画,在中古时期创生或传播时,依照方圆来表现中国传统“天圆地方”之宇宙观恰恰是三教融合、相互调适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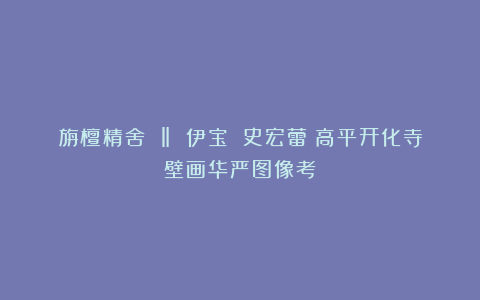 华严一脉发端于印度南部案达罗王朝,此地是雅利安人入侵后与达罗毗荼人冲突、融合之地。公元2世纪之后,由于孔雀王朝式微以及中印度之法难,大量的僧侣逃往南部,由于此地社会稳定,且受大众部教化,成为大乘佛教经典重要的集结之地,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思想皆在此出。《华严经》在早期只是短篇的故事或偈颂,经后世不断补充最终集成经典。
现存的《华严经》有三个译本,分别为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六十华严,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以及唐般若译四十华严。
《华严经》自唐代发扬光大,其中教义之根本为显一乘圆教、法界圆融、事事无碍、无尽缘起等。山西作为华严宗传播弘扬的重镇,其根脉深远,诸寺林立,北宋又是佛教发展重要的时代,位于太行八陉要地的高平,历代香火鼎盛,开化寺创立初期大愚禅师为住持,其后历代高僧云集,且路通开封,京城多有大德前来弘法。开化寺壁画丹青绝妙,毫不吝惜工本。《泽州舍利山开化寺修功德记》对殿内每幅壁画的内容逐一做了介绍,可谓珍贵。正如其中所言:“非特为美观也,是亦教化耳……且愚修此佛殿功德。”东壁之壁画从空间上作为殿内视觉的引导,着重体现华严智慧要义,彰显佛国净土圣境,使人心生憧憬,随之则绘有“弥勒”“观音”,最后及至西壁乃绘《大方便报恩经》,体现了壁画劝善教化之功能所在。大殿内壁画共有9幅,虽然东西两壁的内容不同,但画师巧妙地将“七处九会”穿插描绘于各壁之间,中央毗卢遮那佛象征宇宙的中心,而各组图像则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说法空间,其图像表义及构图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图式的完整性表达。整殿壁画虽然在碑记中已经写明东序华严,然而从图像分析来看,东壁四幅与西壁三幅的图式结构并不对称,但应属于刻意为之,这种空间结构上的安排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佛教教义。开化寺大雄宝殿三壁之上共绘了九幅佛说法的场景,这种巧合显然是通过图式结构来实现的。从东西扆壁来看,壁画空间仍旧承袭了对称样式,据此可以推测,整殿壁画皆暗含在“七处九会”当中,而东壁第二、第三、第四图式的变化是为了避免“普光法堂”的多次再现而进行的调节。
第二,榜题和时间因素。关于壁画中大量白色榜题框中缺少墨书题记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谜团。从西壁起首处《大方便报恩经》的题记来看,这些榜题文框是在壁画绘完之后所加,但为何只是西壁书写十余处而没有接续完成,其真实原因至今不得而知。笔者认为,这或许与壁画完成的时间有关,首先壁画在元祐七年(1092)开始绘作,至绍圣三年(1096)完成,前后历时四年之久,而《泽州舍利山开化寺修功德记》(下文简称《记》)于崇宁元年(1102)写成,大观庚寅年(1110)刻毕,已是壁画完成的十四年之后。《记》文中“工费数千缗、其间错综”的记载道出壁画工成之不易,“错综”二字更是生动反映出其中的艰辛坎坷。壁画从绘制完成到崔静书写《记》文时隔六年,说明期间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画匠作为流动职业者并不能随时传唤到,从绘画水准来看,画匠郭发极有可能来自东京汴梁,这意味着榜题可能是因为画匠的原因而未能完成;另一种可能是,北宋华严宗的再次复兴使得寺庙多以华严图像作为主题进行呈现,此殿壁画虽然涉及四种佛教主题内容,但最为核心的还是华严信仰。因此,画匠将“七处九会”隐含在殿内壁画之中加以巧妙展现,而若榜题之中多杂以《报恩经》或《华色比丘》等内容文字,则有遮蔽华严主题之虞。由于时间久远,虽后世寺院僧人也发现了其中玄妙,但均没有更好的注解办法,不得已只能留白。
第三,壁画作为弘扬佛教教义思想的重要手段,无论显教与密教,都强调广行方便法门,以接引教化广大佛教信徒。佛教,亦被称为“像教”,即通过直观、具象化的图像语言来表达佛教的教义思想。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过程中,佛教的造型艺术也不断地和当地的审美倾向相适应,及至中原之后亦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艺术样式。唐武宗灭佛之后,宋代的佛教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其中佛教艺术的繁荣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华严九会”作为《华严经》义脉络的概括表征,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识读性和巨大的艺术表现空间。此外,开化寺初名清凉寺,虽然未知是否关乎清凉山,但唐代五台山作为华严宗重要的传法道场仅次于终南山祖庭。虽然宋代时寺院更名“开化禅寺”,但从壁画绘制主题来判断,寺院此时应仍将“华严”作为主要信仰内容。
第四,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宇宙空间。目前,大殿中心塑有一尊毗卢遮那佛坐像,应是参考原有损毁佛像样式而重塑的。殿内毗卢遮那佛像位居中心的空间布局体现了佛教的基本宇宙观。殿内部栿、枋、柱、梁等建筑构件遍饰彩绘,并与下部壁画交相辉映,不仅营造出神圣的信仰意境,同时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出佛教独特的对于宇宙世界结构的理解和建构(图3)。在《华严经》中,“七处九会”并非依照“菩提道场”升至“逝多林”之顺序次第来表达的,而是同时化现各处进行说法,这也是《华严经》法界圆融、一多互具理念的直接体现。同时,中央毗卢遮那佛说法空间的立体再现与壁画中“九会”内容又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场景(图4)。
大雄宝殿为腰殿设置,在扆壁(北壁)两侧对称画了“中堂三联”构图。然而东西两壁所绘壁画并未遵循对称的原则进行构图。虽然在碑记中只提到东壁为华严图像,但整殿壁画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浑然一体,虽有题材之不同,然空间布局相互呼应,且壁画中所绘建筑图像亦能与寺院建筑对应,建筑与其上所绘山峦、彩画相互辉映、融为一体,体现了画匠善用空间构造关系来表现壁画主题的高超技艺。开化寺虽为唐代大愚禅师所建,但壁画至宋代方绘,碑记中山川河流、风物草木皆作描述,题记为“绘修佛殿功德”。这就意味着此殿“绘修”之前应就有塑像。虽然碑记中并没有提及塑像,但从大殿现存重塑的“一佛样式”毗卢遮那佛像推断,损毁之前可能就是毗卢遮那佛像,大殿整体空间即是为了表现华严主旨。实际上,现存的元代水陆壁画就体现出了唐密与华严图像相互融合的迹象,而这一迹象在宋代的水陆画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从正殿壁画数量来看,东壁四幅、西壁三幅、北壁东一幅、北壁西一幅,若将图像拼合,则正好有九幅图像(图5-8,中插第1、2页)。如此苦心绘制、经年而成的丹青妙笔绝却只在西壁开头处略写十余处题记便戛然而止,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常理和工程标准。碑记完成时间比壁画绘成晚了几年。如前所述,这种有反常态的处理,或许是为了营造整殿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华严义旨表达。又因为碑记是在壁画绘后数年才写成,故亦未对各幅壁画进行题记。但现在很多壁画细节的安排都暗含着华严“七处九会”的图示结构。西壁三幅图像虽都是“一佛二菩萨”的说法样式,但其中一个细节描绘得耐人寻味,即佛身背后山的透视变化,第一幅图中,佛在山脚之下,第二幅在山腰,第三幅则快要到山顶。这种位置上的变动从表面看只是装饰背景的微调,但若“七处九会”的角度来分析则似有深义。第一会寂灭道场,是指佛在成道地点的说法,也就是在人间弘法。第二会在普光法堂,意味着说法地的地位有所提升。第三会在忉利天宫,其最为主要的依据就是《华严经·升须弥山顶品》,此幅图像则正好处于山顶的位置。很显然,图像中佛背后即为须弥山,而利用佛与山的位置变化表达说法场所不断上升之过程。此外,北壁东侧描绘的弥勒图也与第五会兜率天宫相吻合。最为重要的是东壁最后一幅图像“法界人中图”描绘的正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内容。这种图像样式上的看似巧合的安排显然是画匠精心设计的结果。
综上所述,大殿壁画中,西壁第一幅为第一会寂灭道场、第三幅为第三会忉利天宫,北壁东侧第五幅为弥勒天宫,而东壁最后一幅所绘即为〈入法界品〉之内容。可见,大殿壁画整体呈现出华严思想的要义,这或许也是解释不少榜题空白的原因。
在印度佛教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对本土婆罗门教的思想和神祇系统亦多有吸收和改造。佛教的这一特征,传入中国后,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婆罗门教所创立的种姓制度成为古代印度的主要社会组织结构。虽然佛教是沙门思潮中崛起的教派,在教义上与婆罗门教存在本质不同甚至对立,但同时一些婆罗门教中的神祇被佛教接纳进来,重新改造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当然,这种“接纳”也暗含着宗教竞争的意味,例如作为婆罗门教的创世神“梵天”,在佛教中只能与帝释天相并列。在《华严经》中,大梵天则演化成为无量世界中的护法神。这种变化反映了印度大乘佛教后期与婆罗门教的融合趋势,即有宗与密教的形成体现了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的交涉状态,密教从祭祀对象、仪轨与对陀罗尼的重视三个方面吸收了婆罗门教义。这种排布在密教的图像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包括“千手千眼观音”与“十大明王”,这种多首多臂的造型即来自于印度密教,早在北魏云冈石窟就出现了摩醯首罗天和鸠摩罗天的多首多臂造型,这种样式与汉代某些神秘的民间信仰内容亦有着相似之处,后将西域传来的密教图像进行了融合与变造,尤其在云冈二期中多次出现。也可以说,这些造型是当时来自师子国(斯里兰卡)等地异域工匠将印度佛教造像风格应用于云冈的证据。从昙曜五窟开始,开凿石窟的工匠包括凉州僧人、古印度僧人、师子国工匠以及徐州僧匠,这三批工匠在雕凿石窟时虽有先后,但早期石窟的开凿可以说深受古印度、师子国工匠的影响。密教造像样式的引入体现了公元5-6世纪此类样式在当时印度地区的流行。因此,这些异域工匠在进入平城之后自然会将其最为熟悉的工艺造型运用于石窟寺的建造。及至唐代,中国佛教密宗得以创立,然之后又遭受法难,几近覆灭。之后,在水陆法会图像中融入密宗的元素,并与华严相融,成为宋元水陆法会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山西现遗存最早的水陆寺观壁画青龙寺腰殿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密“曼陀罗”样式与华严说法图中含有不少原婆罗门教的神祇,包括“五十三参”与“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十地”菩萨道次第关系的表达皆是华严的教义。同时,这种融合也是汉传佛教世俗化与融摄“外道”的例证。
佛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除了融合婆罗门教的神祇之外,也不断发展出自己的佛菩萨等圣众体系。就《华严经》中的佛身而言,有二身说与十身说,法身清净,无形无相,无自性,无实体,亦无佛身,但充满法界……就法身佛,卢舍那与毗卢遮那为同一身,这种双重身份观体现了佛教形而上学的理论观。这也是佛教发展过程中从一佛信仰走向三佛再到多佛世界的自我变革,而“法界人中图”恰恰是对《华严经》佛身观的最好图注。
开化寺的“法界人中图”虽承唐制,却在内容上亦有所创新。作为“法界人中图”之中心,须弥山的位置是其与前朝图像最为相近之处,皆在佛之胸口。开化寺之须弥山为倒三角,青绿设色上承托五层楼阁建筑,宝树香花其间,殿内皆有佛端坐,日月祥云环绕,分列山之左右。在须弥山之周围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下方是一圆形,内绘有十佛(手)摩(摸)一佛头像。从图像内容来看,开化寺较之前朝要简略很多,南北朝及唐代“人中图”在须弥山周围还会绘制诸多场景,而下方的人间及地狱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这种图像是建立在两种法相的思想基础之上。从李公麟的《华严变相图》可以看出,宋代对于“净土变”与“地狱变”有着不同的描绘。就开化寺的壁画而言,这幅图像的主要题材包括了三个部分:1.须弥山图,2.十方佛摩顶图,3.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图9)。
开化寺的须弥山图与前朝最大的区别在于殿宇结构只是纵向描绘,敦煌壁画中的这一图像往往是布满前胸,而日月一般都描绘在两肩左右,这是非常大的不同。摩顶图中间所坐为普贤菩萨,作为卢舍那佛的宣教者,普贤在《华严经》中反复出现,并单列一品,可见其地位。〈毗卢遮那佛品〉有偈颂亦曰:
对于普贤的偏重也显示出华严之特点,而此中所言“转法轮”处,按照图像排布应当是“人中图”之核心部分。在早期的表现中,此处多为水之表达。这种描绘可对应于〈毗卢遮那品〉的描述:
诸佛子!彼胜音世界中有香水海,名清净光明。其海中有大莲华,须弥山出现,名华焰普庄严幢,十宝栏楯,周匝围绕。于其山上,有一大林。
这是华严宇宙观的一种表述,对于文中香水海,实则强调一种虚幻的空间,实和虚之间是互为成就的。开化寺将这一部分描绘为“十佛摩顶”。其下,画匠对于佛身所着的覆于莲台之上的袈裟进行了浪漫式的刻画呈现,其以悠长迴转的“高古游丝描”加以刻画描绘,整体的造型宛若碧波清流,或如山峦起伏,技法高妙且兼具禅意,将“莲华藏与世界海”之意趣进行了含蓄表达。镰田茂雄认为,这代表了华严对自性的认识是超越宗教的,并且具有哲学的思考。
“十佛摩顶图”中的圆圈即是普贤愿力所在,自然宣道其中。〈卢舍那佛品〉中云:
尔时,普贤菩萨告诸菩萨言:佛子!诸世界有种种体……或日珠轮体。
这一偈中的“日珠轮体”或“真珠轮”正是普贤愿力之体现。对于华严思想而言,其华藏世界,即为清净无尘,充满光明之意。唐译本八十卷《华严经》在〈华藏品〉之后将卢舍那佛改为毗卢遮那佛的原因有二:第一,唐密系统的形成促使“一佛”信仰需要加强;第二,毗卢遮那佛实则代表了以太阳喻佛身之意,其梵语为“Vairocana”,意为“光明普耀”,卢舍那或毗卢遮那只是音译之不同。
武周时期,八十华严将卢舍那翻译为“毗卢遮那”也是对光明信仰的进一步强化,唐玄宗时期,在善无畏与金刚智的推动下,将印度密教系统引入,构建出以日光信仰为特征的密教宇宙观。佛即皇帝在北魏雕凿“昙曜五窟”时就已成为佛教入世的例证,其五佛的背光当时主要是火焰纹,其后武则天在上位时发展华严同样有此意味,直至玄宗时方成。虽经灭法而在海内消失,但毗卢遮那佛之法身光明成为佛教主体象征,在宋代的佛教复兴过程中迅速崛起,并在各宗发扬光大。
“法界人中图”作为东壁起首第一幅壁画即代表了对华严世界的整体诠释,同时也是佛教宇宙观之外化表现。
东壁南侧“兜率天宫会”表现了释迦牟尼佛在兜率院内说法的场景,佛于莲台之上结跏趺坐,周围围绕诸菩萨众。根据李静杰的研究,这种图像为《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这种图像是综合体现华严、法华、涅槃等经思想之传法图。日本学者吉村怜结合敦煌425窟与云冈18洞及库尔勒壁画,对这类图像提出新的命名“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学界亦称“卢舍那法界人中图”)。目前国内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青州石刻等留存的“卢舍那人中图”有20余幅(图10),整体造型样式有立式与坐姿两类,其中最早的可追溯至北朝时期。新疆克孜尔阿艾石窟之立式“卢舍那法界人中像”为北朝代表,藏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馆。此外,山东临朐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藏有北朝彩绘贴金“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图11),以袈裟状框格样式描绘了31幅图像,内容极其丰富;上海震旦博物馆亦藏有“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图12),而其造型与弗利尔美术馆隋代“人中像”之直挺造型不同,前者身体略带扭动,腿部亦有前后交错(图13)。新疆克孜尔中唐阿艾石窟也属于这种带有古印度风格的造型(图14),并有卢舍那佛相关的题记;在克孜尔17窟中的“卢舍那人中像”更是体态变化丰富,古印度造像风格明显。殷光明对敦煌壁画中的“法界人中图”进行了整理,从北魏至晚唐有14幅之多,其中绘于“报恩经变”中者有5幅。高平开化寺东壁南侧“法界人中图”是坐像样式,其绘画风格迥异于敦煌壁画,是宋代华严法界图像绘画的代表之作。
根据殷光明的统计研究,从结构布局来看,敦煌壁画中坐式“法界人中图”以332窟、31窟、154窟、156窟、12窟最具代表性,也与开化寺跏趺坐像最为接近。这些壁画虽然样式各有不同,表现内容却十分相似,整体内容为“三界六道”,胸前为须弥山,腹部中心部分绘三人、水波等内容。这也是唐代之前“卢舍那法界人中图”的基本样式。此类图像无论立像或坐像,三界是其核心内容,根据图像由上至下,图像表达了“天地冥”三界人物神祇,尤其是立像,常按照等高线的形式将躯干进行划分,这在弗利尔美术馆隋代石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周身图像可达九层,须弥山仅在第三层,以下之人物、畜生、饿鬼、阿修罗以及地狱成为描绘的主要对象,这种影响至唐代坐像时由于躯干空间的限制,将佛衣下摆垂于莲台,再描绘图像于其上,用以描绘下界的内容。李静杰将此类图像总结为“须弥山”中心式构图,这种图像的直接来源是华严系统,并兴盛于南北朝之际,这一时期的“天龙八部”也是此类图像重要的符号特征。如此系统的图像表达也反映了佛教思想体系在隋唐时期的进一步成熟,尤其是对于空间的想象趋于一种“盖天说”的语境。这种整体图式的结构安排在后期的“水陆画”中可窥得其迹。
因此,“曼陀罗”的构图是唐宋时期佛教图像的典型类别。这种中心放射状的结构是以佛为中心进行扩散的,在图像上仍然是二元维度。“卢舍那法界人中图”,于佛身之中绘入法界诸相,体现了华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宇宙观。
自澄观将五台山确立为文殊法地之后,山西即奠定了其在华严宗中的地位,并与华严宗滥觞之地西安成为北方华严之根本道场。晚唐武宗灭佛,华严宗随之一蹶不振。然而,山西地理复杂且佛寺林立,辽代契丹人在引入佛教之后极为推崇华严,因此大兴佛寺,雁门关外的大同华严寺与应县释迦塔皆在这一时期兴建,并与五台山大华严寺(现显通寺)成为山西弘扬华严的重镇。
在此背景下,宋代华严图像得以在开化寺再现其光彩,实属难得。开化寺壁画作为六十《华严·卢舍那佛品》的图像表达,其图像的中心从北朝的风轮转变为日珠轮体,而“法界人中图”的表现内容则是从“三界六道”转为对于〈入法界品〉的阐释,即着重体现“四种法界”圆融无碍的境界。这种图像描绘的变化也折射出当时华严学的新发展,而“善财童子”“文殊”与“普贤”也成为华严体系的代表。
此外,开化寺壁画中的“十佛摩顶”(象征普贤十大愿)与“五十三参”代表的是华严宗的修行法门,而华严净土最为重要的标志则是莲华藏世界海,而图像在表达这一要旨时需要注意体态结构上契合。立式卢舍那佛像在分层表达时有着体量空间上的优势,而坐式则呈现出上小下大三角形的构成样式。这使得人物整体结构更加稳定,开化寺壁画卢舍那佛甚至使用佛衣下摆来表现水波形状,这也符合了宋画追求意境的表达。
此外,随着历代华严学人对于华严净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智俨将莲华世界海与西方弥陀净土联系了起来,而法藏又将之与弥勒净土相关联,使得华严净土与弥陀、弥勒信仰实现了内在贯通。这在开化寺壁画中亦有所体现,东壁三幅图中体现的是弥陀净土,北壁东侧的“弥勒净土变”则表现的是弥勒净土。
可见,宋代的华严学人对于华严世界的阐释已然融通,同时对于莲华藏世界海的中心表达更加趋于“五十三参”的描绘,这是“法界人中图”唐宋时期杂糅式发展后出现的特征。
“法界人中图”中的“五十三参”描绘了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点化进行的一次漫长的求智之旅。与此相应的〈入法界品〉可谓是全经的精髓,也是晋译六十卷中的最后一品。从翻译版本的时间顺序来看,般若本的增译除了新贡文本的原因外,主要是其“依人入证”的理论构建,即通过善财等诸童子求法参悟过程来启示后学,这也是佛教义学重要的历程。
这也是此图唐代前后结构变化的原因。在河南高寒寺及敦煌壁画中,这种图像呈现出须弥山或风轮为中心的结构,整体或五层或七层,内容多数描绘了“三界六道”。开化寺与之前虽然有着一定的相似,但显然弱化了“三界”的描绘,而是上升到对于“法界缘起”思想的诠释和表现。
高平开化寺壁画图像长期以来解读为华严、报恩、弥勒、观音各绘一壁,但空白的榜题也留下诸多疑团,通过艺术考古与文献、图像等“三重证法”进行考证,厘清了“七处九会”图在开化寺三壁上进行整体呈现,且与中央毗卢遮那佛彩塑构成唐密“曼陀罗”宇宙结构模型,展现了北宋佛教变革下新的图式表达。“法界人中图”的再读,展现了北宋华严思想的转向、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圆融互浸。
《华严经》是大乘佛教中影响巨大的经典。华严学倡导之法界无尽缘起、万法圆融互具的教理思想,以及周密系统的全新宇宙观,为华严图像的表达提供了无限的艺术空间。此外,后世华严学人又将华严之莲华藏世界海与净土、法华等诸学相关联,使之相互融通、交相辉映,故而也大大的丰富了华严体系的思想内涵。因此,壁画图像开始突破北朝至唐代单纯的“曼陀罗”样式的呈现,例如开化寺壁画在空间分割上就打破了东西两壁对称的美学范式,巧妙地将全殿壁画进行整体设计,壁画内容更富于灵动变化,这是画匠郭发最为巧思之所在。
因此,无论是“大方便报恩经变”或“弥勒上生经变”都是为了更好地衬托华严世界的庄严。对于“法界人中图”,从海内外现存相关图像来看,此图在隋代达到鼎盛,及至唐代并不多见,开化寺将其作为〈入法界品〉之总结,恰恰代表了画匠或者拥有唐代的粉本,或者说明其能通晓华严义旨。而开化寺壁画中舒朗流畅的法身像构图与创新的图像布局也代表了北宋华严学内在的转向,即不再着重突出关于三千大千世界的抽象表述,而是转而聚焦于“五十三参”“十佛摩顶”等具有教理实践意义的阐释。
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灭佛”浩劫,并未能阻止北宋佛教的再次复兴。此时,佛教的世俗化方兴未艾,俨然成为一种趋势,佛教僧人与士大夫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诗、书、画等亦有受到佛教义理的浸润,而壁画作为佛教神圣庄严的教化区域,其中的意义抉择、思想诠释和艺术表达,可以说是当时佛教之思想特征及现实存在状态的直观体现。总之,开化寺这一殿壁画不仅体现了北宋从绢本到壁上的佛教图像的基本样式,更于细微之处彰显了华严妙旨。
华严一脉发端于印度南部案达罗王朝,此地是雅利安人入侵后与达罗毗荼人冲突、融合之地。公元2世纪之后,由于孔雀王朝式微以及中印度之法难,大量的僧侣逃往南部,由于此地社会稳定,且受大众部教化,成为大乘佛教经典重要的集结之地,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思想皆在此出。《华严经》在早期只是短篇的故事或偈颂,经后世不断补充最终集成经典。
现存的《华严经》有三个译本,分别为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六十华严,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以及唐般若译四十华严。
《华严经》自唐代发扬光大,其中教义之根本为显一乘圆教、法界圆融、事事无碍、无尽缘起等。山西作为华严宗传播弘扬的重镇,其根脉深远,诸寺林立,北宋又是佛教发展重要的时代,位于太行八陉要地的高平,历代香火鼎盛,开化寺创立初期大愚禅师为住持,其后历代高僧云集,且路通开封,京城多有大德前来弘法。开化寺壁画丹青绝妙,毫不吝惜工本。《泽州舍利山开化寺修功德记》对殿内每幅壁画的内容逐一做了介绍,可谓珍贵。正如其中所言:“非特为美观也,是亦教化耳……且愚修此佛殿功德。”东壁之壁画从空间上作为殿内视觉的引导,着重体现华严智慧要义,彰显佛国净土圣境,使人心生憧憬,随之则绘有“弥勒”“观音”,最后及至西壁乃绘《大方便报恩经》,体现了壁画劝善教化之功能所在。大殿内壁画共有9幅,虽然东西两壁的内容不同,但画师巧妙地将“七处九会”穿插描绘于各壁之间,中央毗卢遮那佛象征宇宙的中心,而各组图像则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说法空间,其图像表义及构图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图式的完整性表达。整殿壁画虽然在碑记中已经写明东序华严,然而从图像分析来看,东壁四幅与西壁三幅的图式结构并不对称,但应属于刻意为之,这种空间结构上的安排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佛教教义。开化寺大雄宝殿三壁之上共绘了九幅佛说法的场景,这种巧合显然是通过图式结构来实现的。从东西扆壁来看,壁画空间仍旧承袭了对称样式,据此可以推测,整殿壁画皆暗含在“七处九会”当中,而东壁第二、第三、第四图式的变化是为了避免“普光法堂”的多次再现而进行的调节。
第二,榜题和时间因素。关于壁画中大量白色榜题框中缺少墨书题记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谜团。从西壁起首处《大方便报恩经》的题记来看,这些榜题文框是在壁画绘完之后所加,但为何只是西壁书写十余处而没有接续完成,其真实原因至今不得而知。笔者认为,这或许与壁画完成的时间有关,首先壁画在元祐七年(1092)开始绘作,至绍圣三年(1096)完成,前后历时四年之久,而《泽州舍利山开化寺修功德记》(下文简称《记》)于崇宁元年(1102)写成,大观庚寅年(1110)刻毕,已是壁画完成的十四年之后。《记》文中“工费数千缗、其间错综”的记载道出壁画工成之不易,“错综”二字更是生动反映出其中的艰辛坎坷。壁画从绘制完成到崔静书写《记》文时隔六年,说明期间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画匠作为流动职业者并不能随时传唤到,从绘画水准来看,画匠郭发极有可能来自东京汴梁,这意味着榜题可能是因为画匠的原因而未能完成;另一种可能是,北宋华严宗的再次复兴使得寺庙多以华严图像作为主题进行呈现,此殿壁画虽然涉及四种佛教主题内容,但最为核心的还是华严信仰。因此,画匠将“七处九会”隐含在殿内壁画之中加以巧妙展现,而若榜题之中多杂以《报恩经》或《华色比丘》等内容文字,则有遮蔽华严主题之虞。由于时间久远,虽后世寺院僧人也发现了其中玄妙,但均没有更好的注解办法,不得已只能留白。
第三,壁画作为弘扬佛教教义思想的重要手段,无论显教与密教,都强调广行方便法门,以接引教化广大佛教信徒。佛教,亦被称为“像教”,即通过直观、具象化的图像语言来表达佛教的教义思想。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过程中,佛教的造型艺术也不断地和当地的审美倾向相适应,及至中原之后亦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艺术样式。唐武宗灭佛之后,宋代的佛教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其中佛教艺术的繁荣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华严九会”作为《华严经》义脉络的概括表征,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识读性和巨大的艺术表现空间。此外,开化寺初名清凉寺,虽然未知是否关乎清凉山,但唐代五台山作为华严宗重要的传法道场仅次于终南山祖庭。虽然宋代时寺院更名“开化禅寺”,但从壁画绘制主题来判断,寺院此时应仍将“华严”作为主要信仰内容。
第四,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宇宙空间。目前,大殿中心塑有一尊毗卢遮那佛坐像,应是参考原有损毁佛像样式而重塑的。殿内毗卢遮那佛像位居中心的空间布局体现了佛教的基本宇宙观。殿内部栿、枋、柱、梁等建筑构件遍饰彩绘,并与下部壁画交相辉映,不仅营造出神圣的信仰意境,同时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出佛教独特的对于宇宙世界结构的理解和建构(图3)。在《华严经》中,“七处九会”并非依照“菩提道场”升至“逝多林”之顺序次第来表达的,而是同时化现各处进行说法,这也是《华严经》法界圆融、一多互具理念的直接体现。同时,中央毗卢遮那佛说法空间的立体再现与壁画中“九会”内容又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场景(图4)。
大雄宝殿为腰殿设置,在扆壁(北壁)两侧对称画了“中堂三联”构图。然而东西两壁所绘壁画并未遵循对称的原则进行构图。虽然在碑记中只提到东壁为华严图像,但整殿壁画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浑然一体,虽有题材之不同,然空间布局相互呼应,且壁画中所绘建筑图像亦能与寺院建筑对应,建筑与其上所绘山峦、彩画相互辉映、融为一体,体现了画匠善用空间构造关系来表现壁画主题的高超技艺。开化寺虽为唐代大愚禅师所建,但壁画至宋代方绘,碑记中山川河流、风物草木皆作描述,题记为“绘修佛殿功德”。这就意味着此殿“绘修”之前应就有塑像。虽然碑记中并没有提及塑像,但从大殿现存重塑的“一佛样式”毗卢遮那佛像推断,损毁之前可能就是毗卢遮那佛像,大殿整体空间即是为了表现华严主旨。实际上,现存的元代水陆壁画就体现出了唐密与华严图像相互融合的迹象,而这一迹象在宋代的水陆画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从正殿壁画数量来看,东壁四幅、西壁三幅、北壁东一幅、北壁西一幅,若将图像拼合,则正好有九幅图像(图5-8,中插第1、2页)。如此苦心绘制、经年而成的丹青妙笔绝却只在西壁开头处略写十余处题记便戛然而止,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常理和工程标准。碑记完成时间比壁画绘成晚了几年。如前所述,这种有反常态的处理,或许是为了营造整殿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的华严义旨表达。又因为碑记是在壁画绘后数年才写成,故亦未对各幅壁画进行题记。但现在很多壁画细节的安排都暗含着华严“七处九会”的图示结构。西壁三幅图像虽都是“一佛二菩萨”的说法样式,但其中一个细节描绘得耐人寻味,即佛身背后山的透视变化,第一幅图中,佛在山脚之下,第二幅在山腰,第三幅则快要到山顶。这种位置上的变动从表面看只是装饰背景的微调,但若“七处九会”的角度来分析则似有深义。第一会寂灭道场,是指佛在成道地点的说法,也就是在人间弘法。第二会在普光法堂,意味着说法地的地位有所提升。第三会在忉利天宫,其最为主要的依据就是《华严经·升须弥山顶品》,此幅图像则正好处于山顶的位置。很显然,图像中佛背后即为须弥山,而利用佛与山的位置变化表达说法场所不断上升之过程。此外,北壁东侧描绘的弥勒图也与第五会兜率天宫相吻合。最为重要的是东壁最后一幅图像“法界人中图”描绘的正是《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内容。这种图像样式上的看似巧合的安排显然是画匠精心设计的结果。
综上所述,大殿壁画中,西壁第一幅为第一会寂灭道场、第三幅为第三会忉利天宫,北壁东侧第五幅为弥勒天宫,而东壁最后一幅所绘即为〈入法界品〉之内容。可见,大殿壁画整体呈现出华严思想的要义,这或许也是解释不少榜题空白的原因。
在印度佛教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对本土婆罗门教的思想和神祇系统亦多有吸收和改造。佛教的这一特征,传入中国后,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婆罗门教所创立的种姓制度成为古代印度的主要社会组织结构。虽然佛教是沙门思潮中崛起的教派,在教义上与婆罗门教存在本质不同甚至对立,但同时一些婆罗门教中的神祇被佛教接纳进来,重新改造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当然,这种“接纳”也暗含着宗教竞争的意味,例如作为婆罗门教的创世神“梵天”,在佛教中只能与帝释天相并列。在《华严经》中,大梵天则演化成为无量世界中的护法神。这种变化反映了印度大乘佛教后期与婆罗门教的融合趋势,即有宗与密教的形成体现了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的交涉状态,密教从祭祀对象、仪轨与对陀罗尼的重视三个方面吸收了婆罗门教义。这种排布在密教的图像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包括“千手千眼观音”与“十大明王”,这种多首多臂的造型即来自于印度密教,早在北魏云冈石窟就出现了摩醯首罗天和鸠摩罗天的多首多臂造型,这种样式与汉代某些神秘的民间信仰内容亦有着相似之处,后将西域传来的密教图像进行了融合与变造,尤其在云冈二期中多次出现。也可以说,这些造型是当时来自师子国(斯里兰卡)等地异域工匠将印度佛教造像风格应用于云冈的证据。从昙曜五窟开始,开凿石窟的工匠包括凉州僧人、古印度僧人、师子国工匠以及徐州僧匠,这三批工匠在雕凿石窟时虽有先后,但早期石窟的开凿可以说深受古印度、师子国工匠的影响。密教造像样式的引入体现了公元5-6世纪此类样式在当时印度地区的流行。因此,这些异域工匠在进入平城之后自然会将其最为熟悉的工艺造型运用于石窟寺的建造。及至唐代,中国佛教密宗得以创立,然之后又遭受法难,几近覆灭。之后,在水陆法会图像中融入密宗的元素,并与华严相融,成为宋元水陆法会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山西现遗存最早的水陆寺观壁画青龙寺腰殿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唐密“曼陀罗”样式与华严说法图中含有不少原婆罗门教的神祇,包括“五十三参”与“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十地”菩萨道次第关系的表达皆是华严的教义。同时,这种融合也是汉传佛教世俗化与融摄“外道”的例证。
佛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除了融合婆罗门教的神祇之外,也不断发展出自己的佛菩萨等圣众体系。就《华严经》中的佛身而言,有二身说与十身说,法身清净,无形无相,无自性,无实体,亦无佛身,但充满法界……就法身佛,卢舍那与毗卢遮那为同一身,这种双重身份观体现了佛教形而上学的理论观。这也是佛教发展过程中从一佛信仰走向三佛再到多佛世界的自我变革,而“法界人中图”恰恰是对《华严经》佛身观的最好图注。
开化寺的“法界人中图”虽承唐制,却在内容上亦有所创新。作为“法界人中图”之中心,须弥山的位置是其与前朝图像最为相近之处,皆在佛之胸口。开化寺之须弥山为倒三角,青绿设色上承托五层楼阁建筑,宝树香花其间,殿内皆有佛端坐,日月祥云环绕,分列山之左右。在须弥山之周围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下方是一圆形,内绘有十佛(手)摩(摸)一佛头像。从图像内容来看,开化寺较之前朝要简略很多,南北朝及唐代“人中图”在须弥山周围还会绘制诸多场景,而下方的人间及地狱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这种图像是建立在两种法相的思想基础之上。从李公麟的《华严变相图》可以看出,宋代对于“净土变”与“地狱变”有着不同的描绘。就开化寺的壁画而言,这幅图像的主要题材包括了三个部分:1.须弥山图,2.十方佛摩顶图,3.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图9)。
开化寺的须弥山图与前朝最大的区别在于殿宇结构只是纵向描绘,敦煌壁画中的这一图像往往是布满前胸,而日月一般都描绘在两肩左右,这是非常大的不同。摩顶图中间所坐为普贤菩萨,作为卢舍那佛的宣教者,普贤在《华严经》中反复出现,并单列一品,可见其地位。〈毗卢遮那佛品〉有偈颂亦曰:
对于普贤的偏重也显示出华严之特点,而此中所言“转法轮”处,按照图像排布应当是“人中图”之核心部分。在早期的表现中,此处多为水之表达。这种描绘可对应于〈毗卢遮那品〉的描述:
诸佛子!彼胜音世界中有香水海,名清净光明。其海中有大莲华,须弥山出现,名华焰普庄严幢,十宝栏楯,周匝围绕。于其山上,有一大林。
这是华严宇宙观的一种表述,对于文中香水海,实则强调一种虚幻的空间,实和虚之间是互为成就的。开化寺将这一部分描绘为“十佛摩顶”。其下,画匠对于佛身所着的覆于莲台之上的袈裟进行了浪漫式的刻画呈现,其以悠长迴转的“高古游丝描”加以刻画描绘,整体的造型宛若碧波清流,或如山峦起伏,技法高妙且兼具禅意,将“莲华藏与世界海”之意趣进行了含蓄表达。镰田茂雄认为,这代表了华严对自性的认识是超越宗教的,并且具有哲学的思考。
“十佛摩顶图”中的圆圈即是普贤愿力所在,自然宣道其中。〈卢舍那佛品〉中云:
尔时,普贤菩萨告诸菩萨言:佛子!诸世界有种种体……或日珠轮体。
这一偈中的“日珠轮体”或“真珠轮”正是普贤愿力之体现。对于华严思想而言,其华藏世界,即为清净无尘,充满光明之意。唐译本八十卷《华严经》在〈华藏品〉之后将卢舍那佛改为毗卢遮那佛的原因有二:第一,唐密系统的形成促使“一佛”信仰需要加强;第二,毗卢遮那佛实则代表了以太阳喻佛身之意,其梵语为“Vairocana”,意为“光明普耀”,卢舍那或毗卢遮那只是音译之不同。
武周时期,八十华严将卢舍那翻译为“毗卢遮那”也是对光明信仰的进一步强化,唐玄宗时期,在善无畏与金刚智的推动下,将印度密教系统引入,构建出以日光信仰为特征的密教宇宙观。佛即皇帝在北魏雕凿“昙曜五窟”时就已成为佛教入世的例证,其五佛的背光当时主要是火焰纹,其后武则天在上位时发展华严同样有此意味,直至玄宗时方成。虽经灭法而在海内消失,但毗卢遮那佛之法身光明成为佛教主体象征,在宋代的佛教复兴过程中迅速崛起,并在各宗发扬光大。
“法界人中图”作为东壁起首第一幅壁画即代表了对华严世界的整体诠释,同时也是佛教宇宙观之外化表现。
东壁南侧“兜率天宫会”表现了释迦牟尼佛在兜率院内说法的场景,佛于莲台之上结跏趺坐,周围围绕诸菩萨众。根据李静杰的研究,这种图像为《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这种图像是综合体现华严、法华、涅槃等经思想之传法图。日本学者吉村怜结合敦煌425窟与云冈18洞及库尔勒壁画,对这类图像提出新的命名“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学界亦称“卢舍那法界人中图”)。目前国内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青州石刻等留存的“卢舍那人中图”有20余幅(图10),整体造型样式有立式与坐姿两类,其中最早的可追溯至北朝时期。新疆克孜尔阿艾石窟之立式“卢舍那法界人中像”为北朝代表,藏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馆。此外,山东临朐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藏有北朝彩绘贴金“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图11),以袈裟状框格样式描绘了31幅图像,内容极其丰富;上海震旦博物馆亦藏有“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图12),而其造型与弗利尔美术馆隋代“人中像”之直挺造型不同,前者身体略带扭动,腿部亦有前后交错(图13)。新疆克孜尔中唐阿艾石窟也属于这种带有古印度风格的造型(图14),并有卢舍那佛相关的题记;在克孜尔17窟中的“卢舍那人中像”更是体态变化丰富,古印度造像风格明显。殷光明对敦煌壁画中的“法界人中图”进行了整理,从北魏至晚唐有14幅之多,其中绘于“报恩经变”中者有5幅。高平开化寺东壁南侧“法界人中图”是坐像样式,其绘画风格迥异于敦煌壁画,是宋代华严法界图像绘画的代表之作。
根据殷光明的统计研究,从结构布局来看,敦煌壁画中坐式“法界人中图”以332窟、31窟、154窟、156窟、12窟最具代表性,也与开化寺跏趺坐像最为接近。这些壁画虽然样式各有不同,表现内容却十分相似,整体内容为“三界六道”,胸前为须弥山,腹部中心部分绘三人、水波等内容。这也是唐代之前“卢舍那法界人中图”的基本样式。此类图像无论立像或坐像,三界是其核心内容,根据图像由上至下,图像表达了“天地冥”三界人物神祇,尤其是立像,常按照等高线的形式将躯干进行划分,这在弗利尔美术馆隋代石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周身图像可达九层,须弥山仅在第三层,以下之人物、畜生、饿鬼、阿修罗以及地狱成为描绘的主要对象,这种影响至唐代坐像时由于躯干空间的限制,将佛衣下摆垂于莲台,再描绘图像于其上,用以描绘下界的内容。李静杰将此类图像总结为“须弥山”中心式构图,这种图像的直接来源是华严系统,并兴盛于南北朝之际,这一时期的“天龙八部”也是此类图像重要的符号特征。如此系统的图像表达也反映了佛教思想体系在隋唐时期的进一步成熟,尤其是对于空间的想象趋于一种“盖天说”的语境。这种整体图式的结构安排在后期的“水陆画”中可窥得其迹。
因此,“曼陀罗”的构图是唐宋时期佛教图像的典型类别。这种中心放射状的结构是以佛为中心进行扩散的,在图像上仍然是二元维度。“卢舍那法界人中图”,于佛身之中绘入法界诸相,体现了华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宇宙观。
自澄观将五台山确立为文殊法地之后,山西即奠定了其在华严宗中的地位,并与华严宗滥觞之地西安成为北方华严之根本道场。晚唐武宗灭佛,华严宗随之一蹶不振。然而,山西地理复杂且佛寺林立,辽代契丹人在引入佛教之后极为推崇华严,因此大兴佛寺,雁门关外的大同华严寺与应县释迦塔皆在这一时期兴建,并与五台山大华严寺(现显通寺)成为山西弘扬华严的重镇。
在此背景下,宋代华严图像得以在开化寺再现其光彩,实属难得。开化寺壁画作为六十《华严·卢舍那佛品》的图像表达,其图像的中心从北朝的风轮转变为日珠轮体,而“法界人中图”的表现内容则是从“三界六道”转为对于〈入法界品〉的阐释,即着重体现“四种法界”圆融无碍的境界。这种图像描绘的变化也折射出当时华严学的新发展,而“善财童子”“文殊”与“普贤”也成为华严体系的代表。
此外,开化寺壁画中的“十佛摩顶”(象征普贤十大愿)与“五十三参”代表的是华严宗的修行法门,而华严净土最为重要的标志则是莲华藏世界海,而图像在表达这一要旨时需要注意体态结构上契合。立式卢舍那佛像在分层表达时有着体量空间上的优势,而坐式则呈现出上小下大三角形的构成样式。这使得人物整体结构更加稳定,开化寺壁画卢舍那佛甚至使用佛衣下摆来表现水波形状,这也符合了宋画追求意境的表达。
此外,随着历代华严学人对于华严净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智俨将莲华世界海与西方弥陀净土联系了起来,而法藏又将之与弥勒净土相关联,使得华严净土与弥陀、弥勒信仰实现了内在贯通。这在开化寺壁画中亦有所体现,东壁三幅图中体现的是弥陀净土,北壁东侧的“弥勒净土变”则表现的是弥勒净土。
可见,宋代的华严学人对于华严世界的阐释已然融通,同时对于莲华藏世界海的中心表达更加趋于“五十三参”的描绘,这是“法界人中图”唐宋时期杂糅式发展后出现的特征。
“法界人中图”中的“五十三参”描绘了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点化进行的一次漫长的求智之旅。与此相应的〈入法界品〉可谓是全经的精髓,也是晋译六十卷中的最后一品。从翻译版本的时间顺序来看,般若本的增译除了新贡文本的原因外,主要是其“依人入证”的理论构建,即通过善财等诸童子求法参悟过程来启示后学,这也是佛教义学重要的历程。
这也是此图唐代前后结构变化的原因。在河南高寒寺及敦煌壁画中,这种图像呈现出须弥山或风轮为中心的结构,整体或五层或七层,内容多数描绘了“三界六道”。开化寺与之前虽然有着一定的相似,但显然弱化了“三界”的描绘,而是上升到对于“法界缘起”思想的诠释和表现。
高平开化寺壁画图像长期以来解读为华严、报恩、弥勒、观音各绘一壁,但空白的榜题也留下诸多疑团,通过艺术考古与文献、图像等“三重证法”进行考证,厘清了“七处九会”图在开化寺三壁上进行整体呈现,且与中央毗卢遮那佛彩塑构成唐密“曼陀罗”宇宙结构模型,展现了北宋佛教变革下新的图式表达。“法界人中图”的再读,展现了北宋华严思想的转向、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圆融互浸。
《华严经》是大乘佛教中影响巨大的经典。华严学倡导之法界无尽缘起、万法圆融互具的教理思想,以及周密系统的全新宇宙观,为华严图像的表达提供了无限的艺术空间。此外,后世华严学人又将华严之莲华藏世界海与净土、法华等诸学相关联,使之相互融通、交相辉映,故而也大大的丰富了华严体系的思想内涵。因此,壁画图像开始突破北朝至唐代单纯的“曼陀罗”样式的呈现,例如开化寺壁画在空间分割上就打破了东西两壁对称的美学范式,巧妙地将全殿壁画进行整体设计,壁画内容更富于灵动变化,这是画匠郭发最为巧思之所在。
因此,无论是“大方便报恩经变”或“弥勒上生经变”都是为了更好地衬托华严世界的庄严。对于“法界人中图”,从海内外现存相关图像来看,此图在隋代达到鼎盛,及至唐代并不多见,开化寺将其作为〈入法界品〉之总结,恰恰代表了画匠或者拥有唐代的粉本,或者说明其能通晓华严义旨。而开化寺壁画中舒朗流畅的法身像构图与创新的图像布局也代表了北宋华严学内在的转向,即不再着重突出关于三千大千世界的抽象表述,而是转而聚焦于“五十三参”“十佛摩顶”等具有教理实践意义的阐释。
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灭佛”浩劫,并未能阻止北宋佛教的再次复兴。此时,佛教的世俗化方兴未艾,俨然成为一种趋势,佛教僧人与士大夫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诗、书、画等亦有受到佛教义理的浸润,而壁画作为佛教神圣庄严的教化区域,其中的意义抉择、思想诠释和艺术表达,可以说是当时佛教之思想特征及现实存在状态的直观体现。总之,开化寺这一殿壁画不仅体现了北宋从绢本到壁上的佛教图像的基本样式,更于细微之处彰显了华严妙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