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6 06:39
1951年3月26日,四川荣县杨家场的操场临时搭起木台,冻雨刚停,泥地上满是脚印。数千名群众围着看一名犯人——黄茂才,三十五岁,身着灰色囚服,双手反绑。检察官宣布处决时间就在午后,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就在铁链即将扣上时,黄茂才抬头喊了一句:“请求向人民政府报告一件渣滓洞的机密!”四周哗然,行刑暂缓,一段被尘封的往事才由此翻开。
倒回到1945年初夏,自贡盐场上空弥漫着咸涩的潮气。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在当地强行征兵,穷苦人家怕极了当兵送命。黄茂才的母亲只好去地主刘重威家求情。刘重威正是二处副处长,缺个文书,见黄茂才识字,一纸收条便把人带走。年轻人当时只想混口饭吃,哪里料得到自己将被推入特务系统。
进入“保密局”后,训练雷厉风行:擅长写报告、会用摩斯电码、熟练拆装手枪,他样样拿得起。年底,组织把他派到重庆歌乐山渣滓洞,负责犯人登记和看守。黄茂才穿着崭新的军靴踏进囚笼,还带着“国家安全”的幻觉。可第一天夜班,他就看到一个瘦小党员被吊在杉木梁上,皮鞭抽下去血点飞溅,犯人却咬紧牙关不吭一声。那股子不屈劲头,让站在一旁的菜鸟看守心里一沉。
几个月后,监号里来了一位气质截然不同的女犯——曾紫霞,旧四川财政厅科长的女儿。入档时,她平静报出姓名、出生地、党组织关系,声音不急不缓。黄茂才被那双微微上挑的眼睛盯住,不知怎的,竟有些慌。夜里巡房,他经常看见曾紫霞借着昏黄灯光织毛线。一次他忍不住问:“这种时候还织?”曾紫霞淡淡回了四个字:“给前线用。”这句话像一粒细沙,悄悄嵌进他心里。
次日清晨,两人在铁门边短暂碰面。曾紫霞轻声问:“黄少尉,你真相信自己干的是正义吗?”没人回答。黄茂才回到岗亭,握枪的手出汗。他开始偷读押解单上被捕人员的材料,也偷偷记下渣滓洞里押着的地下党名单。越看越疑惑:这么多知识分子、学生、老工人缘何全成“暴徒”?夜里他翻来覆去,耳边回响的都是“正义”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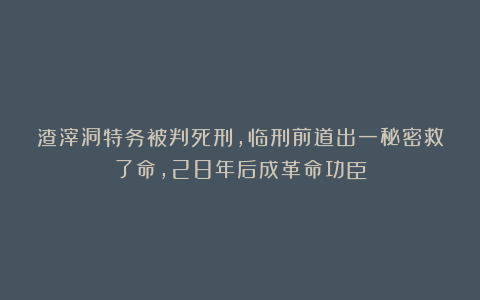
1948年底,重庆战况吃紧。狱方开始频繁提审,甚至制造“集体越狱”借口大开杀戒。黄茂才终于下决心悄悄帮助曾紫霞。他先试水,把几张写有“家中一切安好”的纸条夹进饭桶底部;随后发展到把编号、调防、暗号等信息藏进筷子缝隙,送到女牢房。每次递交情报,他都冒着极高风险,一旦被发现,枪毙毫不含糊。可奇怪的是,那种恐惧被另一股力量压住——他想让自己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
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前夜,黄茂才提前把部分看守调离岗位,掩护了少数革命者逃生。但大势已去,他自己没能走掉。11月30日重庆解放,黄茂才换上平民衣,却被群众指认抓捕。之后的审讯相当严格,他旧档案上写满“保密局”“刑讯”,罪证确凿。可他帮助革命的线索没几个人知晓,口头陈述一时间难以取信,1953年2月终被判死刑。
案子本该划上句号,可行刑队往操场押人时,他提出要见曾紫霞。负责警卫的干部起初犹豫,但考虑到情况特殊,联系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曾紫霞。她立即赶来,向办案组提供了多份当年渣滓洞的暗号本、信件残片,上面都留有黄茂才的字迹。经多方核实,这些情报帮助地下党躲过两次搜捕,还救出被误抓的交通员。材料呈到省军管会,判决被叫停,死刑改为无期,随后改判十五年。
入狱后,黄茂才主动申请扫盲班,从新华日报到马克思选集,他一字不落地啃。白天劳动砸石头,晚上就着煤油灯抄写《为人民服务》。1964年减刑释放,他回到老家种地,日子清苦,却始终与当地党支部保持联系,逢人便劝“有错就认,有路就走正道”。村里组建民兵,他捐出仅有的猎枪;修公路,他带头挖土石。
1981年夏,重庆烈士陵园寄来一份档案复核函。信封有些旧,里面夹着当年渣滓洞逃脱者联名的证明和组织考察结论:黄茂才在渣滓洞期间多次传递情报、协助掩护同志,行为属重大贡献。翌年春,他被授予“革命工作纪念章”,名字正式刻进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旁的铜板。颁奖那天雨后放晴,他站在人群里,神情平静,轻声说了一句:“我只是补交了欠下的债。”
黄茂才的经历诠释了何谓“人到绝境还可回头”。生来贫苦、误入歧途、见义勇为、几度死里逃生…这一连串节点并非戏剧化巧合,而是特殊时代下个体与信仰碰撞出的结果。行刑台前勇敢开口,是对过去的切割,也是对未来的承担。有人常问,他是否后悔早年所为?他回答:“后悔,但不逃避。”短短八字,道出一个动荡年代里最朴素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