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天京城下,爆炸声中,墙体倾塌,尘土飞扬,湘军如潮水般涌入这座沉寂十年的“天国之城”。
曾国荃坐在战马上,汗水浸湿衣襟,心中却只有两个字,胜利!
可就在他满心欢喜、走进太平天国的圣库那一刻,所有的激动突然落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活不长了….
天京破
1864年,天京城外,数十万湘军早已布阵完毕,旗帜猎猎,长枪林立,密不透风。
曾国荃坐在临时军帐中,眼神穿过帘幕,望着城头,那道沉默了整整十年的天京城墙。
几日前,湘军在安庆大捷之后一路推进至此,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
一声轰然巨响突然从太平门方向传来,天摇地动。
早已埋伏好的三万斤火药同时引爆,整段城墙被生生掀起,砖石飞溅,烟尘腾起数丈之高,哀号声瞬间响起,仿佛死神展开了拥抱。
爆炸后的缺口,足有三丈宽,城墙崩塌如山崩海啸,瞬间击垮了天京最后的防线。
“杀!”曾国荃一声令下,湘军呐喊着冲入烟尘之中。他
身披战甲,骑着高头大马,率亲兵直奔前线,他没有看身边的尸体,也没有理会耳边的呐喊。
他只知道,今天是他等待了整整十年的日子。
从吉安初战的意外胜利,到安庆城下与陈玉成斗智斗勇,曾国荃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天赋远非侥幸。
他的“吉字营”被誉为湘军王牌,纪律严明,战力强悍,每到一处,便势如破竹。
他也因此获得“曾疯子”的外号。
天京这座被誉为“太平天国之心”的城市,如今在他面前像一只风干的猎物,再无生气。
他翻身下马,踏着碎石与鲜血,率亲兵直奔城内。
他的目标很明确,水西门后的灯笼巷,那是传说中的“圣库”所在,太平军积蓄十年财富的重地。
探入圣库
水西门内,灯笼巷尽头,一扇朱红大门沉沉紧闭,门上钉着厚重的铜钉,像是要将门后的秘密生生封死。
这里,便是太平天国的圣库,传说中金银如山、珠宝成堆的地方,是洪秀全耗尽心血筑起的“神之财库”,更是无数湘军将士梦寐以求的胜利象征。
曾国荃一行抵达门前,身后是几十名亲兵和几位亲信将领,个个满脸兴奋。
有人已经开始交头接耳,猜测里面究竟是宝石还是金锭堆得更高。
“开门。”
随着曾国荃一声令下,士兵抬起手中的铁锤,“咚咚”两声,朱门在岁月的压榨下发出一声凄厉的呻吟,终于被推开了。
阳光照进去的那一瞬间,所有人的呼吸仿佛都凝固了。
眼前没有黄金、没有白银、没有哪怕一方珍宝。
只有一排排空荡荡的木架,一地残破的布匹与碎瓦片。
仓库中沉寂得可怕,仿佛时间本身也被这荒凉冻结了。
曾国荃站在门口,脸上的血色在顷刻间褪得一干二净。
他缓缓走进去,每一步都像踏在深渊的边缘,他伸手抚过那堆尘封的木架,尘土四起,仿佛回应他的不是圣库,而是一座无底的空冢。
他低低地喃喃了一句:“完了。”
他的随从们仍未回神,有人不死心地翻箱倒柜,还有人开始小声咒骂太平军的“狡诈”。
可没人注意到曾国荃额角渗出的冷汗,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恐惧。
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误会,这是一场可以要他命的危局。
十年来,他的名声虽盛,但并不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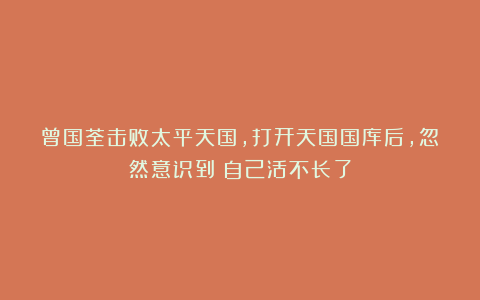
他打下的城池,少有完好保留者,每战之后,屠城、纵兵掠夺几成惯例。
安庆一役,他甚至将成千上万太平军战俘引入谷中,口称“发路费”,结果无一生还。
此事虽未广为流传,但军中上下皆知。
朝中权贵对他心存芥蒂者不在少数,只是碍于战功无人敢言。
如今若有人借此空库为由,将这罪名坐实,岂不是“贼赃在手、罪证如山”?
“曾疯子”三个字,在朝堂之外曾是威名,如今却更像是一柄双刃剑。
他的残酷,他的贪婪,他那“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自述,曾是湘军士气的源泉,但在慈禧与朝廷眼中,却更像一个不受控的杀神。
他们不会相信圣库一空,他们宁愿相信,曾国荃私吞了全部宝藏,只是将空壳留给了朝廷。
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也是最危险的推论,更可怕的是,他竟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辩白自己,他或许活不长了。
这一刻,湘军将士的欢呼声已渐远,曾国荃仿佛听见命运在耳边低语,那不是凯歌的余音,而是一场大难临头前的沉钟。
声音低到只有自己能听见:“我命休矣。”
兄长布棋
天京陷落之后,湘军军营内一派胜利气氛,只有曾国荃自从踏出圣库后,便闭门不出,一反平日的姿态。
亲兵都以为大帅是操劳过度,终于病倒了。
可只有少数心腹知道,这场“病”,是他刻意装出来的。
消息像火一样传遍了朝野,太平天国的圣库空无一物,连一两银子都未寻得。
这本该是大清翻身的金库,竟成了空壳。
一时间,各种猜测风起云涌,有人怀疑太平军事先将财宝转移,但更多人将矛头直指曾国荃,暗讽其“先入为主,将国宝据为己有”。
风声紧急,连夜汇报的捷报都未能冲淡京师的怒火。
慈禧太后看着密折上的那句“库空如洗”,冷笑不止。
她咬牙对身边太监说:“这曾家的小子,真以为本宫不敢动他?”
可说归说,她最终却没有当即下旨问罪。
因为她知道,湘军虽非大清嫡系,但如今八旗废弛、绿营孱弱,唯有这支湘勇还能独挡一面。
如果此时以私吞国库为由动曾国荃,无异于杀鸡儆猴,只会寒了军心。
正当朝堂风声鹤唳,曾国藩却按兵不动。
他表面不言不语,实际上却早已布好一盘保命大棋。
他对弟弟的性格了如指掌,也清楚这次“空库风波”将引来怎样的暴风骤雨。
他派人私下通知曾国荃,速请病假回乡“静养”,以退为进,避其锋芒。
“此刻不退,便退无可退。”这是曾国藩送给弟弟的密信中唯一一句话。
曾国荃收到密信那夜,一言未发,深夜就向军中留守主将交代军务,随即卧床不起,声称旧疾复发。
第二日便由人抬上马车,离开南京,一路向西,车窗紧掩,曾国荃面色苍白,眼神却极其清明,眼下不是争辩是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命留住。
慈禧收到曾国荃“请病假”的折子时,沉默许久。
她原本想要雷霆手段镇住军心,可一想到这“曾家兄弟”一文一武,皆是湘军支柱,若真动手,不但会招致湘军不满,恐怕连淮军、楚军也要心中打鼓。
于是她深吸一口气,将怒火咽下肚里,冷冷批了一句:“准其请假,望其自省。”
但她没有再提起封王之事。
按理说,曾国荃攻破天京,捉拿太平天国残余,其功劳足以封亲王。
朝廷此前也曾口头许诺,若能平定太平之乱,必将王爵世袭。
可当圣库空空、洪天贵福又逃脱的消息传来时,一切承诺便成了虚无。
慈禧最终只是敷衍地赐给他“一等威毅伯”,连侯都未封。
这一切,曾国荃都心知肚明。
而在湖南老家的曾国藩,则继续在朝堂之中周旋,他四处走动、交好权臣,为弟弟求情。
表面看是主持军务,实则步步为营,将曾国荃从风口浪尖生生“藏”了下去。
兄弟二人,一个以“病”为盾,一个以“忍”为刃,结果是,曾国荃活了下来。
余生虽无爵,幸得无刀问
从南京归来之后,曾国荃便隐退至家乡,原本唾手可得的亲王爵位,最后仅止于“一等威毅伯”四字,虚名有之,实权无几。
他心中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大清末年,风雨如晦,动荡频仍。
湘军已非当年威风,淮军崛起、洋务新政推行,曾国荃的位置逐渐被边缘。
但出人意料的是,光绪十五年,他竟被授予太子太保衔,随后升任两江总督。
这份任命像是一份迟来的安抚,也像是慈禧与朝廷的一种默契回应:我们不封你王,但也不动你命。
在两江任上,曾国荃不再骄横,也不再好勇斗狠,自己如今不过是清廷手中的一张“稳定牌”。
曾国荃最终在光绪十六年病逝,终年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