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宗族政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几个问题
——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
臧知非
(江苏 苏州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内容摘要:商鞅变法,离散宗族,强制分户,将宗族血缘关系从国家行政中彻底剥离,国家力量直接控制每家每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为秦与六国社会结构差异,秦朝将商鞅之法推行六国地区,迁徙豪强,“急法”施政,导致社会矛盾大集结。“汉政”宽缓,儒学意识形态化,宗族势力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帝国统治的同时,也分割国家权力。汉武帝打击“强宗豪右、田宅逾制”,强化中央集权,但封建统治的性质,决定了宗族势力的衰而复兴。东汉宗族势力发达,最终异化为国家统治的异己力量,是王朝更迭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离散宗族 土地制度 国家治理 社会控制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特别是基层行政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的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基层治理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与分裂的历史变迁。商鞅变法的离散宗族政策和制度规定则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基础,准确把握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精神和制度内涵、历史意义,不仅关乎商鞅变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是认识秦汉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同时是把握秦汉以后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如所周知,秦是后起之国,在周人故地、因周人之力、在周人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其国家结构本质上是西周的翻版而带自身特色,当东方诸侯国纷纷主动变革传统、弱化族权、强化君权而加速社会转型的时候,秦国还在传统社会的泥淖中艰难跋涉。[1]至孝公继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为“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2]乃任用商鞅,推行新法,彻底改变这一历史局面。商鞅变法是在总结各国变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展开的,以法律手段强化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把宗族血缘关系彻底地从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剥离出去,是新法的特征,[3]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以为禁”、“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4]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离散宗族的彻底性。认识秦汉宗族与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必须从商鞅变法的宗族政策说起。
一
强制分户的历史内涵
商鞅曾自诩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6]这是对“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以为禁”的直接解释,现代学者咸以为“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以为禁”是移风易俗之举。这有其道理,但这仅仅是商鞅针对赵良质疑新法的辩护之词。若置之于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场域下考察,“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以为禁”的历史内涵远不止此。因为“同室内息”并非“父子无别,同室而居”那么简单,其目的也不限于“为其男女之别”。其时之“室”是宗族社会的基层血缘共同体,而非变法以后的一般意义上的“家室”。赵良以关心商鞅命运的口吻批评商鞅剥夺宗室贵族权利,事事依法,轻罪重罚,“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7]不符合《诗》《书》仁义之道,上至公子公孙,下迄平民百姓,对商鞅充满着怨恨,商鞅不会有好下场,劝其主动辞官,中止新法。商鞅明白赵良的立场,遂以移风易俗为据作答,意在说明新法固然改变传统,但“为其男女之别”是《诗》《书》之教的体现,说明新法的合理性。当然,赵良谓“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新法初行时民一度“不便”,但“居三年,百姓便之”,[8]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9]足以说明一切。这要考察 “室”的历史含义。
《说文》:“室,实也。从宀至声,室屋皆从至,所止也”。“宫,室也。” “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室、宫同意,同时室有着财产单位的含义,有大小尊卑之别。在宗族奴隶社会,财富归统治宗族所有,贵族是财富支配者,财富多少和宗族等级一致,有“室”者均为统治宗族,而有“家室”“宗室”“公室”“王室”之别。这些“室”既是经济单位,也是政治单位,国家权力按照宗族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是为宗族贵族政治之下的世族世官制。春秋各国,宗室贵族相互倾轧,胜者对待失败者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分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纳其室”不仅仅是瓜分、占有这些“室”的财产,也包括其世袭的权力,是权力结构重组的过程。商鞅变法以前的秦国,“室”仍是以宗族为特征的财产单位和权力单位。“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意味着大家族分为小家庭,一“室”变多“户”,原来以“室”为单位的土地人口由官府析分、登记在各“户”之下,确认其土地权属关系,均直接隶属于国家,原来的“家长”“族长”失去了对土地和宗族成员的人身支配权,宗族土地所有制变为国有制,民户成为国家课役农。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和土地关系的变动是前贤时哲所未及的问题,需作简单说明。董仲舒谓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买卖”,造成“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的严重结果,[9]历代学者均视之为商鞅变法推行土地私有制的铁证。事实并非如此,董仲舒是地地道道的“过秦”之言,是实实在在的借古讽今。出土资料和研究表明,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土地国有化的法典化时代,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实行国家授田制,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以每户百亩的授田制为基础,商鞅之法严格实行授田制和军功赐田制,授予普通平民百亩(大亩)田、一区宅,军功爵者依爵位高低赐田宅。这里的百亩是国家规定的良田,包括已垦和可垦而未垦之田,劣质土地则增加授田数量,按二百亩、三百亩等授予,仍然按照百亩良田计算、征收田租,即以受田数量调节质量所带来的产出差异,是为“相地而衰征”,[10]其性质是土地国有制,不存在“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问题。从土地制度层面看,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在国家全面控制土地、人口前提下,按照编户民的身份等级统一分配,宗室贵族土地也必须按照法律分配。[11]从形式上看,一室分多户,并不等于宗族关系的消解,宗族血缘关系依然存在,原来登记在宗族主名下的土地分解在兄弟们名下而已,形象的表述就是分散登记,和土地出户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户”隶名官府,其土地在法律层面是由国家授予,法律上已经划归国有,各自立户的“父子兄弟”之间虽然存在着宗族血缘关系,但是,这个宗族血缘关系属于民间关系,不再具有身份等级的贵贱属性,其土地也不再是因其高贵的血统而获得。在这里,宗族关系与土地了无关系,原来的宗族贵族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国有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远非移风易俗那么简单。商鞅此举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为了更深层次地把宗族血缘关系从国家权力分配和运作过程中剥离出去,国家力量不必再依靠宗族力量控制社会,解除了宗族血缘关系对民户的束缚。当然,编户成为国家受田民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租税徭役,徭役即“事”的义务远远大于田租,但摆脱宗族身份限制的民户可以凭借自身努力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富且贵的梦想,空前地激发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可以通过“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身”而致富,通过军功获爵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庶子”,踏入“贵”的政治序列,原来社会结构、个人与国家关系彻底改变。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以为禁”的经济制度表述,凸显了“户”的社会控制意义。授田、征税、起役、社会等级的确定,均以“户”为基础。按户为象形字,即《说文》说的“半门曰户”,出入同一门户的人口是为同户,登记在文书上是为户籍。在等级社会,居住区划分、住房大小、建筑样式,因身份而别,作为建筑组成部分的门户有大小、高低、式样之别,因而门户也就有了区别身份等级的功能。只是在宗族社会,门户所表达的社会关系涵盖于宗族关系之中,尚不作为独立的社会等级标志。当国家权力突破宗族关系束缚、渗透到社会基层之后,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体貌特征,以及土地、房屋、奴隶和其他财产等,均登记在户籍簿上,作为征税起役的依据。人隶属于“户”,个人的毁誉荣辱和“户”的厉害关系一体化,控制“户”就控制所有社会成员,因而“户”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基本单元,对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属性一目了然。
二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与社会控制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并非商鞅的发明,而是战国通制。《周礼·大司徒》有“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赐;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小司徒》有“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五家相受,相和亲,有辠奇邪,则相及”之语。《逸周书·王鈇》谓:“其制邑理都使矔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长退脩其家。事相斥正,居处相察,出入相司。” 《管子·立政》:“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等等。对各书所述略加思考,就不难发现,各国基层行政编制虽然不同,但不约而同地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为基础,什伍之人荣辱与共,“辅之以什,司之以伍”的目的是为实现 “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是为了“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刑罚庆赏,相及相共”的方便,只是思想家们还保留着宗族血缘关系之下的温情脉脉,强调同伍之间的相亲相爱,所谓“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赐”“相宾”就是历史余韵,乡里基层组织之“族”“党”体现了宗族关系的遗存。[12]
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做”当然不是简单的因袭旧制,而是旧瓶装新酒,重点在“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云:“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 [13] 司马迁之语是对商鞅连坐法的原则概括,制度并不一定如司马贞所言是一家违法九家连坐,所谓“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之“奸”也有其特定内容,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奸犯科。但是,同伍连坐之严厉确实空前。云梦秦律《秦律杂抄》有云“战死事不出,论其後。有(又)後察不死,夺後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 [14]按规定,战争中不屈战死,无论死者功劳大小均授其子以爵位。后来发现其人没有阵亡,褫夺其子爵位,剥夺同伍者的奖励,以示对同伍者失察的惩罚;未死而归者,罚为隶臣。《傅律》规定:“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15]没到老免年龄而免老,到了老免年龄未经批准而免老,里典、田典、伍老 “赀一甲”的同时伍人“户一盾”,全部迁往边远苦寒之地。傅籍是乡官里吏的日常职责,核实年龄是乡官里吏的公务行为,出现错误受罚理所当然,结果伍人也要被罚,而且惩罚很重,赀“户一盾”的同时要处以迁刑,就是因为“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是国家行政的一般原则,“告奸”是什伍之民的基本义务,不“告奸”无论是否存在故意,都导致户口统计不实,使国家役源流失,故而一并处罚,从而使邻里之间每时每刻都要盯紧对方,随时举报不法行为。所谓“居处相察,出入相司”之“察”与“司”的内容就是各种违法行为,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百姓日常的控制。这些学界熟知,无需详述。我们只要明白商鞅变法以后,全面建立国家控制社会的制度体系、宗族关系的温情脉脉在国家行政中被涤荡殆尽就行了。
汉儒及后世学者对“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诟病有加,认为是严刑峻法的代名词,但是,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带给秦民的并非如后人理解的灾难,相反是改变命运的制度契机。变法之后,编户民固然要承担徭役赋税,但是这个徭役赋税以国家授田为基础,家家户户生产资料有保障,并可以通过军功和耕织获得爵位和奖赏,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富而贵的梦想。只此之故,才能使“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6]荀子对秦的政风民情,才赞誉有加。[17]
三
秦朝离散宗族与社会矛盾的集中
秦朝统一,在秦始皇及其近臣心目中,是天命使然,秦制是圣制,秦法是圣法,天下万民必须严格遵行秦制秦法,统一行政、土地制度,按照二十等爵制规范社会等级和财产,等等,上合天心,下顺民意,顺理成章,必然会使天下之民幸福欢悦,天下之民自然感恩戴德,做嬴秦顺民,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一世二世以至于万世地传之无穷。但是,历史开了一个真实的玩笑,秦王朝没有传之万世,而是二世而亡。其原因固然复杂,其中离散宗族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于历史传统、资源环境、制度政策等因素,秦与六国之间、六国与六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存在差异,宗族关系、宗族力量对国家行政运转有明显不同。六国制度改革没有商鞅那样彻底,宗族遗存远远大于秦国,不仅宗室贵族分割君权,大家族的存在也远远普遍于秦国,宗族豪强是左右基层行政不可忽视的力量,身份高低、权力大小、土地分配、财富占有以及风俗习惯较多地保留着宗族血缘底蕴,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远弱于秦。[18]无论是手握重权的宗室贵族还是靠经营矿冶盐铁及长途贩运等起家的基层大姓,都以其宗族背景,广占土地,役使农民、奴隶、徒附,同时有宾客死士为之奔走,控制基层政府,拥有诸多特权。从经济和政治层面分析,这些宗族成员与宗主之间、主奴之间、主客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但历史地看问题,彼此又有着依存关系,是利益共同体。以贵族而论,如楚国鄂君启节铭文表明卾君身为宗室,享有封地的同时,拥有庞大的商队,陆路可以免征五十乘车子货物的商税,每一辆的运载量相当于十匹马、十头牛的驮运量;水路免征一百五十艘船货物的商税;所贩货物除了军用品之外,无所不包。[19]这仅仅是楚君允许的免税车船数量,实际免税数量很可能不止此数,卾君所拥有的商队更可能超过五十乘车、一百五十艘船,可见其役使人数之多。铭文记载的仅仅是商队规模,至于其他财富当然不止于此。至于那些富甲一方的地主、矿冶业主、畜牧业主的社会势力尽管不能和卾君这样的贵族相比,但是富甲一方、称雄一地、横行乡里者所在多有。[20]
统一之后,六国贵族、豪强大姓,无论是留在原籍,还是迁徙关中或者其他地区,绝大多数是既无军功、也无事功,和秦的爵位制度没有关系,均为什伍之民,都要互相监督、有罪连坐,原来的田宅、财富、权力均被剥夺。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律、龙岗秦律、里耶秦律、岳麓书院藏秦律关于授田(行田)、户籍等的规定和各种司法案件,足以说明这些。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更具体说明秦朝社会等级与田宅、财富的关系,与宗族大小了无关系。这些官僚贵族、工商业主、地方豪强失去其原来的权势和财富,必然以各种方式抵制新的法律制度。而普通农民也因其故俗不经意间触犯新法而身陷囹圄。但秦始皇以得天命自居,把自己当做天帝在人间的体现,个人意志即上天意志,个人欲望即上天之希望,在受五德终始说的鼓吹之下,无视世异则事异的常识,把秦法推向极致,“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21] 结果使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新王朝,希望回到过去,千方百计地和过去的主人保持联系,离散宗族故旧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如项氏叔侄避难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22]这“宾客及子弟”是包括项氏叔侄原来追随者和依附者在内的,并成为起兵的骨干,其余各国宗室起兵复国均以其故众为基础。岳麓秦律中关于“从人”的种种规定,从反面说明离散宗族的政治意义,值得深入分析。
四
西汉宗族关系的复兴与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
刘邦称帝,接受陆贾“逆取顺守”之论,以“汉政”代“秦政”,为宗族势力的复活提供条件。惠帝四年春,“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23]高后“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24]“复其身”是对孝弟力田的优待,“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是对孝悌力田的尊崇。文帝继位,高举以孝治国大旗,“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25]尽管文帝初衷是以此调节宗室内部矛盾,消弭诸侯王的不臣之心,但三老、孝悌、力田选自民间,与民共处,是道德楷模,以自身行为劝民行孝守法。[26]就平民言,孝道的日常行为是孝敬父母,提倡同居共财、聚族而居,以“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为耻辱。[27]国家既然如此提倡孝道,从郡县到乡里设孝悌、力田、三老成为常制,商鞅以来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制度自然消解废除,宗族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稽诸历史,史家艳称的“文景之治”与宗族势力的兴起是同步的。司马迁曾历数汉初著名的矿业主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齐刀氏以及关中由齐地迁徙来的齐国宗室之后“诸田”的同时,概括谓“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8]这些矿业主、种植业主、畜牧业主、都以其宗族力量为支持,史不绝书的“豪民”“豪猾”“豪奸”“豪富”都是指富豪大姓。但是,就国家治理而言,宗族兴起,以其富厚,交通王侯,和贪官污吏沆瀣一气,操纵乡里,欺压良善,兼并农民,鱼肉弱小,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紊乱、国家权力的分割、国家控制社会的弱化。这与社会有序发展、中央集权的本质属性背道而驰,甚至成为诸侯王割据的依靠。故从景帝开始即以行政法律手段打击宗族大姓的不法行为,将抑制宗族势力纳入国家统治的范围之内。如“济南瞯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瞯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29]郅都因为不再纵容瞯氏的胡作非为,严格执法,被史家列为“酷吏”。
酷吏之所以“酷”,一是不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处理政务,有专杀之嫌,二是诛杀权豪,不避贵戚,以杀戮严猛立威,维护皇权。三是顶格量刑,绝不宽贷。汉武帝鉴于宗族大姓兼并农民形式日益严峻和地方长吏枉法行政、背公向私、维护地主大姓利益的现实,继续任用“酷吏”的同时,设立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是“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淩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均为对二千石充当豪强大姓保护伞等不法行为的惩处,如“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等。[30]不过,这些措施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要想治本,必须铲除豪强大姓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征伐匈奴、开通西域,使帝国声威远扬的同时,也使帝国军费支出剧增。那些“田宅逾制”的强宗豪右不仅不佐公家之急,相反大发国难财,借经营盐铁矿冶之机,大肆盗铸造钱币,哄抬物价,垄断市场,兼并农民,鲸吞国有土地,欲控制地方豪强、宗族大姓的恶性发展,必须在制度层面消除其经济来源。汉武帝遂通过经济制度改革,集中铸币与发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假民公田”、“屯田”等措施,强化国家干预经济力度,发挥国家调整土地关系的作用,剥夺工商业主、畜牧业主、种植业主的敛财基础;同时严格算缗告缗,使“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这些“中家以上”多是豪强大姓之家,“遇告”而“破产”,那些不得不依附于豪强的农民获得自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强化。
汉武帝打击宗族固然严厉,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其发展。因为宗族豪强是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是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而国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郡守二千石之所以“阿附豪强”就是因为他们有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故随着时间流逝,宗族血缘关系必然成为封建统治权力的组成部分。第一,土地私有化,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是宗族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绝大多数官僚出身地主,即使少数官僚出身贫寒,一经为官即成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工商业主三位一体。第三,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儒家伦理法律化、行政化,聚族而居、同宗共荣成为社会榜样,无论是官僚地主、豪强地主还是工商业主无不发展宗族势力,宗族血缘关系成为世家大族的社会基础、控制基层社会的工具,地方行政或者为宗族大姓作把持,或者地方政府必须借助豪强大姓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血缘关系、宗族势力日益渗透于基层行政运作,世家大姓、强宗豪右凭借手中权力、利用制度之便,光明正大地盘剥贫弱的同时,刮削国家资财、分割国家权力。西汉后期,政治黑暗,吏治败坏,土地兼并迅猛,农民破产流亡加剧,和宗族势力发展同步的原因就在这里。
五
东汉宗族发展与王朝解体
两汉之际的战乱,是豪强势力膨胀的助推剂。战乱之中,大大小小的地主无不聚族自保,成为武装割据的基础。刘秀的开国元勋们,绝大多数是大地主,举族追随刘秀,所率族人、宾客,实际上就是私人武装,构成了刘秀军事力量的支柱。如寇恂所将“皆宗族昆弟也。”[32]刘植有“宗族宾客数千人”[33]。耿纯率“宗族宾客”从刘秀,“老病者皆载木自随”[34],又自焚家园以绝宗人反顾之心。冯勤率“老母兄弟及宗亲归”刘秀。[35]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刘縯)”[36]。王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投刘秀大将军邓禹等等。[37]刘秀麾下如此,其余割据武装亦然。无论是割据河西、心系汉家的马融,还是割据陇西、巴蜀、齐地与刘秀为敌的隗嚣、公孙述、张步,手下都聚集着各地的宗族武装。建武三年,冯异定三辅时,曾“诛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 [38]建武五年,耿弇平齐,张步归降,“弇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辆,皆罢归乡里。”[39]这些“罢归乡里”的武装大都以宗族、乡里为纽带,他们“罢归乡里”之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当其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一有风吹草动,还会起兵为乱。桓谭曾语刘秀云:“臣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忘诱,或至掠虏,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40] 这“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 说明“罢归乡里”并没有起到刘秀希望的效果。建武八年,刘秀亲征隗嚣,战幕刚开,关东即乱,“颖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41]。刘秀只好班师,先平叛乱。这些“盗贼”即原来的割据势力。《东观书》载杜林语云:“张氏(即张步)虽皆降散,犹尚有遗脱,长吏制御无术,令得复炽……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42]。就在这次叛乱事件中,投降东汉居住洛阳的张步就“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宏、兰欲招其敌众,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击斩之”。[43]刘秀对此是有所了解的,知道简单的“罢归乡里”不能消除地方割据的隐患,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罢归乡里”不过是为求粗安的临时举措,要想彻底控制基层社会,必须剥夺兵长渠帅的权力基础,即将兵长渠帅控制的人口归于官府,清查兵长渠帅所占有的土地,从而严格“度田”。[44]
因为刘秀依靠宗族力量建立东汉政权,对宗族力量只能是选择性打击,严格“度田”打击的是与新生政权为敌的宗族势力,支持东汉王朝的世家大族则是优容的对象,学界认为东汉政权开国伊始即是大地主利益代表,即因于此。崔寔《四民月令》曾对东汉宗族形态、社会功能有高度概括式说明。宗族成员同宗共祖,每年按时祭祀,一年之中,六个月有祭祖活动,除了因为季节关系祭品有异之外,其程序、参加人员除了宗族成员还包括乡党宾客,除了祭祖,还有着尊敬家长、和睦族人、礼敬高年、商议族内事务以及团结乡里的目的。如正月祭祖礼毕,“乃室家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十二月“祀冢事毕,乃请召宗亲、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这完全是例会的形式。这宗亲、宗人、乡党耆老的土地有多有少,贫富相差巨大,本来属于不同阶级,因为同祖同宗,都“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45]在这里,没有了阶级的差别。当然,贫富是客观存在,“家长”表示彼此相亲的同时,也要扶贫济危,如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十月“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毋或踰越;务先自竭,以率不随。”[46]所谓“分厚彻重,以救其寒”、“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毋或踰越”是指同宗之户按照贫富和亲属关系分摊救助宗人费用,既表示同宗相恤是所有宗人的共同义务,也体现了家长的主导地位。这实际上分担了国家的救助贫弱以化解社会矛盾的义务。这是全体宗族成员的义务也是权力,同时是相互沟通的机会。这些学界论述甚多,不予举证,这里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东汉后期的新生事物,在东汉前期已然,所以《白虎通义》才对“宗族”构成、作用做出专门的定义。
如果说宗主、家长举宗族力量扶危济困、赈恤乡里,在经济层面分担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间接地维护王朝统治,那么武装族人、维持治安则直接行使国家的统治功能。四民月令》谓三月“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47]九月要“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卮之寇。”[48]这个职能更为重要,在西汉后期已经开始。哀帝时鲍宣说民有七亡:“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晋灼注:“迣,古列字也。”师古日:“言闻桴鼓之声以为盗贼,皆当遮列而追捕。”[49]这些“盗贼”实即暴动之饥民,“遮列”之男女就是地主的庄民,也是地主的家兵成员。王褒《僮约》有云:“犬吠当起,警告邻里。枨门柱户,上楼击鼓。荷盾曳矛,环落三周”。[50]说明西汉后期不仅有家兵,而且建有工事,既有候望用的高楼,又有报警用的枹鼓,僮仆也有执兵警戒的义务。至东汉,宗族武装远较西汉发展。这除了《四民月令》所述之外,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砖和坞壁实物模型直观体现了田庄中军事活动的普遍性。著名的如四川成都曾家包和新都的东汉画像砖都有武库图,库内兵器架上有戟、矛,墙上挂弓、弩。[51]广州动物园和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都出土过坞壁模型,而以雷台出土的结构最为复杂:坞壁呈四方形,正面大门上建门楼,四角建两层角楼;正面以外的三面筑重墙,院中筑五层楼阁,正面有门窗以作瞭望和战射之用。[52]在内蒙和林格尔、甘肃嘉峪关东汉墓的壁画中都有坞壁图,并有“坞”字题记。[53]在中原地区此类资料更多,如山东滕县西户口、龙阳店,徐州青山泉、白集出土的画像石均有武库图。[54]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一次出土了七件楼阁模型,均为三层,在第二层、第三层的四角均有武士执兵守卫,注视四周。[55]这些都是墓主生前拥有家兵的生动写照。
东汉后期,阶级矛盾激化,宗族武装更加发达,如初平年间,“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56]许褚于是“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57]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追随曹操官至捕虏将军,封都亭侯, “宗族部曲三千家居乘氏。”[58]江夏平春人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时有周直者,众二千余家,与恭、通外和内违。”“有众两千余家”的周直和李通“外和内违”,起码说明归附李通之“众”和周直相当。后来李通“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59]类似史例,俯拾即是,为学界所熟知,不予赘举。族是家的扩大,族长和家长是合一的,在一个小家庭中,家庭成员要听命于家长;在一个宗族中,宗族成员就要听命于族长,为宗族主执兵作战是天经地义的,保护宗主,也保护自己,得利最多的当然是宗族主。
就国家统治而言,宗族势力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维护国家统治,也可蚕食国家统治。国家机器从形式上看,是社会公正的象征,是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避免在阶级冲突中同归于尽的产物,但是,从本质上说,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东汉也好,西汉也罢,国家权力本质上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只是不同历史阶段因为官僚队伍构成的变化,代表着地主阶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代表”是由各个时期的官僚集团实现的,皇权是他们的统一体现。地主、官僚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具体的人代表着具体的家庭、家族、宗族,而人的欲望、人的追求是变动的,统治阶级的贪婪更是无限的。东汉的宗族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是地主、官僚、工商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单元,这种结构单元以血缘亲疏、“乡党”关系为纽带,在血缘“乡党”关系之下温情脉脉,而对于其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则冷漠无情,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则合全体之力以拼争。因而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宗族地主内部分为不同利益集团,各个集团都想方设法使本集团利益最大化,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和皇权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不过和皇权之间的冲突不是直接表现为与皇权相抗衡,在大一统的皇权体制之下,任何个人、集团都无法和皇权公开抗衡,这里说的冲突是宗族力量的总体对皇权带来的分割而言。宗族主救恤九族乡党,组织家兵防止盗贼,协助官府歼灭不稳定因素,都有助于国家统治,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或者地方长吏不能满足这些“宗族”的利益需求、而有更大的利益诱惑出现的时候,这些“宗族”就会成为国家统治的异己力量,族人、乡党听命于宗族主而置国家法令于不顾、或者把国家法令当做谋取本集团利益的工具。当地方长吏本身也是宗族主的时候,自然将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变为维护宗族利益的工具,在极尽全力兼并土地的同时,极尽全力把原来隶属于国家的农民变成自己的依附民,置国家、皇室、皇帝于不顾,国家势必失去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终导致统治的崩溃。也就是说,宗族力量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原来隶属于国家的农民逐步地在宗族血缘关系的隐蔽之下成为宗主的依附民,国家不能有效地把宗族力量控制在统治秩序范围之内,历史的发展将走向最高统治者愿望的反面。
注释:
[1] 秦源于东方,兴起于西北,学者或以为秦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地理环境因素,秦的社会、文化带有戎狄文化性质。笔者以为,此说有其历史依据,中国大一统文化本来是多种区域文化整合融通的结果,但是,之所以整合融通为大一统文化,乃是因为不同区域文化虽然各具个性,但其本质相通。秦人兴起于西北,其经济生产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风俗,当然带有区域特色,但秦人在正式受封之前主观上向慕周文化而逐步为周认同,护送平王东迁、受封建国之后,客观上因周之地、收周之民的同时,主观上则尽可能地采用周制,以礼乐治国,在东方各国的宗族血缘关系与国家权力逐步剥离、君权逐步集中时,秦国的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则处于一体化进程之中,直至战国初期,秦国的社会结构依然处于传统之中。参见拙文:《相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历史进程——秦国社会结构散论》,《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秦人“受命”意识与秦文化的发展》,《秦文化论丛》第八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拙著:《秦思想与政治研究》上编“天命与国运”,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
[2]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第202页。
[3] 关于西周、春秋、战国宗族血缘关系与国家权力的变迁, 参阅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下同),第17——60,183——213,242——287页。
[4] 《史记》卷68《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第2230页。
[5]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4页。
[6]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4页。
[7] 《史记》卷5《秦本纪》,第203页。
[8]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1页。
[9]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下同),第11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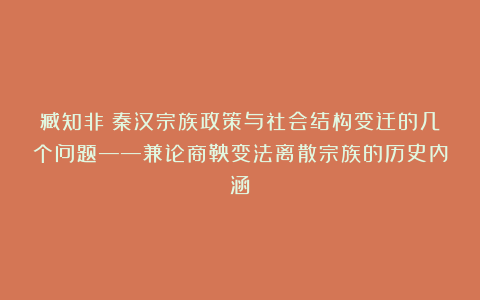
[10] “相地而衰征”是春秋战国授田的一般原则,并非传统理解的按照土地数量多寡征收田税,参见拙文:《人文杂志》,1996年2期。
[11] 关于战国、秦朝、西汉土地制度,参阅拙著:《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中央编出版社,2017年。
[12] 关于战国什伍乡里制度,参见拙文:《先秦什伍乡里制度新探》,《人文杂志》,1994年1期;拙著:《战国秦汉行政兵制与边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
[13]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0页。
[1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下同),第146页。整理小组注“除伍人”:“除,《考工记·玉人》:’以除匿’。注:’除匿,诛恶逆也。’据此,除有惩办的意义。”笔者按:谓此处的“除”为追究、惩处的意思是正确的,但具体追究、惩处内容不明。细察上下文意,“除伍人”除了除了抽象的追究、惩处伍人含义之外,应该有具体的规定,这就是免除同伍者因为“战死事不出”所得的奖励。同伍之人,荣辱与共,一人“战死事不出”,是死者的不屈,也是同伍的荣耀,奖励其“后”的同时,也要奖励同伍之人,以激励同伍者。发现当事并未战死,剥夺其后爵位的同时,剥夺同伍者的奖励。这里的除,即免除。
[15]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3页。
[16]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1页。
[17] 参阅拙文:《“驳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国政治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
[18] 秦国与六国社会差异,参见拙文:《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19] 铭文见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472——473页。
[20] 参见上揭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352——370页。
[21]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8页。
[22] 《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297页。
[23] 《汉书》卷2《惠帝纪》,第90页。
[24] 《汉书》卷3《高后纪》,第96页。
[25] 《汉书》卷4《文帝纪》,第124页。
[26] 从历史背景分析,文帝以孝治国,除了古今学者分析的教化万民目的之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这就是希望以孝道调节宗室内部矛盾,以兄友弟恭自砺,以自身的宽厚温婉,感化诸侯王的不臣之心。这些尚无人论及,特此指出,详论留待另文。
[27] 《汉书》卷48《贾谊传》,第2244页。
[28]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29] 《汉书》卷《酷吏传·郅都传》,第3647页。
[30] 参见拙文:《秦汉里制与基层社会结构》,《东岳论丛》,2005年第11期。因字数限制,刊出时压缩较多,完整版见拙著:《战国秦汉行政兵制与边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68页。
[31]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0页。
[32] 《后汉书》卷16《寇恂传》,第622页。
[33] 《后汉书》卷21《刘植传》,第760页。
[34] 《后汉书》卷21《耿纯传》,第762页。
[35] 《后汉书》卷26《冯勤列传》,第909页。
[36] 《后汉书》卷32《阴识列传》,第1129页。
[37] 《后汉书》卷27《王丹传》,第931页。
[38] 《后汉书》卷17《冯异传》,第64页。
[39] 《后汉书》卷19《耿弇传》,第712页。
[40] 《后汉书》卷28《桓谭传》,中华书局,第960页。
[41]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第54页。
[42] 《后汉书》卷105《五行志三》注引,第3305页。
[43] 《后汉书》卷12《张步传》,第500页。
[44] 关于刘秀“度田”,学者多认为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引起武装动乱,贵族、地主反对,而不了了之。但细析史实,并非如此。关于学界对“度田”认识的分歧及其分析,参见拙文:《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拙著:《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第172——187页。
[45] 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下同),第1, 74页。
[46] 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5,68页。
[47] 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29页。
[48] 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65页。
[49] 《汉书》卷72《鲍宣传》,第3088,3089页。
[50]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42,王褒《僮约》,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下同),第359页。
[51] 四川博物馆:《四川新都县发现一批画像砖》,《文物》1980年第2期。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
[52] 广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动物园东汉建初元年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11期。甘肃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53]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54]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汉墓》,《考古》1981年第2期。
[55]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56] 《三国志》卷11《魏书·王修传》,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第345页。
[57] 《三国志》卷18《魏书·许褚传》,第542页。
[58] 《三国志》卷18《魏书·李典传》,第533.534页。
[59] 《三国志》卷18《魏书·李通传》,第534,535页。
本文删节版曾发表于《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题作《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此据作者原稿推送。如需引用,敬请核对正式发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