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上海,空气里蒸腾着粘浪。2025年7月24日下午,当我的脚步最终落在世博会博物馆门前,一种奇异的清凉感却从心底深处弥漫开来——并非物理温度的陡然变化,而是灵魂深处那片早已干涸于日常琐碎的“地中海”,终于即将被名为“希腊”的远古潮汐重新浸没。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那句回荡在人类精神殿堂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宣言——“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早已成为这次展览无形的精神路标。今天,我就要循着这条古老的度量衡,去丈量一个曾创造出无数现代文明基石的民族。
序章:石头的低语
步入幽暗而肃穆的前厅,耳畔传来策展人沉稳的声音,仿佛历史本身在低语:展品来自希腊境内14家博物馆的精华,多数为希腊本土考古发掘成果,它们“以物证的形式呈现出一部全景式的古希腊历史”。这绝非一个简单的艺术陈列,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人与人的相遇”——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到荷马时代的游吟诗人,从民主城邦的公民,到远征东方的帝王——我们将在这里“聆听他们的话语,观察他们的生活”。因为那里,“我们能找到现代西方文明几乎所有要素与特质”。
第一章:泥土与神性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6800-前3200年):欧洲最早的犁痕
展区的光影由暗转明,温润的灯光打在数件形态古朴却磨制得异常精细的石器上——斧、锛、凿,还有带着使用磨痕的石臼与磨石。它们沉默如金,却在无声地诉说着人类物质文明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解说词如清泉流淌:“新石器时代相较于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取得重大进步……可以制作出表面抛光、功能多样的工具和器皿。正是因为可以制作这些更为精细的器具,人们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农人。”
展柜中那件古朴的黑陶罐,边缘圆钝,其表面的刮削痕迹清晰可见。它属于那些公元前6800年左右的定居者——欧洲农业文明的曙光在他们手中点燃。他们构成了展览“遇见”的第一批“希腊人”——这些生活在“规模通常不大,可容纳100至300人生活”的村社中的男女,在爱琴海之滨的丘陵谷地里,开垦出欧洲最早的农田,播下小麦和大麦的种子,驯养山羊与绵羊。
土地承载着他们的生命,也孕育了他们最初的神祇观念。那些简单粗砺的母神陶俑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角落,她们夸张的生殖特征既是丰产巫术的象征,也是对生命源头最朴素的叩问:是谁让土地生长,让牲畜繁殖?
人开始尝试用有限的认知,去度量掌控万物的神圣尺度。普罗泰戈拉的宣言在此初显萌芽——人开始作为观察者与参与者,尝试去理解和命名环绕他们的世界秩序。他们尚未书写神话史诗,但已在泥土中镌刻下对自然与生命之谜最初的追问。
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200 – 前1100年):抽象之魂与远古的航线
基克拉泽斯岛岛民
向前步入下一个区域,空间骤然变得空灵洁净。这里的主角是基克拉泽斯群岛(名称源于古希腊语“圆圈”)那些著名的白色大理石人像。它们线条极简,几何感强烈——通常为平卧的女性形象,面部只有略微隆起的鼻梁,双臂在胸前交叉环抱。
展柜中一件约公元前1250年的大型陶质女神像,以其独特的姿态占据了视觉中心——她双臂高高扬起,仿佛在天地之间呼唤或是舞蹈。头顶的王冠构造繁复,由“三条分叉条纹、两个舌形元素以及一只鸟构成,可能是一种象征符号”。基座上文字揭示了她的身份象征:“推测神像头部的开口可以用来放置头冠或鲜花。王冠上装饰符号的变化,对应着不同的女神形象……随像所展现的扬臂姿态,可能与女祭司在祭祀活动中的舞蹈动作相呼应”。
这正是米诺斯文明的核心特征——对强大自然女神(或许是大地母神或生殖女神)的崇拜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这些雕像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凡海上能力的见证。环抱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是广阔的爱琴海,而“考古证据表明岛上居民很早便与周边地区往来,这意味着航海在爱琴海早已存在”。他们用独木舟或原始的帆船,沟通着岛屿与岛屿、岛屿与大陆(克里特、小亚细亚),交换着贝壳、黑曜石、陶器,更重要的是,交换着信息、技术与艺术灵感。这种跨海交流如同无形的织机,编织着爱琴海世界早期文明的雏形,也奠定了后来希腊文明开放的海洋基因。在米诺斯与迈锡尼的辉煌之前,基克拉泽斯人以石头的纯粹语言和大海的广阔胸襟,宣告了古希腊艺术追求抽象的永恒与秩序之美的源头。
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宫殿
“国王米诺斯的宫殿”不仅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宗教和经济的心脏——“宫殿是米诺斯社会的行政与经济中心”。克诺索斯宫壁画上那些头戴华丽王冠、手握蛇的女神形象,以及充满活力的海豚、百合、奔牛等自然主题,都在无声诉说着一个与自然紧密相连、可能由女祭司阶层主持祭祀、崇拜生命力的文明。
中央集权机制已在此形成——“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米诺斯人开始在克诺索斯等地建造第一批宫殿建筑群……由官僚体系组织领导”。米诺斯人以宏大的宫殿建筑、华丽的壁画、精湛的手工艺(金银制品、印章、绚丽的卡玛瑞斯彩陶),以及遍布爱琴海的贸易网络(考古发现他们活跃于基克拉泽斯、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构建了“青铜时代早期地中海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如同策展文字所言)。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于海洋、商业、管理能力和深厚自然崇拜的辉煌文明。
迈锡尼:阿伽门农的金面?
展区氛围陡然凝重。黄金——耀眼、冰冷、象征无上权力与荣光的黄金,成为这里的绝对主题。
一顶由无数弯曲野猪獠牙精心缀联而成的头盔,散发着粗粝刚猛的气息,瞬间将人拉入荷马史诗中血腥残酷的特洛伊战场——战士们头戴獠牙盔,“像凶猛的野猪一样”冲锋厮杀(《伊利亚特》卷十,描写奥德修斯与狄俄墨得斯夜袭敌营)。它们是最好的防护,也昭示着佩戴者那被战神阿瑞斯附体般的嗜血勇力。
然而,最令人屏息的,是正前方展柜中那一枚著名的“阿伽门农金面具”。尽管现代考古无情地粉碎了发掘者施里曼的浪漫猜想——“面具真正的主人后经证实是迈锡尼文明早期统治阶层的一员,其所处时代比传说中阿伽门农的时代要早三百年”——但它摄人的威严丝毫未减。
由整张厚金箔精心打制,覆盖在王者遗容之上。轮廓线条刚硬,如刀斧凿就;鼻梁高挺如崖壁;双眸紧闭,睫毛的线条却细密如生;嘴型紧抿,传达出超越死亡的森严意志和权力感。它精准地捕捉并定格了死者的面容——“其形制在史前希腊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反映出以其覆盖面部的死者生前的实际样貌”。
迈锡尼文明继承了米诺斯的贸易网络和部分技术,但其精神气质却发生了深刻转向。施里曼在迈锡尼城堡宏伟的“狮子门”和坚固的卫城城墙(巨石叠砌,彰显军事强权)下发现了数座王族巨墓(如著名的圆顶墓A和墓圈A),其中陪葬着丰富的武器(青铜短剑、长矛、战车零件)、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描绘狩猎与战斗场景的武器镶嵌、华丽酒杯)。
线形文字B泥板(欧洲最早的可释读文字)则记录着一个高度军事化、等级森严、以“瓦纳克斯”(Wanax,意为王)为中心的贵族社会体系——一个围绕“战士国王”、崇尚武勋、将权力聚焦于军事征服和贵族身份的强力政体。
迈锡尼人用青铜和黄金铸造了荷马史诗中那些“胫甲精美的阿开亚人”(Achaeans)的现实躯壳。他们是勇猛的战士、精明的商人(控制着爱琴海的贵金属贸易)和宏大的建设者,他们在荷马史诗的文本迷雾下,真实地存在过。他们是普罗泰戈拉宣言中“尺度”的早期铸造者——以武力和秩序去丈量并控制他们的世界。
第二章:众神照耀中的英雄时代
荷马时代(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崩塌(约前1100年),希腊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
展区光线幽暗,仅几座粗糙的黑陶几何风格瓮罐零星陈列,其上仅饰以回纹、三角形、平行线等极简线条。这与青铜时代的绚烂辉煌形成强烈反差。
然而,历史的叙述并未真正中断,它以一种更为浪漫也更具韧性的方式在口头传唱中延续——“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的神话与传说就是他们的早期历史……被统称为史诗,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荷马史诗》”。
展区中央,一尊约制作于公元2世纪古罗马时期的“荷马头像”复制品沉静矗立。老人须发皆白,浓密卷曲如海浪;额头隆起如山峦,象征着无穷的智慧;他双目深陷空洞——后人想象这位伟大的盲诗人,正是用心灵之眼洞悉神与人的世界。这尊雕像凝聚着后世对荷马形象的全部想象:饱经沧桑、睿智深邃。
无论他是真实存在还是一位集合称谓,正如策展文字所说:“荷马,是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相传由他创作的《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乃至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被誉为西方文学的起点……古希腊人自幼便吟诵《荷马史诗》,以史诗中那些为荣誉而战的英雄为榜样,培养自己的勇气、智慧与品格。”《荷马史诗》——这部由无数游吟诗人口口相传最终定型的鸿篇巨制(《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其重要性“绝不仅在文学层面,它几乎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每一个领域”。
展柜里摊开着两部史诗的关键选段。
“别人都想吃晚饭,享受甜蜜的睡眠 / 唯独阿基琉斯在哭泣,怀念他的伴侣——”
“他望见黎明,立刻把他的快马套在轭下 / 把赫克托尔的尸首拴在车后拖着奔驰 / 沿着墨诺提奥斯的死去的儿子的坟冢绕行三匝 / 然后回到营帐休息 / 让赫克托尔直挺在尘埃里”
(《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王焕生译)
这些词句背后,是阿基里斯为友复仇的火海与赫克托尔被尸体被凌辱的哀鸣,将英雄时代的个体价值置于生死与荣辱的天平之上。另一段则来自《奥德赛》第十二卷,奥德修斯听取女巫喀耳刻的建议,为抵抗塞壬那致命的诱惑歌声,甘愿被绑缚在桅杆之上:
“她要我们首先避开神奇的塞壬们的美妙歌声 / 和她们的繁花争艳的草地 / 她说只有我可聆听歌声 / 但须被绳索牢牢捆绑,使我只能待在原处 / 缚在桅杆支架上,被绳索牢牢绑紧 / 如果我恳求、命令你们为我解绳索 / 你们要更牢固地用绳索把我捆绑”
——这是对人性脆弱清醒的认知(人对诱惑尺度不足),亦是对理性(即使被迫)高于感官欲望的颂歌。
荷马的伟大同行者赫西俄德,则用另一部重要著作《神谱》(Theogony),系统地为希腊诸神确立了谱系与秩序。“希腊神话并非从一开始就如今天这般谱系分明,” 策展文字指出,“它原本也是多地区、多民族神话的融合体。” 赫西俄德的贡献在于,“通过文学创作消除了混乱,为希腊众神确立了谱系”。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在《历史》中的评价印证了这一点:
“从什么地方每一个神产生出来……这一切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因为我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的人并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王以铸译)
至此,通过荷马的英雄诗篇和赫西俄德的神界图谱,散乱的口传神话被纳入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和等级秩序中。神获得了更清晰的属性、性格和相互关系,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起对应联系——宙斯(天空与正义)、赫拉(婚姻)、雅典娜(智慧与战争)、阿波罗(光明、音乐、预言)、波塞冬(海洋)、阿佛洛狄忒(爱与美)、阿瑞斯(战争)等等。神的人格化程度更高了,他们介入凡间事务,成为人理解世界、解释命运、树立道德标准和界定行为边界(何为虔敬?何为僭越?)的重要参照系。
神界的尺度,深刻塑造了人间的尺度。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功绩,如一把巨大的钥匙,开启了希腊人对自身在宇宙间位置的认知大门。
赫拉克勒斯雕像,公元前350﹣前325年。赫拉克勒斯为宙斯与凡人所生,他在完成十二功业的过程中,展现出超凡的力量与才智,也展示了拳击、摔跤、赛跑等各项技艺,最终成为神。他的雕像竖立在古代体育场等多处地点。这尊雕像中他的头部被狮子皮覆盖,狮子皮以“赫拉克勒斯结”的形式系在他的胸前。
还有阿波罗头像和睡熟的厄洛斯雕像等。
第三章:城邦的黎明——古风时代的尺度
古风时代(约公元前800-前480年)
展区光线逐渐明朗,空间也开阔起来,象征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启。展品开始展现出强烈的人性气息和蓬勃的生命力。
从圣火到赛场:奥林匹亚与公共精神的塑造
一件约公元前520年的青铜马具部件虽为残片,其上奔马的浮雕却充满力量与速度感,让人联想到赛道上飞驰的战车。
公元前776年,正是在奥林匹亚宙斯圣林旁那片谷地上,赛跑运动员的足迹踏响了有记载的第一届古代奥运会的号角。Athlos(竞赛/竞技)——这个深深植根于古希腊精神的词汇,在此刻成为时代的强音。正如策展所言:“最初的比赛项目是赛跑,之后发展出跳远、掷铁饼、标枪、摔跤、五项全能、拳击和格斗,以及赛马和战车比赛等多个项目。”
这绝非单纯的体育竞技,其核心是对体能极限的探索、对公正规则(尺度)的绝对尊重(舞弊者将面临严惩和巨额罚款),更是一种面向全体希腊人的神圣宗教献礼(献给宙斯)。奥运会每四年一次,成为固定节奏。它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希腊世界定期“对表”、确认共同身份的核心时刻。
无论来自雅典、斯巴达还是小亚细亚的殖民城邦,参赛者与观众都视彼此为Hellenes(希腊人),共享同一种语言、崇拜同一批神明、遵循同样的竞赛规则。奥运火炬点燃的,是超越狭隘城邦的地域认同感——共同的血缘和语言、共同的祭坛和宗教崇拜,以及共同的在城邦里生活的方式,让身处各地的城邦居民都毫无疑问地确认自己是希腊人。
个体价值的彰显(成为奥运会冠军是无上荣耀)与公共精神的凝聚在此达成完美统一。德尔斐阿波罗圣所那“认识你自己”(Gnothi Seauton)和“凡事勿过度”(Meden Agan)的神谕,正是对这个蓬勃发展时代在个体价值与集体伦理间寻找“度”的警世箴言。
库罗斯与科莱:人体艺术的觉醒
展区核心区域陈列着一排青年男女立像——古风时代的“库罗斯”(Kouros)与“科莱”(Kore)。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标志着希腊艺术史上的重大转向:人类身体成为艺术表现的绝对中心和主题。库罗斯们,通常是裸体的青年男子,如那尊发现于雅典的石灰石雕像:身形挺拔如柱,双臂紧贴身体两侧,一脚微微前跨(埃及雕像的典型姿态),带着一丝不自然的僵硬。但仔细观察,他们腿部肌肉的起伏、关节的刻画已显露出对真实人体结构的关注。科莱少女们则身着精细褶皱的束腰外衣(Chiton)和披肩(Himation),姿态同样端庄直立,但面部浮现出一种被后世称为“古风式微笑”(Archaic Smile)的含蓄表情——一种对内心愉悦状态的早期探索,尽管仍显模式化。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雕塑家开始尝试用更自然的手法表现人体的比例和姿态。”
这标志着“希腊艺术对自身的凝视”——人自身形态的美与和谐,被视为宇宙秩序的生动表达和值得被呈现的最高主题,是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视觉艺术领域最震撼的回响。
贵族、重装步兵与城邦的兴起
古风雕塑群像旁边,是几件重要的铭文石碑和日常用具(如贵族宴饮用的大型陶酒器Mixing Bowl)。它们共同勾勒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图景。“考古发现表明……土地贵族在这一时期崛起,凭借土地、牲畜、掠夺和交易积累巨额财富。随后,城邦应运而生。”
城邦(Polis)——“是以单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农村地区的小型国家”——它不仅是一种国家形态,更是一种“公民共享身份认同的政治共同体”。财富的积累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贵族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
然而,一种新的力量也在崛起——重装步兵方阵(Hoplite Phalanx)。这是一支由拥有一定财产(能负担金属盔甲与武器)、接受过共同军事训练的自耕农公民组成的军队。密集的方阵作战强调团队合作与纪律,强化了公民的平等意识和对共同体安全的共同责任。方阵士兵的勇敢关乎城邦的存亡,个体的价值(战士)必须融入整体(方阵),个体自由与集体责任在方阵的“人墙”中寻求一个共存的尺度。贵族与富有的自耕农(未来的公民中坚)之间,关于政治权力的博弈与分享,成为古风时代后期城邦政治的主线。
第四章:璀璨的古典刻度
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前323年):战争、民主与思想的黄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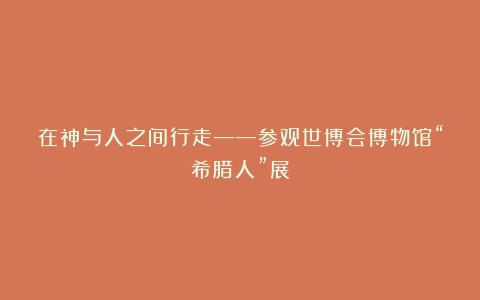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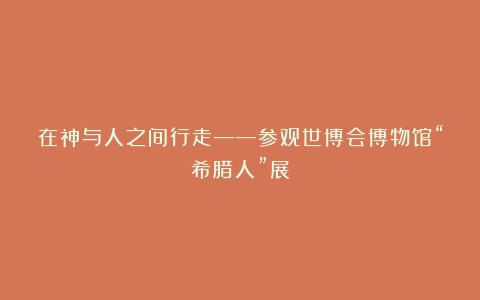
展区进入高潮,光线愈加明亮,格局宏大。这里充斥着竞争与成就的张力,展现出人类文明早期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双头鹰:雅典与斯巴达
展区入口被巧妙地设计为一个精神上的分水岭。右侧,一尊公元2世纪古罗马仿制的“雅典娜头像”高悬。她头戴战盔,智慧女神的锐利目光似乎穿透时空,俯瞰着她心爱的城市(“雅典以她的名字命名”)。那冷峻的大理石面庞原作的灵感被认为来自菲迪亚斯——帕特农神庙的设计灵魂人物。
展厅中“伯里克利于雅典卫城”引人注目。一些展品再现了伯里克利时期的神庙群落:帕特农(Parthenon)傲立中央,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无上荣耀;山门(Propylaea)雄伟壮美;胜利女神小庙(Temple of Athena Nike)精巧挺拔。
沙盘边刻着伯里克利公元前431年葬礼演说中的名句:“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Our city is an education to Greece)。” 这句豪言背后,是改革家梭伦废除债务奴隶、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划分为百个自治德莫(Deme)并创设五百人议事会、厄菲阿尔特削弱元老院权力等一系列向民主迈进的改革累积的成果。
雅典公民
雅典为“人”的尺度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定义——公民身份。“只有公民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
展陈的“公民大会会场模型”(Pnyx hill)、“五百人议事会”构成原则的详细说明表格(10个部落抽签各出50人)
以及一块保存完好的“授予列奧尼德斯荣誉公民的法令石碑”(约公元前440-427年)
共同构成一个精密运转的政治机器——主权在民(年满20岁男性公民)、抽签产生大部分公职、法治高于个人意志、公民对城邦的直接管理与义务担当。
普罗泰戈拉的思想在此第一次找到了大规模实践的土壤——人,作为城邦的公民,通过集体的理性判断(尽管远非完美),成为衡量公共事务与建立政治秩序的尺度和仲裁者。
雅典的精神中心是广场(Agora)——不仅仅是集市,更是公民政治生活、社交、商业、辩论、哲学萌芽的公共空间。“雅典广场建筑复原图”生动展示其复杂功能与勃勃生机:神庙、柱廊、议事厅、剧场、法庭、市场比邻而立——一座开放的城市客厅。
而一件精致小巧的青铜砝码静静地躺在展柜中,上面铭刻着价值单位,它象征着广场交易的公平准则——经济尺度(Economy,源自希腊语oikonomia,家政管理)亦是公民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德摩斯梯尼头像 公元2世纪
演说在雅典政治和法律生活中至关重要。演说家们通过法庭答赛、政治申诉和公开演讲向公民们传达自己的观点。德摩斯梯尼是古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是雅典自由法坚定支持者,反对马其顿的统治者腓力二世,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雅典人为纪念他,于公元前280/279年为其打造雕像,此大理石头像应是依据铜像制作而成。
然而在分水岭左侧,展区氛围陡然变为铁血与纪律。一块巨大的黑釉斯巴达双耳瓶(用于盛放葡萄酒或橄榄油)浮雕上,简练刚硬的线条描绘着战士行进图,传递出斯巴达的军事铁律。
一件打磨光滑的青铜斯巴达士兵胸甲(仅限贵族精锐“骑士”或高阶军官使用),其内侧弧度专为强壮肌肉量身定制,冰冷坚硬中透出力量的压迫感。文字叙述聚焦温泉关战役:“斯巴达战士以勇猛著称,是古希腊军事卓越的象征。
公元前480年,300名斯巴达战士在国王列奥尼达的率领下镇守温泉关……尽管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斯巴达勇士的事迹却被世代铭记与称颂。” 列奥尼达那句著名的“Μολὼν λαβέ”(Molon Labe! ——“来拿吧!”)的回响被镌刻在背景墙上,成为勇悍的千古绝唱。
斯巴达的尺度是单一的、绝对的:个体完全融入集体(国家),生存的价值在于为城邦的生存与荣誉而战。“斯巴达教育(Agoge)”将男性公民从儿童期就进行严酷的体能、忍耐力和服从性的训练,以造就毫无杂念的战士。它的强盛是以牺牲文化艺术多元发展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曾评价斯巴达为“一个训练营而非城市”。雅典与斯巴达,民主的活力与军事的纪律,自由的辩论与绝对的服从——古典希腊呈现出两条几乎相悖的价值坐标轴,却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对组织形态和人性的双重探索坐标。
众神之尺:悲剧舞台上的拷问
雅典卫城的东南侧是西方戏剧的发源地﹣﹣酒神狄俄尼索斯剧场,所有现存的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初创作的古希腊戏剧几乎都曾在此上演。
观看戏剧演出是雅典公民非常重要的一项公共生活,政治、司法、战争、伦理等社会议题被搬上舞台,以戏剧叙事引发观众反思与评判,通过共情时代危机引发社会思潮。
狄俄尼索斯半身像。公元前380-前360年。陶。这件雕像展现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形象,他右手持酒杯,左手持一只蛋。蛋可能象征着生育,也可能代表重生的冥界符号。酒神与醉酒、舞蹈、音乐和戏剧表演关系密切,古希腊戏剧的起源常常归功于他。酒神节上,城邦会组织戏剧比赛,参加比赛的诗人必须创作四联剧(包含三部悲剧和一部萨提尔剧)。萨提尔剧在形式上与悲剧有相似点,但内容轻松诙谐,缓解了观众因观看悲剧而产生的沉重情绪。
更早时期出土于奥林匹亚的“斯芬克斯青铜像”(约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这件本是船只装饰的坐姿人面兽身雕像,以其威严神秘的气质,无言地诉说着泛希腊圣地的古老信仰。
这件斯芬克斯雕像原为一艘船只的支撑构件。雕像呈现为坐姿,头部朝向前方,头戴繁复的头饰,展现出典型的狮身人面的特征。在索福克勒斯最著名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中,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外的山上,传诵一道谜语,问什么动物有时两足。有时三足,有时四足,这东西脚最多时,最是软弱。凡是回答不出来的人,都将被它处死。
一件公元前400-前375年的红绘调酒坛,描绘了爱神阿佛洛狄特在萨提尔们簇拥下诞生的场景,神话母题被搬上舞台。
而最震撼的展品是两件精雕细琢的喜剧面具石雕与悲剧面具石雕(分别约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及3世纪早期)。
喜剧面具扭曲夸张,鼻翼如豆,嘴角咧至耳根,嘲讽尽显(“喜剧的内容主要聚焦于对个人和社会的批判、以及政治讽刺”)。悲剧面具则呈现出肃穆的哀伤,女性角色眼帘低垂,泪痕似乎清晰可见,传递出命运的无常与痛苦之深。
古希腊悲剧里的生命难题
墙面上镌刻着三位伟大悲剧诗人的核心选段,如同三道划破灵魂天空的闪电: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我不听你的话, / 我要把事情弄清楚。” ——真相(尺度)的渴求VS命运的圈套?明知真相将引向毁灭,当信使劝解俄狄浦斯放弃追查身世时,这句决绝的回应是个人意志对既定命运秩序的挑战。当发现自己是弑父娶母的凶手后,刺瞎双眼,流放自我,则是对自身尺度的彻底否定与对神谕尺度的绝对屈服?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可是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 / 而喜欢跟着人爱。” ——神律(埋葬亲人)VS人法(国王禁令)?面对代表国家意志的国王克瑞翁禁止安葬叛国兄长的命令,安提戈涅以人伦天性为尺度,选择遵从神律,结果付出生命代价。她的尺度基于爱(Philia),一种超越政治分野的血缘与伦理亲情。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爱情没有节制,便不能给人以光荣和名誉。” ——疯狂的爱(尺度)VS背叛后的极端复仇?美狄亚的复仇烈焰焚烧了负心丈夫的新欢及其父亲,更亲手将刀刺向自己的孩子。这毁灭性的行为本身,正是对“失去节制”(尺度崩毁)的爱最惊心动魄的控诉——当激情冲垮理性的堤坝,带来的是彻底的灾难。无节制的爱(Pathos)将导向自我的毁灭。
悲剧大师们在舞台上设置了永恒的困境:在人(理性、意志、情感)与神(命运、法则、秩序)之间,在个体价值(如安提戈涅的亲情)与城邦法律(克瑞翁的禁令)之间,在激情(美狄亚的爱与恨)与理性之间,何处是那合理的、可接受的边界?它们探讨的正是普罗泰戈拉宣言中的核心难题——人以何为尺度?以及当不同尺度(神律/人法、个体/集体、理性/激情)发生激烈冲突时,悲剧的命运必然降临吗?
观看悲剧的过程,正是城邦公民在悲剧的“卡塔西斯”(Katharsis,净化/宣泄)功能中集体反思价值冲突、校准个体与共同体行为“合理尺度”的过程。这是雅典民主精神中最深邃也最沉重的实践——面对生命的根本性矛盾,让理性在情感的风暴中艰难导航。
被定义的边界:女性的世界
然而,古典雅典的“人”之尺度,存在一个巨大的阴影地带——女性。展品中,精美但内容受限的图像揭示了她们的生存困境:一件红绘提水罐上描绘了妇女在喷泉房打水的日常;墓碑浮雕刻着女性端坐或侍立于男性亲属旁的画面;白地细颈瓶上女主人与仆人检查珠宝或梳理头发……策展文字清晰而冷静:“雅典公民的范畴里不包含女性,女性那时不能投票,也不能独立拥有财产或继承土地。她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局限于闺房之内……只有在重大的宗教节日……她们才会公开露面。”
雅典娜的荣光庇护着男人们的智慧与战场,却鲜少照耀她们。她们的“尺度”被限定在Oikos(家)的围墙内——照料家庭、抚育子女、管理家务、从事纺织。即便伯里克利颂扬的民主荣光,也并未普照半数的城邦成员。阿佛洛狄特的爱与美之神殿里,女性形象被反复膜拜,然而现实中,真实的阿提卡女性却很少能在公共领域留下自己的声音。她们的存在,揭示了普罗泰戈拉命题中的盲区——“人”在当时往往隐含着成年男性公民的身份定义。
第五章:普世的融合——希腊化的广阔尺度
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从亚历山大到帝国黄昏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是希腊的艰难时期。当时的马其顿王国既要应对希腊城邦间的纷争,又要抵御外族的入侵。当22岁的腓力二世继位时,马其顿已摇摇欲坠,但这位年轻的国王兼具军事天才与政治智慧,在位24年,通过大力改革扭转了局势,使原本地处边远的马其顿王国一举成为希腊北部强国。
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被推选为全希腊人的领袖和远征波斯的同盟统帅。然而,战役尚未打响,腓力二世却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接任。亚历山大大帝,不仅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击溃波斯帝国,更率军东征十年,横扫小亚细亚、埃及,直抵印度河流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将统治范围扩展至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统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年仅33岁,但其建立的庞大帝国宣告了希腊化时代的到来。
国王腓力二世
腓力二世是马其顿王国崛起的关键人物,其一生以军事革新与政治改革重塑了古希腊的地缘格局。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结束后,在科林斯举行的泛希腊城邦大会上,腓力二世被推举为”希腊同盟统帅”。阿伽门农只是传说中希腊联军的统帅,而腓力二世却是希腊历史上首位实现政治统一的领袖。
亚历山大大帝
一尊约公元2世纪的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头像”复制品矗立中央,成为时代的象征。这位年轻的征服者波浪卷发下双眉微锁,鼻梁挺直,目光似乎望向无限远方。头像侧面细节揭示其神性特征:“头部缠绕着一条握状束带,这是祭司身份的象征……在创作过程中,亚历山大大帝被赋予了神性的特质”。这尊“理想化的”肖像展现了后世对他不朽传奇的理解。
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本身是传奇——“击溃波斯帝国,更率军东征十年,横扫小亚细亚、埃及,直抵印度河流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将统治范围扩展至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统领”。但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理念上的变革——“他改变了自古典时代以来希腊与波斯之间长期对抗的军事格局,采取各种举措革除东西方旧有藩篱,催生出融合东西方特征的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创造了一个开放包容、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帝国的行政中心如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安条克等成为新的文化与思想中心,其“开放包容、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极为鲜明。这些城市不仅是希腊文明的辐射点,更成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平台。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后,其帝国分裂为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等希腊化王国,持续三百年的希腊化时代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文明演进的轨迹。
疆域拓宽与文化重塑
一件出土于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希腊式青铜头盔,其基本形制是希腊的,但在装饰细节上融合了东方元素。一件塞琉古王国的钱币,一面是希腊化国王头像,另一面则是当地的神祇或象征。一面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石刻墓碑上,死者雕像融合了希腊雕刻的写实技法与埃及人像的正面律特征……这些物件无声地诉说着Koine(意为“共同”)——一种混合了希腊语、波斯语、埃及语等词汇的新希腊共通语——如何成为官方交流的“尺度”。
希腊化时代的精神面貌与古典时期有了显著不同。展出的雕塑更多展现个体情感的瞬间与挣扎。
“亚历山大酒神雕像”呈现一种迷醉中的狂喜状态;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一尊小雕像,不同于之前的健壮英雄),后期作品中显得沉郁、疲惫,甚至带点忧伤,更强调其作为背负使命的受苦英雄而非单纯的力量象征。
展区一件引人注目的展品是“赫耳墨斯(墨丘利)像”(公元1世纪中期罗马制)——作为商旅之神,他的形象已彻底罗马化,简洁干练的短发取代飘逸卷发,手中握着的钱袋象征贸易繁荣。“赫耳墨斯的特征和神话被罗马人融入在他们原有的神祇墨丘利之中”,这是文化融合的另一面。
尺度的融合与远方的回响
“亚历山大头像”旁陈列着一顶极其华美的“金花冠”,金叶层叠交缠,镶嵌宝石。这是希腊化世界奢华工艺的典范,其所有者可能是总督、富商或某个位高权重祭司阶层的一份子,象征着财富与新贵的崛起。
另一块重要的铭文石碑——“授予阿斯克勒庇奧多洛斯荣誉的法令石碑”(公元前323/322年雅典卫城出土)则揭示着雅典城邦在强权时代试图维护自尊的努力:“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显示,列奧尼德斯是城邦间的外交官,在城邦间的公共事务中为雅典利益服务。” 雅典虽失去独立领导地位,但其文化软实力与历史积淀依然使其在希腊化世界拥有一席之地,法律条文的格式与精神仍在延续。
希腊化时期的最大贡献是突破性思维尺度的拓展。柏拉图学园(Academy)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Lyceum)在雅典延续其哲思;而在亚历山大里亚,依托“缪斯神殿”(Mouseion)——人类早期“科学院”/“大学”的雏形——荟萃群英。这里不仅是巨大图书馆的所在地(当时世界的知识仓库),更汇集了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
·欧几里得(Euclid):在其划时代巨著《几何原本》(Stoicheia)中,以无可辩驳的公理和逻辑演绎,构筑了一个纯粹、抽象、完美的几何宇宙。他确立的数学推演模式(源自希腊语mathema,学问)成为后世理性探索的范式,定义了数理逻辑的尺度。
·阿基米德(Archimedes):他的发现横跨数学、物理和工程。从杠杆原理到流体静力学(“尤里卡!”),从圆周率计算到复杂的几何体体积和表面积的突破性研究,他代表了经验观察与数学抽象能力的巅峰结合——一种前所未有的综合理性(Synthesis)尺度。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这位大图书馆馆长首次精确测算出地球周长(源自希腊语geo土地 + graphia描述)。他以几何学和天文观测为基础,通过精密论证挑战常识,完成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尺度上最伟大的壮举,其方法闪烁着理性光辉。
希腊化的多元融合既是亚历山大大帝雄心的延续,也为后来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文明奠定了基石。神性与人性在此进一步交融,个体的情感体验得到更丰富的表达,知识的尺度随着地理疆域的开拓和系统性研究(历史History,来自historia调查)而无限延伸。“人”的尺度在这个时代,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地理、文化和智力疆界,同时,也因为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产生了独特的焦虑和对个体命运的思考(希腊化哲学如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对个人安顿的追求)。
结语:双河交汇,东西融合
展览即告尾声。公元前138年,正值希腊化时代,在距离古希腊万里之遥的中国,一个名叫张骞的人从长安启程,一路向西跋涉。他穿越河西走廊,历经十载艰辛,终于抵达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西汉称大夏,位于今阿富汗一带)。在此西域之地,他意外发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布匹和竹杖﹣﹣原来中国商品早已通过印度流入希腊化世界。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连接起古老东方与遥远西方的万里通途。
作为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明古国,中希两国如同两条古老的河流,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带着各自的智慧与荣光,共同汇入人类文明的海洋。
我的脑海中即刻浮现这样的场景:玻璃展柜中,褪色的蜀锦残片与依旧闪耀的金花冠隔着两千年的风尘静静对视:一方以汉字铭记天象,一方用金叶编织神话;它们曾同时呼吸在巴克特里亚的阳光下,如今在同一束聚光灯里完成无声的对话。
走出展厅,上海夏日的阳光炽烈依旧,但内心的震撼久久难以平复。8000年的历程浓缩于步履之间,让我重新检视普罗泰戈拉那句箴言的分量。
古希腊人从未停止尝试成为“万物的尺度”——从新石器时代用石斧丈量土地谋生存,到荷马与赫西俄德为众神编织秩序;从古风时期在奥林匹亚的赛场上竞争人的极限,到古典时代在雅典广场确立公民的公共尺度、在悲剧舞台上悲怆叩问人神边界的尺度;再到希腊化时代将文明熔炉的尺度拓展至亚非欧大陆、在知识神殿里建立理性推演的逻辑尺度……这尺度是多元的、冲突的、不断演化的,包含着理性与激情、个体与集体、自由与责任、开放与保守的永恒张力,也隐含着如古典雅典将女性排除在公共尺度之外的巨大缺憾。
“希腊人”展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尺度”具象化为无数的面容、器物、故事与制度。荷马时代流浪战士的粗粝、米诺斯女神扬臂时的迷狂、迈锡尼金面具的威严、伯里克利演说词的激荡、德摩斯梯尼眼神的忧虑、俄狄浦斯王追寻真相的执着、美狄亚复仇的毁灭烈焰、亚历山大凝望的远方…… 无数“人”的具体尺度,共同汇聚成为人类理解自身、构建秩序、创造文明的那些最初的刻度。
它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文明的价值刻度尺,都离不开对人的基本定义、对公共空间的构建、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理解、对理性与情感边界的确认以及对未知不断探索的勇气。这便是“希腊人”为我们留下的,一把衡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永不生锈的精神量具。无论时空如何变迁,普罗泰戈拉的回响——人如何作为自身与世界的主体,去发现、命名、丈量并塑造他的现实命运——依然是我们永恒的叩问与路标。
202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