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雅众」星标,精彩不再错过
让我们准时相见!
回到《没有内容的人》是重要的,
它正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卡洛·萨尔扎尼
《没有内容的人》是哲学家阿甘本在28岁时出版的作品,激进而根本地探讨了美学问题,并从中体现出了极强的问题意识,令人能够领略阿甘本风格和理路在艺术哲学中的发端。
从十七世纪的品位到康德美学的否定性,从狄德罗的小说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从丢勒的《忧郁》到卡夫卡和本雅明,阿甘本以艺术问题的反转钩沉整个西方文化的古今与命运,直视其虚无与异化,并呼唤回归原点和破旧立新。
今天分享卡洛·萨尔扎尼为本书所作的后记。
*本文约5700字,静静阅读约需一刻钟。
在美学之外:
阿甘本方法的起源
卡洛·萨尔扎尼
01
在这篇简短的后记中,我想强调的是,阿甘本在年仅二十八岁时出版的《没有内容的人》,就已经展示出很多标志这位哲学家后来作品的特点了:从极度的博学到风格的优美,再到在他的整个哲学阐述过程中,对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从本雅明到卡夫卡的主要人物的使用。*因此,这部早期作品揭示了一种在更成熟的作品中变得更明确、更有意识的“实践”或“方法”,那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批判当下:寻找当下的概念或意识形态根源(即后来所谓的“发生研究”*),并反过来在语义和词源的层面上研究那些根源。而且,在阿甘本那里,对看似有限的现象(这里是美学)的批判,总是内嵌于一种更加普遍的,对西方“形而上学”——即西方文明的思想从其起源开始的发展——的批判。最后,如果当下被体验为一场“危机”,被认为是一条疏离之路(“形而上学”)的极端的、决定性的极限,那么,我们既不能通过回到文化史上更加“本真的”阶段,也不能通过彻底的克服——这种克服完全把自己从当下的特征中解放出来——而只能通过完整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个当下当作“我们自己的”来接受,来克服这场危机。
不过,就像亚历克斯·默里指出的那样,在这里,这个“方法”还不完整:强烈的海德格尔取向,使阿甘本把现代性假定为一次必须克服,以重获某种更为“原初的”状态的根本断裂。的确,本书的论题正是,美学作为一门艺术“科学”的出现,分离(疏离)了艺术作品和它的自然环境和本质,即人在大地上的“栖居”。在这里,对阿甘本来说,我们时代的迫切任务是对美学的意义本身提出问题;只有“毁灭”美学,艺术作品才能重获其“原初结构”。书中的分析是倒着来的,先从尼采对康德艺术定义(“艺术是一种无私趣的快感”)的批判开始:尼采想要一种重获其在希腊世界中曾经拥有的地位的,作为一种让人充满“神圣的恐怖”的体验的,使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他的城邦的艺术,他因此而举例说明了现代对作品的构想中的一种分裂。今天,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可能重新合而为一的两面:艺术家体验的艺术是一种活的现实,是一种幸福的许诺;而观看者体验到的艺术,则是美学判断中反映的一组仅仅是“有趣的”(也即无生命的)元素。这个分裂也贯穿了美学本身,就它从在从感知(aisthesis)来规定作品的同时,又从一开始就把作品预设为艺术家特殊的、不可简化的“天才”结出的果实而言。
阿甘本把这个分裂追溯到十七世纪中期,随着“有趣味的人”的诞生,天才与趣味、艺术家与旁观者也随之而分裂:如果说趣味的诞生为旁观者的感受力创造了一个运用能力的空间的话,那么,工作的创造,则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生意,他因而把自己和社会活的构造分开,孤立进美学的古怪空间。现在,艺术变成了绝对自由,在自身内部寻找自己的目的和基础,不需要任何自身之外的内容:艺术家变成了书名所说的“没有内容的人”(这个说法又可以追溯到罗伯特·穆齐尔的书名《没有个性的人》),“他除一种持续的出现——从表达的无中出现——外,没有其他同一性,除这个难以理解的位置——在他自己的这边——外,没有其他一致性”。*另一方面,康德理论化的(支撑我们美学概念的)审美判断是一种“否定神学”,它以一种纯粹否定的方式来规定美:没有兴趣的快感,没有概念的普遍性,没有目的的目的性,没有规范的规范性。通过从艺术不是什么来规定艺术,审美判断把非-艺术变成了艺术的内容,阿甘本因此写到(他在这里重复了他未来会使用的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印刷花体,这种印刷方式后来因为被德里达大规模使用而得名sous rature,即“被抹除”),它“在一切地方,一以贯之地把艺术裹进艺术的影子”并使这样的艺术成为美学之地的最高价值。*这种将审美判断建立在一个没有任何规定理念的基础上的奠基,对阿甘本来说,就像是一种没有任何稳固基础的“神秘制度”,但在美学的维度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02
在这里,阿甘本在根本上遵循了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1838)。黑格尔把处在其命运极限上的艺术看作一种自我否定的否定,一种“自我消灭的无”:它贯穿它的所有内容,却永远不能抵达一件肯定的作品,因为它永远不可能与任何内容统一,艺术因此也就变成了纯粹的否定力量,它想要作为无的实在,因此是“虚无主义”。这个术语显然不是黑格尔的,而是海德格尔的,而这本书关于现代性中艺术本质的整个第一部分的结论,也是海德格尔式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达到命运极点的艺术的本质一致:在二者那里,对人来说,’是’都注定是’无’。只要虚无主义依然秘密地统治着西方历史的进程,艺术就无法走出它无尽的黄昏。”*后面的章节则拿这种虚无主义与古希腊人对艺术作品的“原初”构想对照,并且这种构想也是从海德格尔诠释的角度来解读的。共同的线索是这样一个想法,即在过去,艺术是人在大地上“栖居”的基本模式,这种栖居在本质上是“诗的”,就诗(poiesis)是一切事物被生产-引出,即不“是”到在场,而是到“是”的方式而言。这种诠释基于海德格尔的三篇重要论文,《艺术作品的起源》(1950)、《关于技术的问题》(1953)和《……人以诗的方式栖居……》(1954)。在这种构想中,艺术作品的“原初性”不像对我们来说的那样,在于其所谓的“独一无二性”,而在于它接近“起源”:“艺术作品是原初的,因为它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着某种与其起源、与其形式本原(ἀρχή)的特殊关系,即它不只来源于后者,与后者一致,它还一直处在一种永远接近后者的关系中。”*这个作品的“原初结构”就是在poiesis中,作为人在世界中的原初空间即人的“栖居”空间的基础的那个东西:通过它,人*才体验到他“在世界中的存在”,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才会对行动开启;而且,在诗的行动中,人触及一个更加原初的时间维度,时间的线性连续体被打破了,而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找到了他自己当下的空间。因此,艺术的问题(和后来政治的问题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接着,阿甘本按照汉娜·阿伦特在《人的状况》(1958)中的分析,追溯了致使希腊人典型的人的行动的等级结构被反转的演化:现代性把praxis(一种作为意愿的直接表达,人们在作品之外思考的“做”,即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摆到了poesis(即建造世界并因此而开启“真”的空间[海德格尔的去蔽,a-letheia]的生产-引出)的位置上。如果说在古代,人在大地上有一种“诗的”地位,如果是他“以诗的方式”居住于世界,那么,现在他有的,则完全是“实践的”地位。通过详细的“谱系”分析(尤其是对在马克思和尼采那里的发展的分析),阿甘本把这个过程的终点定义为一种“意愿的形而上学”。就艺术而言,这不但意味着美学建立在“艺术是艺术家的创造意愿的表达”这一想法的基础上,也特别意味着艺术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放逐到它自己的本质和起源之外了。
因此,指导这个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以一种原初的方式进入一种新的诗(ποίησις)何以可能?”*答案不明显,也不能到“恢复”失去的“原初性”的方向上去找。阿甘本指出,当代艺术标志着一场美学无法克服的危机,并把现成品和波普艺术识别为作为这场危机的基础的那个分裂的极其混乱和颠倒的点:通过混淆独创性*与可再生产性、诗和技术,它们都在人的“诗的”活动中承载着分裂,把分裂发展到这样的极致,即进入在场的只有诗的力量的“缺乏”本身;但这样,它们也指向美学之外,指向一个依然不确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的生产-引出的活动可以与自身和解。下面这段话,是阿甘本后来所有“生产”都具有的那种哲学实践(praxis)特征的范例:
从“艺术作品”的特权地位的这种自我压制——如今,这种压制把人的生产-引出这个被分成两半苹果的、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两面又聚集到了一起——出发,有一天,走出美学和技术的沼泽,恢复人在大地上的诗的地位的原初维度将变得可能。*
这个对出路的寻找,以这样的假设为起点,即危机本身是它“专有”的。答案和替代选项只可能出自对极限的深入思考。这使得阿甘本在结论章节突然改变了语气:在一个后来几乎变成方法,被勒兰德·德·拉·杜兰塔耶称作“机械降
本雅明”(Benjamin ex machina)*的姿势中,本书强烈的海德格尔取向让位给了强烈的本雅明式的分析,这种分析把美学问题放进一种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历史命运的解读,而在这里,这场危机被解读为一场传统的危机。在现代性中被理论化为一种瞬间的、难以捉摸的显现的美学之美,变成了传递的不可能性、文化可传递性毁灭的形象,现在,文化只能是积累和博物馆化的对象了。在这个累积的文化中,人再也认不出自己,再也找不到自己在时间和历史中的行动的标准了。但波德莱尔,尤其是卡夫卡(强烈的本雅明意义上的卡夫卡)指出了一条出路:通过抛弃艺术假装是“真”的伪装,卡夫卡把传递行动本身当作传递的内容,把人在“真”和历史面前的延迟变成了诗的本原,并以这样的方式,消除了有待传递的东西和传递行动之间的差距,使艺术更加“接近神话-传统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被传递的东西和传递行动)这两项之间存在一种完美的同一”。*
本书以这样一个意象开篇,也以这样一个意象作结:“根据这个原则——即只有在着火的房子里,根本的建筑问题才第一次变得可见——艺术也只有在抵达其命运的极点之后,才会使自己原初的计划变得可见。”*德·拉·杜兰塔耶指出,这个意象改编自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1925)结尾的那个著名意象*:“在伟大建筑的废墟中,计划的理念的表达比在不那么伟大的建筑中更引人注目,无论后者保存得多么完好。”*救赎也要到这些废墟、这些火光中去找。
03
《没有内容的人》还展示出其他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这些特点是阿甘本后来作品的标志。在这第一本书中,马丁·海德格尔和瓦尔特·本雅明已经作为阿甘本的两大“老师”出现了。阿甘本在1966年和1968年参加海德格尔在普罗旺斯勒托尔举办的研讨班(第一次关于赫拉克利特,第二次关于黑格尔)时,亲自见过这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来普罗旺斯拜访诗人勒内·夏尔,而阿甘本最初就是经夏尔的门生之一,作家多米尼克·福尔卡德介绍参加这两次研讨班的。*虽然阿甘本当时已经写完了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与人的概念的学位论文(1965),但对他来说,这次与海德格尔的相遇才使他“真正遇见了哲学”。*2022年,阿甘本把他在这两次研讨班上做的笔记出版为一本名为《思想的时间》(Il tempo del pensiero)的小书*。
也是在那几年,他开始阅读本雅明,读的是本雅明的第一个意大利语译本《新天使》(Angelus novus),并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未对其他任何作家产生过如此令人不安的亲近感”。*阿甘本反复使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奇妙的,被他自己描述为“两位对彼此持强烈批判态度——并且后者很可能甚至都不知道前者(我问海德格尔有没有读过本雅明,他说没有)——的作家组成的星丛”的理论组合:两位“互为解药”*的哲学家拯救了他,或者更具体地说,“一切伟大作品都包含一个影子和毒药的部分,它并不总会为之提供解药。对我来说,本雅明就是那个解药,他帮助我从海德格尔那里活了下来。”*但反过来说也没错:“这两位[哲学家]像毒药和解药一样对彼此生效。本雅明帮我解了海德格尔的毒,反过来说也一样。”*
《没有内容的人》中,另一个将在阿甘本未来作品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人物是汉娜·阿伦特。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她,但他们之间后来有过一次简短的通信:就像阿甘本在后来一次访谈中讲述的那样*,在1968年勒托尔第二次研讨班期间,在休息的时候,他们谈到了1968年五月事件,以及像阿伦特、马尔库塞那样的作家;海德格尔把阿伦特的地址给了阿甘本(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阿伦特档案中保存的那封信中,阿甘本写道是福尔卡德给了他地址),阿甘本给她写了一封信,把他新写的一篇论文《论暴力的限度》(1970)寄给了她,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阿伦特著作的启发。*在《没有内容的人》之后,阿甘本没有在作品中提到过阿伦特,直到《神圣人》(Homo sacer,1995)——或至少是为之做准备的研究——从那时起,阿伦特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参照点。
《没有内容的人》中也出现了阿甘本方法论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到情况最极端指出去寻找救赎这个指导原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起源,那就是来自对荷尔德林的《拔摩岛》一诗的引用:“可危险所在之处,也会生长出/救赎的力量(Wo aber Gefahr ist, wächst / Das Rettende auch)。”海德格尔数次引用过这两行诗,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技术的问题》(1953)和《诗人何为?》(1946)中;而阿甘本虽然直到在《散文的理念》和《奥斯维辛的剩余》中才明确提到它们(也在比如说《不可追忆者的传统》中,在“这是我们不适的根源,也同时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句话中含蓄地提及它们),但他从一开始就含蓄但明确地遵循了海德格尔的教导,并最终把这变成了他的哲学“方法”的核心。*
最后,《没有内容的人》也展示出一种风格上的个人特质,这种风格将变成阿甘本作品的一个“常量”。正如荷尔德林诗的例子所示,阿甘本经常被指责——尤其是在英美学界——不给自己引用的材料明确或恰当的标注。虽然这种做法在意大利学界很普遍(这让英美学界很难接受),但在阿甘本那里,这么做有着非常具体的意义:事实上,就像他经常重复的那样:“对于我爱的作家,与模仿他们、重复他们相反,我试图找到这样的点,即让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发展他们,可以把他们拉到这个点上,可以在这个点延续他们的那个点。”*由此,就像他在《万物的签名》前言中写到的那样,“敏锐的读者”应该自行决定什么是从被引用的哲学家那里参考来的,什么是作者本人的,什么是两种情况皆有的。*不但如此,更确切地说,阿甘本把引用当作一门“艺术”,即本雅明所说的“没有引号的引用的艺术”来使用。阿甘本在《剩余的时间》的结尾提到了本雅明的这一做法,但《没有内容的人》的最后一章开篇就已经提到了本雅明的引用理论,在那里,它被看作一种疏离的潜能,装载“真理,则是它在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其中一个论题中所定义的在最终审判日将它’纳入日程的引用’中,疏离它活的语境出现的独一无二性(unicità)作用的结果。”*在本雅明那里和在阿甘本那里一样,引用通过使某个观念疏离其语境,并重新赋予其语境,质疑了权威的本原,也检验了观念,现在观念只能靠自己,再无其他权威可依靠了。*
就像阿甘本的读者都会认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特点都还会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出现,变成他独创的“风格”和方法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且不论其他原因——回到《没有内容的人》是重要的,它正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注释*
-
本文的一个不同版本发表于卡洛·萨尔扎尼与埃尔马诺·卡斯塔诺合著的阿甘本导读,见Carlo Salzani and Ermanno Castanò, Introduzione a Giorgio Agamben. Seconda edizione aumentata e corretta, Genoa: Il nuovo melangolo, 2024, pp. 14-21.(本文系萨尔扎尼专门为本书改写的后记,再次致谢。——译注)
-
“发生研究”(genealogy, genealogia, γενεαλογία)字面义就是对“创始、发生、生成、生出、生产、世代”(γενεά)的研究。在中文中经常被译作“谱系学”,但这个译法容易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观念在发生后“连续的历史演变”上去。但在哲学中,它主要指对观念的“发生”特别是对其“发生语境”的研究,涉及对观念诞生前的一切事物(既包括在它之前存在的一切传统,也包括它出现的时代的现实)的考察,而不单指从当下观念向其起源的追溯和对其诸历史形态的罗列。它也不同于强调过程(从起点到终点的生成转换)和对过程的动态考察的“发生学”(genetics)。——译注
-
Alex Murray, Giorgio Agambe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79.(中译参见亚历克斯·默里:《为什么是阿甘本》,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3—84页。)
-
Giorgio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trans. Georgia Alber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4-55.(后记中阿甘本的引文均采用了本书译文,下不赘述。——译注)
-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p.43. 译文有所订正。英译者去掉了海德格尔-德里达式的“被抹除的”符号,把“艺术”翻译为“非-艺术”,但作者不是这个意思:被抹除的符号被划掉但依然清晰可读、依然在那里,表示能指不完全适合所知,但依然有一定的、必要的有用性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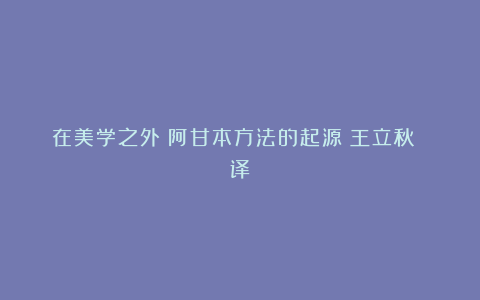
-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p. 58.
-
同上, p. 38.
-
阿甘本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系统地把男的“人”(uomo)当作一个普遍的中性词来指人类。虽然这个用法依然常见——特别是在罗曼语系的语言中——但近几十年来的女性主义批判表明,这个词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这当然构成了阿甘本阐述中的一个盲点,它使很多非常相关的问题没法被弹出来。在阿甘本的系统内部,这点是可不能发展或“纠正”的,所以在这里我不会分析或纠正它。但我觉得指出并强调阿甘本分析中的这个根本局限是重要的。
-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p. 64.
-
独创性性和原初性都是originalità,前者以“独一无二”的意义而言,后者强调对起源的接近。——译注
-
Ibid., p. 67.
-
或危机本身是专属于它的,为找到出路,人必须先“占有”本身就是自己一部分的危机。——译注
-
Leland de la Durantaye, Giorgio Agamb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31.
-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p. 114.
-
同上, p. 115.
-
De la Durantaye, Giorgio Agamben, p. 51.
-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Verso, 1998, p. 235.
-
Hannah Leitgeb and Cornelia Vismann, “Das unheilige Leben. Ein Gespräch mit dem italienischen Philosophen Giorgio Agamben”, Literaturen 2.1 (2001), p. 17.
-
Adriano Sofri, “Un’idea di Giorgio Agamben”, Reporter, 9-10 November 1985, p. 32.
-
Giorgio Agamben, Il tempo del pensiero, Macerata: Giometti & Antonello, 2022.
-
Sofri, “Un’idea di Giorgio Agamben”, p. 32.
-
Roberto Andreotti and Federico De Melis, “I ricordi per favore no”,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in Alias, 9 September 2006, p. 2.
-
Jean-Baptiste Marongiu, “Agamben, le chercheur d’homme”, Libération, 1 April 1999, p. ii.
-
Leitgeb and Vismann, “Das unheilige Leben”, p. 18.
-
Ibid.
-
Hannah Arendt, Macht und Gewalt, trans. Gisela Uellenberg, Munich: Piper, 1970, p. 35.
-
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3.(亦见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译者注)
-
对一些批评者来说,这也是这种方法的“纠结”之处;比如见Eva Geulen, Giorgio Agamben zu Einführung, second edition, Hamburg: Junius Verlag, 2009, p. 137.
-
Andreotti and De Melis, “I ricordi per favore no”, p. 2.
-
Giorgio Agambe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On Method, trans. Luca D’Isanto with Kevin Att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
-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p. 64.
-
De la Durantaye, Giorgio Agamben, p. 146.
BOOK
点 击 购 买
↓
《没有内容的人》
[意] 吉奥乔·阿甘本
王立秋 译
雅众文化 | 商务印书馆
关于译者
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潜能》《为什么是阿甘本?》《散文的理念》《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等。
主理人:方雨辰
执行编辑: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