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樊绰所著《蛮书》卷四记载:
“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
《新唐书·南诏传》也有相关记载,称阁逻凤命昆川城使杨牟利,用兵力强迫西爨白蛮20万户迁徙到永昌城。
杨牟利是洱海河蛮,白子国的臣民,他怎么又成了阁罗凤的大臣呢?
唐初,环洱海周边的平坝地区居住着以河蛮为主的族群。
这一族群又被称为“蛮”“西洱河蛮”。
一般认为,河蛮就是白蛮,也就是现今白族的祖先。
蒙舍诏皮逻阁兼并白子国后,迁都白子国国都羊苴咩城。
洱海水涨起来的时候,能漫到喜洲白蛮聚落的青石板路上。
白子国旧贵杨家门口。
咸腥的浪沫拍打着杨府门前的石狮子。
那尊汉人匠师雕的瑞兽被海水舔得湿漉漉的,像头刚从江里爬上来的水兽。
彼时杨牟利刚满十六,正蹲在门坎上,看父亲用竹篾修补被浪打烂的渔网——
网眼里还缠着几片海菜,绿得发黏,像极了白蛮人被南诏铁骑搅乱的日子。
“阿爹,乌蛮的兵又在村口收粮了。”
他忽然开口,声音被潮声泡得有些闷。
父亲的手顿了顿,竹篾尖刺破了拇指,血珠滴在渔网的破洞上,晕开一小朵暗红。
“收就收吧。”
老人低头用嘴吮了吮伤口,
“去年反抗的邓赕诏,男丁都被捆去拓东城当苦役了,家里的姑娘……”
话没说完,就被远处传来的铜铃声打断——
那是南诏税吏的马队,马铃铛响得越急,就意味着催缴越狠。
杨牟利没再说话,只是盯着石狮子底座的青苔。
那青苔在浪花里浮浮沉沉,却总能在退潮后死死扒住石头。
他忽然想起在成都求学时,先生讲过的“水无常形”。
那时只当是句空话。
此刻望着翻涌的洱海,才咂摸出点味道:
硬的石头会被浪拍碎,软的青苔反倒能活得长久。
三年后,杨牟利背着一篓晒干的乳扇,混在去南诏王都太和城的商队里。
乳扇是白蛮的特产,用牛奶熬成,薄如蝉翼,带着淡淡的奶香。
乌蛮贵族爱用它蘸蜂蜜吃。
他走得很慢,眼睛却像鹰隼般扫过沿途的关卡:
乌蛮兵腰间的铁刀磨得发亮,刀鞘上镶的绿松石是从吐蕃换来的。
关卡的木牌上刻着僰文,笔画像扭曲的蛇,写的是“白蛮过境,十抽其三”。
进太和城那天,正赶上南诏王蒙阁逻凤在广场上处决“叛逆”。
被绑在木桩上的是叶榆(今大理古城)白蛮的首领。
老人的花白胡子上还挂着血,却梗着脖子骂:“乌蛮蛮夷!迟早要被天打雷劈!”
蒙阁逻凤坐在虎皮椅上,手里把玩着颗硕大的夜明珠。
闻言只是挥了挥手。
刀斧手的钢刀落下时,杨牟利正低头给身边的乌蛮兵递了块乳扇,那兵嚼着乳扇,看行刑的眼神像在看一场闹剧。
“这老头不懂变通。”
杨牟利轻声对自己说。
他没去看飞溅的血,而是盯着蒙阁逻凤脚下的地毯——
那是块波斯毯,上面织着狩猎图,却被王靴踩出了几个泥印。
他忽然明白,南诏的王座需要的不是骨头硬的对手,而是能为它铺好地毯的人。
当晚,他用半篓乳扇换了个见南诏清平官郑回的机会。
郑回是被俘的唐朝官员,虽在南诏做官,却总爱用汉文写诗。
杨牟利跪在郑回面前时,没像其他白蛮求告者那样哭哭啼啼,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卷纸:
“先生请看,这是我算的南诏今年的粮税账册。”
纸上用汉文和僰文并列写着数字。
从各部落的稻田亩数,到收获的稻谷、青稞、荞麦,甚至连每户人家的鸡犬数量都记在后面。
郑回捻着胡须细看,越看眉头越舒展:
“蒙舍诏(南诏王族)只知打仗,哪算得清这些?你这账册,比十个税吏都有用。”
杨牟利叩首道:“白蛮人善算,善织,善冶铁。若能为大王所用,胜过刀兵相加。”
郑回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
“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倒比那些活了半百的首领通透。”
真正让杨牟利站稳脚跟的,是那场“苍山马疫”。
开元二十六年,南诏从吐蕃换来的千匹战马突然暴毙,马厩里飘着股腐臭。
蒙阁逻凤急得摔了三个茶碗——
没有战马,怎么跟唐朝争夺姚州?
众臣束手无策时,杨牟利站了出来:
“大王,马疫是因为吐蕃的草料混了毒草。白蛮人在苍山养了百年的骡马,有法子治。”
他带着三十个白蛮兽医,在马厩里守了七天七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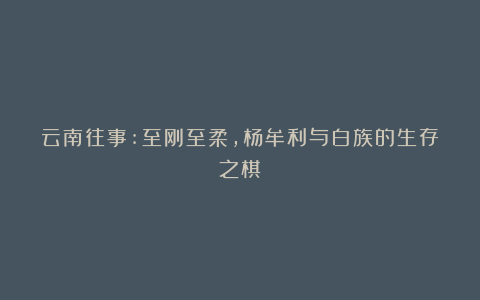
用艾草熏马厩,用龙胆草熬药汤,竟真的控制住了疫情。
最后一匹病马站起来时,杨牟利的眼睛熬得通红,身上的麻布衫沾满了马粪。
他对着蒙阁逻凤朗声道:“大王,白蛮不仅能治病马,还能养出比吐蕃马更壮的战马。
只要给我们三年,太和城外的马场,定能养出三千匹良驹。”
蒙阁逻凤盯着他,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手掌粗糙如砂纸,带着常年握刀的老茧:“你想要什么?”
杨牟利抬头,目光撞进国王鹰隼般的眼里:
“我要做南诏官,管南诏的农桑、工匠、账册。
我要让白蛮人不再被随意抽丁,让他们的孩子能念汉文。
让喜洲的渔网,能安安稳稳地撒进洱海。”
这话一出,满朝乌蛮大臣哗然。
让一个白蛮做官?
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蒙阁逻凤却笑了,他指着殿外的苍山:“苍山有十九峰,峰峰不同。乌蛮是那最高的马龙峰,能挡风雨;
白蛮该是那产茶的感通寺峰,能结出甜果子。少了谁,都不算完整的苍山。”
杨牟利穿上绯色官袍那天,喜洲的族人来了不少。
有人捧着他小时候戴过的银项圈,有人提着刚出炉的饵块,眼里的泪比洱海水还咸。
一个曾骂他“认贼作父”的老工匠,颤巍巍地递上一把锻好的铁剑:“这剑……比乌蛮人的锋利。”
杨牟利接过剑,剑身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却在他手里显得格外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太和城开了所“双语学堂”。
白蛮孩子学僰文,乌蛮孩子学汉文。
第二件事,是把白蛮织工组织起来,改良了织布机,织出的“南诏锦”比蜀锦更耐磨。
连唐朝的商人都争相购买。
第三件事,是定下“按户纳粮”的规矩,禁止兵丁随意抢掠。
有个乌蛮将领不服,被他拿蒙阁逻凤的令牌捆了,打了三十大板。
有人骂他忘了祖宗,说他把白蛮的技艺都献给了乌蛮。
可每当洱海潮声漫过喜洲的青石板。
看着孩子们在学堂里朗朗读书。
看着织工们用换来的盐巴腌腊肉。
看着不再有铜铃声惊飞塘边的水鸟。
杨牟利就觉得,那些骂声轻得像洱海上的雾。
他常站在官署里,望着远处的点苍山。
雪在峰顶闪着光。
像极了他第一次进太和城时,蒙阁逻凤手里的夜明珠。
他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不是妥协,是把白蛮的根,悄悄种进了南诏的土里。
就像苍山的雪水,看着是随溪水流进了洱海,实则早已浸润了整个坝子的田。
关于白子国,留存的文字史料很少。但基本在如今大理白族生活习俗里得到延续。
南诏是基于乌蛮、白蛮为主体建立的政权。
杨牟利是白族先民。
阁罗凤可能基于民族认同和信任,任用身为白族的杨牟利,使其为南诏政权效力,以巩固统治基础。
天宝四年(745年),阁罗凤奉唐朝之命率兵平定云南东部爨氏势力反叛。
杨牟利在此次平叛和其他军事行动中展现出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作战经验与威望,因战功得到阁罗凤赏识,从而被任命为昆川城使,负责镇守昆川(昆明)这一重要地区。
昆川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是南诏经营滇东的关键地带。
阁罗凤为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需要一位可靠且有能力的官员来管理。
杨牟利具备的政治素养和治理能力,能贯彻阁罗凤的统治意图,帮助南诏稳定当地局势,故而获此任命。
天宝七年(748年)。
南诏王阁罗凤命杨牟利率领军队武力胁迫爨地白蛮从滇东迁徙至滇西。
他将西爨白蛮二十余万户强制迁徙到永昌城(今大理、保山一带)。
这一举措使得滇东地区人口锐减。
“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
同时,原来受西爨白蛮压制的东爨乌蛮开始徙居到西爨故地。
此次大规模民族迁徙,对南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改变了云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
晚年的杨牟利,在洱海边修了座“望海楼”。
楼里挂着他亲手写的汉文对联:“潮来汐往皆生计,峰起云舒是江山。”
有个年轻的白蛮后生问他:“大人,您后悔吗?”
他指着楼外正在撒网的渔民。
渔民的孩子正坐在船头念《论语》,声音被风吹得飘飘忽忽。
“你看,”杨牟利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洱海的光,
“渔网撒下去,看似是向水低头,实则是为了捞起满舱的鱼啊。”
那天的洱海潮声格外温柔,像在应和他的话。
杨牟利的故事,就随着这潮声,在白蛮和乌蛮的火塘边,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
人们不再说他是“妥协者”,只说他是洱海潮声里最会下棋的人——
用一颗棋子的退让,换来了整盘棋的生机。
🌲如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海碧波荡漾,渔舟轻唱着白族的传说。而不是如同很多王国一样,在战争中湮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智慧,看得见大势初起,并顺势站立在潮头。
#云南的山山水水#云南的地理和历史#云南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