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昆明,你想到什么?
区域,城市,还是人群。
昆明城,昆明人,昆明族?
Why?还有昆明族?
是的呢,有昆明族,但居住在洱海周边。
来,一起解谜。
现在熟知的 “昆明”,最初,并非城市名,而是因古代“昆明族”长期在此活动。
何为昆明族?如今还有这个族吗?他们在哪里?
昆明族,是先秦至唐宋时期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古老部族。
最早记载于《史记》,核心活动区为今云南洱海、滇池周边及川西南部分区域。
该族群早期以游牧为生,擅长饲养高原牲畜。
后逐步转向游牧与农耕结合的生产模式。
汉代,与中原王朝有过军事冲突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逐渐与爨族、彝族先民、白族先民等融合。
宋元时期,完全融入西南多元民族体系,作为独立族群的昆明族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随着历史演进,“昆明”的指代逐渐从“族群活动区”转变为行政地名。
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正式设置“昆明县”,以滇池畔的鸭池城(今昆明市区)为治所,“昆明”首次成为明确的行政建制名称。
如今,昆明是云南省省会,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
“昆明”彻底演变为地理与行政概念,与古代族群名称的关联仅存于历史渊源中。
西南。
横断山脉纵贯南北,云贵高原起伏绵延。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共生的族群文明。
其中,昆明族作为先秦至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古老部族。
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文明记忆,更以其游牧与农耕交织的生产智慧、独树一帜的文化习俗,在云南及川西南、黔西北等周边区域的民族融合与疆域演进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它如同一条隐秘的脉络,串联起西南边疆,从部落林立,到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成为后世解读西南民族史无法绕开的重要篇章。
从“昆明”到族群标识
“昆明”一词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
这篇被誉为“西南民族史开篇之作”的文献,清晰勾勒出昆明族早期的生存轮廓:
“西自同师(今云南保山)以东,北至楪榆(今云南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这段文字精准界定了昆明族的核心活动范围——
以洱海为圆心。
东抵楚雄、西达腾冲、北接丽江、南至临沧的广阔区域。
更点明了其“编发”“随畜迁徙”的关键文化特征,成为后世史学界追溯该族群的“第一手文献坐标”。
事实上,除《史记》外,汉代典籍中对“昆明”的记载亦有补充。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在延续《史记》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及昆明族“善寇盗”。
侧面反映出其在西南夷各部互动中“流动性强、影响力广”的特点。
《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补充了“昆明夷”与哀牢夷的交往细节,为理解昆明族的族群关系提供了更多维度。
这些文献共同构建起“昆明”作为族群标识的早期形象——
一个活跃于西南高原、以游牧为核心生计的庞大部族群体。
关于“昆明”族称的含义,学界历经百年探讨,形成了多元且具说服力的解读。
其一,从古汉语语义出发,部分学者认为“昆”与“浑”“混”相通,在先秦文献中常用来形容“广阔无垠”的自然景象。
如《淮南子》中“昆吾之山,赤水出焉”的“昆”,便有“宏大”之意。
“明”则暗含“光明”“开阔”。
二者结合,恰如其分地指代昆明族所活动的云贵高原——
这片兼具草原开阔性与高原光照特点的土地,是族群生存的地理底色。
其二,从民族语言溯源来看,现代学者结合彝语、白语、纳西语等藏缅语族语言考证发现,“昆明”与部分民族语言中“人”的发音高度契合。
这一观点认为,“昆明”本质上是族群的“自我称谓”,意为“聚居的人们”。
既体现了早期族群的集体认同感,也反映出其“聚族而居、随畜迁徙”的生活形态。
无论何种解读,“昆明”作为一个稳定的族群符号,自汉代起便长期出现在正史、地方志及文人游记中。
从《三国志》中的“昆明夷反”到《隋书》中的“南宁州总管韦冲招慰昆明”,逐步成为西南夷族群体系中辨识度极高的一支。
游牧与农耕交织
昆明族的经济生活,始终与西南高原的自然环境深度绑定。
呈现出“以游牧为根基、以农耕为补充”的动态演进特征。
既展现了对高寒草场的适应能力,也体现了与河谷平原的融合智慧。
早期的昆明族,以游牧业为核心生计,活动范围集中在洱海、滇池周边的高原草场及横断山区的山间坝子。
这些区域海拔多在2000-3000米,气候凉爽、牧草丰美,为牲畜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牧畜繁衍,牛羊被野”的记载,生动描绘出其畜牧业的繁荣景象——
昆明族擅长饲养牦牛、马、山羊等适应高原环境的牲畜。
其中牦牛不仅是重要的肉、奶来源,其皮毛还可制成御寒衣物,牛角、牛骨则能加工为工具。
马则以耐力强、善走山路著称,既是迁徙时的“交通工具”,也是贸易交换的“硬通货”。
更是军事活动中的“核心战力”。
汉代文献曾多次提及昆明族“善骑射”,其骑兵在西南夷各部的冲突中极具威慑力,甚至在汉武帝经略西南时,成为汉朝军队“难敌其迅捷”的重要原因。
随着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农耕族群(如滇族、夜郎族)的交流日益频繁。
昆明族的经济模式逐渐向“游牧+农耕”的复合型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是中原铁器与农耕技术的传入——
秦代开通的五尺道、汉代拓展的南方丝绸之路,将中原的铁犁、铁锄、灌溉技术带入西南,为昆明族开垦耕地提供了工具支撑。
另一方面是族群生存需求的推动——
单纯的游牧受季节、气候影响较大。
而农耕能提供稳定的粮食储备,降低生存风险。
在滇池东岸的晋宁、江川及洱海西岸的大理、祥云等平坦河谷地带,昆明族开始开垦梯田、修筑沟渠,种植水稻、荞麦、燕麦等作物。
考古发现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确凿证据。
在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群(战国至汉代昆明族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于翻土的石斧、用于收割的骨耜,以及炭化的水稻籽粒和荞麦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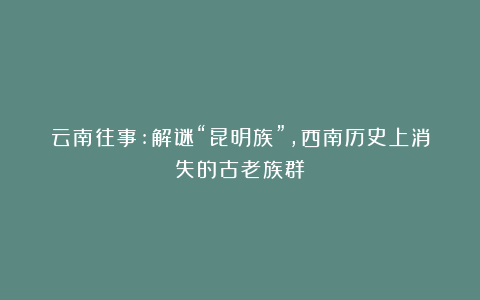
在大理大丰乐遗址中,还发现了昆明族修建的简易灌溉渠道遗迹。
渠道走向与洱海支流相衔接,可见其已掌握基础的水利技术。
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型,不仅提升了昆明族的生存稳定性,更推动了其与周边族群的经济融合。
在南方丝绸之路上,昆明族扮演了“中间商”与“物资供给者”的双重角色。
他们将畜牧产品(如马匹、皮毛、奶制品)运往滇族控制的滇池区域,交换滇族的青铜器物。
再将青铜工具、滇族的稻种运往中原边境,换取中原的铁器、丝绸、盐巴。
这种“游牧产品-青铜器物-中原商品”的贸易链条,不仅让昆明族积累了财富,更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
中原的丝绸纹样逐渐出现在昆明族的衣物装饰中。
滇族的青铜铸造技术也被昆明族借鉴,用于制作游牧所需的刀具、马具。
从部族林立到融入多元
昆明族的历史轨迹,与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同频共振。
从先秦时期的“分散自治”。
到汉代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与交融”。
再到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融合与消融”。
每一个阶段都折射出西南边疆族群发展的复杂图景。
先秦时期,昆明族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以“支系”为单位,散居于西南高原。
史称“毋君长,无大君长”。
这些支系,多以血缘为纽带聚居,
如活动于洱海北部的“叶榆昆明”、滇池西部的“滇西昆明”、川西南的“邛都昆明”等。
各支系间既保持着松散的联盟关系,如共同抵御外敌、共享草场资源。
. 也存在因争夺水源、草场而引发的局部纷争。
此时的昆明族,与周边的滇族、夜郎族、邛都夷等族群处于“相互独立、偶尔互动”的状态——
他们通过贸易交换物资,也因领地边界发生冲突。
但尚未受到中原文化的显著影响,仍保持着纯粹的高原部族形态。
秦代,是昆明族与中原产生间接联系的开端——
秦始皇派常頞开凿五尺道,从四川宜宾延伸至云南曲靖。
这条“西南通途”虽未直接抵达昆明族核心区域,却为汉代中原经略西南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因匈奴阻断北方丝绸之路,朝廷转而探索“南方丝绸之路”(从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
昆明族所在的洱海、滇池区域成为必经之地,双方的互动由此从“间接”转向“直接”,甚至爆发军事冲突。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为打通南方丝路。
“发间使,四道并出……出巂,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
昆明族因不愿让汉朝军队过境,多次袭击汉朝使者与军队,成为“南方丝路开通的最大阻碍”。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等使者前往滇国,途中再次被昆明族阻拦。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郭昌、卫广率军征服滇国后,转而对昆明族发动军事打击,“斩首数万”。
但
但因昆明族“随畜迁徙、居无定所”,汉朝军队始终未能彻底控制该族群。
直至东汉时期,随着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的稳定发展。
中原王朝对西南的管辖力度逐步加强,昆明族的态度也从“抵抗”转向“归附”。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国归附汉朝,朝廷设置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
昆明族部分支系被纳入永昌郡管辖范围,开始接受中原的行政制度与文化习俗——
部族首领被任命为“邑君”“邑长”,需向朝廷缴纳赋税,多以马匹、牛羊等畜牧产品充抵。
中原的汉字、历法、礼仪也逐渐传入昆明族区域,推动了族群的“汉化”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陷入战乱,对西南的管控力减弱。
云南地区崛起了以爨氏为核心的地方政权(史称“爨氏政权”)。
昆明族的发展进入“族群融合”的关键阶段。
爨氏政权以滇池区域为中心,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
昆明族因与爨族(由滇族、汉族移民融合而成)地域相邻、经济互补,逐渐与爨族产生深度融合。
部分昆明族支系放弃游牧生活,定居于爨族控制的河谷平原。
学习爨族的农耕技术与文化习俗,逐步融入“爨人”群体。
另一部分支系则因不愿受爨氏管辖,向云南西部(今德宏、怒江)、北部(今丽江、迪庆)迁徙。
与当地的彝族先民(乌蛮)、纳西族先民(摩沙夷)通婚杂居,成为这些民族形成的“重要基因来源”。
唐代,南诏国的建立(公元738年),加速了昆明族的“族群消融”。
南诏国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统一了云南大部分地区。
昆明族作为南诏统治下的族群之一,广泛参与到南诏的军事扩张与经济建设中——
在南诏与吐蕃、唐朝的战争中,昆明族骑兵因“善骑射、耐高寒”成为南诏军队的重要力量。
在洱海区域的城市建设(如太和城、阳苴咩城)中,昆明族也贡献了游牧族群特有的筑路、架桥技术。
随着与南诏主体族群的长期共处,昆明族的语言、习俗、服饰逐渐与南诏文化融合。
语言中融入大量彝语词汇,“编发”习俗逐渐改为南诏流行的“束发加头帕”,游牧文化特征日益淡化。
至宋元时期,昆明族已完全融入西南多元民族体系——
融入爨族、南诏主体族群的部分,最终成为现代白族、彝族的组成部分。
迁徙至滇西、滇北的部分,则与当地族群融合为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等。
至此,作为独立族群的昆明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仅以“历史回响”的形式,留存于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中。
尽管昆明族已不再作为独立族群存在,但其文化基因却如同“隐形的密码”,深刻影响着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
在语言、习俗、考古遗存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成为连接西南古代族群与现代民族的重要纽带。
昆明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没有文字留存,但通过现代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
仍能在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的语言中找到其“遗存痕迹”。
昆明族的“编发”习俗,在现代西南民族的中仍有鲜明体现。彝族女性的“查尔瓦”头饰(将长发编成多股辫子,缠绕于头顶)、傈僳族男性的“长辫盘头”造型,均与《史记》记载的昆明族“编发”习俗一脉相承。
而昆明族“以皮毛为衣”的传统,也演变为彝族的“羊皮褂”、纳西族的“七星羊皮披肩”,成为这些民族服饰的标志性元素。
在节庆习俗方面,昆明族的“祭牧神”仪式,对西南民族的节庆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先秦时期的“随畜迁徙”,到唐代融入多元民族体系,昆明族在西南边疆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了近两千年。
如今,尽管这个古老族群已不再作为独立个体存在,但其历史印记却早已融入西南各民族的血脉之中——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