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乡鸡”的红灯笼在早餐店门口亮着,“爨碑酒”的陶瓶摆在杂货店橱窗里。
甚至村口的石碑上,都刻着那个笔画繁复的“爨”字。
这个读作“cuàn”、由“火”与“林”构成的汉字,对多数人而言是字典里的生僻字。
可在曲靖陆良、宜良一带。
它是餐馆里飘出的辣子鸡香气。
是陶坊里匠人手中转动的泥坯。
是老人给孩子讲古时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
可若你停下脚步,拨开市井烟火的热闹,往历史的深处走,会发现“爨”字背后藏着一段被《史记》《汉书》轻轻带过、却足以改写西南文明叙事的往事——
那是一个从东汉末年延续到初唐,跨越四百余年的地方政权。
是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梦想与西南夷部的“部落秩序”之间,最精巧的“榫卯”结构。
更是今天我们追问“多民族统一国家”如何从概念长成现实、边疆治理如何跳出“征服与反抗”循环的鲜活样本。
从“中原亡客”到“滇东霸主”
《爨龙颜碑》的复制品静静立着。碑高近4米。
碑文中“君讳龙颜,字仕德,建宁同乐人”这12个字,刻得方劲有力,藏着一段跨越千里的迁徙史。
这块碑的原碑发现于清代道光六年(1827年) 。
由时任云贵总督阮元在曲靖陆良县贞元堡的荒丘中偶然发现——
当时碑身一半埋在土里,碑文字迹被苔藓覆盖。
阮元派人清理后,见碑文记载详实,当即断定其为“滇中第一古碑”。
他亲自撰写《爨龙颜碑跋》,首次将“爨氏”这一被遗忘的地方政权带入学界视野。
碑文中提及的爨氏祖先,本是中原颍川郡(今河南禹州)的大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搅乱了中原。
董卓之乱后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为了避祸,这一族人跟着南迁的流民,先到蜀地,再沿着金沙江往南,最终进入滇池流域的建宁郡(今云南曲靖)。
那时的西南,不是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而是乌蛮、白蛮、叟族等部落聚居的“夷部世界”。
爨氏初到这里时,是“外来户”,既不懂夷语,也不熟悉山地的耕作方式,只能依附当地夷帅生存。
他们聪明的地方在于,没有抱着“中原士族”的架子不放——
男人们跟着夷人学骑马射箭,披上皮甲参加部落间的战事。
女人们学织夷锦,用朱砂在布上绣出图腾。
族里的长者更是主动与夷帅联姻,比如爨龙颜的祖母,就是当地乌蛮部落的首领之女。
通婚成了爨氏扎根的钥匙。
通过联姻,他们获得了夷部的信任,也渐渐掌握了滇东的军政大权。
西晋时,爨氏出了第一个建宁太守。
东晋末年,已经能同时管辖滇池、建宁、兴古三郡,手下的士兵有好几万。
可他们从不称帝,始终用“刺史”“太守”的名号,向建康(今南京)的东晋朝廷上表。
隋朝统一后,爨氏首领爨翫亲自去长安朝贡,带回了“南宁州总管”的官印。
到了唐朝,李世民册封爨宏达为“南宁州都督”。
即便后来爨氏实际控制着滇东的盐井、古道,也从未断过向长安遣使朝贡的规矩。
这种“表面称臣、实则自治”的暧昧,恰恰是古代边疆的常态。
中原王朝远在千里之外,既没有足够的兵力驻守,也不懂夷部的语言和习俗,只能让爨氏这样的“中间人”代为管理。
而爨氏也需要中原的“册封”——有了朝廷给的官印,才能名正言顺地调解夷部之间的冲突。
才能从蜀地运来中原的铁器、丝绸,巩固自己的地位。
四百年间,爨氏把“羁縻”二字玩到了极致。
他们用汉字刻碑记功,却在祭祀时请夷巫跳“鬼主舞”。
他们的子弟读《论语》,却也会用彝语传唱部落史诗。
他们把碑立在滇东的山脚下,让后世的文人以为这是“蛮夷的碑刻”。
可实际上,他们是最早把“中国”的认同,刻进西南山谷的“混血集团”。
爨氏何以重要?
翻开《旧唐书》《新唐书》,关于爨氏的记载不过几百字,远不如李世民、武则天的事迹详细。
原因很简单,爨氏没有像项羽那样“破釜沉舟”,没有像刘备那样“三分天下”。
甚至没有像南诏那样“称帝改元”。
它的历史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没有跌宕起伏的权谋,只有日复一日的“调解冲突”“修桥铺路”“互通贸易”。
可恰恰是这种“不显眼”,让它成了观察“中华”如何在边缘生长的最佳切片——
它不是“中原征服西南”,也不是“西南反抗中原”,而是两种文明在碰撞中,慢慢长出共同的根。
《爨龙颜碑》的碑阴,刻着几十个人的名字。
仔细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的名字是纯汉字,比如“参军爨道文”。
有的是汉字加彝语后缀,比如“功曹爨阿蛮”。
还有的是彝语音译,比如“主簿李万”(“李万”在彝语里是“山鹰”的意思)。
《云南考古》中对这些名号的解读 指出,这种“汉名彝缀”的命名方式,是爨氏“血缘融合”的直接证据——
既保留中原士族的“姓”,又融入夷部的“图腾符号”。
说明爨氏已不再是纯粹的“中原后裔”,而是夷汉混合的“新族群”。
2019年,陆良县清理了一座南北朝时期的爨氏贵族墓葬。
墓葬形制为中原常见的“竖穴土坑墓”,却在墓底设有夷部特有的“腰坑”(用于放置祭祀品的小坑)。
腰坑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鬼主杖头”(夷部巫师主持祭祀的法器)。
墓主人的随葬品里,既有中原风格的青瓷碗、铁剑,也有夷部的铜鼓、玉琮。
对此评价:“一座墓葬,两种文化,是爨氏’夷汉杂糅’最生动的缩影。”
这种融合在“爨体书法”上体现得更极致。
文字学家启功在《代字体论稿》中 曾分析:“爨体的’野气’,不是书法的粗糙,而是夷部文化对汉字的改造——
它让汉字从’庙堂字体’变成了’山野字体’,更适合西南的地理与人文气质。”
这种“杂糅”没有让爨氏陷入身份撕裂,反而让他们成了“双面使者”。
对中原朝廷,他们是“守土有责”的刺史,会把滇东的户口、赋税统计清楚,上报给长安。
对夷部,他们是“能断事”的诏主,会用夷人的“神判”方式(比如让嫌疑人摸烧红的烙铁,没受伤就是无罪)调解纠纷。
就像建宁郡的一个村寨,汉人农户种水稻,彝族牧民养羊。
因为水源起了冲突,爨氏的官员既不按中原的“井田制”分地,也不按夷部的“部落习俗”偏袒一方。
而是让人挖了一条新的水渠,既够稻田灌溉,也够羊群饮水——
这种“不偏不倚”的智慧,让“中国”的概念在西南第一次有了温度。
不是冰冷的法令,而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实在办法。
滇东的地理位置,是天然的“十字路口”。
往北走,过昭通到蜀地(今四川),是中原通往西南的“五尺道”。
往东走,经贵州兴义到岭南(今广东、广西)。
往西走,是滇池流域的粮仓。
往南走,过了红河到交趾(今越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可在爨氏之前,这些路是“断的”——
五尺道到了滇东,成了羊肠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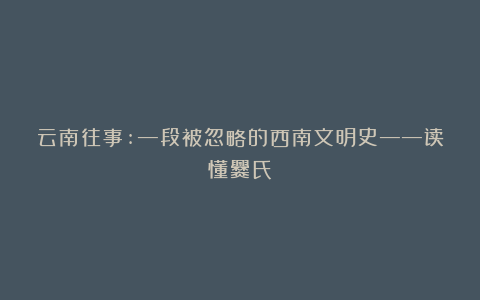
跨越南盘江的地方只有竹筏。
夷部之间还设着关卡,蜀锦要运到交趾,得换好几拨人,走半个月。
爨氏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架桥”。
他们组织夷汉百姓,把五尺道扩宽,铺上青石板,能让两匹马并行。
在南盘江上凿石为基,架起“爨蛮梁”——
这座桥用松木做梁,石板做面,长近百米,直到南宋时还在使用。
取消了夷部的关卡,让商人拿着爨氏发的“通关文牒”,能在滇东畅通无阻。
被《蛮书》称为“步头路”的通道,一下活了起来。
蜀地的锦缎、蜀盐,经这里运到交趾,再从交趾换回来象牙、犀角。
交趾的稻种(比中原的稻种早熟一个月),经这里传到滇东,让滇池流域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
甚至波斯的商人,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交趾。
再走步头路到蜀地,把玻璃珠、香料卖给中原的贵族。
爨氏遗址挖出了一陶罐开元通宝(共97枚),还有3颗蓝绿色的玻璃珠。
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测 ,这些玻璃珠的成分含“钠钙硅”,且含有微量的“钴蓝”。
与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的玻璃制品成分完全一致。
证明它们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波斯运来,再经“步头路”进入滇东。
专家表示:“这些玻璃珠是’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连通’的直接物证,而促成这种连通的,正是爨氏的地方治理——
他们用政权力量打通了商道,让’中国’的经济网络第一次触达印度洋沿岸。”
爨氏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对“名分”的清醒认知。
明明手握重兵,控制着滇东的盐、铁、粮食,却从不僭越——
东晋时,建康的朝廷自顾不暇,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爨氏却按时派人把滇东的贡赋送过去。
隋朝时,隋文帝派史万岁征滇,爨氏虽然打了败仗,却主动交出官印,去长安请罪。
唐朝时,唐太宗要在滇东设都督府,爨氏不仅同意,还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长安当“质子”,表示臣服。
他们不是“胆小”,而是算得清楚。
中原朝廷给的“刺史”“都督”名号,是最好的“合法性证书”。
有了这个名号,其他夷部就不敢轻易反叛——
毕竟反抗爨氏,就是反抗朝廷。
有了这个名号,就能从中原换来铁器、丝绸,而这些是夷部没有的。
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名号,爨氏可以用“朝廷的规矩”来整合夷部。
比如让夷帅的子弟去学习中原的礼仪。
让部落的纠纷按“朝廷的法令”来判,慢慢把“大一统”的观念,植入西南的土壤里。
比如,爨氏每年都会派使者去长安朝贡,贡品不多,无非是滇马、象牙,仪式感十足——
使者穿着中原的官服,拿着写满汉字的表文,在长安的大殿上跪拜,接受皇帝的回赐(通常是丝绸、铁器)。
回来后,爨氏会把皇帝的回赐摆在祠堂里,让夷部的首领来看,告诉他们“我们是朝廷的人”。
这种“自我中原化”的礼仪,不是文化自卑,而是政治智慧。
让“羁縻”从朝廷的临时策略,变成了西南的日常制度。
为后来元代的土司制度,打下了最早的基础。
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指出:
“元代土司制度的’世袭+册封’模式,早在爨氏时期就已成型——爨氏是土司制度的’史前实践者’。”
爨氏与南诏
唐玄宗开元年间,爨氏的统治开始松动——
一方面,爨氏内部因权力分配分裂为“东爨”(以乌蛮为主,居滇东)和“西爨”(以白蛮为主,居滇池周边)。
两部常为争夺盐井、良田争斗。
另一方面,唐朝对西南的策略从“扶持爨氏”转向“以夷制夷”,决意扶持洱海流域的南诏(乌蛮蒙氏部落),借其力量制衡爨氏。
这场权力交替的关键事件,是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的“安宁城之变” 。
当时西爨首领爨归王、东爨首领爨崇道因争夺安宁城盐井爆发内战。
唐朝派御史李宓入滇调解,却暗中授意南诏王皮逻阁出兵“助平叛乱”。
皮逻阁率南诏军抵达安宁后,并未调解,反而以“爨氏内乱,违抗朝廷”为由,诱杀爨归王、爨崇道等20余名爨氏首领。
随后接管滇东20余州。
爨氏四百年基业就此崩塌。
在安宁市发掘的“安宁城遗址”中,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唐代兵器(铁剑、铜箭镞)。
还有带“爨”字的陶片与带“蒙”字(南诏王室姓)的瓦当同层共存。
《安宁城遗址考古报告》 推断,这里正是当年南诏军接管爨区的核心据点。
印证了权力从爨氏向南诏的转移。
但这种“取代”也并非完全文化断裂,有爨氏文明的延续。
南诏虽然灭了爨氏政权,却继承了爨氏的“夷汉融合”传统。
在政治上,南诏效仿爨氏“奉中原正朔”,向唐朝称臣,接受“云南王”册封,同时保持内部自治。
在文化上,南诏碑刻(如《南诏德化碑》)仍沿用爨体书法。
碑文中“汉夷一家”的表述,与《爨龙颜碑》的“夷汉杂糅”一脉相承。
在经济上,南诏继续维护“步头路”的畅通,甚至将其延伸至缅甸,进一步扩大了西南与东南亚的贸易。
大理太和城(南诏都城)遗址出土的一座贵族墓葬,墓中既有南诏特有的“鎏金铜冠”,也保留了爨氏墓葬常见的“腰坑”。
坑内出土的铜鼓纹饰,与陆良爨氏墓出土的铜鼓几乎一致。
考古学家在《南诏文化与爨文化的传承关系》 一文中指出:
“南诏不是摧毁了爨文化,而是将其纳入自身文明体系,成为西南’多民族融合’传统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可以说,没有爨氏四百年的“铺垫”,大概没有南诏后来“以夷治夷、兼容汉制”的治理模式。
更没有西南边疆从“部落分散”到“区域统一”的历史转折。
爨氏镜鉴
四百多年的爨氏历史,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冷文物。
是能给今天的边疆治理、民族融合提供答案的“活教材”。
边疆不是“需要被征服的远方”,是“可以共同生长的家园”。
民族融合不是“谁同化谁”,是“在互动中找到共同利益”。
爨氏的成功,在于它从不逼自己选“做中原人还是做夷人”——
爨龙颜可以用汉字写奏折,用彝语和夷帅聊天。
在祭祀时既拜孔子,也拜夷部的山神。
给儿子取汉名,也给女儿取彝名。
这种“双重身份”不是分裂,而是弹性,是让不同群体都能在里面找到归属感。
爨氏当年修“步头路”,从不管这是哪个郡、哪个部落的地盘,只问“这条路能不能让商队走得通”。
今天的西南,中老铁路开通后,云南的蔬菜从玉溪装车,经过普洱、磨憨,一天就能到老挝的万象,再转卖到泰国、越南。
贵州的大数据中心,通过光纤连接四川的服务器,一起为东南亚的企业提供服务。
陆良的爨陶,也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卖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
这些跨越省界、国界的经济合作,让“边疆”不再是地图上的“末梢”,而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枢纽”
#云南往事#爨氏家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