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猜,拓东,曾经是云南那个城市?👆🏻
横断山余脉,在云南境内铺展。
如今的大理,作为云南十六地州州府之一,苍山横亘西境,洱海似碧玉镶嵌其间。
昆明,如今云南省会城市,滇池似澄澈的明镜,映照着滇中平原的烟火。
这片被群山与碧水环抱的土地,是一部流动的千年史诗——
南诏国,与唐朝并行的东南亚小国。
大理国,以佛音与诗画延伸南诏。
昆明城,则在时代更替中步步崛起。
纵观历史,两地不是孤立的历史切片,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文明链条。
南诏奠基,大理传承,昆明升华,共同写就云南的故事。
西南三国,拓东初立
公元7世纪末。洱海流域,“六诏并立”的分裂格局中——
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如同六颗散落的珍珠,被苍山洱海的水雾包裹。
彼时的唐朝,正与吐蕃在西南展开角力。
地处洱海之南、实力渐强的蒙舍诏(即南诏),成了唐朝制衡吐蕃的关键棋子。
在唐朝的默许与支持下,南诏王皮罗阁于公元738年发动统一战争。
先灭越析诏,再破浪穹、邆赕、施浪三诏,最后迫使蒙巂诏归附,正式建立南诏国,定都于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西北)。
这一年,唐玄宗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从此以唐朝“外臣”之名,行西南霸主之实。
南诏的“雄”,藏在夹缝中求生的智慧与魄力里。
它东拒唐朝、西抗吐蕃。
既曾在天宝年间两败唐军(史称“天宝战争”),将唐朝势力暂时逐出滇东。
又曾与吐蕃结盟,共同抵御中原王朝的压力。
在吐蕃索要重赋时毅然决裂,重新归附唐朝。
这种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南诏在唐与吐蕃的博弈中站稳脚跟。
疆域最盛时,覆盖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甚至延伸至缅甸北部与老挝北部。
是西南边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政权。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辉煌,南诏还为滇地文化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它确立“以儒治国、以佛安邦”的理念。
王室推崇儒家经典,仿照唐朝制度设立官制与科举。
同时大兴佛教,耗时数十年修建崇圣寺三塔——
最初的三塔为方形空心砖塔。
主塔“千寻塔”高近70米,塔身刻有佛经与佛龛。
既是佛教信仰的象征,也是南诏国力的标尺。
现存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更是稀世珍宝。
这幅长卷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南诏始祖细奴罗受佛佑建国的故事。
画中人物服饰,如王室的宽袖长袍、武士的皮甲、建筑风格如干栏式佛殿、宗教仪式如佛教法会,无一不展现着南诏多元的文化面貌。
而此时的昆明,还只是南诏东部边疆的一座军事堡垒,名为“拓东城”。
公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为控制滇东、抵御唐朝,下令在滇池北岸修建此城——
它北依蛇山(今圆通山),南临滇池。
既扼守着滇池要道,又能快速呼应洱海腹地的军事调度。
拓东城初建时,城内驻有重兵,城外开垦农田,是典型的“兵农合一”据点。
但正是这座堡垒,让昆明第一次在云南历史上拥有了“东部门户”的身份,为后来的崛起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鄯阐蜕变的前奏
公元902年,南诏因内乱灭亡。
此后,云南陷入“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朝短暂的动荡。
直至公元937年,白族贵族段思平率领部众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定都仍为阳苴咩城——
大理国的建立,不仅结束了战乱,更将南诏的“雄”转化为一种温润的“雅”,让滇地文化走向成熟。
大理国的“雅”,首先藏在全民向佛的虔诚里。
段氏王族信奉佛教,历代国王多在晚年禅位为僧,如开创王朝的段思平、著名的段正淳(金庸小说原型)、段正严(段誉原型)。
均以“避位为僧”终其一生。
这种信仰渗透到民间,形成“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无老幼,皆念佛经”的景象。
公元1180年,大理国画家张胜温奉命绘制《张胜温画卷》。
这幅长卷纵30厘米、横1635厘米,共134开,绘有638个人物——
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佛教诸尊,也有南诏大理的历代国王、文武官员。
还有苍山洱海的山水、市井中的商贩与工匠。
画中人物衣袂飘举,色彩浓艳却不失雅致。
连佛像的璎珞、官员的玉带、工匠的工具都刻画得细致入微。
被誉为“东方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
至今仍是研究大理国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大理国的“雅”,还藏在与中原的和平共处与文化交融中。
它与宋朝保持了近300年的和平,从未发生大规模战争,而是通过“茶马互市”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当时的贸易路线主要有两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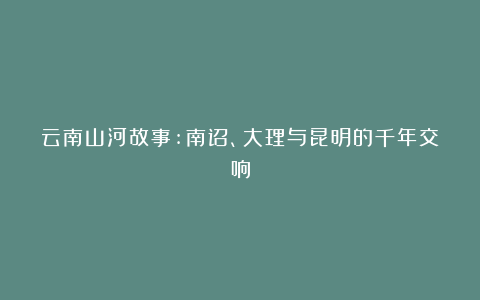
一条从大理出发,经丽江、攀枝花进入四川,最终抵达成都。
另一条经曲靖、贵阳进入广西,直达桂林。
云南的普洱茶、乌铜走银、药材(如三七、天麻),通过这些路线输往中原。
中原的丝绸、瓷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科举制度,则顺着同样的道路传入大理。
大理国甚至仿照宋朝设立“科举”,选拔儒家学子为官。
王室子弟也以研读中原典籍为荣——
这种文化的双向奔赴,让大理国既有边疆的独特风情,又不失中原的儒雅气质。
此时的昆明,已从“拓东城”更名为“鄯阐城”。
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据点,而是逐渐蜕变为大理国东部的经济中心。
滇池周边的圩田得到大规模开发。
大理国工匠改进了“陂塘灌溉”技术,在滇池沿岸修建堤坝与水渠。
将沼泽地改造为良田,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鄯阐城因此成为云南东部的“粮仓”。
城内手工业作坊聚集,既有纺织作坊,生产白族特色的“扎染”与“土布”,也有冶铁作坊打造农具与兵器,还有银器作坊,制作首饰与货币)。
市集上,商贩们售卖着滇池的鱼虾、周边的粮食、来自中原的丝绸。
甚至有从缅甸运来的翡翠与象牙——
舟楫往来于滇池之上,驼队穿梭于街巷之间。
连段氏王族也常来鄯阐城巡游。
传说段正严曾在此举办“滇池灯会”,城内张灯结彩,百姓倾城而出,盛况空前。
从“堡垒”到“都会”,鄯阐城的蜕变,正是昆明崛起的前奏。
南诏与大理的故事,是围绕苍山洱海展开的“王权叙事”。
昆明的崛起,是滇池潮声中奏响的“新主角登场”。
从拓东城到鄯阐城,昆明用了近500年时间。
在南诏与大理的经营中积累了足够的底蕴——
肥沃的滇池平原提供了粮食保障,四通八达的交通构建了贸易网络。
多元的人口(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形成了包容的文化氛围。
元朝的到来,则让昆明正式从“东部都会”跃升为云南的中心。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革囊渡江”,即用皮囊作舟,渡过金沙江,一举灭了大理国,将云南纳入元朝版图。
在考察云南各地后,忽必烈看中了昆明的区位优势。
它东连黔桂,可通中原。
北接川蜀,能连关中。
南达普洱,直达东南亚。
西临大理,可控滇西。
更重要的是,滇池的水利资源能支撑大规模农业生产,让昆明成为元朝控制云南的“粮饷基地”。
于是,元朝决定将云南行省的省会从大理迁至昆明——
这一决策,彻底改变了云南的政治格局,也让昆明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成为省会后,昆明的“融”之特质愈发明显。
元朝在此修建了云南行省署,位于今昆明正义路一带。
设立驿站与驿道,将昆明打造成西南交通的枢纽。
大量汉族官员、士兵、工匠迁入,与本地的彝族、白族、傣族通婚杂居。
语言上,形成了“昆明话”(融合了中原官话与少数民族语言)。
习俗上,既有汉族的春节、中秋,也有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
宗教上,佛教(从大理传入)、道教(从中原传入)、伊斯兰教(从西域传入)在此共存。
圆通山的圆通寺、西山的太华寺、城南的清真寺,共同构成了昆明多元的宗教景观。
这种是南诏与大理文化的延续与升华。
南诏的“雄”赋予昆明开拓的勇气。
大理的“雅”赋予昆明包容的气质。
滇池,则赋予昆明生生不息的活力。
到了明清时期,昆明进一步发展为西南重镇,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南亚的“桥头堡”。
但追根溯源,它的崛起始终离不开南诏时期“拓东城”的奠基,也离不开大理时期“鄯阐城”的积累——
三者如同一条锁链,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如今,大理古城的太和城还留着天宝战争的痕迹。
崇圣寺三塔,塔基下出土的南诏经卷、大理国佛像,默默诉说着当年的佛音缭绕。
昆明,圆通山的断壁残垣相传是拓东城的城墙遗迹。
正义路上的青石板路下,或许还藏着大理国时期手工业作坊的碎瓷片。
滇池边还流传着段氏王族巡游的传说,也会说起南诏士兵曾在此操练的故事。
南诏的“雄”,是铁骑踏遍群山的豪迈。
大理的“雅”,是佛卷与市集的温柔。
昆明的“融”,是多元文化的共生。
苍山的石、洱海的水、滇池的风,共同铸就了云南千年文明的底色——
🌲天气常如二三月
花枝不断四时新
是描述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
#云南的山山水水 #云南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