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决终于下来了。相比一审判决,结果堪称逆转——一审被认定无效的协议,在二审中被改判有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裁判差异?
一、案例:A校违约致合作终止,解约协议却被指“无效”?
2023年初,B公司与A校签订《校企合作办学协议》,约定共同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可合作仅半年,因A校原因,合作无法进行下去。2023年6月,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解除协议书》,明确约定两点核心内容:一是“A校违约是本次解约的根本原因”;二是A校需在30日内支付B公司设备折旧款、前期投入补偿款及违约赔偿款共计200万元,若逾期付款,需按日支付违约金(如日万分之五)。
但付款期限届满,A校却拒绝支付约定的款项。
B公司无奈起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因“超出A校办学许可范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认定该协议无效;同时认为“原协议自始无效,故《解除协议书》中的解约条款、违约金条款等亦随之无效”,仅认可其中“赔偿款、设备折旧款的支付约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567条规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应认定有效。
B公司对此难以理解:
明明是A校违约导致合作终止,《解除协议书》也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为何仅因原合作协议无效,就认定解除协议的核心条款无效?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要厘清上述争议,需先明确三个核心法律问题:
1. 什么是无效合同?
2. 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有哪些?
3.原合作协议无效,是否必然导致解除协议无效?
合同本质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因此理解“无效合同”,需先明确“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民法典》总则编第六章第三节系统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无效情形及无效后的法律后果——若全面展开,非本文篇幅所能涵盖。一言以蔽之,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已成立,但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在法律上确定的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由此,无效合同的定义便清晰可见:即无效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或者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参见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93页。)
《民法典》对合同无效的规定采用“总则统领 分则补充”的体系化框架:总则编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定了所有民事法律行为(含合同)的通用无效情形,分则编则针对特定类型合同的无效情形予以细化——这一框架决定了“合同无效事由需法定”,而非当事人可任意约定。具体而言,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可分为两类:
总则编规定的“通用无效情形”(适用于所有合同)
(1)主体不适格: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44条)
(2)意思表示不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46条)
(3)内容违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
(4)违背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
(5)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54条)
分则编规定的部分“特殊无效情形”(仅适用于特定合同):
(1)从合同无效: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等从合同无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388、682条)
(2)格式条款无效:格式条款具有“免除提供方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法定情形的(《民法典》第497条)
(3)租赁合同超期部分无效:租赁期限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第705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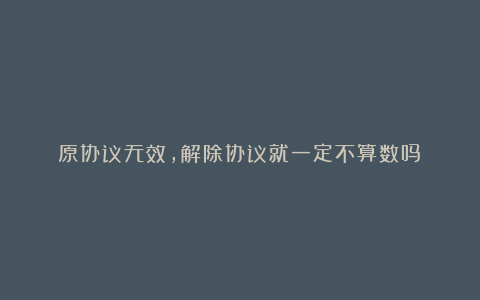
在厘清“无效合同定义”与“法定无效情形”的基础上,可回归案例核心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原合作协议无效→解除协议相关条款无效”,这一逻辑是否成立?答案是否定的,具体可从四方面分析:
合同无效事由由法律明确定义并封闭列举,当事人无权创设。一审法院认为“原合作协议无效,必然导致需对解除协议效力重新评价”,但未提供任何法律依据——纵观《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除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外,均无“一份合同无效必然导致另一份独立合同无效”的规定,故该逻辑缺乏法律基础。
(2)一审逻辑不符合“主从合同无效”的法定规则
《民法典》中唯一“一份合同无效导致另一份合同无效”的情形,是“主从合同关系”(如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此类情形有严格限定:需存在“主合同为基础、从合同依附于主合同”的从属关系,且从合同的目的是“担保主合同履行”。
本案中,《校企合作办学协议》是“合作权利义务协议”,《解除协议书》是“终止合作、清理债权债务的协议”——二者虽有事实关联(基于同一合作关系),但不存在“从属关系”:解除协议的目的是“解决合作终止后的结算与赔偿”,而非“担保原协议履行”,故不属于“主从合同”,不能适用“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的规则。
(3)合同效力评价应“独立判断”,不得与其他合同“捆绑”
评价一份合同的效力,应以该合同本身为对象:需审查其是否具备“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有效要件,或是否存在法定无效事由——除“主从合同”这一法定例外情形外,不得将其效力与其他合同“捆绑评价”,即便两份合同存在事实上的关联。
本案中,《解除协议书》是B公司与A校协商一致签订的,双方均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无欺诈、胁迫),内容(如设备折旧款、逾期付款违约金)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即便原合作协议无效,解除协议本身仍符合有效要件,应认定为有效。
(4)一审法院混淆“条款无法产生效果”与“条款无效”的概念
一审法院认为“解除协议中的解约条款、违约金条款无效”,但这一认定混淆了两个关键法律概念:
一是“解约条款无法产生效果”≠“解约条款无效”。《解除协议书》中的解约条款(如“解除《校企合作办学协议》”),仅因原协议本身无效(自始无法律效力,无需“解除”),导致该条款无法产生“解除原协议”的预期效果——但“无法产生效果”是“事实层面的履行障碍”,而非“法律层面的条款无效”(条款本身内容合法,无无效事由)。
二是“违约金条款效力独立于原协议”。《解除协议书》中的违约金条款,针对的是“A校逾期支付解除协议约定款项的违约行为”,既非原协议的附属条款、补充条款,也不涉及原协议中的违约行为——其效力仅取决于自身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过高),与原协议效力无关。
最终,二审法院改判认为“因《校企合作办学协议》为无效协议,故《解除协议书》中第一条关于解除《校企合作办学协议》的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解除协议书》的其他条款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恪守履行。”
从民法理论而言,二审法院的该部分认定仍有进一步严谨化的空间——更精准的表述应为:“《解除协议书》整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其他法定无效情形,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恪守履行;仅因《校企合作办学协议》自始无效,《解除协议书》中关于’解除原协议’的条款无法产生’解除原协议’的预期法律效果(但该条款本身仍属有效,并非无效)。
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假设《解除协议书》确属无效(即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被认定为自始无法律效力),那么能否适用《民法典》第567条,认定该协议中的结算和清理条款仍然有效?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从法条体例看,《民法典》第567条位于合同编第七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这一章节的规范对象是“有效合同的权利义务终结”,而非“合同无效”。该章第557条明确列举了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具体情形,包括债务已经履行、债务相互抵销、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债权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等——这些情形的共同前提是“合同曾合法有效存在”。
其次,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始终严格区分“合同终止”与“合同无效”的法律边界,明确《民法典》第567条不适用于合同无效情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31号民事裁定书即明确指出:“《合同法》第98条(对应《民法典567条》)关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并不涵盖合同无效情形。”
最后,《民法典》第567条无法适用于合同无效情形,那么无效合同引发的权利义务争议(如财产返还、损失赔偿),应当依据何种规则处理?《民法典》第157条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的专门规制条款”,给出了清晰的解决路径“返还—补偿—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