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风骨论研究发轫于文学理论领域,学界就书学领域中的风骨范畴也形成了一定的认识。较为有影响力的系列结论表示,书学领域也存在着所谓“风骨论”,且具有核心的理论地位,其意涵大体为一种“雄强有力的审美风貌”。而这样的结论存在重“骨”轻“风”的谬误。其表现为对古典范畴群的无效释读、范畴间层级关系的颠倒等具体问题。谬误根源于以书学“骨”论的文献作为建构书学“风骨论”的材料, 存在文献的错置与误读等情况。
风骨这一审美范畴的研究发轫于文学领域。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明确了风骨的审 美范畴,并为该范畴建构了文学领域的理论典范。作为《文心雕龙》理论成就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闪 光点,风骨论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难点。学界在对风骨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过程中拓展 到对其在书学领域的研究。
一、书学风骨范畴的研究现状
(一)发轫于文学研究
《文心雕龙》研究成为学科的标志是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黄侃于北京大学开设了《文心雕龙》专题研究课程。其讲义《文心雕龙札记》成为“龙学”研究的核心参考资料。论及《文心雕龙·风骨》篇时,黄侃的“风意骨辞”[1]101 之说“流行了几乎半个世纪”[2]90,是近现代风骨研究的开端。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通过对范畴语源的追溯认识到,“骨”来自汉代的相人术以骨相甄别人物的个性、命运,沿用于魏晋的人伦品鉴时发挥出其美学价值,继而辐射到书画等门类艺术理论中 ;而“风”可以追溯到《诗经》,有教化之义。然而,“风骨”的确切意义始终没有定论。陈耀南在将 65 家说法整理为11类后,不无慨叹地总结道:“恐怕要请彦和同志回来示现,以破迷惑而广知见。……不过晚年皈佛的他,可能早就拈花微笑,默照无言,对自己三十多岁之时归宗儒学的旧作,恍同隔世,’不可说,不可说’了。”[2]58“风骨”之义,所论最精切者莫过于徐复观写就于 1963 年的《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3]84-117 一文,论述精详地阐释了“文气”在理解风骨时的重要性。徐复观在交代文学风骨时,涉及该范畴从品人到书画再到文学的跨领域发展的过程。由此,书学风骨范畴的研究价值得以奠定。成书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汪涌豪撰写的《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4](以下简称《风骨论》),是对风骨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书作为《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中的一本,并不仅限于单个门类艺术美学范畴的研究,而是具备跨门类的眼光,分别从书法、绘画、诗歌三个维度梳理风骨论的历史发展、逻辑演进与生成机制。着墨上看,论述书法和绘画的体量均占论述诗歌美学的二分 之一不到,但由于独立成编,带动了书学研究对风骨范畴的重视,影响了后来的著述。21 世纪以来, 继续关注此议题的研究有专著《汉字书法审美范畴考释》[5],以及论文《书法风骨论》[6]、《论书法之 风骨》[7]、《六朝书画“风骨论”的确立及其美学内涵》[8]、《书学风骨论在唐代的发展》[9] 等。
截至目前,对书学风骨范畴最具系统性与影响力的研究正是汪涌豪的《风骨论》。作者对该议题的关注在时间上较早,于 1989 年即借该著取得博士学位。此后,该著发行过数次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于 1994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风骨的意味》于 2001 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 年再版);2019 年,商务印书馆又重以《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为名推出其精装修订本。该著援五编以铺陈,其中第二编讨论书法“风骨论”曾以单篇 论文的形式见刊于 1994 年的《书法研究》[10]。此外,汪涌豪还参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1995年)。其中,对“风骨”[11]390 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范畴,如“气骨”[11]147、“风”[11]162、“骨”[11]659、“风力”[11]394、“骨力”[11]394、“丰肉微骨”(与成复旺合著)[11]667,乃至“骨体”[11]661、“筋骨”[11]661、“骨与肉”(与成复旺合著)[11]662、“肉”[11]660、“骨法”[11]564 的阐释与《风骨论》亦高度相关。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2003 年)丛书中,汪涌豪承撰了范畴卷的第六章《风骨 :雄强有力的审美风貌》。[12] 该章的论述结构、逻辑与观点与《风骨论》一致,可视为《风骨论》一书的浓缩。以上情形在在可见 汪涌豪之于此议题的关注。《风骨论》作为第一种系统考察风骨在书学领域意义的成果,其思路或观 点得到了河内利治、方智娟、常亚钧、范立红等学者的沿用,而质疑者陈龙海亦赞其“系统全面…… 立论谨慎,论证缜密,论据翔实”[6]36,由此可见其贡献与影响力。
(二)不同的见解与反思的意识
在汪涌豪的研究对后学产生影响的同时,其本人的学术探索也持续向更宏阔的范畴研究领域推进, 2007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即体现了这一学术追求。随着对范畴体系论认识的深化,他在 2019 年《风骨论》修订版中增补了从范畴位序论的角度对风骨及相关范畴群的观察。但是,一如黄侃“风意骨辞”说的争议性撬动了文学风骨论的学术生命力一样,汪涌豪的研究亦存在着再思的空间,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2004 年陈龙海的论文《书法风骨论》[6] 是目前仅见的明确呈现出反思意识的声音。陈龙海提出书论中的“骨”的范畴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需要结合“筋、骨、肉”范畴体系方能够阐明其内涵,不应被以“风骨”的形式单独论述。陈氏已然发觉“骨”的重要理论价值坐落在“筋、骨、肉” 的理论体系中,从而他坚持应当以“骨”的材料论“骨”的意义,以“风骨”的材料昭明书学对于生命力的崇尚。惜其仍以“风骨论”连言,且未能够通过“风骨”与“骨”的联系而点破二者之间的区别。该文坦言希望能“就教”[6]36 于汪涌豪与书法美学研究者,但目前未见任何回应性研究或引发学术对话。
后续学者的若干研究书学“风骨”或“风骨论”的论文大多延续汪涌豪对于文献的使用习惯,径而多以“骨”论语料当做“风骨”论的文献,因而得到类似的结论 :在起源论的问题上,都认为“风骨论”出现并确立于魏晋南北朝,认为“风骨论”在书学史上具有极高的理论地位。这一对待文献的方式无视了唐以前“风骨”连言从未出现在书学领域的情形,也未正视书学“风骨”的理论材料的多寡与被严肃论述的具体情况。
日本学者河内利治的《汉字书法审美范畴考释》[5] 是以书法美学范畴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对书法理论中的“骨”“遒美”“力”等术语所在文献做了整理和逐条译注,对字义进行考释时,对汪涌豪的研究有所引用和发扬。该书爬梳了书学文献中含有“骨”字的术语,并进行了诠释,其虽以汪涌豪的《风骨论》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但已显露出对一些范畴与文献材料的不同理解。该研究并未以“风骨论”为主线,而是清晰地将这批术语的核心范畴聚焦于“骨”。可惜,河内氏未对汪涌豪的研究提出任何明确质疑。
在书学理论中,如不先入为主地将所谓“风骨论”当作既有的研究对象,不难发现,这些被误置于“风骨论”范畴的研究材料实则属于“骨”论的内容。诚如陈龙海所言,对书之“骨”的理解需联系唐宋以来以身论书的认知系统来理解。书之“骨”位列书法“筋、骨、血、肉”的譬喻体系中,“筋”“骨”表现出有别于“肉”“血”的价值。由此,“骨”论位于书法审美表述的主流范畴地位。高明一就曾撰文揭示在书论中,“神、气、骨、肉、血”作为一个体系性的譬喻植根于感官上的可视性,宋代更多维度的譬喻体系的形成,不仅有传统书论中筋骨论作为铺垫,更与“不早于唐玄宗时期”出现的“永字八法”对于身体动势的观照以及孙过庭《书谱》对自然物象的比拟同构而相成。[13] 这种对“骨”的视觉形象意义下的譬喻能力的肯定有别于汪涌豪所谓的缘于“相术与人物品鉴之风的牢笼”[4]73。
二、重“骨”轻“风”——书学“风骨论”研究成果的讨论
(一)结论的暧昧
汪涌豪将作为中国美学范畴的风骨之义总结为“雄强有力的审美风貌”[12]296,惜其呈现结论时语调略嫌暧昧。他总结属于中国美学范畴的风骨论时说 :“在书、画及文学理论中,它大抵指称一种艺术作品刚健雄强、真力弥漫的特征和风貌,其生成与创作者的郁勃志气和丰沛生命力有密切关系。作品有’风骨’,确乎直接体现为用笔或用语的端直有力,但又绝不仅止于此。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所指称的是一种能使观赏者感受到创作主体内在生命力的艺术品格,用笔或用语的端直有力,只是这种生命力通过相应物质材料所获得的一种表现。”[12]330 从引文的表述语调可以看出,为风骨定义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作者想定义风骨为一种“雄强有力”的风格,但又担心其不准确,于是用“大抵”“与……有关”等进行修饰。定义之后又似觉言不尽意,便进一步做补充说明笔力(或文力)是必要非充分条件。但仍不能放心,又带入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再尝试以更精确一些的标准再做一次定义,然后再补充解释用笔或用语的非充分性之后又要再做举例。
在书学领域的“风骨论”研究中,汪氏试图归纳风骨范畴的具体审美祈尚为“括而言之,书法美学理论中的风骨范畴,指称的是一种与纤圆、疏巧和浮弱无涉的书法风貌”[12]305,作者用否定其反面的方式定义了书学风骨范畴的核心意义是“力”。不同于上述兼容文学的概观,作者遗落下对“气” 的补充,聚焦于“力”。这一结论来源于在建构古代书学“风骨论”时,具体材料大多不介意“风” 的缺席。
(二)材料的误用
以《风骨论》一书为观察对象,可以看到论及“风骨范畴的萌芽 [4]31 时,作者援引的文献是(传) 卫夫人的《笔阵图》中所言“(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取(恐为“其”之误)无骨”[4]31,见“骨”不见“风”。如果此处姑且归因于所论为“萌芽”阶段,那么在论及“风骨范畴的真正确立是在魏晋”[4]31 时,所引文献不论是《笔骨论》,还是《草书赋》《笔阵图》《笔势论》《用笔赋》[4]31-32仍均见“骨”不见“风”,则更难令人信服所谓“’风骨’范畴”的“真正确立”。仅有“骨势”“骨力”等见“骨”不见“风”的词语仅能支撑作者对书法的“骨力”与“媚趣”这对概念做分析与理解,不能作为“风骨论”的萌 生甚至确立的研究材料。这种偏重以“骨”的语料来论“风骨”的情形在书中十分常见,并非如作者 在后文中说“偶以’骨法’、’骨肉’等概念来说明风骨问题”[4]73。而《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中的《风骨 :雄强有力的审美风貌》章,在论述书学领域的“风骨论”时,所援引的从六朝到明清的大量书论材料中,仅见一条含有“风骨”、一条含有“风神骨气”,其余则均不见“风”。
由于书、画共通于笔墨工具,所以书学中的审美于绘画上亦然。汪涌豪为论述“风骨论”于书画相通论上的理论价值,便说张彦远“在讨论’风骨’问题时,已经把书、画连为一体了”[4]253,而细 看其引用内容“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4]253,仅谈“骨气”。汪涌豪在论述伊始提及的“骨”与“风骨”的联系,即“骨”字对“风骨” 范畴起了一定的“意义规范作用”的叙述亦无法引作合理的解释。他说:“风骨范畴……就其历史渊源而言,可上溯至秦汉以来的相术传统和魏晋南北朝人物品鉴。这不仅指组成这一范畴的两个字皆出于此,还因为这两者特别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说,确乎对于此范畴起了一定的意义规范作用,从历代人对它的阐述与运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者间存在的义脉联系。”[4]5 若在材料上使用其一的文献, 却要“看到”两者间存在的“义脉联系”,逻辑上不可行。对仅有“骨”的文献加以诠释,又用以证明“骨” 对风骨的“意义规范”作用之“确乎”,是循环论证。
汪涌豪意识到“风”的缺失时,为免牵强之嫌,解释道:“尽管不能说’骨肉’、’骨格’、’骨法’及’筋骨’等概念实与风骨范畴意义相同,但两者关系密切,借由前者证明后者,当不能算两不相涉的附会。”[4]72 然而若真是“两不相涉”的内容,便无法“附会”到一起了。汪涌豪在此处以“骨”与“风骨”之间的“关系密切”为由,弱化了两者的差异。事实上,出现在书学语境中的“风骨”,除却 “骨”所代表的“力”的义素之外,也含有与“气”“神”“韵”等相关的精神审美层面的美学意义。而这类的意义则更多是由“风骨”这个双音节词中的“风”来承载的。语料选取上的见“骨”不见“风”,势必导致重“力”不重“神”的释读结果。
(三)诠释的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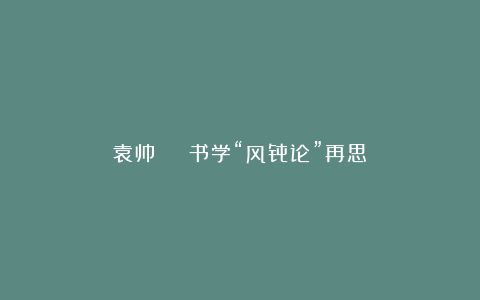
成复旺曾谈论范畴研究要注意方式。他在《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引论》中提倡,要正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因为中国概念大多轻逻辑思辨而重心灵体验,在使用中并不遵守概念的同一律。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故而复合词的词素之间关系灵活,大都可分可合。于是,在解释古代概念的时候要注意既要避免以一个近似的现代词语去解释,即“变古为今”,如以“形象”解释“象”;又要避免“以古解古”的无效释读行为,如以“风神骨气”解释“风骨”,以“风神韵致”解释“神韵”。再者还要避免用西方美学做简单比附,如用壮美、优美去框定中国美学范畴。[11]10-12 汪涌豪的研究未能成功规避上述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汪氏著作中将大量仅支撑“骨”的材料用于风骨范畴的研究与阐释,属于材料误用,那么,当作者面对少量的直接使用“风骨”字眼的材料时,其疏解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则可称为误读。在解释“风骨烂漫,天真纵逸”时,汪涌豪说王世贞“以’烂漫’释风骨”[4]62。显然,原文中“风骨”与“烂漫”并非以后者解释前者的关系,而是一种主谓关系。
当面对一些不在论“骨”的材料时,汪涌豪却又刻意拉入“骨”的概念作解。面对张怀瓘在《书议》中所说的“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 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4]60,汪涌豪评论道 :“从其所谓’戈戟铦锐可畏,物象生动可奇’云云可知,他之不满王书’乏神气’,正是就其书法缺乏风神骨气而言的。”[4]60 首先,用“风神骨气”解释“神气”,则正中成复旺所谓“用四个字替换两个字”的“无效诠释”之说 ;再者,于无骨处强加“骨”,扭曲了原文原意。汪氏欲将“戈戟铦锐可畏,物象生动可奇”拉到“骨”的范畴内,作雄强之解。然而张怀瓘意在明其“乏神气”,“戈戟”“物象”之谓是从战况与物象两个维度去修辞,以揭示书法的“神气”,并非批评其“力”弱。从“虽”字可以看出,“圆丰妍美”亦非对“力”弱的批判,而是说“格律”“功夫”之弊是不可通过“圆丰妍美”之利来弥补的,终不能达到有“神气”层面。“神”在张怀瓘的书论观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是高于“力” 与“媚”这一层级的风格评判的。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瓘所重视的“神”恰恰与其“风骨”的语用相契合。汪氏弱化了对“神”层次的理解,而将其归于“顿挫”“力”“雄强”的风格倾向。这与其将书学风骨范畴归纳为“雄强有力”一致,犯了类似成复旺所谓用“壮美、优美”去“框定”中国的美学范畴的错误。
三、书学“风骨论”再思
(一)“骨”等于“风骨”吗?
材料可以混用吗?尽管书学史上没有关于“风骨”与“骨”之异同的专论,但古代书论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判断的依据。例如,唐代张怀瓘在比较虞世南与欧阳询的高下时说 :“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族子纂,书有叔父体则,而风骨不继”[14]286,张怀瓘认为虞欧之间高下难分,但若从“君子藏器”角度来考量,虞世南则胜过欧阳询。但看其视觉效果,欧书则胜在“筋骨”(尽管以略带贬义色彩的“外露”方式呈现)。此后,又言虞世南的族子纂的书法有自家叔父的体则,但是没能够继承虞世南的“风骨”。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到,未能够以“筋骨”胜欧阳询的 虞世南也是有“风骨”的。可见,张怀瓘评论欧虞时,“筋骨”不浑同于“风骨”。再如,(传)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论王献之时说,“骨势不及其父,而媚趣过之”[14]15,可见其肯定了王羲之的“骨势”。张怀瓘认可这一说法,于是引述(放在王僧虔名下的相同表述)曰 :“王僧虔云,献之骨势不及父,媚趣过之”[14]309,但在其《六体书论》中提到,王羲之与张芝、钟繇相比,“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14]60。可见,张怀瓘评价二王之时,“骨势”不浑同于“风骨”,“风骨”的有无不以“骨势”为判准。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瓘在认定王献之草书与王羲之相较“媚趣过之”,但与齐高帝比,又是有“风骨”的, 他说 :“齐高帝……善草书,笃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风骨”[14]299。是知,“风骨”的有无不以是“媚趣”取胜还是“骨势”取胜为判准,不以风格上倾向“雄强”还是“流媚”,不限于“力”感,而重在提倡“神气”。
作为单音节词的“风”与“骨”,本身都具备极高的构词能力以及随语境而滑动的意义。作为一个复合词,要识“风骨”之义,需要认清复合词与原本的单音节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也需关注其与该单音节词构成的其他复合词之间的意义关系。
与“骨力”“骨势”的意义不同,在张怀瓘的认识中,他批评王羲之草书所缺少的“风骨”意义更接近于“神气”。他在《书议》中指出王羲之草书的问题在于“乏神气”之外,表明草书应当有“风骨”,他说 :“或烟收雾合,或电激星流,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14]155。结合“体用”的概念,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相对于“烟收雾合”“电激星流”般的用笔变化之能事,草书要以坚守不失的“风骨”正是张怀瓘提倡的草书之“神”。这里的“神”之义,仅靠“骨”字的出场是不够的,更多须由“风” 字来承载。
“风骨”与“骨”之间不能画上等号,还在于二者的形神之别。“筋、骨、肉、血”等的系统譬喻属于技法层面的风格要素的比譬,从形神论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形”的范畴。而不论是对人物还是艺术作品的赏析中,风度、风神、气韵、神采就是“神”的范畴了。然后,“风骨”这个概念,其实也属于“神”的范畴。由此可见“风”在“风骨”中的重要意义。
周汝昌在 1982 年发表的文章中论及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风骨”在文学上与书学上是不同的, 并且他十分清晰地提出书法中的“风”与“骨”分属于“神采”与“形质”,他说:“文学上所谓骨力劲健,那是文辞上的事;而风力的俊爽,则是文气上的事。这个分别,并不总是被弄得清楚的。风, 正是’气’的一个换算,气流动而为风,正如庄子所云,风是’大块噫气’。我们中国说的’风神’、’风度’、’风貌’等,是指精神面貌,而不是’五官四肢’这个躯体。’遒媚劲健’,其实正是分言书法艺术上的’风’、’骨’——神采与形质。”[15]246
不能将“骨”混同于“风骨”的同时,还应当注意书学与文学的差别。宗白华曾将笔墨的“骨力” 与文学“风骨”对举,论及书画用笔时仅谈“骨力”,论及“风骨”的部分则回到文学领域,谈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16] 在宗白华看来,骨力与风骨有别,一如书法与文学异质。这种论述充分尊重了在不同门类的理论史中,“骨”与“风骨”作为不同语料文献的多寡有别。
(二)书学“风骨”足以称“论”吗?
在对书学领域的风骨范畴进行具体解读之前,汪涌豪的研究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判定, 即书学领域存在所谓“风骨论”。这一点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篇章题名即可观察到,其影响力亦可从 后来学者在行文与题目中往往以“书学风骨论”连言的现象中观察到。“书学风骨论”连言的情形在 后来学者的表述中亦不鲜见。然而,“论”代表了相应的理论成熟度,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范畴要“成论”,一方面必须“被论述”,即须经历过系统的论述,具备理论深度 ;另一方面在历代的论述中也应该具备一定的使用频率,具备理论广度 ;而其意涵,也应随之而具备相应的稳定性。令人遗憾的是,与文学不同,书学领域的风骨范畴呈现为“有用无论”的状态。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如这个命题般成熟又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典范在书法等其他门类的理论中是未曾得见的。因此,不同于文学上的风骨,书学理论中的“风骨”并不具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也未见成体系的理论论述。所以,书学领域虽存在风骨范畴的语用现象,却不足以称“论”。
汪涌豪认为风骨范畴在书学史上具有核心的地位,他说 :“’风骨’这个美学范畴几乎是与书学理论的萌芽一起(于魏晋之时),进入书法美学体系的中心”[4]31。但在书学史上,自“风骨”出现,乃至后世的使用中,并没有形成专论著述或篇章段落,亦未见该范畴理论成熟化的迹象。故而,称“书学’风骨论’”与书学风骨范畴的理论价值之间的匹配程度值得再思。而汪氏用以诠释“风骨”的诸多材料恰恰可以构建出“骨”范畴的面貌。在书学史中,是“骨”范畴从被提出伊始,便以“论”的形式呈现,且长期保有理论的重要地位,被不断深化论证。书学领域内由“风骨”“骨”“骨肉”“骨力”“骨气”“骨格”等所组成的范畴群中,核心范畴当选定为“骨”。
(三)书学领域里的“风骨”是核心范畴吗?
以“骨”论“风骨”,自然会重“骨”而轻“风”,以“骨”为“风骨”的意义规范。以“风骨论”来为大量的“骨”论语料命名,则相当于以“风骨”为所在范畴群的核心范畴。这一推断在汪氏2019 年的修订版《风骨论》所增补的论述中得到了昭示。[17]236 从范畴研究的角度去看,孰为元范畴, 孰为衍生范畴的位序被颠倒了。
包括汪涌豪在内,杨星映、党圣元、蔡钟翔、陈运良等多位学者指出,不同于西方文论范畴系统是按照由本质到现象分门别类而建构,中国文学范畴间的关系呈现阶梯状。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系统由元范畴推衍出基本范畴即子范畴,再互相交融及衍生出诸多范畴群,从而整体贯通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梯级范畴网络。[18]1-2 阶梯性是指元范畴与衍生范畴之间存在着阶级关系、衍生关系。鉴于阶梯性, 要对于一个美学范畴进行认知,就必须搞清楚其与阶梯中上下左右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文 学批评范畴既是连锁展开牵衍成序,为一可以运作的动态系统,那么就各个范畴考察必然有前后甚至主次的区别。”[19]485 汪涌豪曾清晰界定范畴序位之上下前后的关系问题——前位范畴与后位范畴是按照诞生时间的先后来区分的,而上位范畴与下位范畴的命名是根据衍生关系得来的。上位 / 母范畴又称“种范畴”“母范畴”,下位范畴又称“子范畴”“后序范畴”,如“格”是“气格”“格力”的上位范畴,“境”是“意境”“物境”的上位 / 母范畴。所谓元范畴,即“不以其他范畴作为自己的存在依据,不以其他范畴规定自己的性质和意义边界的最一般抽象的名言”。[19]486 元范畴具有绝对上位范畴的身份,衍生出的子范畴又可再衍生出更下位的子范畴。此即所谓阶梯性。通过汪涌豪的叙述与举例可以发现,衍生范畴往往是通过再度构词的方式生成。比如“气”这个范畴的衍生的下位范畴有“文气”“骨气”“血气”等。相较于子 / 衍生 / 下位范畴而言,母 / 种 / 上位范畴往往使用率较高,内涵较为复杂而又固定。但是因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的,我们往往又可以通过衍生范畴的使用情况进一步了解元范畴的意涵,而非反其道而行。
秉持这样的范畴研究原则来看书学领域的审美范畴,应当可以理解不应用所有“骨”的语料去解释“风骨”,一如我们不能够用所有含有元范畴“气”字眼的材料去解释“骨气”或“气韵”这些衍生范畴的意涵。若以“风骨”为范畴群的核心,则是认为“风骨”和“骨”的关系是“风骨”在上位, “骨”作为衍生范畴,在下位。这显然与书学史上这两个范畴的衍生顺序不符。
在面对不同门类的相似范畴时,宗白华在 1979 年的论述中就未将骨力与风骨混同而观。[16]53 宗白华在仅一千八百多字的篇幅内,谨慎地从绘画的骨法谈到书画笔墨之骨力,最后论及风骨时落脚在文学,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范畴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归属。宗白华在讨论绘画美学时说 :“骨力、骨气、骨法,就成了中国美学史中极重要的范畴,不但使用于绘画理论中(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几乎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都要提到’骨’字),而且也使用于文学批评中(如《文心雕龙》有《风骨》篇)。”[16]53这段话隐隐揭橥了“骨”才是在笔墨艺术的审美领域具备核心理论地位的范畴。与此同时,点明了“骨” 范畴与“风骨”范畴的位序关系——在衍生顺序上,“骨”先在于“风骨”,衍生了“风骨”。而用于笔墨审美的“骨”在进入文学领域之后,衍生出了风骨范畴。是知,“骨”是上位,“风骨”是下位。“风骨”在笔墨领域并不具备很高的理论地位与使用频率,具有高的理论地位的是书“骨”论。
结语
在书法理论领域的风骨范畴研究中,前辈学者以有“骨”字眼之材料及其用法来诠释“风骨”的含义,并得出书学“风骨论”在书法理论中拥有核心的理论地位,书论中的“风骨”代表的是一种雄强有力的审美风貌等结论。首先,这一材料选用上的失当带来的是范畴意义解读的偏差——重“骨” 轻“风”,重“力”轻“神”。再者,将书论中关于“骨”的论述冠以“风骨论”之名,有颠倒范畴间层级高下关系之嫌。值得注意的是,前人用于建构书学“风骨论”的可观材料恰恰构筑了书法美学的一个焦点,即书“骨”论。
从学术史的视角推断,前辈学者对书学“风骨论”的先在判定或许是由于在文学领域风骨论的实存。文学史上的“风骨”以《文心雕龙》作为理论典范,得以在不同时代被系统论述,且确乎有以“风” 和“骨”同作为“力”义承载者的情形。[20]19-20
从门类视角看,书法与文学相较,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媒介差异。书法的媒介是笔墨,文学的媒介是语言。前者是视觉的、具身的,而文学的媒介则是相对抽象的符号。于是“骨”在不同门类理论中会侧重显露不同的譬喻能力。因为汉代有过相人术,因而“骨”在生理维度的意义演化成了相术层面的意义,但其视觉层面的意义并没有丢失。在视觉审美活动中,“骨”的本义则更为轻松地承担了喻体的角色。骨与肉、筋一样十分形象地指涉着笔墨技法、风格 :瘦硬的行笔、果决的笔锋翻转或方切等都清晰地给人以骨力之感 ;用墨的厚重,行笔的迟滞犹疑被戏称为“墨猪”,是肉的感觉 ;行笔肥瘦适中,圆转连绵的同时又不失劲健,便是筋。书法的“骨”,在筋骨肉的譬喻系统中依赖的并非骨的相学意义,而是其形象意义。相较于肉而言,骨不肥而坚,于是以其瘦硬的形象特征,可以直观地表达笔力的概念。而当它要表达不仅有力而且有神的意涵时,另一个更加能够承担“神”义的字眼必须参与进来,帮忙承担这个意义,比如形成“风骨”“神骨”“气骨”这样的双音节词。但这些概念都不成“论”,在书学史上,呈现“有用无论”的情形。
在《风骨论》的末章,汪涌豪曾点出风骨范畴的通感价值。但要知道,文学与书法因媒介有别,同样的词语能够发挥的美学理论价值亦有别。对于文学而言,力是通感 ;而对于书法而言,力是实存。因此,以通感作喻,“风骨”与文学的距离更近 ;以实感作论,“骨力”与笔墨的关系更切。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