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蒙古国像极了一个中年人,被生活夹击得喘不过气。明明祖上阔过、风光一时,转眼自己却成了“缓冲区”,不是这里拉一把,就是那里按一手。有时候想想,命运开这种玩笑,还真有点扎心。
1945年的8月,这一天本不是个历史节点,却被一纸条约,写进了无数中蒙家庭的命运里。外蒙古,原本是清朝统治的一方土地,突然间就能“宣布独立”了,一瞬间,地图上多了156万平方公里的新国家。这156万,是草原上的星星点点羊群,也是几代两地亲人的心头结。朝廷、国界、族群,在大国博弈面前,都不过是地图上一层不大稳固的颜料。
想想蒙古的位置吧——天冷,风大,矿下藏着点银子,山头挂着牛羊,剩下的都是距离。隔着几千里,外面的人总觉得蒙古“穷”“闭塞”,靠着矿和牛羊,挣扎了80年。可要是你走进乌兰巴托的小巷,冬天看到姑娘们系着头巾排队买煤饼,也许对他们的艰难会多一分理解。
等到新中国成立,一纸合作,两个邻居开始搭话。那天,可能下着点毛毛细雨,也可能风很大。外交官们握手,现场拍了照片,可照里的蒙古人到底是真心,还是有些勉强,谁也说不准。毕竟,这邻里关系一直像拧巴的床单,时好时坏,尴尬又亲近。
有些事,人心知道。蒙古的老百姓更喜欢俄国人,哪怕俄国人冷峻,比中国人“有距离感”。也难怪,再怎么说,彼此的牵绊太复杂。八十年代,排华事情闹得可真大——乌兰巴托的华侨一夜之间成了“外人”,被要求搬到莫名其妙的外省,说不去就要驱逐。事后亲历的人回忆,48小时里一家老小抱着被褥往外跑,谁还管得了多少祖国情感?后来九十年代,类似的风波卷土重来。民间多少人到现在还耿耿于怀,谈起外蒙古,话音里总带着那么点疙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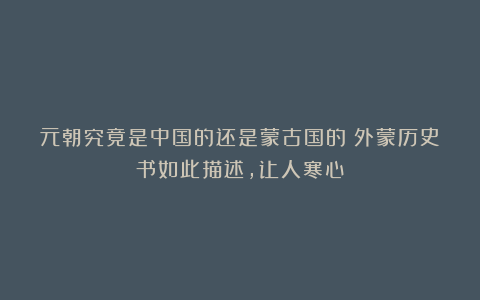
话说回来,亲戚再怎么不对付,还是亲戚。几轮折腾,中蒙关系又有了新变数。今年,随着蒙古邀请中国参与自己曾经只跟美合作的维和演习,朋友圈突然打开了。你说值得高兴吗?总觉得心里有颗石头没落地,大概谁都怕下一步又走回头路。历史教会了人谨慎。
其实,“外蒙就是落后”的印象,已经太根深蒂固了。但这地方太容易让人一叶障目。地广人稀,经济命脉掌握在几个家族手里,牧区生活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过度放牧”听着像环保词,在这里,是实打实的生存难题。你去查数字——330万人,国民平均一年只能挣7000美元。除了矿,其他事都靠天吃饭。草原沙化,连带着影响了内蒙古。骑马的牧民,如今也要被风吹得找不到营地。
我见过一些蒙古朋友。大部分很务实,不多谈政治。一到晚饭,聊的是牛羊肉、盐、冬天要囤多少煤、俄罗斯电视节目什么时候换新。问他们怎么看中国,很少正面回答——笑着岔开话题,偶尔说“历史太复杂”。其实哪国小民都一样,操心的是眼前。
这份尴尬还要谈多久?蒙古受惯了“大国夹缝”,被动得狠。今天是靠俄罗斯,明天可能拉中国一点好处。中国倒是真心实意想推近关系,但也明白“历史这本旧账”,不是一纸协议能结清。
现在倒好,历史又被拎出来聊了。想想元朝,一千年前草原上的覃音涛声。有些蒙古人喜欢在教科书上写——元朝是大蒙古国的顶峰,不是什么“华夏王朝的一段插曲”。两边人都自认为说的是实话。但要我说,读历史没啥复杂——就是谁也不服谁。大陆的孩子会背“宋元明清后”,把元朝当自家王朝;可蒙古教科书却教自家的孩子:“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草原的主。”
忽必烈的故事,架在这分歧中间。历史书上,他是黄金家族的代表,是开国皇帝,是一统江山的大人物。可蒙古教科书,宁愿记他是“大蒙古国的大汗”,更不愿提“他是中国的元祖宗”。河套地区、农耕文明,这些词在蒙古青年眼里,是“被侵占被改变”的标志;在中国人眼里,却是国家疆土的变迁。你说谁对谁错?有时候,版本多了,各自都觉得自己是正义之神。
不止一次听蒙古年轻人抱怨:“我们要去中国化,做自己的主人。”历史课本就成了工具,把元朝那段统治说成“我们征服了南方”。每读到这些,不免心里一咯噔——情感的距离,早写在一句一句教科书里。中蒙旧恨新仇,最后都化作现实里那些不合拍的小摩擦。
回头想想,这种分歧,大抵改变不了什么。但却让人微微难过。明明曾经是一家人,血缘和文化至今还留着相似的轮廓。可就是这样,大国的棋局、历史的分岔,把草原上那点亲近感消磨得所剩无几。
其实,历史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争的。我倒愿意蒙古国真能迈出几步,摆脱那种“夹缝”和对谁都要点头哈腰的局面。可这得需要很大的勇气。邀请中国参加演习,是靠近一步,还是偶尔给大国一点面子?没人敢断言。历史的大漠烟尘,有时吹到现代,还蒙着人的眼睛。
最后,老生常谈一句:忘了曾经,大概就和自己划清了界限。但记得太多,又难免心头有疤。中蒙,是不是还真应了那句话——剪不断,理还乱。以后怎么走,大概也只有时间能说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