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素师晚年最佳之作,所谓:“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意境似之。
——于右任跋怀素小草千字文
民国二十三年春,于右任在南京寓所的书房里来回踱步。窗外雨打芭蕉的声音让他想起三十年前在西安碑林初见怀素《小草千字文》拓本的情景,那绢本上蜿蜒的墨迹像极了终南山间盘旋的云雾。
‘院长,上海来的急件。’秘书捧着个桐木匣子匆匆进来。于右任拈起放大镜时,手指竟有些发抖——匣中正是他苦寻多年的怀素真迹。展开卷轴的瞬间,松烟墨香混着千年时光扑面而来,纸色已呈深秋银杏叶般的暖黄,可那些字迹仍如新发于硎的剑光。
他忽然笑出声:’这老和尚,越写越懒了。’只见卷尾处分明是’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却硬生生少写个’韵’字。秘书正要解释可能是残卷,于右任摆摆手:’怀素晚年中风后右手不便,这是用左手写的。’说着指向’纨扇圆絜’的’絜’字,那本该对称的部首歪得像醉汉的斗笠。
夜深人静时,于右任在案前铺开六尺宣纸。他想起去年在黄山见到的奇景:八十老僧独坐云海,用枯枝在岩上写字,写完便被山雾抹去。此刻笔锋触及纸面,他突然改了主意,竟用怀素最擅长的狂草体写下’松风流水天然调’,可写到’抱得琴来不用弹’时,笔势忽然收敛成温润的行楷。
‘有意思。’他摸着胡子自语。当年在东京学书时,老师说过’草圣’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此刻他忽然明白怀素晚年为何返璞归真——那歪斜的’银烛炜煌’四字,分明是老僧深夜抄经时被风吹动的灯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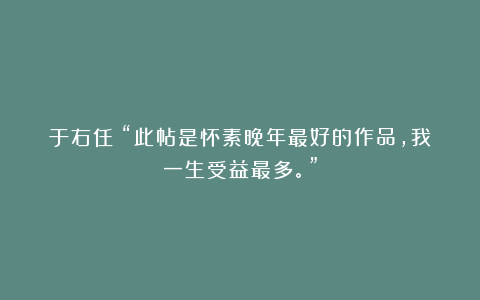
次日清晨,秘书发现书房地上散落着数十张废稿。于右任正在用裁纸刀小心修整跋文边缘:’你看这’敕’字最后一捺,像不像古琴的雁足?’他突然说起昨日在中央大学听闻的趣事:德国汉学家认为怀素书法充满’非理性冲动’,而日本学者坚持这是’禅定的结晶’。
‘都错了。’于右任将完成的作品举到窗前,晨光透过宣纸显出纤维的脉络,’这是老和尚在教我们写字要像山涧流水——该拐弯时拐弯,该跳崖时跳崖。’说着指了指跋文中突然加粗的’不’字,那墨色浓处竟露出绢本的织纹。
三个月后,这篇跋文与怀素真迹同时在上海展出。展览图录里,德国记者将’不用弹’译作’无须演奏’,而日本学者则坚持应是’不必弹’。于右任在开幕现场笑而不语,只让工作人员在展柜旁放了台老式留声机,循环播放着古琴曲《流水》的第七段——那正是表现泉水跃下悬崖的章节。
展会最后一日突降暴雨,展厅穹顶的漏水在玻璃柜上蜿蜒出细流。有位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学生忽然惊呼:’快看!’只见水痕流过跋文投影时,那些字迹竟在波纹中轻轻摇曳起来,宛如千年前某个春夜,长安慈恩寺的烛光正映照在素绢上颤抖的笔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