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廖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自2016年起从事商业摄影。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他将镜头转向了故乡的土地——那些缭绕着香火与传说、被现代性叙事日渐边缘化的民俗现场。中元节(普渡仪式),尤其令他着迷。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民间信仰的展演,更是一场生者与亡者之间的深邃对话,是潮汕人关于敬畏、记忆与生存哲学的年度实践。
摄影师廖廖
95后,潮州潮安人
然而,他也注意到,当下人们对普渡的认知正被误解与猎奇的话语侵蚀。许多参与者并不理解其背后的文化与伦理维度,甚至仅是为了追逐流量而介入。正是这种断裂,促使廖廖萌生了以纪录片进行系统记录的愿望——他想要以冷静而尊重的镜头,重返仪式的现场,触摸这一民俗真正的脉搏。
以下文字,根据廖廖的口述整理而成,是一个从视觉工作者走向文化观察者的内心独白,也是一次朝向民族志影像的尝试。
字数: 7000字 | 阅读时长: 20分钟
潮汕普渡仪式
从商业摄影师到民俗记录者:一场血液里的召唤
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早年在外工作,只有春节返乡时,我才会偶尔拍摄一些民俗场景,更多是出于视觉兴趣,还谈不上文化上的自觉。
转变发生在2020年。疫情让整个世界停摆,我决定回来到故乡生活。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更深入、更系统地去记录这些仪式。潮汕民俗于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越拍越沉浸,越拍越上瘾。如同受到血液深处的召唤,抓住我不停去挖掘更深层的信念: 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入口,通向更庞大的叙事网络。
2020年,廖廖从广州回到潮汕金石, 前往潮南拍摄的英歌舞现场
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个所谓“专题”。我只是持续地拍摄七月期间的各种仪式,后来有人看了我的素材说:“你这不就是在做一个专题吗?”我才意识到,也许是的。于是我把它命名为「潮汕七月」——而不拘泥于“中元节”或“盂兰盆节”这类名称,是因为潮汕地区在整个农历七月甚至八月都在进行不同形态的普渡,用一个时间指称这样的活动反而更贴切,也更开放。
2021年,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去拍摄普渡,是由一位朋友带我去的。去之前他特别叮嘱我:不要乱说话,也不要乱碰东西,一定要带着敬畏之心。那次拍摄并不顺利。村里人很警惕,担心我是来“曝光”的。同行的朋友一再解释:只是做文化记录,没有恶意。可是拍到一半,在对方很不客气的语气里:“你们在这里,会搞砸仪式!”,我们还是被“请”走了。
后来才知道,反对拍摄的并不是村民,而是主持仪式的“西公”。西公,另一种叫法为香花僧,是明末清初起源于闽粤地区的佛教教派,融合佛、儒、道三教;他们多是居家修行的居士,而非出家的僧道,主持仪式时诵的经文是以潮汕话杂糅古官话进行的。朋友告诉我,七月的法会必须由功力深厚、经验老到的西公主法,就连他们自己在此期间都格外谨慎,有所忌讳。这件事刷新了我的认知,它不再是童年模糊的恐惧,而成为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严肃性的文化实践。
到2022年,我开始更系统地拍摄记录。疫情缓和后,我走了更多地方,从潮州潮安区到汕头潮阳,逐渐意识到哪怕同属潮汕文化区,不同地方的仪式形态、供品制式甚至纸扎样式,都存在差异。江河山脉的自然分隔,使得各个村落发展出独特的祭拜传统。尤其是潮阳一带,其民俗形态之丰富、仪式之完整,令我尤为着迷。
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记录这些差异。渐渐地意识到,表面上统一的“潮汕普渡”,内部其实洋溢着地方性的多元活力。而这,正是民间文化最真实的状态——它不是博物馆中标准化的展品,而是活生生的、在流动中不断变异成长的实践。
普渡:生死之间的教育剧场
在潮汕人的宇宙观中,祖先若是善终,通常已升天为神;而无主孤魂,则沉沦于地府之中,受尽苦难。普渡,便是为这些亡灵施行超度的大型仪式。
但我在拍摄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普渡表面上是为亡者,实则更是为生者而设。它是一场道德教化的年度剧场,借助幽明之际的仪式,重申社群的价值秩序和人伦理想。
普渡的环节繁复而有序:放水灯是为了引请孤魂前来,法事用以超度亡灵,烧纸扎是供给阴间所用,而“抢孤”则构成仪式的高潮与收束。整个农历七月,潮汕人称“鬼节”,但其实它融合了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以及儒家的孝道思想,成为三教合流的民间典范。
道教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中元节祭祀地官,赦免阴间罪鬼。“盂兰盆”一词来源于汉传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为“解倒悬”之意,即将人的灵魂从苦厄中解救出来。《盂兰盆经》记载,目连为救母亲脱离恶鬼道,依佛祖指示,于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以百果饮食供养十方僧众,终借其合力救出母亲。由此形成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强调供养僧众、救度亡灵的功德。
自南北朝起,这一节日逐渐深入中国民间,唐代甚至由国家主导举行大规模法会,以超度阵亡将士。原本偏重佛道的宗教仪式,因此逐渐演变为融合儒家孝道与祭祀伦理的民俗实践。
佛言:“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之力所奈何。汝虽孝顺声动天地,天神地神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当需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吾今当为汝说救济之法,令一切难皆离,忧苦罪障消除。”
-《盂兰盆经》节选
祭祖是重要的开场。我们在普渡前会先祭拜自家的先人们,而后才会施孤。所谓“施孤”,即以食物、衣物等施予无主孤魂,助其超生。事实上,整个七月,潮汕乡野几乎无日不祭,无村不拜。家家户户备办祭品,一般在指定的地方,持香跪拜,并将香火插遍路边沟畔,象征着遍济四方的慈悲。
各大善堂与寺庙也会搭建“孤棚”,举办盂兰胜会。孤棚上供地藏菩萨,棚前则矗立纸糊的“鬼王”,又称“孤王”。民间传说,是因为施孤时万鬼云集、争抢激烈,连观音都难以制止,只好化身鬼王镇坛,以维持秩序。这种充满戏剧性的设置,实则隐喻了仪式对“混乱”的警惕与对“秩序”的渴求。
有些地方会放置招魂幡,招魂幡越大,招魂越多
潮汕地区现存的「面燃大士」祭祀传统,主要集中于潮阳区南阳、濠江区河浦及汕头存心善堂三处。这一古老仪式蕴含着独特的文化逻辑:纸扎祭品的规模被视为法力的具象化呈现——造得愈宏大,所召引的孤魂野鬼便愈众,其施孤善行的功德亦愈显深远。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纸扎神像还承担着阴间秩序维护者的神圣职能,如同阳间的礼官,确保前来领取香火与生活用品的亡魂们循规蹈矩,不致引发混乱。这种对幽冥世界秩序井然的想象与构建,恰恰折射出潮汕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伦理观,以及通过仪式维系阴阳两界和谐共处的古老智慧。
孤棚上堆满食物、衣物,甚至日常用品;棚侧往往有装满银纸的“观音宝船”。为区分不同亡魂,棚中还设男女老少不同的灵牌。一些地方还增设了“抗战阵亡将士”的牌位;存心善堂增添了汕头“七·二八”风灾的抗洪英灵牌。这些细节,清晰映照出历史在民间仪式中投下的影子。
不同善堂孤篷的搭建也有所不同
法会开始的前一天,会先放水灯旨在引导亡灵前来听经和享用祭品,之后金刚上师主持开坛,诵经念咒,手结印契,并向四方抛撒面桃、米饭,称为“放焰口”。佛经中说,饿鬼喉细如针、口吐火焰,无法吞咽,“放焰口”即藉佛力打开其喉,令得进食。这是仪式中最具表演性和视觉张力的环节之一。
金刚上师主持开坛,诵经念咒,手结印契,并向四方抛撒向四方施撒,俗称放焰口
放水灯旨在引导亡灵前来听经和享用祭品
法会现场
随后所有纸扎祭品、观音船和鬼王将被抬至河边,焚化送走。人们相信,只有通过火焰的转化,物资才能送达亡灵之手。
焚烧纸扎物品更是重要环节,衣物、汽车、摩托车,甚至精致的纸扎直升飞机,都会在祭祀后化为烟火,寓意着让孤魂在阴间也能拥有实用之物,这份细致与厚重,正是潮汕人对传统的珍视与传承。
焚烧纸扎物品是祭祀仪式的核心环节。这种独特的仪式,既是对逝者的深情馈赠——愿其在彼岸世界仍能享有现世的便利与尊严;更是潮汕人用心血书写的文化密码,每一缕升腾的烟火里,都跃动着对传统的虔敬守护与代际传承的庄重承诺。
最后是“抢孤”,往往将气氛推向高潮。工作人员将孤棚上的物品抛下,民众纷纷争抢,有用特制“孤承”兜接的,也有徒手捡拾的。在老一辈人的叙述中,以前的抢孤甚至包括农具、家畜,乃至贫穷人家女儿的赎身牌,夺牌者凭牌领人。如今虽已无此旧俗,但抢孤仍保留着强烈的互助与共济性质。
抢孤仪式的高潮,是主事人将写有祭品的竹签高高抛向棚下。刹那间,台下众人屏息凝神,手持自制的渔网、竹圈等工具,目光如炬地追踪着空中翻飞的竹签。待竹签下坠的刹那,他们看准时机,奋力一跃,或挥网兜住,或持圈套取,动作迅捷而精准。这场看似简单的竹签争夺,实则是生者与亡魂之间一场神圣的交接——接住竹签者,不仅赢得了祭品,更承担起为孤魂野鬼传递人间香火与关爱的使命。
在我走访的过程中,有一个念头逐渐清晰:那些战死沙场的英雄,本当升天为神,而非年复一年地返回人间享受施舍。这或许反射出普渡更深的一层结构矛盾:人们既希望通过仪式安抚亡灵,又渴望它们终得超脱、不再归来。
这种张力,恰恰体现出普渡作为生死教育的深刻性。它构建了一个道德的宇宙观:善者登天,恶者堕地,而未得超度的亡魂,则成为现世行善修德的参照。通过年复一年的仪式,生者被提醒:生命的价值,在于此生此世的言行与选择。
抢孤:民间智慧的互助机制
“抢孤”或许是普渡仪式中最被外界误解的环节。在很多人看来,这仿佛是一场混乱的抢夺,甚至带有“陋习”的色彩。但当你真正走入其语境,会发现它实则是一套高度组织化的民间互助机制。
不同村落的抢孤形式略有差异。有些是将祭品直接摆放在地上,仪式结束后开放争抢;也有些村庄专门用竹竿搭建“孤棚”,离地一人多高,将祭品置于台上,等时辰一到,就向下抛掷。
能抢到什么,往往取决于村子的经济状况和当年理事们的筹备。物资来源多是本村老板或外出乡贤的捐赠。米、油、蔬菜是基本配置,有些地方还会有单车、电动车、家电等大件物品。不过实际抛撒的是代表这些奖品的竹签,人们抢到签后再凭签兑换。
我意识到,这表面上是给予另一个世界的“施”与“舍”,但其物资最终流向的是此生此世中需要帮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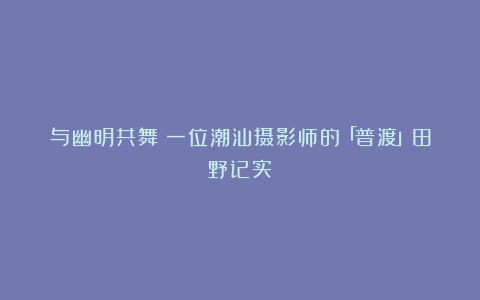
像潮阳一带,许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祭拜后捐米的习俗。一部分人自带两袋米来,祭拜后便留在庙中,由义工或妇女组织收集起来,仪式后分发给村里的五保户、孤寡老人或经济困难的家庭。
我曾听闻一个村子收到三万斤捐米,其中一万斤用于抢孤,剩余两万斤则送往孤儿院或贫困地区。这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机制,是民间自我组织的慈善实践。
来参与抢孤的,除了本村人,更多是外来务工者、环卫工人、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抢到一两袋米、一瓶油,或许就能减轻大半个月的生活负担。本地人越来越少参与争抢,他们认为,这些物资本就是为有需要的人准备的,自己再去抢并不合适。村庄往往也会预留一部分,用于照顾本村的困难户。这不是排外,而是社区内源性保障的一种体现。
抢孤收获
抢孤中有一个有趣的物件:斗笠。许多人会特意争抢它,因其象征“起厝”(建房子)的吉兆。抢斗笠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彩头,带有游戏和祈福的成分。
需要什么,就抢什么。仪式并不刻意强调道德,却自然呈现出人各有需、各取所需的民间理性。
整个仪式藉由抢孤收尾:它提醒亡灵法会已毕,勿再流连。
正如俗语所说:“又怕它们不来,又怕它们乱来。”这种恭敬与谨慎并存的态度,折射出潮汕人对待超自然存在的务实智慧:既怀慈悲,亦守分寸。
孤衣:跨越阴阳的纸扎艺术
去年,我在一座善堂连续拍摄了三天。最初到场时,几位老人对我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颇感意外。普渡期间,极少有家长带孩子前来,人们都保持着一份慎重的距离感——不是恐惧,而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
第一天无人与我交谈,第二天才有人开口问:“你来做什么的?”等我说明来意,对方便自然地邀我:“中午在这儿吃饭吧。”
善堂最忙的是普渡前的一两周。大家往往留堂吃斋,他们叫我来吃饭时,说了一句特别温暖的话:“来,给阿公请!”——“阿公”指的是祖师公,语气如同呼唤家中的长辈。那一刻我体会到,“阿公”早已超越具体的神明,成为善堂共同体精神的象征。
他们当时正忙于制作“孤衣”,即普渡时焚化给亡灵穿的纸衣。我由衷敬佩这些老人。从二月初到六月底,整整五个月,几十位七八十岁的长者聚在善堂或闲屋里,一边喝茶聊天,一边不停的折纸、粘贴、绘制。五个月下来,孤衣总量可达数十万件。
这些衣服涵盖所有年龄与性别:婴儿服、青年装、老年衫,甚至西装、裙装、传统盔甲。他们并不因循守旧,会研究当下流行什么,不断尝试新的样式。每一件孤衣都极其讲究:扣子、暗袋、腰带、拼色、渐变……毫不马虎。
一套完整的孤衣,包括外套、裤子、内衣、毛巾,再加上纸钱和往生咒,被整齐收入纸盒中,仿佛真的是一套即将售出的服装产品。
一位阿姨一边糊纸一边讲:“来这里听完经,穿好新衣服,就去见佛祖了,不要再回来。”我听了特别触动。她们年复一年做这些,是希望那些亡灵能吃饱穿暖,体面地去往极乐世界,不再于地狱辗转。
她们是不是一边盼着“他们”来,一边又希望“他们”不再来?看似矛盾,却非常温柔的愿望:或许总有一些灵魂尚未被安顿,需要年复一年地被纪念、被抚慰。
我甚至看到她们做三寸金莲——那种原以为早已绝迹的小鞋。我不禁想:这么多年过去,还需要穿这种鞋的灵魂,应该都已被超度了吧?但也许,这些衣物不只是被送去“下面”,也可以被送往“天堂”。
最年长的阿婆今年已九十五岁。她精神矍铄,每到二月,就约上老姐妹一起做孤衣。我有时会想,明年、后年呢?这群人当中,总会有人慢慢离开,会有新的人加入吗?
孤衣制作者,最年轻的也已七十三岁。一位本地人告诉我,隔壁村已经没人亲手做孤衣了,都是直接去买。纸扎店卖的,远不如阿姨们做得那么精细、那么用心。我很想用影像记录她们——不只是作为做孤衣的人,更是与我们渐行渐远的传统民俗文化的载体。
他们真心相信:这些衣服烧化之后,是真的会被收到且穿上的。
有一次,我看到她们把纸衣用线串起来晾挂。风一吹,小裙子轻轻飘动,非常好看,“因为小孩子就喜欢花花绿绿的”。后来拆架时,工人粗手粗脚扯坏了衣服,阿姨们急忙制止:“你扯破了,他们怎么穿!”阿姨们将扯坏的衣服重新缝纫,小心翼翼挂上。这些带着人们美好心意的孤衣,即便最终要被焚化,但在那之前,它们必须是完好的、体面的。
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不是迷信,是一种极致的尊重。
善堂:潮汕民间的慈善之核
在汕头达濠,有一片特殊的墓园,它不属于某个家族,也不纪念显赫的英雄,而是1943年潮汕大饥荒死难者的集体安葬地。那一年,干旱与战乱交加,粮价飞涨,路有饿殍,估计约有50万人因此丧生。这片墓园,是从德善堂主持收埋到的3440具遗骸的长眠之所。
自宋代大峰祖师开创善堂以来,收殓无主尸骨就是其核心善举之一。即便在今天,若发现无名遗体(如意外身亡的无亲者),警方完成勘查程序,仍常请善堂协助后续收殓。他们或将遗骨安葬于“百姓公墓”,或暂时安置、定期集体安葬。这种对无名亡者的善待,深刻体现了潮汕民间的伦理观念。
此外,善堂还承担着施医赠药、免费供餐、关怀孤寡、助残助学、救灾救难等慈善职能。如汕头的存心善堂,至今每日为孤寡老人送餐,并义务为他们料理后事。活动的经费多来自民间捐赠,凝聚着社区的共善力量。
因此,当我们谈论普渡、谈论祭祀文化,看到一些为博流量而声称“无人知孤魂之墓在何处”的内容时,应格外警惕。潮汕的善堂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社会价值。它不仅是民俗信仰的外显,更是一种扎根民间的慈善体系,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社群责任的担当。
那些由善堂世代维护的墓园,以及它们持续的善行,是对历史最真切的铭记。我们应当努力理解这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尊重一代代善堂人的付出,不能因追求流量而伤害这份珍贵的文化传统。
拍摄即修行:影像人类学的思考
三年跟拍,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拍摄伦理:保持距离,保持敬畏。不打扰、不干预,只做静默的记录者。珍视人们的用心,感受场域中神圣庄重的氛围。
一碗祭饭、一筐祭菜,都承载着深沉的仪式感。私人祭拜通常是一碗一碗地准备,而集体普渡时,则常以大桶蒸饭、整筐蔬菜,郑重的摆放于祭台。许多人以为这些祭品之后便被丢弃,其实不然。它们最终常被送至贫困家庭,或用于喂养牲畜。
尤为令我动容的,是人们准备祭品时的态度。从淘米到洗菜,一切都皆有章法:米要洗三遍,掉落的米粒拾起后要重新冲洗;蔬菜要剔除老叶烂叶,反复清洗干净,烫熟后调味。他们是用为家人准备餐食的心,来准备这场给“他界”的宴席。这种近乎固执的认真,令人肃然起敬:无论对象是谁,无论是否被看见,做事的态度本身即是一种修行。
法会的场所常搭起高台,西公或僧侣于其上诵经行仪。我的每次拍摄,都坚守一个原则:绝不踏上那座台。我只在台下记录,与台上维持一段自觉的距离。
高台上面供奉的是佛祖,进行的是神圣的法会,整个道场是清净肃穆的。那几日,行仪者斋戒净心——我虽非素食者,但仍愿保持一份敬畏。这不仅关乎征得同意与否,更是一种自我约束:我怕自己无意间携带了什么,冒犯那份庄严。
这份谨慎,也与法会自身的性质有关。在民间信仰中,这类仪式不仅为超度,也涉及“招请”。所迎请的,并不全是“善灵”;若仪轨有失,行法者甚至可能受到反噬。这里有一种说法:心不诚或行不端者,或会被“无形的力量”推下台。
背后蕴藏的,是一套深厚朴素的因果观念。为何我们既行普渡,又心存敬畏?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多是尚有执念、或在世作恶的亡灵。按道佛两家的说法,这些灵魂正因生前未能行善积德,才会滞留阴间,需靠法会超度。而潮汕人普遍相信,自家祖先若得善终,早已登天为仙,并不会在七月流连人间。
所以,普渡表面是“祭鬼”,实则是“育人”。它藉由仪式传递一种宇宙观和因果叙事:人要活得正直、善良、有担当。此生积德行善,不仅是为了死后免于沦为“孤魂”,更是为了超脱轮回之苦,不再需要人间年复一年的“施舍”。它最终指向的是:人应如何自省,如何修行,如何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生命的态度:从民俗记录到价值重思
三年记录,若说心境的改变,那并非是指颠覆性的震撼,而是一种认知上的提升:我越来越相信,人要行善。
这种善未必宏大。它可能只是为人指一次路,或是接过善堂老人递来的一碗凉茶——那不仅是一碗水,更是一份无声的布施。我们接受,也应传递。
海祭-晨光初现时,渔民们携三牲五果、纸钱香烛肃立于滩头。主祭者素衣执香,面海三拜九叩,诵念渡厄引魂古咒。祭品奉上:米粿成莲,喻超度;活鱼虾蟹归海,示轮回;朱砂纸船载黄符,随潮远逝。此海祭乃阴阳之契。渔民信祭品入海时,亡魂循潮受飨。沉海供品既敬水府诸神,亦慰溺亡先灵。
为婴儿孤魂设立的祭祀台
它也让我反思许多被标签化的行为。比如“抢孤”,常有人觉得争抢祭品者“低人一等”,但我认为,众生平等。他们只是此时有需要,不代表就比你卑微。今日他接受,明日或许他就能给予。这本身就是一个循环,一种流动的善意。
包括有人批评祭品被浪费:“拜完不就扔了?” 他们不知,这些祭品从不被糟蹋。连掉地之米粒都会被拾起洗净、蒸熟,祭拜后,再用于赠人饱腹、或喂养动物。
所以我常说,如何看待这一切,取决于你的心。心向善,所见皆善;心若恶,再多的好意看来也只是表演。普渡表面是一种民俗仪式,但其内核是劝人向善、教人惜福,告诫我们:万物有灵,众生皆值得尊重。
甚至谈到死亡,我也变得更坦然。有人忌讳纸扎,我说:“待你百年之后,有人烧这些给你,不知该有多欣慰。”说到底,这是生者心意的延伸,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温柔想象。
每年普渡,我都会提醒友人:七月夜晚,尽量不带小孩外出。这不是宣扬恐惧,而是出于保护。就像潮阳有些地方,普渡法会连办三天,到最后一天放大焰口,大多数家长绝不会带孩子去。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慎重的教养。
以影像重返精神现场
接下来,我计划以个人视角完成这部关于潮汕七月的纪录片。不试图为普渡做任何权威定义,而是聚焦这三年来的所见所闻、表达我个人的理解与认知。作为潮汕人,我对自己所记录的文化内容、所说的每一句话、记录的每一个场景,都须负起责任。
我想做的,是一部真实、负责、有深度的纪录片。它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还原记录这项古老民俗的当下面貌,也期待能唤起更多人对民间文化内在价值的关注。
或许最终,普渡仪式教会我们的,并非如何与亡灵相处,而是如何与生者共存,如何在缅怀、敬畏与共善之中,活出一个更温暖、更庄严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