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亚马逊,肯定要看亚马逊的人。
今天向导带我们探寻亚马逊原住民。几个中国游客又碰巧一起了。
我们出发时雨还没停,我胡乱披着那件在雨林小屋花了10美元买的一次性雨披——薄得像保鲜膜,本以为毫无性价比,这时却庆幸有了这层膜。风大雨大,我死命扯着聊胜于无的帽檐,披着雨披缩在无篷的船尾风中零乱。
好在船靠岸的时候,雨停了,上岸的地方,是一片泥泞的滩涂。空气里弥漫着青草与湿木的气息。
我们刚跳下船,脚一落地就陷进了松软的泥里。向导笑说:“这才是真正的亚马逊。”我脚下泥泞,步履踉跄。狼狈中顽强保持平衡。
雨水褪去的土地上,几幢木屋伫立在高脚木桩上。木板拼成的墙,缝隙能透风,屋顶是几片生锈铁皮。屋内没有灯光,只有昏暗的天光从缝里漏进来。
屋檐下,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好奇地看着我们经过,身后的黑屋里隐约可见还有比她更小的孩子。向导低声解释:“他们的家里没有卧室、客厅或厨房,一切都在同一个空间。”
我走过这些木屋,心里忽然生出一种矛盾的情绪——
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却过着最简陋的生活。
这种落差,不是悲情,而是一种现实。亚马逊的丰饶属于自然,而非人类。
泥路两边是一片片混杂种植的农地。
不同于我们印象中整齐划一的田垄,这里的作物像森林一样混杂:木薯、玉米、香蕉、辣椒、番薯都在一起生长。
“为什么不分开种?”我问。向导说:“因为明年可能这块地又要被水淹。这里的地是活的,种子自己会选位置。”
亚马逊一年分旱季与雨季。雨季洪水漫天,吞没村庄;旱季退去,人们回到原地重新种。
他们没有肥料,也没有机械,靠的是“自然的筛选”——能活下来的,就是这一年的收成。
这种看似随意的“混种”其实蕴含着亚马逊生存哲学:
不抗争,不执拗,顺其自然。
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征服,而是共生。
向导说,亚马逊里的村庄也像呼吸一样,一涨一落,随水漂移。
我想,也许在亚马逊,连“生存”都是流动的。
人不属于土地,而是与土地一起漂泊。
转过一片林地,一个当地男孩迎面走来,手上停着一只绿色鹦鹉。他骄傲地举起鸟儿,示意我们拍照。鹦鹉乖巧地歪着头,阳光打在羽毛上,绿得发亮。
大家都觉得空手面面相觑不好,互相问是否带了糖果啥的,但显然都没准备。幸好我随身带的腰包有钱,递给他十比索,他熟练接过微笑鞠躬。那笑容,单纯又带着某种向往。
来到原住民的保护中心,这只是一个有几个茅草屋围着的空地,一圈挂着一些当地特色手工艺品。
雨后的泥地上,一群红裙女孩正抱着树懒迎客。
那一幕让人一时恍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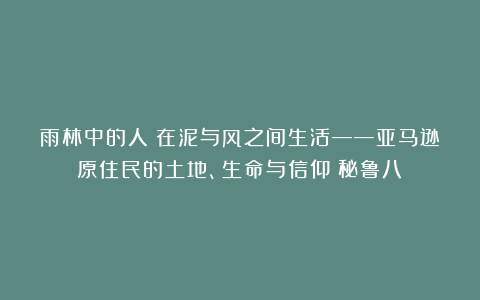
树懒懒洋洋地趴在女孩怀里,毛发还湿漉漉的,女孩们看着我们来都围上来。
有几个走上前,微笑着递过树懒让我们抱。一行人纷纷抱过村懒除了怂人我。
我一向敬畏野生动物,在她们眼中,树懒是朋友;在我眼中,它仍属于森林。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也许就在于“谁主谁客”。
接着,族长取出一支长竹吹管,演示他们的传统技艺——吹箭。
他将羽箭轻轻塞入竹管,深吸一口气,只听“啾”的一声,箭精准地射中远处的树干。
同行的团友有好奇的试了试,力道很难把握,我想如果这是他们的武器,武力值确实堪忧,丛林生活太难了,如果是我,估计难活过两天吧。
那时我再次庆幸我腰包随身带,可以随时给小费而心安。果然,给了小费后,族长高兴地带我们进了部落村的“中心”表演。这是一处圆形的茅屋,棕榈叶?屋顶下,旋长打起低沉的鼓声。族人们聚集过来围成圈跳起简单的舞。
草裙飞扬,鼓声震动土地,节奏原始而热烈。孩子们欢呼,部落气氛热烈。
他们的生活简单到极致,却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和谐的秩序——
鼓声是他们的语言,节奏是他们的历史。也许“文明的原点”就是如此简单。
离开部落,我们乘船前往附近的猴岛。
那是一个由NGO运营的“猴子援救中心”,专门救助被捕猎、被弃养的猴子。
志愿者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喂食、清理、治疗这些动物,再让它们重回雨林。
猴子在林间自由攀爬,像重获新生的灵魂。
这片雨林不仅养活人,也养活希望。
就在那时,我想起珍·古道尔。
不久前,她离世的消息刷屏,世界为她哀悼。
她的一句名言此刻在我心中回荡: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
站在亚马逊河畔,探访了雨林中的原住民和雨林生物,我更能理解这句话的分量。
在这片土地上,“了解”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汗水、蚊虫与泥泞。
回程时,雨又下了。
雨点打在河面上,像无数细小的心跳。
我望着远处的部落,那些木屋、孩子、狗、鹦鹉、树懒、鼓声——
一切都逐渐融入雨雾。
我们这些外来的旅人,带着相机、药片、驱蚊液和时间表,看似在“探索”自然,其实是在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也认识何为真正的“敬畏”。
在亚马逊,连风都有灵魂,连泥泞都在呼吸。而那些生活在雨林中的人,或许早已懂得——文明不是建筑出来的,是顺着自然活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