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天,我们背着塞得鼓鼓囊囊的军被行囊,踏进福州梅峰路6号的校门。右手边水泥柱上挂着块白底木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卫生学校”几个黑字,在九月的太阳下透着沉静的庄重。那时候谁也没料到,四年后这儿会改成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而我们,成了用这个老校名毕业的最后一届学员。
这所学校依山而建,满眼都是绿意。从校门到教学楼的主路两旁,从教室往坡顶宿舍去的小径边,都整齐地长着高大的白玉兰树。树干粗壮,树皮斑驳,刻着年岁的痕迹,想来该是建校时就种下的。它们就这么静静伫立着,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员成长,也陪伴我们走过了两年时光。
我分在学员二队,担任二区队的区队长。队里一共三个区队:一区队是医士班,我们二区队和三区队是护士班。每个区队又分四个班,每班大约十二个人。学员中大多是南京军区各单位选送的战士,也有少数部队子弟直接招进来的“内招生”。可不管来自哪里,进了这个门就都一样了——都是军校学员,肩上扛着同样的期待与责任。
开学第一关就是九月的军训。福州的初秋依然又湿又热,训练场上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我这刚上任的区队长,不光要把“一二一”喊得响亮,还得用余光时刻留意队伍是否整齐。有趣的是,即便是在部队待过的老兵,这时也得从最基础的摆臂重新练起——在这片操场上,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军训时最让人惦记的是英子。她矮矮黑黑的,眼睛不大,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一开口就是憨厚的家乡话。可她走正步总“顺拐”:左腿迈出去,左胳膊也跟着往前甩,活像只认真却总踩错步点的小企鹅。教员越纠正,她越紧张。队伍里偶尔飘来的笑声,让她脸涨得通红,只会攥着拳头小声嘀咕:“咋又错了哩!”
大概是不想拖队伍后腿,每天晚饭后,她总会悄悄来找我:“区队长,陪我练练?”我俩就蹲在玉兰树底下,她自己喊着节拍一遍遍练习,额角的汗珠滚下来,砸在草地上。哪怕只练顺了一步,她也咧开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你看!俺就说能行!”那股子认真劲儿,比九月的太阳还要热烈。
军训一结束,规律的学习生活就正式开始了。每天天刚蒙蒙亮,六点的起床号就划破晨雾,我们得在五分钟内穿戴整齐,冲下楼集合跑操。跑完回来,真正的“战斗”才拉开序幕:抢水龙头洗漱,把被子捏出棱角,连毛巾、牙缸都得摆成一条直线。忙完这些,才能列队去吃早饭。
早上七点五十,我们整齐地走在玉兰树掩映的大道上。四人一排齐步向前,左手统一拎着黑色人造革书包,右手跟着口号规律摆臂。晨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绿军装肩头轻轻跳跃。那些挺拔的玉兰树,像沉默的哨兵,日复一日注视我们从宿舍走到教室,再从教室走回宿舍,见证着我们平凡却饱满的每一天。
除了上课和日常训练,游泳课也是不少女学员的头疼事,我也不例外。有次实在不想下水,就悄悄躲在泳池外边,听见里面教员洪亮地喊着“收翻蹬夹,注意节奏!”,心里还暗自庆幸不用挨冻。直到多年后,和我转业到同一单位的秋影在泳池里轻松自如地来回穿梭,我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学。那些逃掉的游泳课,成了军校记忆里永远补不上的小缺口。
军校生活不只有训练和学习,还有突如其来的纪律检查。军务科的赖科长是大家最怕的人,他总喜欢在玉兰道上搞突击检查。记得一天早上,我们正列队走着,他突然从树后闪出来,“立定”一声如同打雷。“成何体统!”他指着有些松散的队伍喝道,“全体原地踏步五十遍!”我们只好乖乖在落满花瓣的路面上踏起步来,直到他微微点头:“这才像军人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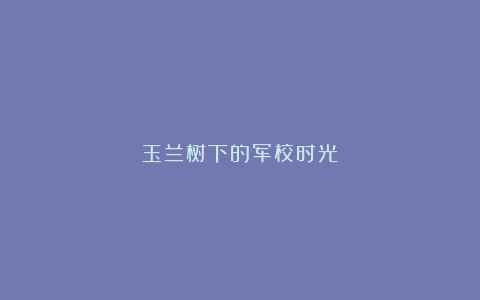
不过纪律虽严,也有轻松的时刻。帮厨就是每个班都盼着的轮值任务——主要是能暂时躲开训练。炊事班有位高个子阿姨,说一口叽里呱啦的闽南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她性子急,看我们干活慢,就一边比划一边大声嚷嚷。虽说语言不通,可她往灶台边一站,我们手底下都不自觉地快了起来,生怕被她“念叨”。
开学大概两个月后,队里办了场联欢晚会,每个班出一个节目。学员队里藏龙卧虎,吹拉弹唱都有高手。二班长周在峰和季晓凤还常去军区参加汇演,水平更是不一般。我们班没什么文艺骨干,最后合计着演个逗乐的节目。班里高高壮壮的小陈自告奋勇反串男角,我则被大家推上去演女角。上台时,她僵硬地搂住我肩膀,我别扭地拽着衣角,俩人像被线牵着的木偶。可就是这生硬又夸张的互动,反倒把全场逗得前仰后合,成了晚会最热闹的片段。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燕子成了要好的朋友。她走路有点外八字,身子轻轻摇晃,像只蹦蹦跳跳的唐老鸭。我们私下里常这么逗她,她也不生气,还学着鸭子“嘎嘎”叫两声,逗得大家直乐。别看她走路模样憨,胆子却很大,打球时敢冲敢抢,唱歌时沙哑的嗓音别有一番味道,身边总围着一群玩得好的同学。
有段时间她迷上了架子鼓,上课都坐不住。总把黑色人造革书包摊在腿上,手指跟着心里的节拍敲击,肩膀一耸一耸的,早把上课抛到了脑后。时间长了,书包边角被敲得脱了线,她也不在意。有一回教员点她回答问题,她猛地站起来,书包“啪”地掉在地上,课本散了一地,她自己还懵懵的,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更“大胆”的是,为了去校外琴房打真鼓,她居然敢爬墙。我撞见过两回,她蹲在墙根下,看见我就摆手:“就一小时!马上回来!”说完扒着墙头,身子一扭就翻了过去,动作干脆利落。我看着她的背影,只好摇摇头,心里默默祈祷队长和教导员千万别撞见。
军校明令不准谈恋爱,可青春的心思哪是规定拦得住的?队里有个从医院考来的姑娘,是我们私下公认的“队花”。她男朋友是某院院长的儿子,开学时那位年轻军官开着吉普送她来学校的场面,好多人都还记得。虽然队领导找她谈过几次话,但这段恋情仍是全队公开的秘密。在严格的纪律底下,悄悄藏着一丝属于那个年纪的浪漫。
军校的夜晚通常很安静,可一到考试前,宿舍里就有了心照不宣的“地下活动”。晚上熄灯后,我们屏住呼吸贴在门边,听着队干部查寝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楼道尽头。确认安全后,先用毛毯仔细遮严窗户,然后蜷进闷热的被窝里拧亮手电,一边复习,一边竖起耳朵留意走廊的动静——稍有异响便立即关灯。说来也怪,那些在提心吊胆中背下的知识点,反而记得特别牢固。有时半夜起床如厕,仍能看见邻床被窝里透出点点微光,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还有一阵子,队里几个女学员迷上了织毛衣。虽然明文规定不允许,可女孩子家那种细软的心思,总想在紧绷的日子里寻个透气的地方。于是,一到周末,宿舍里便有了些悄然的动静。阳光好的午后,有人会挨着窗坐下,借着自然光,让毛线针在手指间灵巧地穿梭;若是晚上,便在床头借着手电筒那一圈昏黄的光晕,一针一针地勾着。有位从浙江来的姑娘,手艺最是精巧,竟能用彩线织出活灵活现的小鹿,那鹿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会说话,惹得我们围着她,又羡慕又赞叹。
这秘密活动终究没瞒过队长。一次突击检查,她从几个柜子里搜出了好几件织了半截的毛衣,什么都没说,只是沉着脸一并收走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以为再也见不着了。没想到毕业前夕,队长板着脸在队部门口放下一摞收缴的“半成品”,对经过的我们说:“拿回去吧。以后……等你们真有闲工夫了,给男朋友织。”我们愣在原地,这句话从一向严厉的队长口中说出,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随即心里涌上一阵复杂的暖意。
还有一次查房的乌龙,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笑。深夜值班的教导员巡视女学员楼,正好撞见一个睡眼朦胧起夜的姑娘。那妹子迷迷糊糊看见个男干部的身影,吓得用家乡话大喊:“抓流氓啊!”安静的楼道瞬间炸了锅,不少人披着衣服跑出来看。第二天这事传遍全队,那姑娘羞得一整天都没敢抬头,成了大家偷偷笑话又觉得可爱的小插曲。
岁月流转,玉兰依旧年年盛开。每到花开时节,空气中便浮起那熟悉的清香。这香气仿佛从未间断,轻轻袅袅地穿过时光,将那些斑驳的记忆一一唤醒:英子额角滚落的汗珠和咧开嘴时的小虎牙;燕子蹦蹦跳跳的背影和翻墙时的麻利;深夜里被窝中手电筒的光晕,以及队长归还半截毛衣时那句让空气瞬间安静的话。
如今,南京军区卫生学校已成为历史,梅峰路6号大院也渐渐在记忆中模糊。但那些玉兰树下的时光,却沉淀为生命深处的底色。操场上被烈日灼烤的坚持,纪律下悄悄滋长的情谊,紧张与活泼交织的日夜——它们无声地融进我们后来的人生。无需刻意提起,却在每个抉择的关口悄然浮现。那份被玉兰树见证过的挺拔与韧性,如年年如约的花香,默默陪伴我们走向更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