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授权 侵权必究
□吕贵德 / 文
我花甲之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限,可仍在为医学事业忙碌,案头还摞着待整理的学术会议资料,笔记本上记满了待与同行探讨的辨证思路,办公室里还放着学术交流的草拟方案。常有老友问我,这般年纪为何还在奔波?我望着窗外的晨光,看它穿过梧桐叶隙洒在桌前的材料上,恍惚间便想起了父亲——我的从医之路,我的人生底色,皆由他亲手铺就。他如同一座永恒的灯塔,不仅照亮我过去治病救人的征途,更指引着我如今投身学术交流、传承医学薪火的方向,终究是因为对医学事业的舍不得。
从医以来,我与浮沉尺数的脉象为伍,与君臣佐使的方剂为伴,看惯了病痛中的挣扎与生命里的坚韧。多少个深夜,我对着病历蹙眉沉思,总觉得父亲就坐在我对面的那张旧木椅上,仿佛时刻为我拆解某个疑难证候。时光滔滔流逝,父亲离世已有二十余载,可这份感觉却愈发真切——斯人未远,音容宛在。他从未真正离开,只是化作了我心中的光,化作了处方笺上的斟酌,化作了诊脉时候的凝神,化作了面对患者的温暖,始终指引着我的从医之路。
若将岁月铺展成一幅长卷,父亲的名字或许只是浩瀚沙海中一粒平凡的沙,未曾留下显赫的名姓,也没有著过传世的医案。但在我生命的版图上,他却是一座巍峨的山脉。之所以巍峨,无关声名地位,只源于那份植根骨髓的医者仁心,那份泥土般质朴纯粹的善良。父亲的医术全然自学而成,家中那个旧式书柜里,没有华丽的文凭,没有耀眼的证书,只有一册册被翻烂的中医典籍。他尤善经方,深得“药简力专”之妙,一方不过四五味药,剂量轻灵飘逸,却总能精准直击病源,为那些被贫苦与疾苦缠绕的乡人,带去希望、解除疾苦。
我至今记得父亲桌上放着几本书:张仲景的《伤寒论》、徐灵胎的《难经讲义》、吴谦的《医宗金鉴》,还有一本《中医方剂学讲义》。书页早已泛黄发脆,边角被无数个夜晚的指尖摩挲得起了毛边,薄如蝉翼,几乎一触就会碎裂。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狼毫小楷批注,有的是临证心得,有的是未解疑问,还有的是详细验案。如今我仍常翻阅这些书,指尖抚过那些带着温度的字迹,仿佛能感受到父亲当年挑灯夜读的孤寂与执着,那是他与张仲景、孙思邈等先贤灵魂对话的见证,是他对中医真理不懈追求的最深沉印记。
最让我震撼的一次临证经历,发生在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那是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夜,蚊虫在灯罩外嗡嗡扑飞,院中的老枣树叶子纹丝不动,空气黏稠得像浸了水的棉絮。深夜时分,一阵急促脚步声打破宁静,邻村村民抬着一个壮年汉子匆匆赶来,汉子疼得蜷缩如虾,额上冷汗如豆,牙关紧咬得泛出白痕,双手死死按住腹部,发出压抑的呻吟。几位乡医已经看过,都说是“绞肠痧”,束手无策。父亲闻声立刻起身,披着衣服就走到院里。他蹲下身,三指稳稳搭在患者腕上,凝神诊脉许久,又轻轻翻开他的眼睑看了看,再用掌心按压其腹部,患者疼得发出一声闷哼。父亲目光久久停留,又低头沉思片刻,随即提笔在纸上写下处方:白芍三钱,炙甘草二钱,制附子一钱(先煎)。
我那时年轻气盛,仗着学了些理论知识,忍不住上前质疑:“他疼得这么厉害,就这三味药能管用?要不要加些元胡、细辛、川楝子这类止痛的药?”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只有平静却不容置疑的坚定:“此乃寒邪直中少阴,阳气被困,气血不通所致。芍药甘草汤缓急止痛,附子温通阳气,药虽少,却对症。”他亲自抓药,又将附子先煎一个时辰,直到尝着没有麻舌之感后才纳入其它药。煎出药后,让病人服下,随后,他又细细嘱咐村民,若有变化随时来报。我心中满是疑虑,这般重的急症,真能靠这三味简单的药缓解?谁知服药不过两个时辰,那患者的腹痛竟霍然而止,沉沉睡去,次日清晨便能喝下稀粥,脸色也渐渐红润。父亲这才对我解释:“中医治病,不在药多,而在辨证精准。经方的妙处就在此处,对症则药到病除,不对症则徒增负担。”那一刻,望着父亲平静的面容,我心中所受的震撼远胜于读任何一本教科书,也真正懂得了何为“思经方,演其所知”,何为“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若说医术是灯塔的光束,那父亲的品行便是坚不可摧的基石。他极重家风教养,对我们兄弟几人的品性要求极其严苛,而饭桌上的时光,经常是他的“德育课堂”。他由“君子慎独”,讲到“一诺千金”;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到“医者,仁术也,君子寄之以求生者”;从古籍典故,说到乡里见闻,皆是做人的道理。如今回想,那些古老道理,正是伴着人间烟火的滋味,一点点沁入我们年少的生命,成为我们立身处世最牢固的圭臬。他的教导如同一把无形的戒尺,丈量着道德的边界,也刻下了行医的准则——心要正,手要净,眼要明,情要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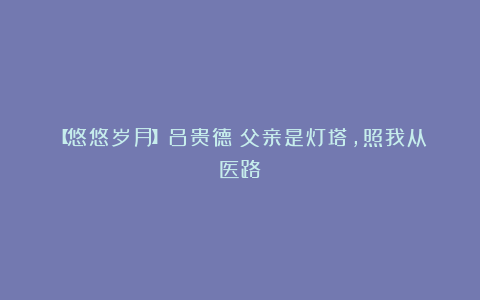
父亲的中医启蒙,更是融入了日常的点点滴滴。空闲的午后或夜晚,家里的堂屋便是我们的“学堂”。他让我们依次坐好,从“望、闻、问、切”四诊教起。教望诊时,会让我们观察路过的村民,“你看那妇人面色萎黄,唇舌淡白,定是气血不足”;教闻诊时,会让我们分辨草药的气味,“这是陈皮,理气健脾,有一股清香”;教问诊时,会模拟患者的症状,让我们逐一追问,“哪里不舒服?多久了?吃了什么东西?”;教切诊时,先让我们在自己手腕上感受脉象,“浮脉如木浮水,沉脉如石沉底,你仔细体会”。
《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这些深奥拗口的歌诀,便是在他温和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伴着院外枣树的影子,一字一句刻进了我的童年。清晨,带着我们在院中吟诵:“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夜晚,油灯下,把一包包药材摊开在桑皮纸上,让我们看色泽、摸质地、闻气味,甚至尝味道。黄连的苦直透舌根,甘草的甜温润绵长,细辛的麻窜入鼻腔,干姜的辣暖遍脾胃……我的指尖最早感知的并非玩具的新奇,而是这些草木的灵魂与温度。正是在这日复一日、春风化雨般的熏陶下,我心中那颗名为“中医”的种子悄然发芽,茁壮成长,直到后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父亲走过的道路。
父亲常说:“热爱中医,首先要敬它,像敬奉神明一样。爱岗敬业,便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无论深夜几更,无论风雨多大,只要听见窗外传来焦急的敲门声或呼唤声,他便会立刻披衣起身,二话不说就踏入漆黑的夜色里。大雪封门时,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出诊,裤脚沾满雪水,到家时早已结成冰碴;盛夏暴雨,他顶着草帽、披着雨衣出门,浑身湿透地归来。他用精湛的医技折服患者,更用那颗悲悯滚烫的心,温暖了无数濒临绝望的家庭。
如今,我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鬓角早已染满霜华。许多老友劝我该歇歇了,在家含饴弄孙,享享清福。可每当我走进医学会的办公室,看到桌上待组织的学术交流议程,想到能为年轻医生搭建探讨医学精髓的平台,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当为学术会议主题构思感到困惑,每当组织交流活动遇到阻碍,每当因忙碌感到疲惫想要退缩时,我总会阖上眼,静一静心神。这时,父亲的身影便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马上就会点亮心中那最温暖、最明亮的那盏灯。
我知道,父亲这座灯塔的光,从未有一刻熄灭。它照着我从懵懂少年走到意气风发的青年,再走到如今霜染两鬓的暮年;它照着我过去辨证施治时的审慎,照着我如今组织学术交流时的热忱,照着我对中医事业始终不变的执着与坚守。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父亲啊,您是我永恒的灯塔,光耀着我的从医路,也光耀着这人间的疾苦与希望,更照亮着中医文化传承的漫漫长途。
吕贵德 主任医师,现任安阳市医学会副秘书长、安阳市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在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喜欢写作,先后在《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中国改革报》《中华儿女杂志》《河南日报》《安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