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流变,这世界上竟没有一件事、一件物可以恒久不变而抓得住的。
《红楼梦》开头,通灵宝玉入世前是块无补天之才的石头,在无稽崖青埂峰偶听到僧道两位仙人对话,动了凡心,想要到那温柔富贵乡里享受一回。
仙人说,“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石头凡心已炽,断然不听,仙人只好带它去红尘走一遭。正好宝黛前世的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等仙也要入凡尘历劫。
后来通灵宝玉将其游历记在石头上,被空空道人抄录,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因空见色,自色悟空,故名空空道人。也有人说,空空道人或情僧,即贾宝玉也。
其实,《红楼梦》正是一部以“色空”转变为主线的悲剧史诗。贾府从“烈火烹油”的盛景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终局,宝黛“木石前盟”的深情与“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幻灭,王熙凤“机关算尽”的权欲与“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凄凉,都在演绎着一场“由空生色,由色转空”的人间大梦。
一、贾府:从“色”的盛宴到“空”的荒原

小说开篇,贾府已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钟鸣鼎食之家,却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便埋下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伏笔。
作者偏从“盛”处起笔,让读者目睹“色”的极致。元春封妃后的省亲盛典,“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大观园的雕梁画栋,象征着权力与财富,连元春都说过于奢华了。元宵夜宴上,贾母带着阖家老小猜灯谜、行酒令,脂粉香与笑语声织就的温柔乡,将“盛世”幻象推向巅峰。这些热闹场景越是璀璨,越是为后文的凋零铺垫出触目惊心的反差。
当“色”的泡沫逐渐破裂,“空”的本质显露无遗。探春远嫁时“一帆风雨路三千”的孤舟,惜春“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寂寥,迎春“一载赴黄粱”的悲惨,乃至王熙凤被休弃时“哭向金陵事更哀”的狼狈,都在诉说着家族大厦的倾颓。
贾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当属“抄检大观园”。绣春囊引发的风波,让曾经诗意盎然的女儿国沦为权力倾轧的角斗场,司棋被逐、晴雯屈死、芳官出家……那些鲜活的生命在“色”的虚妄中凋零,大观园最终“落叶萧萧,寒烟漠漠”,成为“空”的象征。
贾府的兴衰史,恰似一场盛大的幻术,当锣鼓停歇,宴席散去,唯有“忽喇喇似大厦倾”的余响,在天地间回荡。
二、宝黛:从“因缘和合”到“镜花水月”

宝黛的爱情,始于“还泪”的神话,是“色”的最动人形态。
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前世纠葛,让他们在今生相遇时便有了“似曾相识”的默契。黛玉初见宝玉时“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更是直言“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跨越时空轮回的因缘,让他们的情感从一开始便沾染了宿命的浪漫。
在大观园,他们共读《西厢记》的耳鬓厮磨,黛玉葬花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悲叹,宝玉挨打后黛玉“眼肿得桃儿一般”的泪光,都是“色”的极致温柔,是红尘中最纯粹的情感绽放。
然而,“色”的美好终敌不过“空”的无常。“金玉良缘”的舆论如无形的网,罩住了这对有情人。元妃的赐礼、王夫人的属意、薛宝钗的“贤德”,让木石前盟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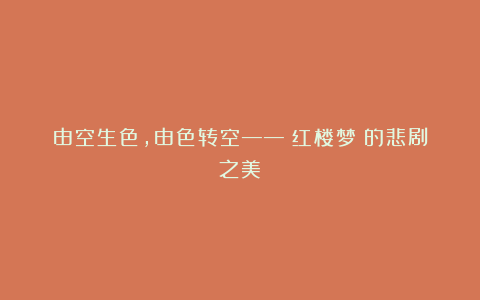
黛玉焚稿断痴情,“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她用生命完成了对“色”的告别;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场婚姻骗局,让他彻底看清了“色”的虚妄,最终出家为僧,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中走向“空”的境地。
他们的爱情悲剧,美在那如流星般短暂却绚烂的“色”,更美在这“色”的破灭中照见的灵魂纯粹——当世间万物皆可被称量、被交换,唯有他们的情感始终保持着不被污染的洁净,即便凋零,也闪耀着超越世俗的光芒。
黛玉葬花最具象征意义:质本洁来还洁去。落花的凄美与少女的夭亡形成互文,个体生命的脆弱与天地无常的苍茫融为一体。
三、王熙凤:从“执迷于色”到“勘破成空”

王熙凤是“色”的热烈追逐者,她对权力、财富、尊严的渴求,让她在贾府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才干。
协理宁国府时,她“威重令行”,将混乱的丧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展现出惊人的管理能力;生日宴上,她被贾母宠溺着“攒金庆寿”,成为众人簇拥的焦点;弄权铁槛寺时,她为了三千两银子轻易拆散一对鸳鸯,尽显权术的阴狠。
她的生命是“色”的狂欢,是“脂粉英雄”在男权社会中的突围,她的张扬与精明,让她成为“色”的极致代表。
然而,“执于色”必受困于“色”。贾琏的背叛、贾府的衰落、女儿巧姐的危机,一步步将她推向深渊。“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当她失去了权力的依仗,当她曾经的“精明”变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谶语,她终于在病榻上领悟到“色”的虚幻。临终前,她将巧姐托付给刘姥姥,这个曾经被她轻视的“乡下人”,却成了她最后的恩人。
王熙凤的悲剧,美在她对“色”的热烈拥抱,她在追逐过程中展现的生命张力,更在她坠落时的苍凉与醒悟。
四、悲剧之美:在“色空”之间照见永恒
《红楼梦》的悲剧之美,首先是其笼罩的神话与宿命色彩。女娲补天遗石的通灵神话,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灌溉之缘,人物的命运暗示在太虚幻境的判词以及其后的诗、谜、戏文等。这种“预言式悲剧”让读者阅读时有着清醒的痛感——人物越是奋力追求,越显其徒劳。
《红楼梦》的悲剧之美,又在对“美”的极致铺陈与骤然崩塌的张力上。曹雪芹以工笔细描大观园的青春与诗意:海棠诗社的风雅、宝黛共读《西厢》的纯情、湘云醉卧芍药花丛的烂漫……但美好如琉璃般易碎。随着抄检大观园、晴雯屈死、迎春被虐、黛玉焚稿等情节推进,诗意世界被世俗权利逐渐侵蚀,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的悲剧之美,又美在对佛教“色空”哲学的超越。当我们为贾府衰落、宝黛爱情以及众多人物悲剧叹息时,我们叹息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更是对世间万物“无常”的敬畏。书中的“好了歌注”早已道破天机:“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一切繁华终将成空,一切执着终将消散。
但正是在这“色”与“空”的轮回中,那些鲜活的生命、真挚的情感、热烈的追求,才显得格外珍贵。黛玉的孤高、宝玉的痴狂、探春的果决、晴雯的刚烈……他们在“色”的世界里尽情绽放,即便最终走向“空”,也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生命印记。
《红楼梦》的这种悲剧之美,不是让人陷入虚无,而是让人在“色空”的观照中,学会珍惜当下的“色”,同时不执着于“色”。就像黛玉葬花时懂得“花谢花飞”的必然,却依然为落花举行庄重的仪式;宝玉明知“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却依然用心对待每一个美好的生命。
这也解决了我早年心中的疑惑,既然一切终必成空,曹雪芹为什么还要写下《红楼梦》。既然空空道人“由空见色,由色悟空”,为什么还要改名为“情僧”。
《红楼梦》教会我们,真正的悲剧之美,在于直面“万境归空”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烈地活着——因为“色”的存在,本就是“空”的馈赠,而在此中显现的有情有义,才是永恒的“美”。如黛玉的还泪之旅,用尽生命去热烈地爱;如刘姥姥的知恩图报,倾家荡产要救出巧姐;如贾芸、小红的仗义,贾府败落后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红楼梦》,生命的意义就在这“由空生色,由色转空”的过程中,那些曾被我们用心爱过、恨过、追逐过的瞬间,早已成为记忆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