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温州、贵阳,毫不相关的三个地方,却让我看见三种截然不同的中国。
闽南红砖厝、瓯越巴洛克、黔地吊脚楼以各式不同的形态躺在我的手机相册时,我找到了一周内跳跃三地的意义。
泉州,我待了7年的城市,五一的回访居然有种一期一会的感觉。
按照老泉州人的传统,碰头必然是钟楼,我和阿珊、雅芳也不能免俗。
这座矗立于中山路和东西街交汇的白色地标,于1934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是泉州首座公共报时装置,哥特式尖顶、四面钟表、花岗岩基座和谐共生,东指九日山,西接明清馆,南承天后宫,北望清源山,承载了太多太多闽南记忆。
当我们几个老友接头成功后,便进入了人挤人的西街。
骑楼连廊、回字暗纹、商宅合一、出砖入石,走进小巷,更能体验归国华侨的精致生活,似乎这个马可波罗笔下“东方第一大港”穿越时空隧道向我们走来,又似乎这本来就是泉州人普普通通的一天。
相比于中山街的繁华,不得不提五店市,这已经是10年前的记忆了。
五店市由唐代“五间饮食店”演化成市,宋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内港商贸枢纽,后在2015年修复获遗产保护奖。和中山街不同的是,五店市里的“番仔楼”更南洋——除了类似的燕尾脊,更有菲律宾花窗、罗马柱廊,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蔡氏家庙,每座建筑都在“穿西装戴斗笠”。
在农业文明时代,泉州可以是璀璨的东方第一大港,受海洋文明冲击后的泉州,仍是海洋文明的践行者。
“半城烟火半城仙”,烟火袅袅,众仙云集。
阿珊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来开元寺了,上一次是高中时代!”作为泉州土著,家住洛阳桥附近,对,就是余光中《乡愁》里的那座洛阳桥,离这也就16km,原因也很泉州,“家附近的庙已经拜不过来了”。
理解理解,这次庙我们走得也不多,就开元寺、南少林、承天禅寺、文庙、关岳庙、天后宫,路过了泉南堂,参观了清净寺。
“大隐隐于市”,开元寺就是这样一座千年古刹。寺内东西塔作为中国现存最高的石构佛塔,在西街这美丽的画卷上,将佛法精义与世俗烟火熔铸,而波斯绿岩柱、印度林伽浮雕、藻井妙音鸟则是凝固的艺术。
广场上香火鼎盛,穿过焚香的幻影,檐角的鸽子能否听见婆娑世界求而不得的般若,看见斗战胜佛金箍棒斜倚佛塔转身离去的释然,窥见弘一法师红尘转身的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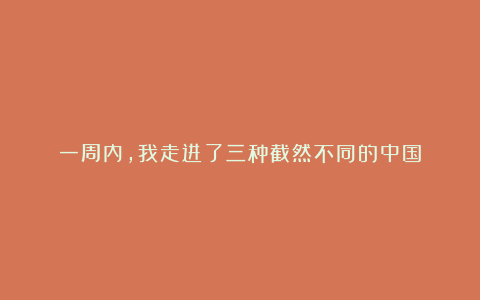
转身,我们去清源山麓禅武圣地泉州南少林走走。
相比于皇家禅修圣地嵩山北少林,出生于乡野的南少林有种“爱拼才会赢”的韧劲,这是其从秘密结社到全球道场华丽转变的根本所在。
在寺中,你很难不被这尊观音像吸引——高2.16米,深褐色,采用闽南独有的“沉香樟”和宋元“曹裳出水”手法雕刻而成的明朝英气勃发“勇猛丈夫观自在”,为避免焚毁被武僧藏匿于放生池淤泥中,直到1987年才重见天日,多么庆幸,她避开了那场革命,多么庆幸,今时今日,她还能看见梅花桩上晨练的武僧,藏经阁内典藏的禅武经典。
这种幸运也在与天后宫、关岳庙构成“一公里信仰圈”的清净寺上得以体现。古清净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清真寺,对,是清真寺,在众神云集的泉州落地生根,可不就是一场奇幻之旅?
这座于1009年建立的寺庙,经历千年风雨,麦加是永远的守望,哪怕经历地震,经历坍塌,经历朝代更迭,经历辉煌与式微,礼拜的朝向永远是麦加(考古发现礼拜朝向线正对麦加,误差仅0.5度)。
五一后,为达湘西辗转了与泉州大相径庭的两座城市。
温州江心屿,中国诗之岛,我将其视作温州建筑的缩影,“一水分城都,双塔镇波涛”,拉着行李箱,乘往江心屿的轮渡,有种到往鼓浪屿的恍然。
直到看到江心寺,看到“秃顶塔”,看到瓯江浑浊的水,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江心寺门前宋朝的楹联再给我几个上下五千年我也读不准,而谢灵运诗赋中的“孤山与媚中川”,陆游摩崖石刻上的“奇峰迎送野僧来”、朱自清散文里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让我相信了这里就是诗之岛。
我是中午到达的,为了寻找“秃顶塔”最佳拍摄点,在岸边走了好久,夏天的太阳有着南方独有的“热烈”,透过树影斑驳、轻触暗礁拍浪,我看见了百年樟榕合抱的君子之交,看见江心代代相传的渔火渡船。
岛屿还有一处是领事馆旧址,江心寺与其“平分”了这座岛,但“旧时王谢堂前燕”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却不想踏足领事馆。还好,殖民建筑代表的那段屈辱岁月,随着温州1980年个体工商户的浪潮,已经成了过去式了。
随着飞机降落,走在贵阳仿佛“梯田”的住宅区,我在心里呐喊:喀斯特山城的古典与现代真是生命力爆棚!
夜郎谷里,当代雕塑家宋培伦花了20多年创作的“夜郎国”,石头王国在现实中有了样板,平路上的天主教堂,一半哥特式一半黔中古楼,凝结了侗族、苗族的建筑精华,融合了圣经和仡佬族的“竹王传说”。你可以相信,贵阳可以接受任何文化,也不会丢下任何文化。夜幕降临,白宫华灯初上,甲秀楼人潮涌动,青云市集的广告牌在细雨中被揉成了迷幻的彩带,中国数谷贵阳的神秘身份是该浮出水面了。
暮色漫过甲秀楼的飞檐、温州的巴洛克雕花、泉州的红砖古厝,我用一周时间走过山海相隔的三座城,忽然懂得:中国从不在一种叙事里固守,她总在迥异的屋檐下生长出新的年轮,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永远有新的中国等着被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