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杜永卫先生早年发表在博客的一个答网友贴,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文中所述80年代莫高窟曾向美院师生大开临摹方便之门而后又断然关闭的真正原因,以及一些关于临摹研究的鲜见的知识与观点,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文物保护、鉴赏“敦煌艺术临本”、了解和认识“敦煌临摹研究工作”都颇具启示。故小编特将此文编辑发表,以餮网友!
有多少人真懂敦煌临摹?
——答卑盦先生质疑敦煌艺术大展
(原标题:卑盦先生曲解敦煌临摹为哪般?)
文 / 杜永卫
中国美术馆/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拜读了卑盦先生的《敦煌艺术大展观感》一文,作为第三代敦煌临摹工作者,我认为卑盦先生的有些意见比较中肯,而有些意见纯粹是对敦煌临摹工作不了解的主观臆断!
卑盦先生对敦煌临摹工作的看法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
1、敦煌研究院“有些霸道”、“垄断石窟壁画原件的临摹权”;
2、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的整体线描水平是很低”,“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统的学习过美术”;
3、“他们竟然不会书法……这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一批不会书法的人垄断了对线条要求极高的敦煌壁画的临摹,那是一批怎样的画家呢”?
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莫高窟158窟卧佛复制
卑盦先生的这番议论和质疑,实属对敦煌临摹工作性质的不了解。我本无意与卑盦先生就这些肤浅的认识做任何辩解,但卑盦先生的文章发出后毕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处于一种敦煌临摹者的责任感,有必要对有些事情说明一下。
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莫高窟249窟模型
敦煌研究院自八十年代中期,确有不对外提供直接拿画架、画板、颜料进入洞窟临摹学习的规定,但这不是“霸道”,也不是为了“垄断临摹权”,而是一种不得已的保护措施。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各地美术院校师生陆续前来莫高窟临摹学习,当时的敦煌研究院,曾非常热心地为学子们进窟临摹大开方便之门。不仅段文杰、史苇湘等这样的大专家经常亲自为师生讲解洞窟,引导他们去认识和理解敦煌艺术。而且,每个师生都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任意选择一面壁画进行临摹,只要你做个登记就可以领到一串钥匙,在任何一个洞窟里支起画架爱临多久临多久。当今著名画家袁运生、孙景波、陈丹青等,都曾在那个时期驻扎莫高窟,激情地为自己临摹了很多作品。
1981年春,中央美院油画系壁画工作室师生在莫高窟考察、临摹。右4袁运生、左2孙景波
但为什么后来这扇方便之门又断然关闭了呢?说来令人扼腕!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入莫高窟临摹,他们当中一些人缺乏对文物的爱护意识,在窟里临摹随意甩笔、不是把颜色、碳素墨水搞到壁画上去,就是把洞窟污染得脏乱不堪;甚至在窟内吸烟、擦伤壁画、题写字迹的情况也时有发现;更有恶劣者,为了获取画稿,竟投机取巧,用图钉把薄纸直接订在壁画上进行考贝,在壁画上留下了不可修复的针眼和印笔痕。当出现了这些情况以后,管理者曾三令五申,开导教育,屡不奏效。在这种情况下,敦煌研究院处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才迫不得以采取禁止学生直接进入洞窟临摹的措施。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进窟临摹的学生越来越多,已严重干扰和影响了莫高窟正常的保护研究工作,加上旅游兴起,游客暴增,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古老石窟,已无法再承受太多的压力了。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是保护、研究、弘扬,而保护是第一位的。如果当初不是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任由不良学生“恶性临摹”,允许全国美术大专院校师生涌入洞窟作画塑像,恐怕今天的敦煌壁画会损失的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敦煌壁画很脆弱,经过千百年的自然风化,很多恐怕已到了它寿命的大限,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而敦煌研究院对此加以科学的保护和采取管理上的必要手段,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这是它神圣的使命,它不这样做怎么办?卑盦先生你有什么好办法么?
50年代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工作现场
其实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内部临摹人员,也同样受到严格的管理,他们并不能够随便进入洞窟为自己临摹,这里没有“垄断”和“霸道”,有的只是为工作,为国家的事业。他们进入洞窟工作,是要根据计划,经过部门所长到院长的批准,以及保护所、保卫处、石窟管理等多个部门的手续管理,还要切实做好围栏、护膜保护措施,才能开展工作。这一切烦琐手续和监管措施,临摹工作人员也都能够理解,因为敦煌石窟不是哪个个人的,也不是某个单位的,它是国家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谁都有责任去爱护它、保护它,并自觉地服从管理。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人员在莫高窟工作现场
卑盦先生质疑敦煌研究院临摹人员的整体线描水平和绘画素质,否定《敦煌艺术大展》的展品质量,实属对敦煌艺术缺乏了解。正如你自己所说你没有到过敦煌也不懂画,那你完全是凭借你个人之见和一点书法认知,妄加猜测敦煌艺术,然而敦煌艺术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它与你知道的宣纸上的国画、工笔画并不能相提并论的,它的技艺以及发展轨迹也不能混为一谈。而敦煌临摹工作者的临摹目的,和他们所掌握、传承的一整套绘画技术,也跟你所认知的美院画家的那种临摹完全是两个路数。
著名雕塑家孙纪元先生在莫高窟205窟临摹彩塑
首先我们的临摹不只是为自己学习传统而临摹,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壁画、彩塑的科研、保存,以及弘扬、传承工作。我们的前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临摹意义有三个:一、存档。敦煌艺术是有寿命的,而且他在不断的自然消损,一旦有一天它消亡了,我们手中毕竟还存有一份摹品,不至于使文化遗产的信息彻底消失;二、展览。石窟里的壁画、彩塑无法拆下来拿出去巡展,只有用临摹的复制品替代,让那些到不了敦煌的世人,通过我们的摹本了解敦煌、学习敦煌。三、研究。通过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等方法,研究敦煌艺术历代绘画的技法、风格、审美以及演变发展等,以服务与科研,服务于艺术,服务于社会。
50年代敦煌研究院前辈在莫高窟中临摹壁画 左2段文杰、左3李其琼
50年代敦煌研究院前辈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右1欧阳琳 右2李承仙
从这三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临摹水平,和卑盦先生所认为的那种临摹水平就完全不是一挡子事了。其实,自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开始,我们的临摹宗旨就是:客观临摹,忠实原作,不能有丝毫个人主观意志。具体地说我们是一种复制、一种再现,而不全然是临摹,我们是在做把壁画如何真实地转换在临本上的研究,是如何尽量准确无误地向世人传递古人作品的真实信息,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的是古人的创造,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的体现。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在洞窟中研究临摹壁画
如果说这里面有“自我”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对古代艺术的忠实与膜拜,一种发现和感悟到古代工匠那种执着精神的感动,一种随着年龄的上长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渺小转而对自己几近苛刻的严格要求,以尽量准确地反映原作的精神和技法,把临摹的画作做到乱真,做到与壁画尽量不差分毫,经过这样制作的模本才有价值,才能起到备份存档无愧于后人的作用,才能拿出去让世人相信这就是敦煌艺术的真面目。我们临摹一幅壁画,从起稿、修稿、过稿、着色……要需要投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最大化的和原作一模一样。这种“客观临摹”的宗旨,经过几任院长的重视和几代画家的追求,呈现出越来越高标准严要求的趋势。
50年代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在莫高窟研究临摹
就线描来说,我们追求的线描和卑盦先生所要求的线描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用“十八描”去概念地对待临摹,我们遵循的是,原作上是什么样,就必须描成什么样,甚至原作上是笔误,我们也必须做到一样的笔误。我们的老师段文杰、李其琼等先生,在初教我们线描时就强调,要研究和掌握历代线描的规律,但也要注重每条线都有它的个性,都不能主观化、概念化。尤其当一幅摹作在最后完成的“提线”阶段,都必须要在纸上反复练习,直到练得和壁画上的线描一模一样了,练得自我感觉跟古人那一刻的状态、激情似乎重合了,再去轻松、坦然地落笔于临本之上。
50年代敦煌研究院老专家李其琼先生在莫高窟研究临摹
就敦煌壁画的线描技法,它并不按照“十八描”的技法要求,“十八描”技法总结于明清时期,而此时敦煌艺术已经诞生、发展了一千数百年了。敦煌壁画包含十八描的某些描法,但也没有尽现十八描;它属于工笔重彩的绘画体系,但又不等于工笔重彩,它有它自成规律的技法和审美意趣;甚至有些壁画的线描,明显感到它所用的描线工具都与通常的毛笔不尽相同。敦煌壁画的线描非常丰富、自由,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描法,不同画者有不同的性格。尤其,敦煌因地接西域与中土之间,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地位,它汇集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一千多年的各种画风和技法,远远不是你卑盦先生坐在家里读两本中国画技法的书,就能够认识和理解的。
50年代敦煌研究院老专家万庚育先生在莫高窟研究临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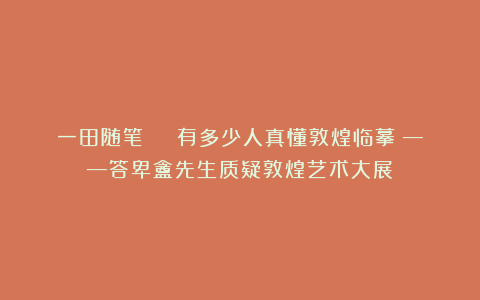
关于临摹,我们的临摹和美术学院画家所希望的临摹迥然不同。我们各自临摹的出发点、目的、概念以及对临摹的理解都不相同。你们是要来学习古人的技法,获取创作素材,为自己成名成家奠定基础而临摹。而我们不是为自己临摹,我们在临摹中需要尽量摒弃自我、克制主观;在技法上抽离自我,面对壁画任何一处都尽量客观对待,不能因为自己的审美好恶、造型习惯而不自觉的加入主观情感。可以说,敦煌研究院的几代临摹者,都是为保护古人的伟大艺术临摹,为到不了敦煌的世人临摹,为给后人保留一份忠于原作的值得信赖的备份临摹。这样的临摹,反映的是一种无私无我,反映的是一种大匠的执着,反映的是一种专家的严谨和淡然的超脱。他们陶醉于深山佛窟,犹如修行的苦僧,不为财利荣禄,不屑于外界的名利角逐之场,又何必在乎临摹权利之“垄断”?!
50年代敦煌研究院老专家史苇湘 欧阳琳先生在洞窟中研究临摹
卑盦先生还认为我们连书法都不懂怎么会线描?是的,中华美术书画同源,书法跟十八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谁又敢说不是书法家就不会描线?古代的那些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用艺术弘传佛法的外国大师,那些敦煌当地世代相传的画工塑匠,那些哪里需要哪里去的民间“画庙人”,也许他们很多不是书法家,甚至不会书法,不识字、不会汉语,但他们却创作了伟大的敦煌艺术,他们的线描登峰造极,为世人膜拜。当然,我们当中很多也不是书法家,也许在你书法家的眼里,我们这些不是书法家的临摹匠根本算不上一个画家,但有这么一种国家需要的特殊的美术工作,总该有人去做吧卑盦先生?此外,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们当中有不少人的书法很不错,尤其那些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他们受的教育非常深厚,他们的书法造诣相当之高,只是他们一生守望莫高窟,潜心于敦煌研究事业,潜心于真正的艺术追求,无暇或不屑参加那些书画展会和书画组织以博取一些虚名而已。
56年敦煌研究院老专家霍熙亮 李复 关友惠先生在莫高窟临摹研究
说到张大千,那是开创敦煌临摹先河的前辈之一,他的勤奋,他在那个艰苦岁月对敦煌的痴迷与丰硕的成果,曾启发了很多人来敦煌献身。他老先生在敦煌一呆就是两年七个月,给自己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然而从今天我们的临摹角度看,他老人家应该算是在给自己临摹,是他个人学习、研究古代艺术的一种实践。他的临摹作品的确很见功底,但很多情况下他是在一边临摹、一边修正、一边发挥,可以说他的临摹带有相当的主观成分。从这个方面讲,张大千的作品,可以作为“张大千眼中的敦煌艺术”独立展出,但却不能归类于敦煌研究院的壁画摹本内进行展出。卑盦先生质疑《敦煌艺术大展》“其中居然(竟然!!)没有张大千……的作品”,完全是你没有弄懂张大千的摹品与敦煌临本不同性质的区别。
40年代初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最后,我还要向卑盦先生说明一点,《敦煌艺术大展》的展品,是几代敦煌艺术家历经半个多世纪心血的结晶。他们当中包括常书鸿、段文杰、李其琼等一批卓越的老艺术家的作品,也包括一大批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在敦煌研究一生的专家的作品,并不是你所想象的一群没有系统学习过美术的、整体线描水平很低的人的画作。
谢谢卑盦先生引出这些话题,也很高兴与你探讨,不当之处,还望拍砖!
注:本帖于2017年8月15日修改
50年代,敦煌研究院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一批美术家,在他们的美术创作品前合影。
后 记
那年和卑盦先生“砖来砖往”讨论激烈,也碰撞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火花。时过境迁,当时的火气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一些有趣的对话,回看原帖,还多少有些怀念。以下略去那些唇枪舌剑的对话,仅附录卑盦先生的主贴,仅供参考。
《敦煌艺术大展观感》
文:卑盦
2008-03-11
还没见过哪个展览使得中国美术馆如此大费周章,初次看见整栋美术馆大楼被装扮成敦煌模样的新闻照片,我大为惊讶。耽搁了好久,上周末终于去参观了,观感颇多。
其一,观众的激情。在北京,除了大学生招聘会、公交车上和火车站里,如此拥挤的地方还真是少见。记得06年上海博物馆与日本合办的书法大展上,第一件就是王羲之的《丧乱》三帖,呵,看的人多了去了——实际上,《丧乱帖》旁边的两三米内,就有《鸭头丸帖》、《上虞帖》和日本三笔三迹的作品——都没有人看,而其他的帖子,就更是“无论唐宋元”了。人们围在《丧乱帖》展柜旁边久久不忍离去,令得工作人员不得不实行疏散。但比起此次展览,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整个中国美术馆一层到处是人,大家接踵摩肩,往往必须列队而行。实际上,展品多数只是敦煌壁画的现代仿品,而竟然得到了如此多粉丝的激情追捧,实在是令人惊讶,从而亦可见艺术——真正的艺术的吸引力。北京的美术展馆不可谓不多,为什么平时门可罗雀的多呢?是观众没有激情吗?我觉得挺值得人们思考。当然,观众的激情并不是没有负面效果,展馆里此起彼伏的闪光灯和“请勿拍照!”的提示同在,令人很无奈。
其二,画家的素质。年前曾与一位在敦煌工作多年的朋友聊天,他在敦煌研究院有朋友,多次进入未开放的石窟参观,甚至在石窟里过夜。他透露,石窟壁画原件的临摹权被敦煌研究院垄断,而各地美院的教授、学者去到敦煌后,只能去临摹研究院工作人员从洞中临出的摹本。我当时虽然觉得研究院有些霸道,却引起了我对敦煌研究院画家临摹、创作功力的兴趣——学习书画的人都知道,范本对学习欣赏很重要,比如字帖、画册的印刷水平…对一般人来说,天天面对古人真迹进行学习几乎就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但是敦煌研究院就可以给人这样的机会。我对此很期待,很想一见“天天面对真迹”的敦煌研究院画家们的佳作,但是当天的参观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不懂画,却依稀觉得敦煌壁画的灵魂应该是线描,而此也应该是壁画临摹者的基本功。但是由敦煌研究院的临本看来,工作人员们的整体线描水平是很低的。例子很多,虽然现场没有壁画原件,但是有一些现当代名家的临本被独立列出展览,其中居然(竟然!!)没有张大千和潘絜兹两位的作品,但是却有叶浅予先生的。恰巧的是,在叶先生作品的不远处就有同一壁画的另一摹本,只不过临摹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罢了。两相比较,高下立见,我甚至怀疑后者是否系统的学习过美术。我很疑惑。后来,敦煌研究院的创作作品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竟然不会书法!!如果说线条的好坏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那么,在一幅表现魏晋时代僧人的《译经图》中出现了羊毫大斗笔这一事实起码证明了作者确实就不懂书法了。这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一批不会书法的人垄断了对线条要求极高的敦煌壁画的临摹!那是一批怎样的画家呢?
其三,我的感动。壁画令我感动——虽然临本只是古人作品的影子,却使没有去过敦煌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待到见到当天展览中位数不多的木雕、泥塑和经卷原件后,那样的征服是压倒性的。在敦煌经卷面前,古人似乎刚刚起身走开,墨迹甫干,他们的气息是那样亲近;在一尊残损的四臂菩萨木雕前,一个瞬间,身心一时落地,自己仿佛已经并不存在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古尊宿们一朝打破桶底的感受难道就是如此吗?我不知矣。
2008-03-11
作者在莫高窟临摹彩塑
杜永卫 曾用名:杜一田。非遗敦煌彩塑技艺传承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高级环艺设计师,教授。历任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副所长、敦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东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东京艺大客座研究员;中央美院雕塑系传统课兼职导师;兰州交大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师大敦煌学院客座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客座教授;酒泉职业学院特聘教授;江南石窟艺术指导专家。敦煌中国画研究院学术院长,《当代敦煌》总编辑。
作品曾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并赴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展出。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国驻澳大使馆、埃及开罗市政府等机构收藏陈列。敦煌菩萨银币设计获美国世界硬币大奖赛最佳奖;龙门石窟卢舍那银币浮雕获新加坡国际钱币博览会金奖。其他美术作品屡获国际、国家和省级各种奖项。雕塑作品《水月观音》获云冈国际佛教艺术大展最高学术成就奖。
品读之后
愿享同感
以 往 期 刊 推 荐
-
从拉面拉出的中日
-
我给民工做头像(雕塑)
– END –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