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Sower
米罗斯瓦夫·巴尔卡(Miroslaw Balka),《现状如何》(2009年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装置现场)© PA Images / Alamy Stock Photo。摄影:菲奥娜·汉森
我们已步入一个审查盛行的时代,艺术家的悲惨经历和政治立场比作品本身更重要。欢迎来到“语境暴政”的统治之下。
我的朋友皱了皱眉。他问我如何看待最近一场抽象画展,我如实相告:我觉得糟透了。满墙都是那种令人大脑僵化的、温吞的、行尸走肉般的抽象画——几十年来艺术市场的主流货色。浮夸、空洞、装饰性过剩的无意义涂抹,大块混乱的原色颜料,既无冒犯性也无特色,比墙纸还平庸,注定被遗忘的作品。
“你不能这么说,”他回答,“考虑到他们的经历。” 原来这位艺术家曾历经悲剧、苦难、痛苦或创伤——具体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一些糟糕的事”。这些苦难甚至未体现在作品中,但艺术家的经历——他们的“语境”——似乎让作品本身凌驾于批评之上。
这种令人窒息的观念无处不在。过去十年间,博物馆、画廊、策展人,甚至评论家和普通观众,都明显从关注作品本身转向聚焦其背后的政治、经历和情感背景。在几个世纪的系统性歧视(阶级、性别、种族)之后,新一代极力推崇以身份政治主导艺术创作和展览,导致艺术家的个人故事比作品本身更具分量。
如果一件作品涉及奴隶制、大屠杀或阿片危机,或者艺术家本人饱受苦难,你如何敢说它“有缺陷”,甚至“糟糕”?这种环境催生了一种自我延续的审查机制——观众和艺术从业者形成了一种新的防御机制,抵制批评本身。
当代艺术家如今被迫顺应时代的道德要求,在作品中利用自己的身份,甚至自己的创伤。艺术越来越因其政治性而非美学价值受赞誉,尤其是左翼将艺术视为表达立场的工具:如果你认为某位黑人具象画家是同代最佳,你显然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而若质疑其作品水平,则会被视为否定艺术家“对抗逆境的成功”所象征的宏大意义。
与此同时,博物馆重新包装已故作家的作品,以最可能吸引观众的叙事展出。例如伦敦巴比肯近期举办的诺亚·戴维斯(Noah Davis)回顾展,聚焦他32岁因罕见癌症早逝的经历,几乎扼杀了对其作品质量的讨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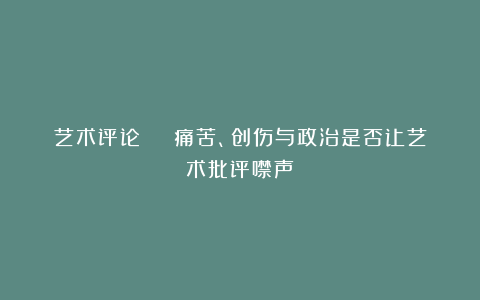
诺亚·戴维斯,《40英亩与独角兽》(2007),布面丙烯与水粉,76 × 66 厘米。摄影:安娜·阿尔卡。© 艺术家遗产。由艺术家遗产与伦敦大卫·卓纳画廊提供
我明白:我们身处政治极化的时代,立场比细节更重要。但这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痛苦被资本化的问题——画廊主、策展人和艺术家在利用悲剧牟利。出版业亦然:如今畅销书似乎都在暗示,只有兜售自身或家族的边缘化经历,才能获得出版机会。
这造就了我所称的“语境暴政”。我们陷入一种象征性道德主义:认同作品的政治立场并共情艺术家经历=“好人”;质疑或忽略这些背景=“坏人”。这不是有意义的艺术参与方式,而是一种自我中心、自我美化、自我防卫的手段——用艺术向世界宣告“我不是坏人”。
别误会:语境确实重要。杰出的当代作品平衡语境、概念与执行,而拙劣的作品往往过度依赖其一以掩盖其他缺陷。绝妙的点子但无语境且执行差?烂艺术。技法精湛但无深意或有趣背景?烂艺术。但若语境压倒概念与执行,观众更难直言“这很糟”,因为它的政治意图或悲惨背景成了免死金牌。
几年前,我在社交媒体随意评论了南·戈尔丁(Nan Goldin)一张失焦、歪斜的海景照片,结果某摄影作家私信狂轰滥炸。它的辩护核心是:戈尔丁拍摄时正受阿片类药物成瘾折磨。显然,我有义务对“诞生于悲剧的图像”保持敬意。
我不认为戈尔丁近八年对抗阿片危机的壮举意味着她所有作品都伟大,也不信她会自认作品不容批评。但我对一件作品的厌恶被解读为道德缺陷,甚至是对她反对普渡制药和萨克勒家族的P.A.I.N.运动“缺乏支持”。
南·戈尔丁在哈佛艺术博物馆。由奥巴马基金会提供
我也曾陷入这种道德绑架。米罗斯瓦夫·巴尔卡(Miroslaw Balka)对大屠杀的长期挖掘每次都让我心碎。比如2009年他在泰特涡轮大厅的巨型黑箱装置《现状如何》,将参观者吞没于黑暗中,直击我的泪腺——因为我的家族与这段历史有切肤之痛。2014年他在弗洛伊德博物馆的展览(灵感来自一名纳粹军官索要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建材的信件)让我狂热追捧。但多年后我记住的不是它对历史恐怖的真挚探索,而是它揭示了我如何被情感蒙蔽,忽视了艺术家对“揪心悲剧”的廉价甚至懒惰的消费。
或许这种极端的即时情感卷入正是艺术应有的力量。但当语境、政治、背景和叙事压倒一切时,我们剩下的只有行动主义和悲伤故事——而非好艺术。在AI垃圾、科技亿万富翁媒体大亨和纸媒衰亡的时代,这对艺术批评的威胁最为真实。如果我们无法在不被骂作偏执狂的情况下表达对艺术质量的真实看法,就等于告诉艺术家:贩卖创伤比作品本身更有价值。
你或许想:“哦,白人艺术评论家破防了,因为他不能对弱势群体艺术家的作品毒舌。”但这不仅是评论家的困境,更是对所有观展思考者的冒犯。如今每位艺术家都仿佛历经浩劫、受尽压迫、手足残缺且永远悲伤。现在,请直视他们的眼睛说:“你的画很烂。”**你做不到。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幼犬”的艺术世界——而你不能踢幼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