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勇一直享有诸多老朋友均愿与之共勉的一项殊荣——大家的撇画对象。这个历程不仅是经历了三十多年共处时光可以记载成册的大量故事和酒后谈资,而且在新的世纪的最近十年内成为攻防两端战术升级的系统案例。
随着蒋勇画作价值的逐年走高,以及知识产权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他最近的口吻和语言艺术已呈现出神学色彩——“要不送你一幅屏保吧,我今年一幅新画的局部……”
难以置信,这是一个了耍三十多年毛笔的人从嘴里磕绊出的字符音调,引用莎士比亚《麦克白斯》里的名句:……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送屏保”作为蒋勇拥抱时代拥抱科技的典型案例必然载入历史,成为他保卫自己合法财产不受侵占的新思维新手段,这多少已超过了老朋友的认知范围,属于降维作战,一时间,大家对这一措辞均表示瞪目结舌,说不出话来。这一回合结束,老蒋又胜一局。
其实大家数十年来热衷于与蒋勇同志玩这个游戏,完全是基于对他审美的认可程度比较高,加上他对自己劳动成果所有权捍卫力度出奇地高,再加上他长期住青藏高原每年回家的日子有限,这导致朋友们自觉地将三点因素综合起来以便在聚会时大大地热闹一番,如果再顺便搞到一张画作那更是善莫大焉。借拜年之机突袭蒋勇家的画室诞生了多少言之不尽的话题,已经无法细数。但每年的上门拜访和随机聚会时大家都能一睹他的新作和新的探索。
作为七〇后,作为热爱艺术的一群朋友,我们这些人,这些年的生活其实无不与之相关。我们重视这个,视之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并且毫不松懈,在大家均已步入五十岁的生涯里适当地做个总结和回顾可能会有点意思。
前段时间看到蒋勇的水墨正是一个契机。他以前画油画,超级唯美,无论是“西藏芭比”系列,还是“仙佛图”系列(说“仙佛图”多少有些轻易,但想不出更准确的词,因为我相信蒋勇毫无宗教情结),它唯美,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这个无可非议,蒋勇是我认识的好朋友中唯一的依靠卖画生活得很好的人。
但这两个系列以及其他更早时期的所谓现代性画作都没有打动我,没办法,或者“我”这个主观的词的出现让这个叙述走向了片面,或者那些画作也是打动了许多人的。但没办法,促使我写文章的就是那个未被打动的“我。”
但蒋勇的水墨画把我看傻了,当时还是在手机上看的,没看原作,更加没看裱好的原作,就已看傻了。
这是什么?一打眼就只能看见技术,墨分五色。他用很便宜的宣纸,也肯定是街上就能买到的便宜墨汁,然后墨分五色,问题是画什么了?
当墨和水相遇,再加宣纸,生宣,一切都不确定,不确定的东西我们不称之为画,我们称之为随机,但是怎么能随时得到一幅画呢?是人在创作还是水和墨在创作?
那个晚上被迷住了,然后又约了一场酒,然后又聊。那天我们换了称呼,改叫蒋勇老师了。
当大家热爱了三十多年的艺术,那么艺术是什么,怎么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表述出来,或者说扔出来,说:这就是!或者干脆说谁能在现在当下有勇气有资格更是有能力地扔出来,只有蒋勇,只有蒋勇的水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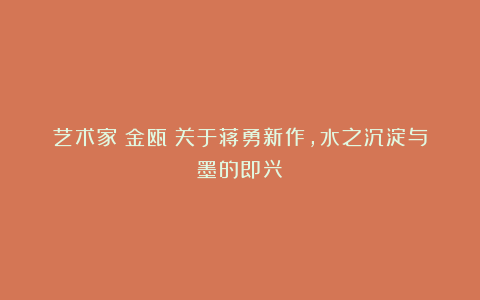
你瞠目结舌地看见:这是什么?
这就是全部。当晚夸张地叫蒋勇大师,第二天也没有脸红后悔。可能他就是大师。
墨分五色是祖宗教的,后来画成了什么大家有目共睹。这是技术,画个鱼,画个鸟,兰花和水草。
当我们学了美术史,当我们懂了杜尚,波洛克,当然再近一点,我们懂了安迪沃霍尔,也就是说,除了毕加索也还有这些人,而且我们也懂了他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是说我们不懂还是说我们只是没有大师?
他们拿油画笔,而我们的人拿毛笔。我们拿毛笔,我们墨分五色,而我们很内敛,我们只画金鱼和鸟、兰花和水草,最多画画虾和驴。我们以为最大的世界就是这个。
画是什么,还是人生观么?画是世界观吗?画只是只是中堂,挂在堂屋起装饰作用或者表达审美意趣的东西,再配两副对联。对了,没有对联可能都不是我们的文化,所以,画倒到底是什么?
学美术史,学艺术史,学文化史,我们学学学。学会美术史,学会了艺术史,学了一知半解的文化史,魔怔了。学文化史必然魔怔,当学会了以符号、象征和意义看待世界,必然不懂美术,不懂画,不懂水墨。
这个人叫安迪沃霍尔,他剽窃爵士乐。剽窃比波普,他可能还抢劫了布鲁斯,只不过我没看出来。我只看出他表达了欲望,除了重复其实他更大的企图是欲望,其实波洛克也一样,没有什么能阻止表达,问题是表达永远有两个问题:你表达什么?你怎么表达。
当蒋勇拿出了水墨并且扔出来的时候。我只能管他叫大师。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画仍然说不出所以然,画家大都言语迟钝,但蒋勇显然不是,他还写诗,并且最新发明了“送屏保”,他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傻蛋”艺术家,他在银川十多天就画了一百多幅并且仅送出了三幅就大卖。他压根不是那种人,我们智斗了三十多年我们了解他,他是卖画的好手。
但是他开始画水墨了,他的油画更赚钱他是知道的。
水墨里有什么?
当米尔斯·戴维斯拎着小号,挥洒他因高龄而自动获取的声望并任意指点几位听他招呼而来的乐手飙出雪片般飘来的一张张唱片时,他收获爵士乐自动贩卖机一样的即兴产出。无论画什么,多年的自我训练使蒋勇获得了技术,他不需要乐队的即兴,他只需要宣纸毛笔和墨。
水自己就会沉淀,我们看不见。墨的世界是宣纸,墨只需要这个二维的世界,我们也看不见,它在我们的认知外,或者它压根就不需要认知,它自动生成。
毕加索认识到线条,认识到勾勒,蒋勇认识到是生成,是即兴。所以水沉淀就是墨的沉淀,水的即兴是墨的生成。最初是时间的艺术,熬啊熬啊,熬成水壶上的碱,层层叠叠,其次是平面的艺术,把层层叠叠向四周推演,专注眼前这个非特定时刻,专注于水墨纸的互相成就,世界只好是两维的,把二维整明白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爱美术,这是我们的命定的路途。当我们画画只有二维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