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Sower
Culture菌:张老师,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如何与艺术结缘的?
张友来: 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大概五六岁时,我就开始想将来靠什么吃饭。上小学时,正值文革后期,学工、学农、学军占了大部分时间。母亲担心我学不到知识,就请了一位大叔教我拉二胡,可惜后来考文艺学校没考上。于是,我开始自己学画画,最初就是找小人书临摹。画得像了,父母一夸奖,我心里就高兴,一来二去,真的喜欢上了,也越画越像。记得我画雷锋像,同学还以为是拷贝的。
后来,经人介绍,我去了印刷厂学设计。介绍人指着孙文超老师说:“你就跟他学。”每个星期六去厂里,老师给我订了本子,要求我每天画速写——在家画,下课画,见什么画什么,也画同学。就是从那时起,我在这条深浅不一的艺术道路上,正式开始了蹒跚学步。
Culture菌:您的求学之路似乎并不平坦?
张友来: 是的,充满了波折。初中毕业时,我看到青岛美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心里想去,却犹豫不决。高中毕业后,我干过打石子、分拣邮政包裹这些体力活,但心里总不甘心。夏天,我先考了青岛纺织工学院,没考上;后来又参加山东省轻工美术学校的招生考试,我的成绩在烟台市算比较好的,终于考取了装潢1班。那是1983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到的专业课是西方的教学理念,我感到非常新奇,学得也格外下功夫。
学校的老师很好,第二年级还特意从天津请了老师,我记得有李克强老师、蔡老师等(注:此李克强非彼李克强)。李克强老师对我的评价和点评,让我在专业上进步很大。但也是在那时,由于长期熬夜完成作业,加上同学间的复杂关系,我劳累过度,不幸患上了忧郁症。我本是个喜欢安静、独自画画的人,常带着画具去学校山上画日出日落,之前也常去很远的地方画水粉、画大海、画教堂,但病还是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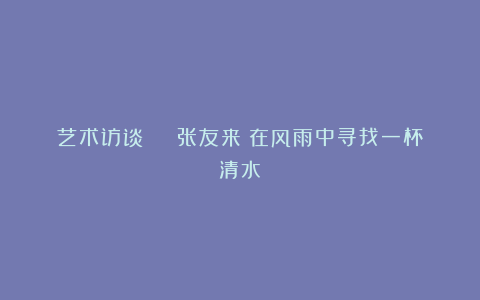
Culture菌:这段生病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友来: 这段经历非常沉重。毕业后,家人起初没意识到是心理问题,给我吃了很强的抗镇静药物,结果反而更严重,住了无数次院,甚至惊动了公安机关。我在那种模糊不清却又残存着理性的世界里挣扎了很久。我喜欢大海,喜欢所有人,唯独不习惯服务对待我的方式,尤其是我的妈妈。她在我吃药晕死过去时,她却说:“我对不起你呀,友来。”我爸爸问道:“他死了吗?”是父母养育了我,却对我没有一点真心关怀。但即便如此,我毕业后也一直没有停止画画和做设计。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明与暗,也让我知道,艺术是我在风雨中寻找平静的方式。创作于我,就像在不安的时空里找到一块安宁之地。
Culture菌:能谈谈您的创作理念和灵感来源吗?
张友来: 我的创作理念,简单说就是“气顺理清”。每次创作,我都要找到那个让自己心意顺畅、道理清晰的时刻。灵感从哪里来?童年的美好是我创作的源泉,童年就像一杯清水,我每一次创作,都可以说是从这杯清水开始的。我接受生活中一切不经意的“是非”,并努力表达其中的自然之美。
我欣赏很多画家。比如毕加索,他能在方寸之间连接起不同的点线面与色彩;夏加尔用童话诉说人间天堂与战争;胡安·格里斯用色块拼接情感;吴冠中的江南水乡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炽热。但最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绘画语言,找到自己喜欢的理念,不断创新发展。
Culture菌:您如何看待艺术与外部因素,比如政治、道德的关系?
张友来: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思想有。把艺术当成政治标准的答案是不正确的。同样,把艺术仅仅当作道德或法律的工具,也不是绘画创作的本源。创作本身是一件很纯粹、很美好的事,是在是非非的不平常中,找到那份平常心。
Culture菌:回顾您的艺术人生,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友来: 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没有那些教过我的老师,就没有我的艺术人生。艺术之路有春天的气息,也有下雨的时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每当拿起画笔,我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如何更完善地画出一件让自己、让他人满意的作品。我喜欢大海,喜欢所有人,尽管生活中也有遗憾和伤痛。创作是艰苦的,但只要你怀着喜欢的心情去面对,它就是最重要的。好画三千,可能只得一张,但为了那“一杯清水”的源头活水,一切的等待和坚持都是值得的。我知道,我总会在山的那边,等着与下一个灵感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