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被父亲掂量了许久的玉米种子,终于落进了豫东平原焦渴的土里。土地是灰黄色的,被盛夏的日头晒得起了浮尘,脚一踩,噗的一声,一股轻烟。父亲的汗滴下去,竟不渗,只在土坷垃上滚一下,变成一个混浊的小泥点,随即就被空气蒸发了。
这平原,坦荡得让人心慌。一眼望去,除了天,就是地,天地之间,是一排排矮下去的、沉默的村庄。风是滚烫的,带着一股土腥气。玉米苗就在这煎熬里,挣扎着探出头,叶子蜷着,像一只只握紧的、求救的小拳头。那些日子,父亲的眉头锁成一个“川”字,他半夜起来,蹲在田埂上抽烟,烟头的火光明灭,和天上那几颗稀疏的星子对望。井越打越深,水泵呻吟着,吐出来的水也是温吞的,浇到地里,只听得到土壤“嘶嘶”的吮吸声,像永远也喂不饱。
我们这些平原上的孩子,是跟着庄稼一起长大的。赤脚踩在滚烫的土地上,能感到那种从地心传来的焦躁。我们帮着大人拉水管,那胶皮管子软塌塌地躺在田垄上,像一条垂死的长虫。水艰难地流着,渗入裂缝,可裂缝张着干渴的嘴,仿佛永远也填不满。那时节,整个平原的命,就悬在那一条越来越细的水线上。
谁都没想到,天的脸色说变就变。
七月尾,玉米正抽雄吐丝,那是它们一生中最娇贵、最需要定数的时节。雄穗刚刚顶出天缨,像一片淡紫色的薄雾,雌穗也吐出了柔嫩的、丝绦般的红缨,等着风来做媒,完成生命里最紧要的一次交合。可风没来,雨来了。
起先是闷,闷得人胸口像堵着一团湿棉花。然后,天蓦地沉下脸,黑压压的云,从平原的尽头,排山倒海地推过来。雨,不是下,是倒。像天河决了口,哗啦啦,没有间隙,没有节奏,只是纯粹地、野蛮地倾倒。只一夜,世界就变了模样。
田垄不见了,路不见了。目之所及,是一片浑黄的、无边无际的水。高一点的玉米,还顽强地露出半个身子,像溺水的人;矮一点的,已完全没了顶。那曾经娇嫩的红缨,此刻沾满了泥浆,耷拉着,在浑浊的水里无力地漂荡。雄穗上的花粉,本该乘着微风去远行,如今全被雨水打落,溶进了这一片汪洋里。完了。父亲披着雨衣,站在地头,一动不动。雨水从他雨衣的帽檐流成一条线。他就那么站着,像一尊被遗忘在洪水里的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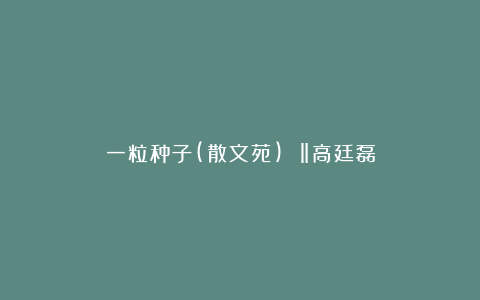
水退得极慢。短暂的太阳出来了,毒辣地照在这片泽国上。蒸腾起的水汽里,弥漫着一股植物腐烂的、甜腥的气息。玉米们东倒西歪,叶子破烂,那曾经象征生命的红缨,变成了污糟的褐色。没有授粉的玉米棒子,瘪着,像一句无法说出口的叹息。
父亲下到田里,扶起一株,又扶起一株。他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徒劳。他掰下一个发育不全的棒子,剥开。里面的籽粒稀稀拉拉,像豁了牙的嘴,大多只是些苍白的、水泡过的痕迹。
他拿着那枚畸形的玉米,走回田埂,坐下。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它递给我。
我接过。它很轻,几乎没有重量。那歪扭的籽粒,记录着一场干旱的起始,和一场洪涝的终结。我捏着它,仿佛捏着整个豫东平原的夏天——那焦灼的期盼,那狂暴的打断,以及最后,这无言的、沉甸甸的收成。
平原依旧沉默。风吹过积水未干的田野,吹过那些空荡荡的玉米秆,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大地一声悠长而疲惫的呼吸。
作者简介:
高廷磊,河南省淮阳区大连乡人氏,现为《宛丘文学》主编,《百度》之百家号责任编辑,烟台市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签约作家,大西北文学纸刊签约作家,曾多次获得金奖,优秀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