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执壶,掌心的温热便悄然印上壶身,宛如细语附着于泥面;每一次茶汤的浇淋,便如一层层幽邃的光泽,无声潜入壶身纹理深处,仿佛泥胎在吮吸着汁液,又似在呼吸着岁月。久而久之,壶表竟渐渐覆盖上一层温润如玉的包浆,内敛而深邃——那是时间与使用共同写下的诗行,将冰冷的器具慢慢转化成了有体温、有记忆的伴侣。
它来自山深处,由大地深处最沉默的泥土与矿料揉捏而成。制壶老匠人掌间布满沟壑,那是与泥土日日相搏的印记。他手指摩挲着未经烧制的泥胚,如同抚摸着大地之骨,将泥团反复锤炼、拍打、塑形。当泥胚终于送进窑炉,火舌便以最原始的烈焰之力,将泥土的魂与匠人的心紧紧熔铸在一起,再以涅槃之姿,重见天日。
初入我手,壶身带着初生般粗涩的肌理,犹带火气与泥腥。我小心捧持,如同迎接一个陌生而羞涩的生命。初时泡茶,茶汤入壶,它几乎显出几分笨拙的滞涩,仿佛正屏息凝神,默默体悟着新世界的滋味。它默默吸吮着每一道茶汤,吞咽着每一次倾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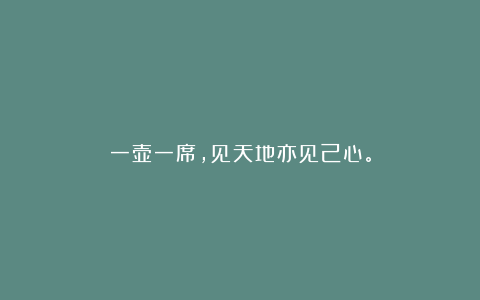
时光流转,茶汤早已记不清倾注过多少回,我手心的温度也早已浸润了壶身。壶表渐渐浮泛出温润如古玉的光泽,幽深内敛,仿佛浸透了日月之辉。这光泽不事张扬,如光阴本身,沉静厚重,却又分明映照出人影的轮廓。手抚过壶身,便如触摸着温热的肌肤,那包浆之下,是时光的沉淀与茶汤的滋养,也渗透了我掌中的温度与心魂的印记。壶在掌心,便仿佛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无言而贴切的默契,早已在反复摩挲与浸润中浑然天成。
月华如练,铺洒庭院,我独坐于此,清茶一壶,小杯一只。茶烟氤氲,袅袅升腾,消融于月华。此时执壶,便似执着一方浓缩的天地:那壶泥源于大地深处,茶汤采自山间云雾,而手中这壶,更仿佛成了与我共同走过光阴的故人。
壶中倒尽最后一滴茶汤,壶内温热的水汽便幽幽升起,宛如一声无声的轻叹。物我之间,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壶身温润的光泽,正是时间凝成的一首诗,也是我灵魂在壶上投下的一抹倒影。
一壶一席,如此简单。然而,壶中泡开的又岂止是茶叶?它映照的是天地之大,亦烛照出内心之微——岁月无声,壶却以那日益温润的包浆作答。它在掌中默默诉说:原来最幽微的光泽,需经时光之手反复摩挲;最深沉的回响,常寓于最寂静的器物深处。
这壶中天地,既是归宿,亦是明镜:映照山川,亦照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