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白斑驳的墙面如干涸的土地,其上绿影婆娑似无声低语。唯见那只托壶的手静定微屈,如捧起晨露般慎重——将一丸温润深棕托现于人前。暗棕陶骨,光影如流泉滑过弧壁;壶身若饱满秋柿,饱满中隐露六道浅浅棱线,恍若果实蒂端痕迹未褪。细嘴如玉茎,圈把如藤环回绕于腕际,珠钮似垂露凝在盖心。斑驳老墙隙漏里挣扎的几茎苍影,悄然遥映着柿子圆满如珠的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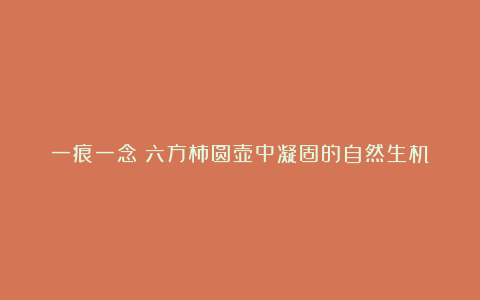
柿圆意蕴于此壶里,竟不囿于柔润表象。那些棱线自壶底悄然上浮,聚于盖周,是方正风骨在浑圆肌理中藏起的小小风雷。手造器物的“温度”,不在直白外露,恰存于这般方中寓圆、圆中见方的巧思密合,圆融周至而内里自有精神挺立。这沉潜内省之态,仿若老墙苔痕里几丛生而不灭的绿意,低微不显,却与壶色一暗一明,为厚重古意添了呼吸之隙。绿影摇曳处,仿佛窥见制壶人凝睇柿实的瞬间:“神遇”在心头微动,澄澈素朴的气息刹那凝固成器物之身。
当绿影退作苍远背景,斑驳墙面渐趋淡远,而壶仍沉厚地立于掌心。它已越过时间的荒原。掌心此刻便是它的天涯——墙色老去,藤痕漫灭,唯壶体如初生般映着光,深浓陶色如古木化石泛着柔光,棱角与弧面的对峙愈显其深藏的生命。造者指尖抚过泥胚的心迹,已凝作细嘴圈把的温柔轮廓,比老墙更无言地透出长久。
世间器物,总在粗砺中留痕,于磨蚀里存身。那捧起的壶便是一枚“柿”的诗篇,是泥与人相互成全的一痕一念:自然灵气渗人陶土,指尖微温抚作形状,绿影老墙皆作衬词——终将永恒流转的生机锁于一方壶天。
那托举的手掌,恰似承托了天地间圆融而坚忍的一息气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