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07 16:04
第一章 陌生的使命
1930年4月的上海,春雨绵绵。
【 一个红军无线电破密专家的传奇人生】
宋侃夫撑着油纸伞,在法租界的一条弄堂里快步走着。细雨打湿了他的长衫下摆,他却浑然不觉。方才江南省委的同志匆匆传来口信,要他立即到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这种突如其来的紧急约见,在地下工作中往往意味着重大变故。
推开咖啡馆的门,风铃叮当作响。角落里,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抬起头——是陈寿昌,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
“小宋,坐。”陈寿昌的声音很低,手指在咖啡杯沿轻轻划着圈。
宋侃夫坐下,跑堂送来一杯清咖。他注意到陈寿昌面前摊开一份《申报》,但报纸是倒着的——这是预先约定的安全信号。
“组织上有个重要决定。”陈寿昌推了推眼镜,镜片直视着他,“中央特科需要懂无线电技术的同志。我们知道你念书时学过电机。”
宋侃夫一愣。电机?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组织上有个重要决定。”陈寿昌推了推眼镜,镜片直视着他,“中央特科需要懂无线电技术的同志。】
五年前,他还是杭州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就在那时,他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转党。从此,书本里的电机原理、电路图,渐渐被传单、标语、秘密会议取代。这些年,他在法南区委做青年工作,整天在工人夜校、学生社团间穿梭,那些曾经学过的,早就“丢光了”。
“陈同志,我……”宋侃夫苦笑,“那些东西,真的都还给老师了。”
“有基础就能捡起来。”陈寿昌的语气不容置疑,“现在是边学边干的时候。苏区需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白区的地下联络也需要新技术。你学过,就是优势。”
咖啡馆的留声机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甜腻的歌声与此刻严肃的谈话格格不入。窗外,巡捕房的警车呼啸而过。
宋侃夫沉默了。他想起上周在杨树浦工厂区因为叛徒告密,三个同志被捕。地下交通员老李冒死送来消息时,嘴唇都在抖:“电台被破坏了,和中央的联系……断了三天了。”
三天,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可能意味着一个联络网的覆灭,几十个同志的牺牲。
“我服从组织决定。”宋侃夫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
陈寿昌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用铅笔快速写下地址:“明天下午三点,到这个地方。记住,只看一遍。”
宋侃夫接过纸条。地址是沪东华德路处里弄。他默念三遍,将纸条揉碎,撒进咖啡杯里。褐色的液体瞬间将纸屑吞没。
【侃夫接过纸条。地址是沪东华德路处里弄。他默念三遍纸条揉碎,撒进咖啡杯里。褐色的液体瞬间将纸屑吞没】
第二章 三人学习小组
华德路的住处是一间临街的亭子间,不到十五平米,朝北的窗户永远照不进阳光。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木箱。
和宋侃夫同住的,是两个从湘鄂西苏区来的年轻人。矮壮些的叫阿广,广东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客家口音,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另一个姓周,大家都叫他小周,才十七八岁,脸颊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绒毛,眼睛亮得像星星。
“宋大哥!”小周见到宋侃夫,兴奋地搓着手,“组织上说你会教我们无线电!我在苏区见过一次电台,那么大个箱子,能跟几百里外说话,神了!”
阿广比较沉稳,只是憨厚地笑着,从怀里掏出两个还温热的烧饼:“宋同志,还没吃吧?巷口买的。”
三个人的学习小组就这样成立了。宋侃夫是组长,负责技术学习和三个组织生活。说是“教”,其实他自己也要从头学起。那些欧姆定律、电磁感应、电子管原理,在记忆深处早已蒙尘。
第二天,一个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男子敲门进来。他三十岁左右,面容清癯,眼神锐利。
“我姓翁,单名英。”来人声音很轻,从公文包里取出几本书,“今后由我来讲课。时间不多,我们必须抓紧。”
从此,每个周二、周四的下午,翁英准时出现。他讲课条理清晰,从最基础的电路开始,用粉笔在墙上挂的小黑板上画图。那些电阻、线圈的符号,渐渐在宋侃夫脑中重新鲜活起来。
“无线电通讯,关键是发射和接收。”翁英在黑板上画出发射机的结构图,“振荡器产生高频信号,放大器增强功率,最后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接收则是逆过程……”
小周听得入神,手指不自觉地跟着比划。阿广则埋头在笔记本上刷刷记录,他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极认真。
【理论之外,是翁英带来一堆零件:电子管、变压器、电容器、电阻、线圈,还有一块钻好孔的胶木板 】
理论之外,是翁英带来一堆零件:电子管、变压器、电容器、电阻、线圈,还有一块钻好孔的胶木板。
“先从三管收音机装起。”翁英说。
三个人围在方桌前,像在做最精密的工艺品。宋侃夫按照电路图,用焊锡将零件一个个连接起来。焊枪烧红了,锡丝融化,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的味道。小周负责递零件,阿广则在一旁默记每个零件的名称和作用。
第一次通电时,三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宋侃夫深吸一口气,按下开关。
电子管慢慢亮起橙红色的光,像黑夜里的萤火。转动可变电容器,喇叭里先是沙沙的噪音,然后——突然传出了声音!是电台的播音,虽然夹杂着杂音,但确确实实是人的说话声!
“通了!”小周跳起来,差点碰倒焊枪。
阿广咧开嘴笑,露出白牙。宋侃夫看着那闪烁的电子管,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这微弱的电波,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革命的未来。
第三章 指尖上的密码
技术学习渐入佳境,更艰巨的任务来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敲门声响起,三长两短。宋侃夫开门,一个穿着邮差制服、戴鸭舌帽的男子闪身进来。他摘下帽子,露出一张朴实憨厚的脸。
“我是伍云甫。”来人伸出手,手掌粗壮,指节突出,“从今天起,教你们报务。”
报务,就是收发电报。伍云甫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手键——这是发报用的电键,还有一个耳机。
“电报用的是摩尔斯电码。”伍云甫在桌上铺开一张纸,上面画着点和划的组合,“点(·)读’滴’,时间短;划(—)读’答’,时间是点的三倍。每个字母、数字,都由不同的点和划组成。”
他示范:食指和中指轻轻搭在手键上,手腕悬空,只靠手指的力度按压。“滴答答答,是A。答答答滴答,是B……”
宋侃夫试着按下去。“咔哒、咔哒”,手键发出清脆的响声。看似简单,但要快、要准、要稳,却不容易。小周第一次练习,手指僵硬得像木棍,发出的电码时长时短,毫无规律。
“放松,手腕要活。”伍云甫纠正他的姿势,“这不是力气活,是巧劲。”
收报更难。伍云甫让宋侃夫戴上耳机,自己到隔壁房间,用手键发送电码。耳机里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时快时慢,夹杂着干扰的噪音。宋侃夫必须全神贯注,在纸上记录下每一个点划,再翻译成字母。
“C……Q……D……”他写下一串字母,额头渗出细汗。这比组装收音机难多了,需要极致的专注和敏锐的听力。
伍云甫回来后,检查他的记录,用红笔圈出错误:“这里,应该是’滴答滴’,你记成了’滴滴答’。差一点,意思就全变了。”
除了伍云甫,王子纲也常来指导。他是个老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飞舞时,快得几乎看不清动作。他发报的声音,清脆、均匀,像钟表的滴答声。
“速度要快,但不能乱。”王子纲说,“每个’滴’、每个’答’都要清清楚楚。收报的人,就靠这个分辨。”
练习是枯燥的。从早到晚,屋子里只有手键的“咔哒”声和抄报的沙沙声。宋侃夫的指尖磨出了茧,小周的肩膀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痛,阿广则因为听力高度集中,晚上睡觉时耳朵里还嗡嗡作响。
【宋侃夫已经能每分钟抄收120个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能达到80到100个。小周和阿广慢些,但也都能独立收发】
但进步也是显著的。两个月后,宋侃夫已经能每分钟抄收120个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能达到80到100个。小周和阿广稍慢些,但也都能独立收发了。
一天傍晚,翁英带来一台十五瓦的发报机。这是他们自己组装的,外壳是用木箱改的,天线从窗口悄悄伸出去,沿着屋檐拉到屋顶。
“今晚试通报。”翁英神情严肃,“呼叫频率是7500千周,呼号’春风’。对方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地下台,呼号’秋月’。”
夜里十一点,万籁俱寂。宋侃夫戴上耳机,手指搭在手键上。小周负责调整频率,阿广在窗口望风。
“开始。”翁英点头。
宋侃夫深吸一口气,按下手键:“滴滴答滴滴答……”(CQ CQ,这里是春风,呼叫秋月)
发送完毕,他转为接收。耳机里只有沙沙的噪音。一秒,两秒,三秒……正当他的心渐渐下沉时,一个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响起了:“答滴滴答答……”(秋月收到,春风请讲)
!
宋侃夫几乎是颤抖着发出预定的测试码:“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敏捷的棕色狐狸跳过懒狗——这个英文短句包含所有26个字母)。这是测试信号质量和收发准确性的标准句。
对方完整地重复了这句话,一个字母都不差。
“成功了!”小周压低声音欢呼,眼里闪着泪光。阿广紧紧握住宋侃夫的手,手掌滚烫。
翁英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好,很好。但记住,这开始。”
第四章 风暴前夜
试通报成功后的兴奋持续了几天,但很快就被紧张的气氛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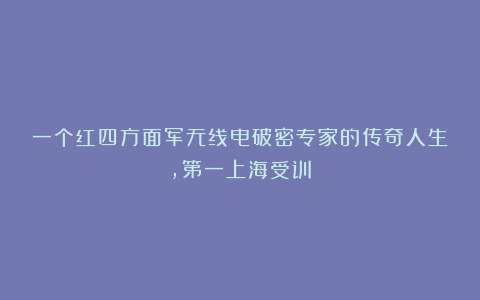
设备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子管是易耗品,变压器烧了要换,电阻电容也常常损坏。这些零件在市面上能买到,但频繁购买容易引起怀疑。
一天,一个穿着长衫、提着皮箱的男子找上门来。他四十岁上下,面容和善,说话带着四川口音。
“我姓吴,吴永康。”来人皮箱,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各种无线电零件,“我在北四川路开了个’永康电器行’,你们需要什么,列单子给我。”
吴永康不仅提供零件,还常常带来一些市面上少见的新器材。有一次,他甚至搞来几只美国产的真空管,性能比国产的好很多。
“吴老板,这太贵重了。”宋侃夫过意不去。
“什么话。”吴永康摆摆手,“你们在前线拼命,我在后方做这点事,应该的。”
他说的”,既指苏区的武装斗争,也指白区这条无形的战线。宋侃夫后来才知道,吴永康1924年就入党了,他的电器行是中央特科重要的联络点和物资供应站。1937年,吴永康参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壮烈牺牲——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安全考虑,一个地方不能久住。夏天,学习小组搬到了沪西小沙沟路和康脑脱路交界的一处房子。这里更偏僻,邻居多是做小生意的,不太关心别人的事。
搬家后不久,湘鄂阿广和小周接到命令,要返回苏区。
“宋大哥,我们要走了。”临别前夜,小周眼睛红红的,“苏区要建电台,组织上调我们回去。”
【宋大哥,我们要走了。”临别前夜,小周眼睛红红的,“苏区要建电台,组织上调我们回去】
阿广默默收拾行李,把几本无线电教材仔细包好,塞进包袱最底层。“宋同志,这些日子,谢谢你。”他说话还是那样简短,但握着宋侃夫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宋侃夫心里也堵得慌。三个月同吃同住、一起学习,虽然不是血亲,却比亲人更亲。他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苏区的斗争更残酷,无线电工作更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
“保重。”他只能说出这两个字。
“你也保重。”小周抹了把眼睛,“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再一起装电台!”
阿广和小周走后,组织上又派来两个新同志。一个姓王,来自湘鄂赣苏区,二十出头,聪明机灵,学东西很快。另一个年纪稍大,沉默寡言,名字宋侃夫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新组合需要重新磨合。宋侃夫既要自己学习,还要教新人,忙开交。就在这时,翁英、伍云甫、王子纲来联系的次数突然减少了。有时约好时间,却不见人来。宋侃夫隐隐感到不安。
九月的一天下午,雨下得正大。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不是约定的信号。宋侃夫警惕地从门缝往外看——是陈寿昌!
他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阴沉得可怕。一进门,他就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纸包着的钞票,“啪”地放在“小宋,”陈寿昌的声音又急又低,“听着,从现在起,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开水,不要出门。吃饭让饭铺送,钱在这里。”
宋侃夫心里一紧:“出什么事了?”
“别问。”陈寿昌走到窗前,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了看,“翁英、伍云甫、王子纲,近期都不会来了。你们自己学,保护好设备,销毁所有文件。”
“要多久?”
“不知道。可能很长。”陈寿昌转身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宋侃夫从未见过的凝重,“记住,无论听到什么消息,都不要擅自行动。等我来联系你。”
说完,他拉低帽檐,又冲进雨里。
屋里的气氛骤然凝固。姓王的同志脸色发白:“宋大哥,是不是……”
“别瞎猜。”宋侃夫打断他,但自己的心也在狂跳。他想起最近报纸上的一些消息:租界巡捕房加大搜查力度,好几个地下联络点被破坏。难道……
他们严格执行陈寿昌的指示。除了每天轮流去巷口的老虎灶打一壶开水,绝不出门。一日三餐由街角的小饭铺送来,每次都是不同的伙计,放下食,一句话也不多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消息。无线电零件用完了,他们不敢去找吴永康。教材翻来覆去看,已经能背下来。实在无事可做时,他们就练习收发电报,但不敢真的开机——谁知道电波会不会被侦测到?
焦虑像霉菌一样在屋里蔓延。姓王的同志开始坐不住,有时傍晚说要“透透气”,一去就是一两个钟头。宋侃夫提醒他注意安全,他只是笑笑:“放心,我就是走走。”
十月初的一天,姓王的同志很晚才回来,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宋侃夫皱眉:“你去哪儿了?”
“就……随便逛逛。”
“这种时候,怎么能’随便逛逛’?”宋侃夫压低声音,但掩不住怒气。
几天后,陈寿昌突然又出现了。他看上去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但神情比上次稍缓。
“警报解除了。”他坐下,接过宋侃夫递来的热水,喝了一大口,“是顾顺章叛变了。”
顾顺章!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着几乎所有核心机密!
“他四月底在武汉被捕,立即就叛变了。”陈寿昌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供出了武汉的地下党组织,还要来上海指认中央机关。幸亏我们在南京政府内部有同志,钱壮飞截获了电报,提前报警。中央机关连夜转移,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宋侃夫听得脊背发凉。如果让顾顺章得逞,整个党中央可能被一网打尽。
“那翁英同志他们……”
“翁英已经转移去中央苏区了。伍云甫、王子纲安全,但暂时还不能来。”陈寿昌顿了顿,“另外,那个姓王的同志,组织上决定调走。”
“为什么?”
“我们发现他常去舞厅。”陈寿昌神色严峻,“这种时候,太危险。无线电工作,首要的是隐蔽和纪律。”
姓王的同志很快被调离。剩下的那位沉默的同志,不久也被派往别处。小小的学习小组,又只剩下宋侃夫一人。
第五章 独守空城
十一月的上海,已经有了寒意。
宋侃夫独自住在亭子间里。组织上派了新的同志来同住——徐以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读过几年书,说话做事都很稳重。
“宋同志,今后请多指教。”徐以新很客气,把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包袱、几本书——整齐地放在床头。
两人相处融洽。白天一起学习无线电技术,宋把翁英教的内容,一点点转授给徐以新。晚上,他们轮流值夜,一个睡觉,一个在窗口警戒。
但平静很快被打破。他们渐渐发现,房东很不对劲。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杜,身材矮胖,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他很少正经做事,但家里经常有三教九流的人进出:有穿绸褂的生意人,有短打扮的苦力,甚至还有一两个巡捕房的人。
一天傍晚,杜房东敲开他们的门,满脸堆笑:“两位先生,还没吃吧?我让老婆多炒了两个菜,一起喝一杯?”
宋侃夫婉拒:“谢谢杜老板,我们吃过了。”
“别客气嘛!”杜房东挤进来,眼睛在屋里扫视,“两位是读书人吧?做什么营生?”
“教书的,在补习班代课。”这是预先准备好的身份。
“教书好,教书好。”杜房东嘴里应着,目光却落在墙角堆着的木箱上——那里装着无线电零件,虽然盖着布,但形状还是能看出来。
等他走后,宋侃夫和徐以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警惕。
“这个人不简单。”徐以新低声说,“我打听过,他是这一带的’老头子’,手下有一帮徒子徒孙,专干些欺行霸市、收保护费的勾当。跟巡捕房也有往来。”
宋侃夫心里一沉。这样的房东,太危险。无线电设备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所有无线电教材、笔记、电路图,全部转移到徐以新在法租界租的一个信箱里。重要的零件分散藏匿:有的塞在屋顶瓦片下,有的埋在屋后的花坛里。屋里只留最基础的几样,而且都做了伪装——发报机零件混在一堆旧钟表零件里,电子管用报纸包好,塞进米缸底层。
最关键的改变是:他们不再在屋里进行任何无线电操作。不组装,不调试,更不发报。所有技术学习,只停留在纸面讨论。
杜房东还是常来串门。有时拎一壶酒,有时端一盘花生米,东拉西扯,拐弯抹角地打探。
“两位先生,我看你们屋里有不少铁家伙,是做啥用的?”
“哦,那是些旧钟表,我业余喜欢修修补补。”宋侃夫面不改色。
“钟表?我看看?”杜房东伸手要掀盖布。
徐以新抢先一步,掀开布,露出几块旧怀表和一堆齿轮、发条:“杜老板对钟表也有兴趣?”
杜房东看了几眼,似乎没看出什么名堂,悻悻作罢。
但他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这个房东太精明,也太好奇。必须更加小心。
宋侃夫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只有一把房门钥匙。无论谁出门,都把钥匙交给房东的老婆。
“杜师母,我们出去一趟,钥匙放您这儿。”每次,宋侃夫都说得格外自然,“免得您要打扫,进不来。”
这一招果然有效。房东老婆是个老实巴交的妇人,每次都笑眯眯接过钥匙:“宋先生太客气了。”
而杜房东见他们如此“坦荡”,疑心似乎也消减了些。有时在楼道遇见,还会点头打招呼。
但宋侃夫知道,危险远未解除。顾顺章叛变的阴影仍然笼罩,租界的搜查越来越频繁。而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十二月初的一天,陈寿昌带来了新指示:中央已任命乐少华同志接替他的工作,领导无线电小组。
“乐少华同志是工人出身,对无线电是外行。”陈寿昌说,“技术上,你要多担当。不仅要自己学,还要教后来的同志。另外……”
他压低声音:“中央决定,要尽快建立上海到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联络。苏区那边,曾三、刘寅他们已经在组建电台。我们这边,必须加快速度。”
“可是现在……”宋侃夫看了一眼窗外。弄堂里,一个穿着黑褂子的男人正在慢悠悠地踱步,已经来回走了三趟。
“困难我知道。”陈寿昌拍拍他的肩,“但形势不等人。苏区急需和中央保持联络,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小宋,这副担子很重,但必须挑起来。”
陈寿昌走了。宋侃夫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尽头。夕阳西下,将整个上海染成暗红色。远处,外滩的海关大楼传来报时的钟声,沉重而悠长。
他转身回到屋里,打开米缸,取出那几只用报纸包着的电子管。橙红色的玻璃壳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微弱而执拗的光。
这条无形的战线,刚刚拉开序幕。而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面。
(未完待续)
注:
- 法南区委: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和南市地区的地下区委。
- 陈寿昌: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1934年在湘鄂赣苏区牺牲。
- 中央特科: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情报、保卫等工作。
- 翁英:原名翁瑛,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技术负责人之一。
- 普通电码:指摩尔斯电码。
- 康脑脱路:今康定路。
- 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叛变,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