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一把咖啡壶
和
咖啡结缘
李北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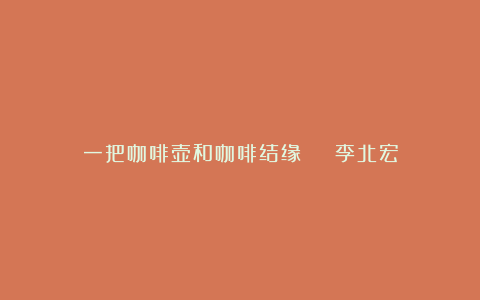
我对咖啡有印象是从咖啡壶开始,那是上世纪0年代中期我记事时。缘因家父早上有吃咖啡的习惯,我看见家中煤气灶上一个容器上的玻璃球内不断有气泡翻滚,好奇地问父亲在煮什么、为何冒泡。由此知道了咖啡,也晓得了冒泡是水煮沸产生。以后,人长大了,开始了解这把咖啡壶。该咖啡壶是铝制品,把手是胶木的,壶盖十分密缝、开合服贴,壶身上有刻度,显示6 CUPS,壶底部分呈鼓起状,出水壶口连接用似乎是焊接,但不见焊的痕迹。胶木把手固定用的是铆钉,把手下面有铝制挡板,可防止煤气烈焰损坏把手。从外观看,此壶设计美观,制作工艺精良。
打开壶盖,别有洞天。拉出圆形咖啡篮(容器)顶部的管子,打开布满小圆孔的篮盖,可见盛放咖啡沫的咖啡篮内部,高度约三四厘米,它有密密麻麻孔洞。咖啡篮插进空心的管子两者合为一体,放置在咖啡壶内,底部架空。这些觉得蛮新奇,但不知其奥妙处。读初中时,知道了蒸汽原理。该咖啡壶在水煮沸后,架空的底座中空管子将蒸汽输送到顶端透明玻璃球处,蒸馏水遂落下透过密布咖啡篮的孔洞对咖啡沫进行渗滤,不断循环,数分钟后沸水变成咖啡,大功告成。这样做成的咖啡很科学,做到了豆、咖分离,使香气浓郁,尽显咖啡本味,谓之“小壶咖啡”,这比将磨好的咖啡豆直接放在鑊子里煮要好吃交关。这样的咖啡壶当年少见。
上世纪80年代,听家父说起40 年代学校复员回上海,该咖啡壶在中央商场(沙市路)购置,是所谓二战剩余物资,比较便宜。吃咖啡,他不独享其美,有时学生到家中听课,他或是用咖啡,或是用绿茶招待。1966年,这把咖啡壶结束使命;即便在1976年以后,家父也不使用,只吃西湖龙井茶和安徽毛峰茶了。
咖啡壶底部文字 LIGHT、COFFEE POT、ALUMINUM,MADE IN CHINA
这把美式咖啡壶产自何处?值得关心。既然是剩余物资,应该是洋货。在咖啡壶底部发现有模糊英文字,经过仔细辨认为:LIGHT、COFFEE POT、ALUMINUM,MADE IN CHINA。其中,LUGHT为大写字母,应该是牌名,以后文字分别为咖啡壶、铝制、中国制造。让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是剩余物资,应该是国外输入,怎么是中国制造?这把咖啡壶的制作如此精致,甚至在80年代上海工厂生产的相仿咖啡壶也比不上,也让人不解。英文中有Assembled in China,意思为在中国组装;Made in China则意为材料、生产均在中国,推测此壶有可能当年在中国上海代工生产。这把咖啡壶的质量没得话讲,历经80寒暑仍可使用,让人称奇。
上海牌咖啡 一罐227克/半磅
上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复旦工会二楼有间小屋专供部分教员凭卡供应紧俏商品,记得有群英牌香烟四角五分一包、牡丹牌香烟四角九分一包,还有红塔山、中华牌等香烟;上海牌咖啡三块五角一罐(听)。家父有时差我去购买货物,于是对咖啡有了更多了解。咖啡是上海咖啡厂出品,真空包装,227克(半磅)装,听头面板附有一把开罐器。开罐时将开罐器下部开口处插入罐头上部一伸出铁片,遂不停转动开罐器捏柄,转毕罐头一圈,罐头盖即可打开,香气顿时喷出。
60年代中后期,工会小卖部关张,咖啡断供。市场上7分一包的“咖啡茶”应市,我开始尝试。咖啡茶也由上海咖啡厂生产,拆开长方形纸包装,可见外裹糖衣,放入杯中,开水一泡、搅拌,即成黑咖啡色,上口甜甜的,有寡淡咖啡味。回想起来,当年这种咖啡茶其实是由咖啡豆下脚料研磨成粉,加糖粉压制做成。70年代,杨姓同学有吃咖啡偏好,曾邀我一同骑车去过一些咖啡馆。南京东路东海咖啡馆、南京西路喜来临、南京西路黄陂北路东南角的海燕咖啡馆等都曾光顾,曾骑车踏到新成游泳池西面一开间门面的小“凯歌”。印象深的是东海的清咖一角八分,奶咖两角三分,柠檬派三角五分一块、喜来临奶油素菜汤一角两分一盆,海燕的炸猪排两角五分一块。东海咖啡馆名气较大,它是俄国犹太人1935年开设,开在南京东路“朋街”女子服装店对过,原名马尔斯MARS咖啡馆。1954年,老板去苏联后更名东海咖啡馆,如今迁至不远的滇池路。
金中点心店
以后,杨同学打探得金中点心店新增小壶咖啡供应,特邀前往。踏脚车到店,领教了这家中西结合餐饮店。该店位于金陵中路柳林路口,故名“金中”。这家店主营生煎馒头、鸡鸭血汤、咖喱牛肉汤等,时令季节有糟田螺、冷面等供应,店堂内摆放几张八仙台子,条凳若干,生意本来就相当好,加了小壶咖啡,开始起了蓬头。回想起来,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店经理加出这档咖啡节目,中西混搭,路子蛮怪,却又出奇制胜。金中生意更好了,它填补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的空档,让人称奇的是,它家清咖只卖一角一分(玻璃杯),是通常人家的一半价钿。以往我吃生煎搭咖喱牛肉汤,到金中吃两客全发酵清水生煎(两角四分),吃罢,买一客清咖打打油水。金中的做法后无来者,空前绝后,可载入上海滩餐饮史册。
70年代中后期家住西区,考进高校读书,对咖啡关注少了。重新燃起兴趣是在80年代初有次在成同学家碰到他妻舅黄先生,他说:“今朝我吃到了雀巢咖啡Nescofé Coffee,开了洋荤,味道呒没闲话了,一级。是朋友在华侨商店用侨汇券购买,同时还买了咖啡知己Coffee mate和方糖。”第一次听到雀巢咖啡这名词,新鲜,于是我请他作了兴致勃勃的介绍。他说:“雀巢咖啡和传统烧的咖啡不同,是速溶咖啡。这主要是部分欧美人生活节奏比较快,讲求方便所致。知己则是牛奶的替代品。雀巢咖啡粉 知己 方糖放在一起冲泡。”我听后,第一次受到了雀巢启蒙教育。以后市场出现雀巢咖啡,价格昂贵,但云南散装咖啡豆上海食品一店卖4块多一斤,比较便宜。当时,我是购买云南咖啡豆,自己制作小壶咖啡。美国人讲销售策略,记得当时电视上出现雀巢公司“味道好极了”连续广告。我注意到,并关注发展。90年代,东莞的雀巢咖啡有了生产厂,我捷足先登,开始吃雀巢速溶咖啡。雀巢速溶咖啡迅速撬开中国市场,它的市场教育为以后进入的麦斯威尔咖啡客观上开了道。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务活动、到沪旅游人员增加,咖啡成为交际的媒介之一,我感到周边吃咖啡的人多了,吃雀巢咖啡也成为一种时髦,那个阶段恐怕是上海开埠后新一轮咖啡热的缘起。
八九十年代,曾数次光顾南京西路铜仁路(原哈同路)西北角的“上海咖啡馆”,人称“上咖”。清楚记得门口有个岗亭,岗亭西面是一个铁制书报亭。1989年曾在该书报亭买过新出的郑念所著《上海生死劫》。“上咖”贴对过是东风沙发厂门市部(紧贴北慈厚里),结婚时曾购买一对单人沙发124元。“上咖”店堂进入店堂右侧是一个半人高玻璃橱柜,内有两层玻璃搁板,摆放奶油蛋糕、花生排条等西点;店堂中央摆放着长形餐台。靠南京西路是大玻璃窗,挂有白色纱窗帘,靠窗一排火车座,窗外看里面模糊,里面看街景则一目了然,蛮有浪漫情调。店柜台内有个煮咖啡的大玻璃壶,随着咖啡水的翻滚,香气不断溢出,喷香。有朋友回忆,“上咖”二楼有营业,本人只记得“上咖”是两层楼房子,不记得二楼有营业。比较起来,“上咖”环境比东海清雅。“上咖”咖啡材料用国产咖啡豆,清咖两角,奶咖两角五分。当年,早上、下午以中老年顾客居多;夜晚则是青年情侣的天下,应该是男友会钞,向对方显示一下够潮流,有档次。“上咖”90年代动迁,建造了43层中欣大厦。“上咖”一度曾迁至愚园路,以后关门歇业。
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
南京西路这家“上海咖啡馆”90年代曾听老人回忆,原名德胜C.P.C咖啡馆,老板张宝存前店后作坊,自己摸索烘焙咖啡技术,终于研制出赢得顾客良好口感的咖啡,和名牌霞飞路(淮海中路)DD’S弟弟斯咖啡馆(国泰电影院斜对过)、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凯司令西菜社(1966年曾更名“凯歌食品商店”)、沙利文咖啡馆竞争,名声不断扩大。作家任溶溶《喝咖啡》文曾专述去吃咖啡事:“我曾经是个咖啡迷,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时,一早就到南京路铜仁路口的C.P.C咖啡馆喝咖啡,喝完了再上班……”。任先生的记忆应该停留在1958年之前,1958年,C.P.C改国有,更名为上海咖啡馆。同年,上海咖啡厂成立。张宝存凭一手绝活,出任上海咖啡厂厂长。
南京西路1442号
网上信息显示:德胜咖啡馆1935年在静安寺路1442号创办。据我考证,该店由21岁张宝存创立,最初该店开在百老汇路(大名路),后因八一三战事迁到静安寺路1442号。查询《老上海百业指南》(该书根据1947-1948《上海市行号图录》整理编撰),静安寺路1442号被标注,证明有店铺,没有显示店名可能是版面太小原因。陈同学当年住慈厚里,他记得幼年时“上咖”在南京西路西康路东北角,来喜饭店对过。“上咖”数十年并没有搬过场,不过,南京西路多咖啡馆,陈同学可能张冠李戴。
德胜C.P.C咖啡馆老板张宝存的孩子在店门口
80年代红的是“红宝石”,红宝石老板是英籍上海人过先生,1986年在华山路开了第一家门店,卖西点,堂吃咖啡。红宝石以后不断扩张,在江宁路开出门店,瑞金一路向明中学租借蔡光天前进大楼门面开店,又在新闸路等处开出多门家,生意兴隆。该店下午是老克勒时光,当年见到过手持斯迪克,身穿双排纽西装或休闲服的老者在吃咖啡,聊天,不时夹两句英格里希。
上海滩咖啡历史可谓悠久,在中华大地领先。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的1853年,有英国人劳惠霖将咖啡带到上海,在花园弄(南京路)开办老德记药房出售咖啡,上海人称它为“咳嗽药水”。1845年,“英国咖啡馆”British Coffee House开业,这是上海第一家咖啡馆。以后“虹口咖啡馆”1866年在浜北(苏州河北)开业。“咖啡”的称呼有个演变过程,曾被叫“磕肥”“加非”“茄菲”等,还是《申报》(1949年5月27日停办)权威,它在1875年11月10日刊载的一文中用了“咖啡”二字,从此定版。
上海人喜欢吃咖啡,应该是一百多年来的门户开放,逐渐在市民中形成习惯。据说,当下,上海滩有8000多家咖啡馆。我居住的康定路附近一两百米内竟然有七八家咖啡馆。曾经,卖咖啡店铺的一般叫“咖啡馆”,以显高尚。上海人一般会说,“到咖啡馆吃咖啡”。如今店名奇出怪样,有叫咖啡馆、咖啡店、咖啡屋、咖啡房不一而足。
康定路上咖啡馆
有人问起,普通话都说“喝咖啡”,为什么上海方言讲“吃咖啡”。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恐怕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上海方言“吃”字应用比普通话广泛,常将带有液体的食物归并到“吃”(qik入声字)来表示,如吃茶、吃粥、吃老酒、吃汤;不过,另也有和液体无关的“吃香烟” 等。普通话不同,通常将固体食物称之为“吃”。二是上海话承接已有的表达习惯。在咖啡落地上海滩后,市民将“吃茶”衍生到“吃咖啡,符合方言的演进,顺理成章。三是英文“Have coffee、Have lunch”,运用蛮灵活,在食物方面干湿混合使用。上海话则如法炮制,化洋为沪,化干为湿。“吃咖啡”的用语既是语言学问题,又是海派文化的一种特别解读。犹如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那般,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又融合西洋的元素,包容并蓄。“吃咖啡”是上海文化的微观显示,周立波先生曾有“吃大麦茶和吃咖啡”之说,透露海派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
如今,人到老年,我采取的是茶、咖并举,土洋结合。早上一杯雀巢 伴侣(过去称知己),接下来是红茶一杯消食养生。
2025.4.11
来源:“梵皇聚墨楼”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