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海城隍庙看民间宗教的兴衰
晨光穿透桃源南路的梧桐叶,斑驳光影落在朱漆重彩的庙门上。宁海城隍庙的八字山门如一位垂暮老者,诉说着一城百姓的市井弦歌与千年信仰。这座始建于唐广德年间的庙宇,在浙东大地上屹立了十二个世纪,供奉着梁武帝殿前将军田什化身的安仁侯城隍爷①,与守护城西的白鹤大帝境主爷。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窥探中国民间宗教千年兴衰流转的一扇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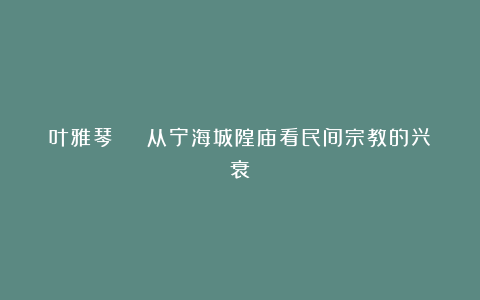
无论是城隍爷、境主爷、观世音、药师佛,还是白鹤大帝、胡公大帝,金身泥塑共享着人间香火。其根源,在于人心的七情六欲与现实的各种落差。在“人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的喟叹中,在“求不得,留不住”的生命注脚里,人们需要一方神位,来安放对命运无常的忧惧,来消解邪祟恶行带来的负罪感,也寄托超越尘世困顿的几多想望。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对无知的恐惧,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渴求,构成了民间信仰最朴素的基石。宁海百姓对城隍爷的虔诚,早已超越简单的敬畏,化作骨血相依的信任与托付,将神庙铸成存放抗争、守护与终极希望的精神圣所。
民间宗教的长盛不衰与教派纷呈,亦是历史权力博弈的投影。统治者深谙此道:或假“天启”谋夺皇权,或将儒释道视为巩固统治的棋子,演绎出“独尊儒术”、“灭道兴佛”、“兴佛灭道”等宗教公案,唐僧西行亦成“官方外交”的美谈之一。地方官员则成为信仰体系的重要环节。明成化十二年,宁海县令郭绅见城隍庙倾颓,心中惊惧,深知怠慢神明即是渎职于民,当即捐俸重修。这源于大明律令:新官上任必先宿庙,翌日与神立誓:“予倘怠政奸贪,神其降殃!”城隍庙,俨然成为儒教礼制与神道设教的契约之所,是统治者借神权约束官僚、安抚民心的重要工具。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上至帝王下至农夫的共同期盼,抬神像“求雨”的仪式千年不绝,正是人力面对“天意”时最直观的祈求。
城隍庙不仅是祈愿之所,也曾是抗争的烽火台。光绪二十九年秋,北乡书生王锡桐率反洋教义军万人冲入庙门,指挥部便设在判官殿。焚毁教堂的火焰映红天际,城隍金身静默不语,殿内香火却炽烈如起义者的信念——他们深信神明默佑着护佑乡土的抗争。更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风暴中。一对老夫妻趁夜色将城隍木像藏进谷仓,神祇在潘姓老太的稻谷间蛰伏三十年。虽无香火供奉,老人心中日日祝祷,视其为阖城安危所系。直至九十年代,文物干部循密报寻回神像,安仁侯方重登神座。这谷仓中的三十年,是信仰在极端年代里顽强存续的缩影,彰显了民间宗教深植于个体生命与集体记忆的惊人韧性。
曾经的农历正月十四,五凤楼藻井下旋出平调“耍牙”的天籁。西门白鹤大帝的神轿穿过人海,城隍与境主这对“亲家”的互访,是全城虔诚的狂欢。戏台梁枋上,北伐演说、抗日呼号的彩绘犹存,革命激流曾在此与古建飞檐共振。戏台西侧,麻糍飘香,油墩翻滚,爆米花的巨响惊飞麻雀。摊主们不忘将第一份吃食供于神前,长辈则低声告诫儿孙:“莫忘本分,城隍爷的算盘可都记着呢。”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涌入,庙宇周遭诞生了宁海首批万元户,鎏金发簪与台球绿绒相映,少年在化妆品摊前做着戏台上演绎的仗剑天涯、人间繁华、爱情成真的各种好梦。即使在新潮喧嚣中,那源自农耕社会的敬畏与道德律令,依然在烟火市井间低回。
今日的城隍庙在霓虹焕彩中得以重生。白墙黑瓦的院落里,苔菜饼咸中带鲜,紫砂壶腾起茶烟,青石板路延伸向“桃源里”新街区。游人依然在城隍金身前驻足,向境主神位投去敬畏一瞥。古戏台下,平调传人再度开嗓。古戏台博物馆内,雕花牛腿、彩绘额枋将与AI技术共舞,讲述田什将军的护城传说。这些故事的核心,正是城隍爷与境主爷在百姓心中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以及民间信仰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暮色镀亮鸱吻,城隍与境主的神影在电子灯笼的光晕中叠合。田什将军的铠甲泛起金属光泽,仿佛仍在无声守护。当年藏神的谷仓木板,静卧于民俗展馆,与隔壁网红奶茶店的纸杯仅一墙之隔。这庙宇的魂魄从未消散,将神明的威严与慈和,化入青石板路上的麻糍香、戏台藻井的檀板响,在市井烟火中续写着人与神、古与今的永恒契约。而那端坐于宁海人心灵殿堂最深处的金身,昭示着民间宗教在时代洪流中不竭的生命力——它根植于最深沉的人心需求,随世态流转而兴衰嬗变,却总能找到存续与重生的土壤。
注①:田什的身份与封号:
田什原籍陕西凤翔,是梁武帝时期的殿前将军,封爵武冈侯。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中,他保护邵陵王萧纶逃至宁海,因忠勇护主,后被封为靖边侯,镇守临海郡,总部设于宁海。梁朝灭亡后,田什拒绝效忠新朝,解甲归田,带领民众开垦荒地、疏浚河道(如桃源河)、开辟街市(如盛家街),奠定了宁海县治的基础。因其对宁海开发的贡献,百姓尊其为地方保护神。吴越国时期(907—978年),田什被追封为“安仁侯”,成为宁海城隍神的正式封号。明代初期,朝廷整顿神号,去除前代封爵,改称“宁海城隍之神”,但民间仍沿用“安仁侯”尊称。
作者简介
叶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