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山的沙葱花红艳艳
暮色漫上窗棂时,马哥的电话打进来:“老冶,明儿下午去南大山采沙葱不?我和王哥、张哥约好了,你可得来。”窗外的银杏叶沙沙响,我望着茶几上那罐去年晒的沙葱干,指腹轻轻摩挲着咸菜罐壁上细密的纹路——那是母亲当年用的,边角还沾着几星暗褐色的老垢痂。
九月的风里已浮起秋意,却仍裹着最后一缕夏的温软。我们四人沿着头顶树枝纠缠、脚边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山里走,王哥提着装衣服的塑料提包走在最前头,包沿还挂着几枝今早采的野菊。张婶攥着手机拍个不停:“你们瞧这花多美呀!”马哥弯腰摘了片野薄荷,揉碎了凑到我鼻端:“香不?我记得你当年说这味儿像民和师范门口卖的茉莉花茶。”
风掠过耳际时,忽然裹挟来一丝熟悉的气息。那是混合着泥土腥甜与草叶清苦的味道,像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捅开了记忆的门——1983年的夏天,我也是这样站在南大山的山梁上,望着脚下翻涌的绿浪。
那时的南大山是座“秃山”。民和师范的操场紧挨着山脚,我们这些住校生总爱往山上跑。清晨的露水压弯狗尾巴草,正午的阳光把芨芨草晒得发白,到了傍晚,整座山便成了调色盘:紫色的马兰花铺成地毯,白色的沙葱花像撒落的星子,粉红的则是野豌豆的花串,在风里摇摇晃晃。我们常说,这山是大地的素描本,画的全是野孩子的涂鸦。
最难忘的是和阿强、秀芳他们结伴登山。我们背着搪瓷缸子装凉白开,兜里揣着母亲烤的馍馍,沿着羊肠小道往上爬。阿强的球鞋总沾着刺玫果的浆汁,秀芳的花布头巾被山风吹得鼓鼓的,像朵移动的山丹丹。等爬到山顶的“瞭望台”,日头刚好斜到山尖,整座民和县城在脚下铺展——土黄色的土坯房挤成一团,炊烟是淡灰色的丝带,偶尔有辆解放牌卡车颠簸着驶过,扬起的尘土能在空气中飘好半天。
“看!”阿强指着远处,“那片白的是学校后墙的石灰,那片绿的是张奶奶家的菜园子。”我们笑作一团,把带的沙葱分成小把,用草茎扎成小捆。下山时路过村口的老柳树,张婶正蹲在树下择菜,看见我们就喊:“又偷采沙葱呢?”秀芳把最嫩的一捆塞给她:“婶子,这是山顶刚开的沙葱花,您拿回去炒鸡蛋。”张婶的皱纹里漾着笑:“你们这些娃娃,把山都掏空喽。”
可那时的山哪里需要“掏”?它太慷慨了。春有沙葱抽薹,夏有野花漫坡,秋有沙蒿结籽,冬有芨芨草在雪地里挺得笔直。我们在山里采蘑菇、挖野蒜、追着野兔跑,连山涧里的冰凌都要敲几根含在嘴里当冰棍。沙葱是最寻常的,却也是最金贵的——母亲把我们采的沙葱用盐水腌在瓦罐里,能吃一整个冬天;邻居家娶媳妇,母亲装两罐沙葱当嫁妆,新娘子抹着眼泪说:“比城里的桂花香多了。”
转折发生在2004年的春天。那天我回民和办事,路过南大山,远远望见山脚下支起了帐篷,成千上万挥动着铁锨的人,铁锨把子在阳光下闪着光。穿蓝制服的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县上要绿化南山,十年后要让荒山变青山!”放羊的老汉蹲在路边抽烟:“荒了一辈子的山,还能绿?”后来我在南大山的山坡上看到了“立下愚公志,绿化南大山”十个白色大字,在阳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芒!真的,第二年春天,山脚下真的冒出了小树苗;第三年,南大山的绿毯有了层次感;第五年,杏树抱团绽放杏花,犹如白云落户山腰,新栽的松树站满了山坡,各个挺拔,酷似人民战士;到了第十年,我站在山顶的“瞭望台”,望着脚下翻涌的绿浪,忽然想起阿强说的“掏空”——原来最珍贵的不是山给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回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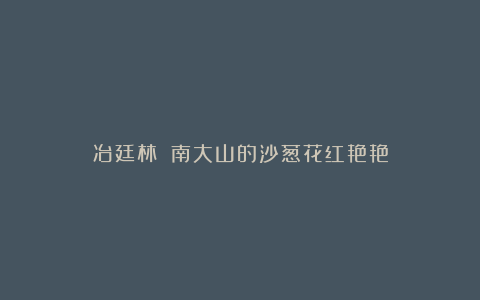
“老冶?发什么呆呢?”王哥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正踮脚采一丛白色沙葱花,指尖沾着细密的绒毛。张哥的袋里已经塞了沙葱,嫩绿的叶子上还凝着晨露。王哥指着不远处的观景台:“走,上去看看,听说能看全县城。”
塔周围的荒草换成了修剪整齐的花灌木。观景台的玻璃围栏擦得锃亮,倒映着蓝天白云。我们扶着栏杆往下看,民和县城像被施了魔法:曾经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了鳞次栉比的楼房,柏油路像黑色的缎带串起各个街区,红色的跑车、白色的SUV、黄色的出租车在路面上织成流动的网。最让我震撼的是城海鸿广场——那里曾是一片晒麦场,如今立着不锈钢雕塑,孩子们在喷泉边追逐,老人们在树底下乘凉,掩不住他们心底里溢出的幸福感。
“你看那栋楼!”马哥指着最高的那栋,“那是我闺女上班的地方,去年她搬进去时还说,从窗户能看见南山。”张哥眯着眼向西指着遥远的拉脊山:“那边是不是当年的野花山?我记得背柴要走十里路,路过葱花湾……”王哥接口:“可不就是那儿!我上个月还去转了转,沟里的沙葱长得比膝盖还高,我采了一大捆,给我老伴儿炒了盘鸡蛋,香得邻居们都来敲门。”
暮色渐浓时,我们坐在和塔下的石凳上整理沙葱。马哥把沙葱分成几把,用稻草扎好:“给老张家带两把,王哥家留一把,剩下的我送学校食堂。”张哥把沾着泥土的沙葱在手里抖了抖:“你们闻闻,这味儿和当年一模一样。”山风送来阵阵花香,我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人呐,就像沙葱,看着不起眼,可根扎得深,总能活出新滋味。”
沙葱的生命力从来都不容小觑。它能在干旱的山梁上扎根,在贫瘠的土壤里抽芽,能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存活,也能在盛夏的骄阳下绽放。就像南大山,曾被风雨剥蚀得千疮百孔,如今却在人类的呵护下重获生机;就像我们,从山脚下走出来,见过城市的繁华,最终又回到这里,带着对土地的敬畏与感恩。
月亮爬上合塔的飞檐时,我们的筐里已经装满了沙葱。山脚下的村庄亮起了灯火,像撒在绿毯上的珍珠。马哥忽然哼起:“南山南山高又高,沙葱开花满山腰……”这是当年我们在山上常唱的民谣,调子有些跑,却比任何时候都动人。
回家的路上,王哥的手机响了,是他孙子发来的视频:“爷爷、爷爷,我在课本上学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不是说咱们南大山呀?”王哥笑着应:“可不就是嘛,你看这山多绿,咱们的日子多甜。”张哥把一把沙葱在王哥镜头前晃来晃去,又抢镜头喊话:“你看,这是太爷小时候采过的沙葱,比糖还甜。”笑声在南大山上蹦蹦跳跳,像豆子一样滚到山下。
夜风掀起我的衣角,我摸了摸兜里的沙葱干。那些被岁月晒干的记忆,此刻正泛着淡淡的清香。原来有些东西从未远去——它们藏在沙葱的叶脉里,刻在南大山的年轮里,融在我们的血脉里,等待着某个黄昏,某阵山风,某次重逢,将所有的故事重新唤醒。
南大山的沙葱密码,原是时间的诗。它写在荒山变青山的奇迹里,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里,写在每一个低头采撷、抬头仰望的瞬间里。当我们捧着新鲜的沙葱走向家门,我们捧着的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对过往的致敬,对当下的珍惜,对未来的期许。
山风还在吹,沙葱的清香还在飘。我知道,明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漫过和塔,南大山的沙葱又会舒展叶片,迎接新的日出。而我们,也会带着这份清香,继续走在生活的路上——脚步或许匆匆,但心始终向着土地,向着记忆,向着那些被沙葱温柔包裹的岁月。
作者:冶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