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区域国别学作为新晋一级学科,致力于从多学科视角系统研究不同国家与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因而更需要跨学科的交融互鉴。地理学因其强调空间视角与人地关系,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支撑力量。从学科发展思想史来看,两者具有共同的渊源。从本体论视角来看,地理学分支学科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空间视角,其中区域地理学描绘空间的特征和原因,地缘政治学则更关注空间的战略意义;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区域的概念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社会历史过程建构,当前仍被广泛使用的许多区域地理概念,往往也是历史上大国利益的产物;从方法论视角来看,现代地理学中发展出来的区域比较、遥感、GIS方法,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理论起源、核心议题和研究方法上存在深度交叉,二者的融合不仅是学科体系整合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我国区域认知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布局的现实路径。
作 者 简 介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
目 录
一、地理学中的区域国别知识发展:一种思想史的视角
二、本体论视角下的学科互动:分支学科的交会
三、认识论视角下的观念影响:区域地理概念的建构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借鉴:空间研究的科学方法
结 语
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之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也表明当前中国对“理解世界、定位自身”的需求日益增加。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进行全面研究的交叉学科,其任务是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蕴含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
然而,作为以区域与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一级交叉学科,除了政治学、世界史、经济学、文学等主干学科外,还需要外部学科资源。在此背景下,地理学因其长期关注空间维度及人地关系,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新的共鸣点和增长点。区域国别研究中涉及的诸多要素都需要以空间为载体,地理学以其对空间结构、人地关系与区域分异规律的深刻洞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不可替代的认知基石。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性规律,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布不均和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异是理解区域国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开展区域国别比较研究的基础。
地理学和区域国别学有着相同的思想渊源和当下学科间的交会。地理学通过理论支撑、历史认知和方法工具,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全方位的学术支持与思维启发。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以跨学科视野介入,将地理学的空间逻辑与政治学的权力分析方法深度融合,从而更好地理解、解释和预测政治事件,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因此,二者的交融互鉴既是学科范式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地缘格局剧变的实践选择。本文试图从二者的思想渊源出发,通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讨论区域国别学和地理学的互鉴交融之处及其对当前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意义。
一、地理学中的区域国别知识发展:一种思想史的视角
地理学中的区域国别知识发展,本质上是一部人类试图通过空间秩序理解区域与国别发展和不同区域国别之间文明差异的思想史。从古代对山川疆域的感知,到近现代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系统描绘,人类始终在用“空间”组织对世界的认知。这种以空间为核心的理解方式构成了区域国别学的思想基础。
(一)古代地理思想中的区域国别理念
在古代世界,不同文明中的思想家普遍将空间视为理解世界的重要维度,尽管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出现,但古代地理学的思想中已展现出区域国别研究的理念雏形。早期对于地理信息的记录往往是以史料的形式存在,许多关于地理、民俗、资源与政治组织的信息往往由史官加以搜集和整理,或者以个人的游记见闻等形式被记录,因而体现出历史地理不分的特征。
在古代中国,区域国别和地理学思想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描绘中原内部人文与自然地理信息以及记录中原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尚书》将天下分为“九州”和“五服”,前者翔实地记录了各州的交通、物产等地理信息,后者则是“以五百里为一服”,描述从中心向外部延伸的信息。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历代的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绘了各地的民风物产,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则分析了游牧民族的生计方法和军事组织。班固在《汉书》的《地理志》中以行政区划分单位,记录全国各地的疆域、户口、山川、物产等信息;在《西域传》《匈奴传》等传记中则记录这些区域的风土人情。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水系为纲,通过自然地理脉络理解人文活动,详尽记录了沿岸的山川物产与风土人情,展现出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大唐西域记》则是中国古代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代表作,玄奘通过实地考察,对西域上百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交通物产、生活方式、宗教民俗等进行了系统记录,成为后世这些区域古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文献。
在古希腊,最初的区域和地理概念以一种模糊和半神话的形式出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开启了区域描述的传统,借助战争史的视角阐述了古代地中海周围亚非拉区域诸国的地理、民俗、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斯特拉博(Strabo)的《地理学》是早期优秀的区域地理著作,提供了古希腊罗马世界中各国的自然资源、经济活动、水陆通道等区域国别知识。随着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地理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交织愈发明显的标志是制图术的出现。到公元2世纪,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开始依据更多的数学方法,试图以经纬度和投影法来绘制世界地图。制图术不仅使得区域国别之间的边界概念更为直观和明晰,也为此后的大航海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二)近代早期地理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
近代欧洲地理学与区域认知的发展,最初源于对欧洲之外世界的兴趣与探索。在中世纪末期,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游记中记录了从威尼斯出发,途经西亚和中亚,最终抵达中国的旅行经历,并详细考察了这些地区及中国周边国家的风俗、地理和人情,这些带有部分夸张色彩的“东方见闻”激发了欧洲内部对“东方世界”的想象与探求。文艺复兴后,欧洲开始逐渐摆脱教会的束缚,人文精神觉醒的同时也推动了空间认知革命,开始以一种“地球”视角来看待地理与区域研究,并逐渐同历史学分离。与此同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遗产开始复兴,如托勒密的《地理学导言》被重新“发现”,成为地球知识的源泉。
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在促进文明交流的同时也迫使欧洲加强对其他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研究,从而为其海外扩张提供信息和依据。随着殖民扩张的深入,欧洲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了大量关于欧洲之外广大区域与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人口种族等方面的一手信息。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sales de Mendoza)通过搜集大量资料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成为16世纪关于中国的“区域研究”经典。
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后,思想家们不仅研究不同区域的地理,还试图对这些差异进行科学解释。伏尔泰(Voltaire)在《风俗论》中试图将西方之外的地区纳入相对平等的叙事中,对古代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区域的社会风俗、文化特点和历史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中介绍了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法律制度差异,并详尽阐述了环境对国民性、法律和国家的塑造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地理决定论的观点。
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的兴起标志着现代地理科学的诞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跨大陆考察的基础上,推动了过去作为经验描述的地理学的科学化。在《宇宙》的第一卷中,洪堡将自然视作“生动的整体”,认为只有当不同地区搜集到的大量事实被纵观全局的目光所统领,被纵横联合的理性所整合时,比较地理学才能获得全面性和缜密性。李特尔(Karl Ritter)相信各大洲具有相似的结构,在《地球学》中发展了以大洲为地理单元的区域概念和新的区域描述法,在每个区域先说明地形主要特征和水系,接着是气候、物产和人口。这些思想也为此后区域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
(三)近代晚期地理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
19世纪末以来,地理学逐步确立其学科地位,尤其是大学中地理学系的建立推动了地理学的专业化。与此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仍隶属于政策研究机构或依附于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尽管两者的研究路径逐渐分化,但地理学分支学科的细化与理论深化依然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知识基础。
首先是人文地理学实现了同自然地理学的分野,强调环境对于区域内人类社会的影响。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相对于历史学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事件,因此,他的《自然地理学》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涵盖不同研究对象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要素的总纲,包括数学地理学、道德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神学地理学等诸多内容。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继承和发扬了洪堡和李特尔等学者关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学说,其两卷本《人类地理学》(1882年和1891年)可以视为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而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则代表了人文地理的一种特殊发展,他将地理学应用于研究具体的人类过程影响,并将国家视为地理学最高的研究对象。埃伦·森普尔(Ellen Semple)继承了拉采尔等人的环境决定论思想,试图通过广泛的比较来研究地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其次是区域地理学成为弥合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桥梁。法国的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德·拉·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认为,地理环境提供或然论而非决定论的概念,他认为需要进行小范围的区域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到人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上,他强调自然对人类居住限定了条件并提供了可能,但人们对于这些调整的反应和挑战仍依赖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将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生态学,推动了区域研究中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主张区域研究应聚焦人类对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并将其转化为“文化景观”。洪堡和李特尔之后的德国地理学家则强调对区域差异的比较和解释,如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认为,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区域内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阿尔弗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则采用实证论,强调空间差异的区域独特性。
再次是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实现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空间权力分析。拉采尔创建了政治地理学,提出将国家看成是一个由人民和土地构成的有机体,并提出了此后有较大争议的“生存空间”概念。区域的政治地理学旨在解释政治过程的空间成因和作用。 1899年,瑞典学者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提出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概念,而真正将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用于区域研究和战略分析的则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他提出了著名的“陆权说”,将东欧和中亚这些欧亚内陆区域视作“心脏地带”,认为控制心脏地带是控制“世界岛”的关键。
由此可见,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融最初源于人类对世界的共同认知方式与思想渊源。近代以来,随着学科体系的逐步分化,两者的界限日益清晰。然而,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理解世界与构建空间秩序的方式上始终存在深层的共生逻辑。二者共同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空间”理解差异,并以此解释权力格局与发展路径。相较而言,区域国别学侧重以政治、文化与制度为分析框架,而地理学则以空间过程与结构为主要路径,二者相互借鉴又彼此支撑。在当下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基于二者对于空间问题的共同思考,重启两个学科间的思想对话,不仅是跨学科整合的应有之义,更是应对当前挑战和机遇的现实需要。
二、本体论视角下的学科互动:分支学科的交会
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交融互鉴,并不仅仅停留于历史上共同的思想渊源,而更体现为一种本体论视角上的一致性。两者在本体论层面的深入对接,源于对空间的高度关注与深刻理解:空间不仅仅作为客观的物理实体存在,更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制度实践与文化表达持续互动、相互塑造的产物。这种理解促使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在探讨空间的内涵与意义时,能够超越表面现象,更深刻地揭示空间差异背后的本质机制与社会文化意义。
地理学在中国学科分类中具有明显的文理结合特征,这种特征体现为学科归属在不同教育阶段的转变:中学阶段的地理学与历史、政治共同属于典型的“文科”,而进入大学阶段则明确地归为理学学位。这一独特定位使得地理学在与区域国别研究展开对话时能够提供双重视角。一方面,作为理科的地理学更强调地球科学或空间科学的传统,研究地表或空间的特征。而区域国别研究则属于典型的社会科学,将地理视作无法被完全还原的“外生结果”,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或“场域”而存在。在经典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地理作为“场域”提供了空间差异比较的情境和案例选择的依据,通过将地理因素作为情境变量加以控制,研究者可以有效减少其他变量的干扰,提高研究结论的因果解释能力。另一方面,从人文学科角度出发的地理学则高度重视人地关系的互动过程。这一传统与区域国别研究在研究视角上有深度契合之处,即强调对具体区域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区域国别研究非常注重研究对象的“在地性”(locality),即强调区域内部的社会结构、文化逻辑与环境互动的具体性与独特性,而非抽象地概括或普遍化理论。这在许多经典的区域研究作品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例如,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通过细致的文化与人类学式调查,深入揭示了日本社会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心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则是通过具体的东南亚乡村社区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了弱势群体如何进行日常抵抗。
细化到具体的分支学科,区域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为本体论层面的融合提供了关键的交会点,即强调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威廉·帕蒂森(William Pattison)总结了地理学的四种传统,分别是空间传统、区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和地球科学传统,这四种传统逻辑上独立,但可以共同发挥作用。本文将从这四种传统出发,分别探讨作为分支学科的区域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借鉴意义。
(一)区域地理学对区域国别学的借鉴
区域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核心分支之一,主要研究地表区域的形成、结构、特征和演化过程,侧重于讨论区域空间差异的本质,强调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区域综合。这种综合视角正是区域国别学理解国家内部复杂结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尤其是在进行空间上的国家—地方关系、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研究时,二者的分析单元与理论假设高度契合。现代区域地理学通过整合上述四大传统,不仅深化了对特定区域的系统性认知,也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政策分析、战略制定与文化理解提供了重要支撑。
首先,区域地理学中的空间传统专注于区域内特定资源的空间分布。空间传统赋予区域地理学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通过详细的地理数据和空间分析,描绘出各个区域的自然环境、资源分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空间差异,有助于为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在自然地理领域,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等人通过模型分析评估了全球变暖对美国农业的具体影响,量化分析了其对美国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产生的不同影响,认为提高农业技术、改善水资源管理和优化农作物种植布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人文地理领域,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关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经典讨论中提出一种空间集聚机制:制造业集聚受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市场需求的双向影响,并且当某些条件达到临界点时,集聚效应会被放大,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区域地理视角下,国家也是一种空间现象,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提出了一种功能主义的政治地理学说,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空间整合,即通过特定的理念或目的将区域整合为一个政治单位。
其次,区域研究传统以跨学科的方法为特征,整合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以理解不同尺度上的区域发展。区域地理研究涉及一些经典议题,包括国家边界的划分、不同“位置”塑造了不同的整体和局部政治生活、不同民族、语言或宗教的地域基础以及冲突来源等等。通过空间分析,区域地理学能够揭示国家与地区在地理上的独特性,识别并解释产生差异的原因。例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比较了温带和热带的区域发展差异,认为在热带地区由害虫引起的疾病会更加泛滥,而过量的降水会冲走土壤的营养成分,让种植更加不易。
再次,人地关系传统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如何改变自然环境。区域地理学通过这一传统,分析了自然环境对区域内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并揭示了人类如何根据地理条件进行适应与调整。人地关系传统为区域国别研究更好地理解区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例如索尔研究了西班牙殖民早期对加勒比地区和墨西哥的地理与文化影响,分析了殖民者如何塑造新大陆的文化景观。在区域发展理论中,“资源诅咒”也是人地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区域内部过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有利于发展,也可能会阻碍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部门的发展,忽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容易产生寻租型制度等。
最后,地球科学传统着重对自然环境的科学分析,特别是气候、地质、地形和资源等方面。区域地理学利用地球科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区域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政策依据,包括水资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诸多全球治理问题都需要借助地球科学知识。例如瑞典水文学家马林·法尔肯马克(Malin Falkenmark)等人提出了区分“蓝水”(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和“绿水”(土壤中的水分)的新范式,重新定义了水资源管理的框架,认为提高绿水利用效率是未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从而为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粮食的短缺问题提供新思路。另一个案例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3年发布的气候变化综合报告,向决策者提供了最新的科学评估,全面解析了全球变暖的确定性、极端气候事件的加剧、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以及海平面持续上升等关键问题及未来趋势,并提出适应策略与政策建议,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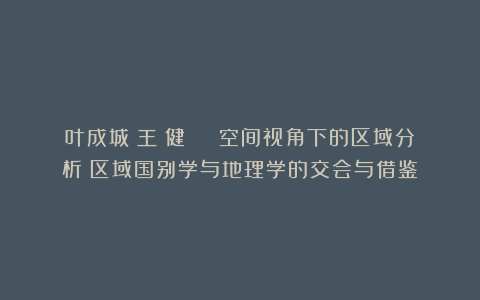
(二)地缘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会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区之神,“polis”是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地缘政治的概念涉及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它们所构成的物质世界以及人类整体之间关系。地缘政治学揭示了地理位置、资源分布与战略控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空间—权力的耦合机制是区域国别学分析国家对外战略、地区安全格局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学近年来的发展已超出了传统军事战略范畴,逐渐纳入技术空间、舆论空间与数字基础设施等“非传统空间”,这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理解21世纪国家竞争新场域的理论武器。地缘政治学同区域国别学的诸多天然交会之处同样展现在如下四个地理学的传统之中。
首先,地缘政治学考察国家与自身环境(空间)之间的关系,试图解决由空间关系导致的问题,相比政治地理学只关注国家空间状况,地缘政治学更关注国家的空间要求。地缘政治学中的空间传统主要体现在区域的战略研究中,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基于地图学的战略分析。从麦金德开始到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其战略分析都是基于地图上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展开,他们主要的差异仍然是对于“世界岛”中心和边缘区域的偏好。麦金德基于铁路的便利性,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东欧和中亚地区来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全世界;斯皮克曼则基于人口、气候、农作物等经济生产理由,认为控制欧洲滨海地带和亚洲季风区更加重要。
其次,区域研究传统侧重于强调各地域的地缘政治差异,试图总结这些区域的地缘特征并进行跨区域的地缘政治比较。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秉承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传统,将欧亚大陆看作最重要的“大棋局”,根据不同地区的功能和战略地位差异,总结出其中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印度)和一些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认为美国应当防止任何潜在对手的出现。索尔·科恩(Saul Betnard Cohen)则基于区域内的联系,尤其是依据整合化程度将世界政治区域运作进行分类和比较,列出了5个主要阶段,分别是专业化整合(滨海欧洲地区和马格里布)、专业化(北美、中美洲和亚太沿岸地区)、差异化(心脏地带俄罗斯、东亚、中东、南美和南亚)、无差异(外高加索—中亚、印度支那)、原子化(撒哈拉以南非洲)。
再次,地缘政治学中的人地关系传统则不局限于自然禀赋,而是尝试纳入更多的人文地理要素。在地缘政治学中,最初对人地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传统源于马汉,他认为滨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在于海权,海权的发展不仅仅源于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这些自然要素,同时还取决于另外三个人文要素,即能够充当水手和生产海军物资的人数,具有从事商业习惯和热衷于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民族特点,以及按照人民的偏好办事和坚决维护海权发展的政府和制度。此外,地缘政治理论中也存在一种类似的文化景观理论,即基于地缘文化的分析。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国际体系描绘为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更知名的理论当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他根据文明/文化的差异,将全球划分为八大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他认为文化的割裂会造成分属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冲突,造成文明的“断层线战争”。
最后,地缘政治中的地球科学传统偏重从自然地理禀赋及其变迁过程来看待具体资源的地缘分布对于国家战略的影响。由于技术的日新月异,不同自然禀赋的相对价值不断发生变化,这就需要结合该传统不断更新对于资源禀赋的认知。一个案例是空中力量(空权)的出现削弱了传统水陆枢纽和屏障作用,从而让地缘政治研究拓展到地表之上的空间,思考空战对于大国战略的影响。另一个案例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推广对传统能源地缘政治造成了冲击,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量化指标来测算,当前传统能源国家成为能源革命的“输家”,而积极发展新能源技术和拥有关键稀缺材料的国家则成为“赢家”。除此之外,太空(以及星际空间)、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等发展也同样会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因而也需要基于地球科学的传统进行研判。
总体而言,两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本体论上实现真正交会,关键在于它们共同从上述四个空间分析传统出发讨论空间的非中性特征,认为空间是国家行为者通过制度安排、技术变革与话语建构而不断塑造的场域。国家通过边界划定、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区划调整等方式,在空间中嵌入秩序和权力关系,这种空间分析传统正是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共享的本体逻辑核心。
三、认识论视角下的观念影响:区域地理概念的建构
在认识论层面,空间不仅是客观的对象,还是一种观念建构的结果。因此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的另一重要交会点在于区域概念的建构过程。区域并非单纯的地理实体,而是植根于领土空间的社会共同体,其成员共享特定的自然资源,并通过文化价值观与历史塑造的社会秩序纽带凝聚在一起。区域的特殊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社会建构形成:一方面,国家拥有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资源,有助于在现有边界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区域建设;另一方面,无数复杂的网络、关系和不同地方之间的流动构成了开放的和不一致的边界的功能区域。批判理论认为,全球政治地理格局既非必然,也非静态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文化与政治互动的持续建构。因此,区域不应被简单视为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而是一个在话语、制度、战略意图与认知网络中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性概念。从古代到现代诸多著名的区域概念和地理观念变迁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认识论层面的变化。古代社会的地理认知通常局限于特定区域,对于区域之外的世界则充满未知与想象。因此,早期文明在构建区域地理概念时,往往带有一定的自我中心主义,反映出对自身世界的认同和对外部空间的模糊理解。
在古代中国的地理观念中,最初将中原地区视作世界的中心,并将其他方向的民族称为“四夷”:“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在这种叙事体系中,王城方圆一千里为“王畿”,从内到外每五百里分为“九服”,分别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到汉代时,班固提出了“西域”这一概念,指代中亚部分地区以及更远的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古代欧洲也同样如此,地中海的说法源自拉丁文Mediterraneus,可以解释为“被陆地包围的海”,这一名称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地理观念。古罗马人则更直截了当地将地中海视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逐渐将罗马所处的空间视为围绕地中海分布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ecumene)
的中心。因为宗教的缘故,公元7世纪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以盘形展现,将圣城耶路撒冷置于中央,这种地图被称为“T及O地图”,其中“O”指亚、欧、非三洲形成的圆形陆地,“T”的垂直线相当于地中海,水平线则是将亚洲与欧、非两洲隔开的一些水陆。
到了近代以后,地理大发现彻底颠覆了古代社会的区域认知体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认知体系逐步形成。这些地理概念不仅构筑了殖民时代的世界认知体系,也成为欧洲主导下全球权力格局重塑的重要工具,深刻影响了现代国际政治秩序的空间划分。从西班牙到英国,它们建立的全球殖民网络都自称为“日不落帝国”,即无论何时何地,帝国的疆土上总有阳光照耀,这不仅是一种地理认知,也反映了一种全球的统治视角。在欧洲列强向东方探索和征服的过程中,它们按照离自己距离的远近,分别把东方不同的地区称为“远东”“中东”“近东”,此后这三个概念就通用于国际社会。
除此之外,对当地影响深远的几个地理概念的建构也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早期的殖民逻辑。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该条约以南北极间距离佛得角370里格的线,将世界分别划属葡萄牙和西班牙各自一边的势力范围。欧洲人对非洲的区域划分服务于殖民统治,他们通过语言和种族的划分,创造了关于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的殖民叙事,并构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概念,将其与北非和中东区分开来。这一界定不仅蕴含欧洲人的文化划分逻辑,也突出了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经济落后的悖论,从而合理化欧洲的经济掠夺与政治干涉。与此类似,拉丁美洲的概念同样源于殖民历史。在19世纪,法国为了在美洲扩展影响力,将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国家定义为“拉丁美洲”,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理和文化实体,将其同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相对立,同时也掩盖了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群体的存在和贡献。到19世纪和20世纪,伴随着为欧洲寻找市场、资源和殖民地的扩张活动,欧洲的“东方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并几乎等同于“区域研究”,东方学也完成了从学术话语到帝国主义机制的转化。
进入现代以后,区域建构还依赖观念与权力之外的一系列制度手段的实现,如各类国际组织涉及的对地区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建构机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表述”自身区域,也影响外界对该区域的知识结构与政策判断,因而这些区域概念的构建又同“美国治下的霸权”密切相关。美国作为全球性的霸权,不同于传统大国以自身领土设立战区,美国战后陆续形成的六大司令部是以世界地图来划分的,分别为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尤其是随着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规则化,美国推动和构建的地理概念不仅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还往往伴随相应的区域性组织的建立,以强化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北美殖民地独立后,美国在19世纪构建了独特的地理观念,并以“天定命运”理论支撑其领土扩张,构建了美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1823年,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认为任何试图在美洲建立新殖民地的欧洲国家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强调美国对西半球的领土扩张和主导权。 19世纪末,美国提出“泛美主义”,强调美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推动美洲国家组织等地区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半球的主导权。
冷战期间,美苏围绕全球势力范围展开竞争,区域地理概念的构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富尔顿演说中提出了“铁幕”的概念(Iron Curtain),形象地描述了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对立,此后也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区域军事同盟。为遏制苏联,美国在欧洲推动欧共体(EEC)和马歇尔计划,而在亚洲则塑造了“东南亚”这一区域概念,以取代过去的“远东”称谓。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在其国家部门中用“东南亚事务部”取代“西南太平洋事务部”,此后在1954年马尼拉会议中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于1955年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七国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试图在亚洲打造军事同盟体系。此外,第三世界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概念,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批判和反思。左翼学者基于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提出“中心—外围”的区域概念,认为美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贸易、产业链和技术体系,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调整全球战略以适应其全球霸权体系,并推动新的区域概念的构建。“亚太”(Asia-Pacific)概念的兴起正是冷战后美国战略调整的结果,克林顿政府推动了“亚太”概念的制度化,促成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立,以此来强化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进入21世纪后,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强化在东亚的存在。201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强调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区域整合。日本所提出的“印太”(Indo-Pacific)概念进一步被美国接受,美国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使用“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意在将印度、东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纳入统一的战略框架,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总体来看,区域国别学在认识论层面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划分区域,区域划分服务于何种政治目的。这涉及地理空间、观念认知与权力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区域国别概念的划分并非纯粹基于地理位置,而是基于安全战略、资源配置和话语权建构的需要。人们通过制图术、地区划分等手段建构区域认知,但这种划分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化或权力烙印。这种空间的社会建构既反映了话语权对地理的重塑,也揭示了区域国别学研究中必须处理的“主观划分”与“客观空间”之间的张力。因此,区域国别学应吸收批判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中的空间建构理论,超越将“区域”作为固定对象的理解,揭示区域建构背后的话语逻辑与权力机制。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借鉴:空间研究的科学方法
尽管随着地理学的日益科学化,使其同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分野日益增加,但这种差异化的发展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新视角和再借鉴的意义。地理学方法在更好地理解区域和国家的空间联系性和异质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而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加直观和深刻的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区域国别学问题与地理方法的适配度还会因议题而存在差异: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外交政策更多受制于制度与领导人偏好,难以直接与地理学融合,但地缘政治、资源开发、族群冲突、经济发展等问题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属性。因此,学科交融互鉴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方法选择的针对性与问题导向性。由于地理学本身是一门方法众多的交叉学科,以下仅挑选具有地理学特征且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借鉴意义的部分研究方法进行讨论。
(一)区域比较分析
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解释区域或空间的差异性,因此比较分析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而地理学中的比较分析可以给区域国别研究带来的借鉴意义则是空间分布差异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李特尔在《比较地理学》的前言中提出,需要将地理同时间联系起来,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地理学,对科学形成过程所掌握的实证越少,我们的错误就越明显。理查德·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中系统阐述了区域地理学的方法论,他反对只看重相似点而不顾区位的简单比较,主张建立以文化要素复合体为基础的一般区域比较系统。阿里尔·阿赫拉姆(Ariel Ahram)认为,区域比较分析传统上依赖定性方法,而未来则需要鼓励使用区域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更好地理解区域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一比较传统对于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的启发,因为二者在研究对象上高度重合。通过对不同区域、国家或次国家单位的系统比较,研究者可以深入理解其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当下的制度特征,也揭示了历史制度沿革与地理空间之间的深层关联,从而为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性研究。具体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案例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使用定性方法,以地理轴线解释了人类社会初期各大洲之间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认为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相较于南北走向的美洲和非洲大陆更有利于农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更精细的社会结构。上述理论对于区域研究的启示在于,它揭示了欧洲大陆以外许多地区国家建构不完全的地理根源,为国家对外合作与投资提供了重要的风险识别视角,同时也为国际治理模式的差异化演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遥感(Remote Sensing)
遥感是一门通过未直接接触被研究区域的设备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科学。遥感技术通过非接触性、大范围、实时、高精度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资源管理和灾害预警等领域,能够有效感应地表的人类活动。遥感涉及两个基本过程:第一个是数据采集,包括使用机载或卫星传感器等设备记录地表特征反射和辐射电磁能量的变化,从而采集区域内各种资源的类型、范围、位置和状态的信息;第二个是数据分析,包括使用各种查看和解释设备来分析图像数据使用计算机分析数字传感器数据。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遥感技术的意义在于能够跨越传统田野调查的时空限制,突破传统统计数据时效性差、获取难度大、空间尺度有限等瓶颈,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动态、客观且有空间连续性的实证数据。具体而言,遥感技术可以通过卫星图像和飞行器的空中摄影等手段获取大范围、高精度的空间数据,帮助分析环境变化、资源分布等重要因素,为政策制定和区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一项著名的研究是劳伦斯·史密斯(Laurence Smith)等人利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1997—2004年的卫星遥感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西伯利亚地区的湖泊面积的变化,发现气候变暖导致的冻土融化没有促进湖泊面积的扩大,反而导致湖泊数量的显著减少和面积的收缩,因为冻土融化增加了湖泊底部的渗透性,从而造成了湖水的流失。在具体政策研究中,遥感技术也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王燕等人通过遥感技术在测量中国对非援助时发现,中国基础设施项目在当地和邻近地区产生显著的正溢出效应:在一个二级行政区中,如果至少存在一个中国基础设施项目,会使该地区的夜间灯光亮度直接增加约5%,夜间灯光亮度间接增加约10%—15%。此外,遥感技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同样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包括油气开采的时空信息挖掘、社会经济参数的估算、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估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重建等。
(三)地理信息系统(GIS)
GIS通过对空间数据的管理、分析和可视化,能够帮助研究者直观地展示区域与国家的空间关系。1854年伦敦霍乱疫情中的“幽灵地图”可以视为GIS的渊源。约翰·斯诺(John Snow)利用可视化分析方法,通过绘制霍乱病例地图,揭示了疾病传播的空间模式。现代GIS则更多借助于计算机软件分析地理信息,有多种分析软件,例如ArcGIS、GeoDa和QGIS等,其中ArcGIS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GIS软件套件之一,包含了ArcMap(用于地图制作和分析)和ArcCatalog(用于数据管理)等组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GIS在方法论层面催生了新的研究路径,其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使其成为理解和研究地理现象、区域发展、冲突研究和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涵盖了资源管理、经济发展、族群冲突、地缘政治分析、灾害管理等诸多议题。通过对空间变量的量化、建模和动态分析,GIS方法有效地弥合了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中宏观地缘结构与微观社会过程之间的知识断裂。例如有研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比分析了非洲地图上未被国家边境线分割与被分割的民族群体,发现被国家边境线分割的民族群体不仅在政治暴力的强度和发生概率上显著高于未被分割的群体,还更易陷入由政府主导的歧视和民族战争的恶性循环,并且在经济上也处于劣势,从而揭示了非洲殖民时期的边界划分对当代非洲政治暴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例子是有学者研究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外的渗透和贸易之间的联系。作者基于解密文件用GIS绘制了CIA全球范围内对他国的干预程度图,并发现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往往被用来为美国那些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开辟更广阔的外国市场。
(四)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是一种用于衡量地理现象是否呈现空间聚集或离散模式的统计方法。沃尔多·托布勒(Waldo Tobler)在研究底特律地区城市增长的动态过程时,提出了著名的“第一地理定律”,即“所有事物都相互关联,但近处的事物比远处的更具关联性”。这一规律不仅为地理学奠定了空间分析的基础,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一方法分析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或社会现象如何与周边区域或国家的现象相互联系,有效识别国家间、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回归分析的方法较多并且日益成熟,包括地理加权回归、空间误差模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最为基础的模型则是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卢卡·安瑟林(Luc Anselin)在其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著作中提出了空间自回归模型,介绍了如何通过空间统计方法研究地区间的互动关系。当确信每个样本的“y值”受到其“周围值”的直接影响时,就可以使用空间回归模型,该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将包含“空间滞后”因变量的y作为协变量加入回归方程的右边。空间计量方法的引入,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实证层面的拓展,不仅使研究者能够更科学地识别区域内行为体间互动的空间逻辑,也为理解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制度扩散、政策外溢、社会稳定性等核心议题提供了方法支持。例如有学者通过空间回归,分析了从1816年到1998年间邻国的民主化对国家制度转型的影响,发现邻国的民主化程度显著提高了本国民主转型的概率,从而表明民主化进程在地理上具有扩散效应。
(五)系统分析方法
地理学中系统思想的历史紧密地与功能方法、有机类比、作为复杂相互联系整体的区域概念以及地理学的生态方法相联系,在李特尔、维达尔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系统思想的因素。在区域内部,人文和自然的过程是交织的,因而考虑区域问题的原因时,时常需要一种综合性、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方法。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系统效应”,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同人类社会政治系统的复杂性进行对比,强调了复杂系统中“不能只做一件事”:例如森林的枯木成为以害虫为食的鸟类的住所,移走枯木导致虫害增加;国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单纯的双边关系,双方的互动会导致其与第三国的关系变化。系统分析方法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促使研究者跳出线性因果推理的范式,从而关注制度、生态、经济、文化等多种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与反馈机制,理解这些变量在不同层级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度嵌入本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生态、能源等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牵动区域治理能力、大国战略布局及全球权力结构的复合性议题。系统思维有助于识别“混沌系统”中潜在的结构性与跨层级的联动效应,为把握区域系统的复杂性提供理论支撑与分析框架。从亚历山大·墨菲(Alexander Murphy)对乍得湖萎缩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系统思维对于区域研究的重要性。20世纪70—80年代乍得湖萎缩的分析不仅要记录湖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变化特征,还需要看到一系列连锁反应:湖泊萎缩→采采蝇繁殖→牛群疾疫→养牛为生的岛民被迫迁徙→破坏了迁居地的生态与民族平衡。墨菲认为,在分析现象的原因时不能囿于流域内的因素,要认识这种变化的外部原因:殖民秩序催生的政治格局导致流域被分割为互相竞争的个体,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当地水资源密集型商品农业的扩张,同时法国和美国腐败地方当局的支持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环境。
结 语
地理学和区域国别学有着相同的思想渊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加以阐释。在本体论层面,地理学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分析区域特征的空间场域与在地性视角,区域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等分支领域尤其在描绘空间特征及解释空间意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认识论层面,当前区域的界定不仅是自然或单纯地理条件的结果,更是历史上政治主体互动与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方法论层面,现代地理学中的诸多现代地球科学方法,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因果解释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技术支持。
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的融合并非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在理论结构、认知方式与分析工具层面的深度交会。具体而言,未来实现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的交融互鉴,应在以下四个方面推进。第一,要强调学科融合的问题导向,以区域重大现实议题为牵引,如地缘政治、能源和关键矿产分布、族群冲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在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选择合适的地理学理论与工具开展分析,提升研究对国家战略的回应能力。第二,要着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构建跨学科能力体系。区域国别学的课程体系需要系统引入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遥感技术与空间计量方法,培养具备空间思维与技术能力的研究者。第三,鼓励区域研究机构与地理学研究中心共建数据库与模型库,实现学科资源共享和推动联合研究平台建设。第四,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借助AI在遥感图像识别、地理信息自动标注、政策文本挖掘和因果关系建模等方面的强大能力,实现对区域国别现象的高维建模与动态预测,为复杂决策提供智能化支持。
总之,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应系统吸纳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与方法论,突破经验叙述的局限,构建跨学科的解释体系。只有在理论融合、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机制协同等层面联动推进,区域国别学与地理学的学科互鉴才能释放其战略潜力,为国家全球战略布局提供学术支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区域认知基础,为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往 期 推 荐
周建勇 | 政党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战略选择与比较优势
许罗兰 韩 潮 | 全景机制的路径差异:以福柯对边沁公开性思想的误读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