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的记忆里,那些推车挑担、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比如卖盐倒醋的小推车子、戗剪子磨菜刀的长板凳子、一头凉一头热的剃头挑子、卖豆腐的大木架子、香气扑鼻的换油篓子……拨浪鼓声、木梆子声、小铜锣声夹杂着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像一幅交响乐。当然,童年记忆里的这些商贩,留下的印象有深有浅,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的货郎们了。
货郎担在我的老家被称作“货郎挑子”。作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按照过去江湖行规,货郎担归为“八根系”行。所谓“八根系”,是指货郎担两头的货箱子,各用4根绳系住一角,顶端挽一扣,挂在扁担两头,前后共八根。货郎挑着担子走四乡、串八村卖货,俗称“行商”又称为“盘乡”,意为走到哪儿卖到哪儿。
据史书记载,货郎这种活跃在大江南北,靠走州过县卖日用杂货的商贩,宋代时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即有两架货郎担子。元朝《桃花女》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我待绣几朵花儿,可没针使,急切里等不得货郎担儿来买”。”鼗鼓街头摇丁东,无须竭力叫卖声。莫道双肩难负重,乾坤尽在一担中”。南宋李嵩的《货郎图》的这四句诗则详细再现了古时货郎担的形象。
货郎挑子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但对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来说,却是比较熟悉的。那时候,乡村商贸尚不发达,村里没有代销店,村子离乡镇集市又远,交通也很不方便,农村人很少进城。对乡亲们来说,货郎担就是个流动的小型杂货店。
之所以叫货郎担,是因为货郎只有一个人,他头戴一顶旧草帽,雨天挡雨,晴天遮阳。春夏秋冬,常年游走在乡村之间。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箩筐里放着货物,箩筐上面是两个木头制成的长方形木匣子,木匣子被木条分隔成许多小格,格子里放着小件的商品,匣子上面盖着玻璃,透着玻璃就可以看到喜欢的商品。比如妇女做针线活的用的针头线脑、箍轮子、扣子;擦脸抹手的雪花膏;姑娘喜欢的卡子、头绳和圆镜子;老太太头上用的木梳、篦子、包网子、簪子和孩子喜欢的气茄子、哗啦棒槌、皮老鼠,砸炮、米花团子,农村人常用的松紧带、茶瓶塞子、皮鞭稍子等物品。虽然都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小百货,但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货郎还有一样重要的行头,那就是拨浪鼓。这是他们走街串巷招揽生意的响器。拨浪鼓呈圆筒形,碗口大小,两面牛皮,下面安一木柄手把。鼓旁两侧,各钉了一条细绳子,绳子两头挽两个疙瘩。下面的手把一摇,两边绳子上的小疙瘩就打在鼓面上,发出“嘣嘣”的响声。这货郎鼓虽然不大,但是货郎们能把它摇得很响、摇得很好听,就像打击乐似的。浪鼓一摇,“嘣嘣,嘣嘣,扑棱咚咚”的声音能够传出老远。村里人一听,就知道是货郎挑子来了。
货郎一进村,一手扶着肩上的扁担,颤颤悠悠,一手将拨浪鼓举过头顶,有节奏地摇动,“蹦蹦,蹦蹦!”,边走边摇边吆喝:“烂胶鞋、烂凉鞋、小孩穿的烂球鞋;破铺衬、烂套子,老头戴的破帽子;铁也换、铜也换,就是不要石头蛋,都拿来换东西喽… …”声音拖得很长,传得很远。不吆喝不行走,这是货郎的特点,不吆喝就做不成生意;吆喝过了,还得放慢脚步,或者停一停,等人家从家中走出来。
那时的农村比较贫穷,几乎就没有什么钱,主妇们兜里有个块儿八毛的,也会捏在手心里攥出汗来,舍不得花,想着把它用在刀刃上,买煤油、火柴、盐等生活必需品。这些必需品虽然也能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里买到,但是供销社的商品只能用现金交易而且不能讲价,而在货郎这里,获得你需要的东西不仅可以用钱买还可以用家里的农产品、家禽蛋、甚至是破烂交换。
在生活窘迫的日子里,穷怕了的人们格外的惜物,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女人们甚至就连梳头掉下的头发也舍不得扔掉,握一握,搓一搓,一次一次的缠在一起,塞到墙窟窿里攒着。那些生活中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废铜烂铁、牙膏皮、旧棉絮、烂鞋帮子、烂鞋底,破塑料盆等都可以在货郎担这里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大的东西换不了,也就是换点针头线脑,缝衣服的针,女人头上的发卡,做衣服的纽扣。这种送货上门,可以讨价还价、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深受乡亲们喜爱。既可以换到急需的物品,又可以把家里的破破烂烂处理掉,人们乐意换,货郎乐意收,一举两得,两全其美,这生意就做的顺顺溜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时的货郎更像个走乡串户收废品的。
货郎担子不是天天都能来,十天半月才会来上一趟。一旦拨浪鼓的声音从村口传来,小孩子们就知道,那是挑着扁担的货郎来了,有的向屋里跑,有的向地里跑,火急火燎地把消息告诉大人,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着拨浪鼓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货郎一看见小孩,就故意把他的拨浪鼓摇得更加响亮。货郎担子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踉踉跄跄地挪动到空地上,刚一落脚,玻璃匣子前便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脑袋。货郎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一把汗,操着浓浓的乡音驱赶着:“别挤乖乖!给俺腾点地方,等摆好摊你们慢慢看。”
拨浪鼓声伴随着那拖着余韵的叫卖声,沉寂的乡村立刻变得热闹起来。正在做针线活的姑娘,放下了针线笸箩;正在做饭的妇女,放下了手中锅碗瓢盆;正在喂着鸡鸭的小脚老婆婆,放下手中的面瓢,她们互相招呼着,或拎着或抱着早已拾掇好的破烂,高喊着:“货郎挑子,甭慌走!”从屋里或院子里三三两两的急忙赶来。
大人、小孩围在货郎周围,各选所好,各取所需。七嘴八舌,叽叽喳喳,有哭有闹,有说有笑,清冷的村庄很快沉浸在欢快热闹之中。大姑娘、小媳妇,捋捋毛线、戴戴花卡……嘻嘻哈哈,相互欣赏。主妇们瞅瞅肥皂、看看火柴、……掂量再三。挤来挤去的孩子们,围着货郎挑子, 指指点点,眼睛不时地盯着自己所喜欢的玩具、糖果……更有一些调皮的孩子,会趁着货郎忙于生意的时候,悄悄的拿起拨浪鼓,你争我抢的摇上几下,以满足好奇心。
货郎担里的小商品都很便宜,缝衣服的大号钢针1分钱一根,玻璃球2分钱一个,那月亮状的小镜子也只要1毛钱。这些东西多是供销社里难以买到的。女人们爱美爱生活,买针线做衣服,买梳子、镜子梳妆打扮。老婆婆则手里握着两个还有余温的鸡蛋,要换的,不是肥皂火柴,就是针头线脑。上了年纪的老汉们,也拿出了几分威严,以老者的身份扯开嘶哑的嗓子喊着:”货郎挑子!到这边来,让我看看!”精心挑选以后,从裤腰里三层外三层摸出一个小腰包,再里三层外三层打开,取出皱巴巴的纸币,买上一个翠绿的玻璃烟嘴,喜滋滋地欣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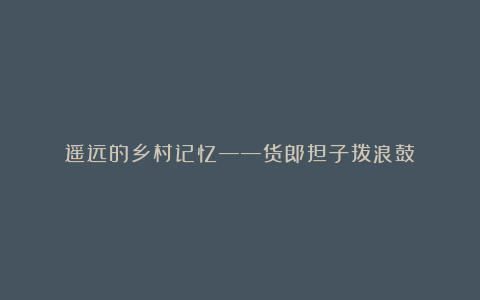
交易过程中也免不了讨价还价。“这棉花套子多少钱一斤?”“5分。”“6分吧?”“好,你这棉套成色还可以,6分就6分。”接着,货郎从木柜里拿出一杆秤,称棉絮,算账,折成钱。如果双方同意的话,干脆也不用秤称了。货郎用手掂一掂,便喊出“值5分、8分、1毛、2毛”等价钱来。有时货郎说“破烂”太少,不能换镜子、梳子之类的东西。但主妇们已将需要的东西拿在手里,便陪着笑脸说:“咱们还是老主顾呢,下次来,再多给你找点破烂。”“好的,说话要算数哟。”货郎也笑了,便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有的为了多卖几分钱,就跟货郎长时间讨价还价,但这并不会让货郎先生生气。走南闯北的货郎早已谙熟这些伎俩了,争吵之中,大家却是乐呵呵的。该买的买下了,不买的货郎也不责怪。
货郎大都为人和气,朴实厚道,一不哄,二不骗,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有时却也寸步不让,如大姑娘小媳妇要买的头绳、松紧带,货郎会在木箱的边沿上刻好了尺寸,按着尺寸测量,一寸也不让。看到货郎担认真的样子,小媳妇们会开一花玩笑,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有些小伙子也因此会用嘲讽的口吻来逗弄货郎担,引来一丝丝不快,但这并不影响货郎担们的较真,因为是小本生意,不得不计较。
货郎担对于孩子们的诱惑力自不必说了。哗啦棒槌、皮老鼠、花米团,五色糖豆等吃的玩的应有尽有,一分钱可以买上5个花米团或一排砸炮,更为诱人的是,货郎担上永远悬挂着五色的气球和小猴爬杆之类的玩具,虽说没钱买,但可以满村跟着货郎跑,看着他吹着气球玩弄着小猴爬杆,孩子们被引诱的心理痒痒的,虽不能得到,但总是可以饱眼福的。
哗啦棒槌
货郎虽然叫“郎”,但是行此道者多是上了年纪的长者,记得经常到我们村的那个货郎牙齿都没了,背也驼了,但是总是笑咪咪、乐呵呵的。他为人善良,对东西不怎么计较,不论换什么都好说好商量,对我们小孩子更是“关照”有加,你随便给他一点东西,他都会给你几粒糖豆,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那时候,可能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样,做梦都想成为货郎家的孩子,以为那样就可以拥有好多的玩具、大吃特吃那些美味零食了。既然做不成货郎家的孩子,那就来点现实的,平时多注意收集那些废旧物品,分门别类的放好,只要一听到拨浪鼓那熟悉的响声,就立刻蹿到街上,先把那些破烂让货郎察看过,收起,然后露出他林林总总的商品来,我咬着手指犹豫半天,才指着自己最后的选择,多数是玩具和零食。一面吃着玩着,还不忘招摇炫耀,胃口和虚荣心,同时得到了满足。
小时候在货郎担上换过的东西很多,现在大都已经忘记了。记得我曾经用一些破铺衬,换过最心仪的玩具“气茄子”。就是一只五彩缤纷的气球,口上有竹制的小笛子,气球吹大后,松开,出来的气流受阻,小笛子就尖利的响起来。优点是随时随地可玩,缺点是容易吹爆。
换过一个泥捏的小鸟样子的哨子。这哨子声音很尖,虽然不悦耳,但是小鸟的样子非常可爱,摸着光滑,还涂着色彩,从背上的小口灌入水,然后对着鸟嘴吹,不但能发出“㘗㘗”的鸟叫声,而且会从背上持续喷出水来。吹着它过瘾了好一阵子。还换过一个白色的卫生球,拿着它到处找蚂蚁,在蚂蚁周围画个圆圈,就像有了孙悟空金箍棒画圈的魔力,急得蚂蚁怎么转都逃不出来,感到又神奇又好玩。
还有只能在过年时才可以换到的“琉璃蹦蹦”,琉璃蹦蹦是玻璃制品,一根细管连着圆鼓型底子,底子很薄,一吹一吸,引起底面震动,发出好听的清脆的“咯嘣咯嘣”的响声。手拿着放在嘴上,一呼一吸,力气不可太大,也不可太小。大了,就吹破了,小了则吹不响。不吹时,要轻拿轻放。掉到地上也会粉碎。俗话说:琉璃蹦蹦吹三吹,吹破的是多数,好赖不值几个钱,是过年特有的娱乐器具。大人小孩都爱玩。可惜,现在见不到了……
货郎挑子里的大部分商品是批发的,也有一小部分是自己制作的。比如,用麦芽糖熬制的糖稀,用高粱杆蘸着卖,两分钱一蘸,物美价廉。拿到糖稀的孩子,非常小心地用舌头在那上面舔来舔去,脸上洋溢着幸福、自豪和喜悦。站在旁边看的孩子顿时垂涎生津,下意识用自己的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仿佛也尝到了一丝丝甜味。馋孩子们的当是那五颜六色的小糖豆,边看边咂吧嘴唇,口水直流。实在忍不住了,飞也似地跑回家寻找废品。钻床底,掏窟窿,翻箱倒柜,犄角旮旯,统统搜个遍。实在找不到,淘气的孩子,就拿着还能穿的旧衣物,或还能用的铁制小工具,极速返回,不问价,不讲价,如愿以偿。孩子们拿着换来的小糖豆,放在嘴里,舍不得咀嚼,慢慢含化。吃在嘴里,甜到心里。一整天,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神采飞扬。
最吸引孩子们的当属“打彩”了,那真是惊心动魄。货郎自制的“打彩”道具极其简单,用比较硬的纸板做一个正圆形的靶子,周围均匀的贴上写有商品名称的红纸条,靶子的对面是类似机关枪的木架,上面装有用胶皮筋控制的射针。货郎根据废品的多少,确定“打彩”次数。“打彩”开始,货郎转动靶子,打彩者屏气凝神,目不别视,把握时机,扣动扳机,射针快如闪电,飞向靶子,插在什么物品的名称上,即可以得到什么。如射在空白处,货郎会赏给几粒糖豆,以示安慰。如果对射中的物品不喜欢,也可以等价调换或者征得货郎的同意再打一次,往往是一次不如一次,最后打个空挡,唏唏嘘嘘,垂头丧气,悄然离去。整个场面紧张、热烈,阵阵喝彩声,引来众人围观,有的人被这场景所吸引,心荡神摇,急忙回家找点东西,来上一靶,一试手气。
货郎这一行,走街串巷时间久了,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盘,见到的大部分也都是些老主顾。主顾有什么要求,货郎便会尽量满足。倘若谁想买点什么,恰巧货郎这次没有,甚至从不做这些生意,货郎也会尽力想办法在下次过来的时候捎带过来。有时,相距十里八里的亲戚间有事,若不是太紧急,恰巧彼此又在货郎“盘乡”的范围之内,主顾也会委托货郎为对方捎个口信。只要能办到,货郎都会尽力帮忙。因此,货郎又像是乡村里的义务“邮递员”。
货郎的工作看上去十分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走街串巷地卖货即可,但其实十分辛苦。他们起五更睡半夜,披星星戴月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肩挑一对笨重的货箱,走街串巷奔忙。有的时候,还远走他乡。日晒雨淋,风吹霜打,饿了就从衣襟里拿出馒头,向村里人讨要一碗水,就着水咽下,有时就拿一些日用品向村里人换碗饭来充饥。有时走得远了来不及回家,天黑了就在农家的柴禾垛里睡上一晚。吃的是百家饭,睡的是柴禾床。由于卖的都是本小利薄的小玩意,利润极低,即便如此终日奔波,也不过是一点点的毫末之利,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因此在过去,只有家境贫困的人才会选择去做货郎担的营生。记忆中,有过逃荒经历的祖父会经常挽留路过的货郎在家吃饭歇息,还常常告诫后辈们:一定要善待这些出门在外的受苦人。
货郎担,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年代,它的到来,无疑给人们的生活注入了不少的乐趣,提供了不少的方便。从九十年代开始,农村陆续出现了小卖部、日用百货店,再后来连锁超市也走进了乡镇农村,村口的土泥路上,再也见不到佝偻着身子、挑着担子、拖着沉重步伐的货郎担的影子、再也听不到拨浪鼓的声音了……世事更迭,如过千帆。“货郎担子”这一古老的行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定格在遥远的岁月深处。可我依然无法忘记那个货真价实的纯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