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起源可追溯至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 4000 年,苏美尔人将医学与神祗尼纳祖关联,其象征健康与疾病的蛇杖符号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流传至今,常见于现代医疗相关机构的标识中。在医学发展早期,学界普遍反对专利制度,认为知识应作为公共财富服务全人类。
专利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 1404 年,英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反倍增工艺法案》,将 “使用倍增工艺私下制造黄金和白银” 定为重罪,目的是限制私人财富增长以避免其威胁王权。16 世纪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君主开始通过颁发特权控制特定商品的生产与贸易,将这种垄断权作为协调君主、专利权所有人与王国利益的临时社会契约。1624 年,英国《垄断法》正式确立现代专利制度框架,禁止 “有悖于王国律令” 的垄断,同时允许 “第一个真正发明人” 拥有 14 年的独家使用权,这一制度设计影响至今。
美国的专利制度发展始于 1790 年,乔治・华盛顿签署了本国第一项专利,授予塞缪尔・霍普金斯生产化肥用钾肥的新方法 14 年专有权。19 世纪,美国出现大量专利药,这些所谓的 “万能药” 实际功效存疑,逐渐被贴上 “江湖郎中骗术” 的标签,遭到正统医学界的蔑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国化学-制药企业率先通过专利构建市场垄断。其中,拜耳公司因围绕突破性药物构建专利壁垒而声名远扬。1899 年,拜耳推出 阿司匹林后,因专利问题与美国同业产生激烈冲突,1909 年至 1917 年间引发了美国史上范围最广的走私行为,号称 “阿司匹林战争”。
这一时期,医学界对药品专利的态度开始转变。纽约医生斯图尔特打破传统道德禁忌,与帕克 – 戴维斯药物公司合作开发治疗消耗性疾病的药物,成为 “有道德地取得药物专利” 观念的早期推动者,使得医药垄断的伦理禁忌逐渐松动。
20 世纪的制度化转变加速了医药垄断的形成。1923 年,威斯康星州生物化学家哈利・斯廷博克发现紫外线可产生维生素 D,为规避道德争议,他于 1925 年推动成立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ARF),专门处理学术成果的专利与授权事务。这一机构成为大学参与专利管理的转折点,打破了学术科学不涉商业利益的传统道德规则。到 1930 年代中期,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开始申请专利,学术研究人员为商业利益延迟发表成果、阻碍知识流动的现象日益普遍,《美国医学会杂志》编辑莫里斯・菲什拜因的言论深刻反映了当时医学伦理秩序崩溃的痛苦与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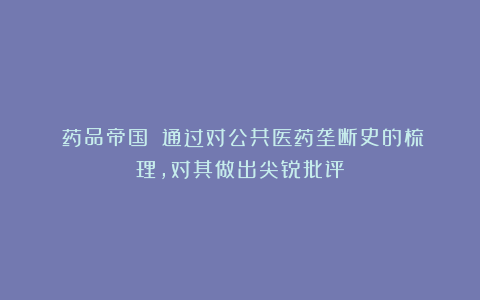
新政时期,罗斯福政府试图恢复反垄断传统,并于1938 年明确表示将大力执行反托拉斯法,重塑产业格局。1941 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胰岛素垄断》一文,揭露多伦多大学授权的胰岛素生产企业存在价格垄断问题。但随着 1946 年共和党接管国会,美国战后经济重心转向刺激消费,反垄断运动逐渐衰退,制药产业几乎切断了与反垄断传统的所有联系。
二战后,美国政府成为医学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但专利政策逐渐向企业倾斜。围绕公共资助研究成果的归属权,形成了两种对立主张:范内瓦・布什推行产业优先政策,使大型企业和精英大学获得更多资源;哈利・基尔戈则坚守公共利益立场,反对将公共资助的发明权垄断给企业。
1950-1980 年代,医药产业加速扩张并摆脱道德束缚。1959-1961 年,基福弗与知名药物公司就 20 至 30 倍的加价幅度展开激烈斗争,暴露了行业的贪婪本质。1980 年《贝多法案》通过后,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成果向商业领域开放,大学为牟利纷纷热衷专利申请,哈佛等传统学府也放弃了将医疗相关专利归入公有领域的政策。1984 年《哈奇 – 韦克斯曼法案》促使大量无商标药物进入市场,为应对竞争,药企通过 “垄断常青化” 操作——对原产品进行微小改动(如改变颜色或标语)后重新申请专利——人为延长垄断期限。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充分暴露了医药垄断的弊端。1985 年艾滋病爆发后,制药企业因传染病研究利润低而减少投入,首款治疗药物齐多夫定被宝来威康公司定价高昂,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药物,政府未动用《贝多法案》的介入权进行干预,引发广泛抗议。2020 年新冠疫情中,专利壁垒严重阻碍了疫苗研发与生产,尽管 WHO 启动 C-TAP 计划推动知识共享,140 个组织呼吁开发 “属于人民的疫苗”,但这些努力遭到强大阻力,导致全球抗疫进程受阻,少数资本家却借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总而言之,关于药品专利问题,经济层面,2010 至 2018 年,全球最大的 35 家药物公司累计毛利润达 9 万亿美元,比全球黄金储备总额高出约 2 万亿美元。这种超高利润并非源于药物本身的价值,而是专利律师和游说者通过垄断手段创造的 “政治魔法”,专利制度成为药企从公共投资中攫取私人财富的工具。
伦理与社会影响层面,医药垄断严重侵蚀了医学伦理,背离了医学作为人道崇高职业的传统。药企花费重金宣扬 “垄断促进创新” 的谬论,通过资助伪科学 “回音室” 制造舆论,混淆价格、利润与创新的关系,削弱监管力度,阻碍公众对垄断本质的认知。
在全球公共利益层面,77 国集团和 WHO 等国际组织持续尝试打破药企垄断格局,但多年来屡屡碰壁。比尔・盖茨等垄断资本势力凭借巨大影响力,阻碍将医学研究成果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努力,使得医药垄断这种背离数世纪道德传统的制度得以持续存在。尽管其弊端已被广泛认知,但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