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地区汉墓所见“多人葬”问题
――以烧沟和西郊墓群为中心
杨哲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多人葬的种类和数量
根据《洛阳烧沟汉墓》(以下简称《烧沟》)和《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以下简称《西郊》)的有关报道和附录的墓葬登记表,笔者对这两处汉墓群的埋藏人骨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所得结果如下(表一):
表一 《烧沟》和《西郊》汉墓群埋藏人数统计表
需要说明的是:《烧沟》自称报道墓葬225座,可能是由于少数形制特殊的墓葬(指墓号带A、B者)在统计时有分合的差别,原报告第II型和第III型墓所附“墓葬形制分述表”(即《烧沟》“表三”和“表四”)中所列举的墓葬数量均比报告中相关的“墓葬综合说明”多出2例,故报告末尾所附的《墓葬总表》(即《烧沟》“表六七”)实际所列墓葬可统计为229座[5]。其中,因受盗扰以及保存状况的影响,人骨情况不明者共计58座。其它171座墓葬中[6],埋葬人数为1人的(本文以下均称“单人葬”)有84例、埋藏人数为2人的(本文以下均称“双人葬”)有73例、埋藏人数为3人的(本文以下均称“三人葬”)有10例、而埋藏人数在3人以上的墓葬总共只有4例。具体来说,在这4座墓中,M1034和M416各埋葬4人(本文以下均称“四人葬”);而M36,原报告“表三”统计为5人,但“表六七”统计为4人,且《烧沟》页33称该墓为“一墓四棺”,故本文暂以4人计。准此,则《烧沟》报道的汉墓中,埋藏人数为4人的可统计为3座。而埋葬人数在4人以上的就只有M1035一例了,共埋藏6人(本文以下称“六人葬”)[7]。
《西郊》报道的217座汉墓中,人骨情况不明者29例,其它188座墓中的埋藏人数可分为四种情况,即单人葬87例、双人葬89例、三人葬10例、四人葬2例。未见埋葬4人以上的墓例。
图一
由于洛阳西郊汉墓群与烧沟汉墓群地域邻近,均位于汉河南县城的北郊,加上墓葬的规模、形制和年代范围均大体一致,故本文将这两处墓群的资料综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在如上所述两处墓群的累计446墓例中,排除人骨情况不明的87例,《烧沟》和《西郊》所见埋藏人数明确的主要有5种情况,分别是:单人葬171例、双人葬162例、三人葬20例、四人葬5例和六人葬1例。这五种情况应该说大致反映了汉代洛阳地区中小型墓葬中埋葬人数的基本面貌。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随着埋藏人数的增加,墓葬的总数量呈现出显著减少的趋势,其中又以从双人葬到三人葬的墓葬总量变化最为悬殊。前两者(单人葬和双人葬)加起来约占墓葬总数的75%。而后三者(即本文所说的“多人葬”,包括三人葬、四人葬和六人葬三种情况)分别约占墓葬总数的4.5%、1.1%、0.2%,累计还不足墓葬总数的6%(参见图一)。若再考虑到比这两处汉墓群年代要早的西汉早期洛阳当地主要流行单人葬的情况[8],多人葬在洛阳地区整个两汉时期墓葬中所占的比例显然还可能更低一些。即便是排除人骨数量不明的墓葬,就烧沟和西郊两处墓群中埋藏人数基本清楚的359座墓而言,26例多人葬亦只占7.24%。因此,从数量上讲,可以说单人葬和双人葬仍为洛阳地区汉代丧葬的主流。证之洛阳地区已报道的其他汉代墓葬,这一点也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若单就多人葬考虑,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所见又明显是以三人葬为主,约占多人葬总数的77%,四人葬和六人葬则各占19%强和4%弱(参见图二)。从陕县刘家渠汉墓群[9]、西安白鹿原汉墓群[10]等有关统计数据来看,多人葬的种类和数量比也都大致和上述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接近。可以认为,相应的比例关系对于从整体上把握洛阳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汉代多人葬的真实情形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图二
二、多人葬与墓葬形制之关系
按照《烧沟》对墓葬形制的划分(《西郊》基本同《烧沟》),可将烧沟和西郊两处汉墓群中各型墓葬中的埋葬人数情况统计如下(表二):
表二
从表二的统计数据可以推知,前述洛阳烧沟和西郊两处汉墓群中各型墓葬所见多人葬的数量及所占比例大致是:
第I型墓77座,未见多人葬;
第II型墓230座,多人葬7例,包括三人葬5例和四人葬2例,占II型墓总数的3%;
第III型墓91座,多人葬11例,包括三人葬8例和四人葬3例,占III型墓总数的12.1%;
第IV型墓24座,多人葬3例,均为三人葬,占IV型墓总数的12.5%;
第V型墓18座,多人葬5例,包括三人葬4例和六人葬1例,占V型墓总数的27.8%;
另外还有存疑墓葬6座,人骨情况均不明。
通过上述的统计发现,从数量上讲,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中的多人葬是以《烧沟》所界定的第II型墓和第III型墓为多,累计18例,约占多人葬总数的70%;第IV型和第V型墓本身数量相对较少,所见多人葬亦达到8例;而第I型墓则未见多人葬。就各型墓中多人葬各自所占比例来看,从第I型墓到第V型墓是呈现出比例逐渐增加的趋势。若以各型墓葬中埋藏人数明确的墓葬数量计算(具体数据参见表二),则第I至V型墓中多人葬各自所占比例分别是0%、3.7%、15.5%、18.8%和31.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第II型墓和第III型墓之间似有一明显分界。这似乎表明,墓葬形制的某种变化(在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中主要表现为前后分室的出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多人葬的实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不过,从三人葬在第II至第V型墓中均有发现、而四人葬主要见于第II型和第III型墓的情况来看,从第II型墓到第V型墓并未出现随着墓葬形制的变化而单座墓葬中埋藏人数显著递增的趋势。相反,在各型墓中多人葬的墓葬数量仍明显少于同型墓中双人葬和单人葬的墓葬数量之和。由此可见,尽管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为多人葬的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前述III型墓中多人葬所占比例相比II型墓的显著增加),但墓葬形制变化的动因恐怕并不是为了埋藏更多的人。事实上,在多人葬的墓葬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埋葬人数与墓葬设计之间的明显不协调现象:除了主墓室中正常陈放的棺柩以外,不少墓葬中还在本应放置随葬品的耳室或前室之中陈放了尸体[11]。这种非正常埋葬现象似乎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墓葬中埋葬人数的增加并不一定都是出于预先的安排,而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或特殊性。
三、多人葬的阶段性变化
按照《烧沟》和《西郊》的分期研究,两处汉墓群中多人葬的出现时间似略晚于双人葬的流行。被认为是夫妇同穴合葬的双人葬在《烧沟》第一期即西汉中期偏早阶段已经流行,而多人葬大约出现于《烧沟》第二期即西汉中期偏晚阶段。统计数据显示(具体参见表三), 洛阳地区汉代多人葬中最早出现的似为三人葬。从第二期2例、第三期3例、第四期3例、第五期6例、第六期6例的情况看,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三人葬的墓葬数量还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大约西汉晚期至新莽前后(即《烧沟》第三期),四人葬也开始出现。然而,这两处汉墓群中四人葬的墓葬数量不仅比三人葬显著减少,而且其发展趋势也似与三人葬不同:总共5例中属于西汉晚期至新莽前后的有3例,属于东汉早期(《烧沟》第四期)和东汉中期(《烧沟》第五期)的各1例,至东汉晚期则未见。至于六人葬,亦仅见东汉晚期(《烧沟》第六期)的1例。
表三
为了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中多人葬的发展趋势,试将其阶段性变化归结如下图(图三):
图三
从图三中可以看出,在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中,多人葬的墓葬数量并非呈现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而是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时期:一是西汉晚期至新莽前后时期(《烧沟》第三期),二是东汉中晚期(《烧沟》第五期和第六期)。结合表三的统计可知:在第一个高峰期内主要流行的是三人葬和四人葬(各3例);至第二个高峰期出现了六人葬,但数量极少,仅有1例,占主流的仍是三人葬。
关中地区汉墓所见,多人葬的出现时间似乎略晚于洛阳地区,但东汉中晚期数量较集中的情形却是一致的[12]。介于关中和洛阳之间的陕县刘家渠汉墓群中,多人葬的年代基本上也都属于东汉时期,唯一的1座六人葬M158中还出土有“阳嘉四年”朱书罐,为我们了解此类多人葬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13]。其实,汉代多人葬的例子较集中于东汉中晚期这一现象,不少学者早已注意到[14]。弄清了多人葬的主要流行时间及其阶段性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探讨其出现原因和性质问题。
四、关于多人葬的性质及出现的原因
多人葬的性质应该是由多人葬墓葬内埋葬的人数及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由于汉代墓葬中墓志之类的直接文字证据还非常缺乏,在现代科技手段(如DNA技术)介入之前,对于墓葬内各埋葬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根据有关埋葬现象、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进行推测。
依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可知,在流行夫妇合葬的汉代,人们常引用《诗经》中“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来解释实施夫妇“合葬”(尽管未必是指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同穴合葬”)的理由,其主要观念便是所谓“夫妇一体”[15]。“同穴”在当时似乎也成了实施夫妇合葬的代名词[16]。《白虎通义·崩薨篇》则明确说:“夫妇生时同室,死同葬之。”所谓“合葬者,所以固夫妇之道也”。基于这种观念,目前学界通常将汉代墓葬中所见到的一男一女同葬一墓或并列一室的情形视为一对夫妇合葬(尽管这一前提尚需证明)。
图四 洛阳西郊M9002平面图
图五 洛阳烧沟M36(左)和M1034(右)平面图
从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来看:无论三人葬或四人葬,基本上都是以一对成年男女居于主室(或后室)的情况为主,另外1-2人(成年或未成年)多位于耳室或侧室、前室之中。推测其主体仍应该是以最基本的家庭结构为单位,是以一对夫妇合葬为基础、附葬子女1-2人的两代人合葬的可能性为最大,个别四人葬中也有可能是两对夫妇合葬。如西郊M9002(图四),属于单穹窿顶前后室墓,前室左右两侧带有耳室,在砖筑的后室中放置双棺,而位于土圹前堂南壁的另1棺则“横陈于南耳室入口处”。烧沟M36(图五,左),属于“弧顶双棺室小砖券墓”,除了主室内放置的棺柩外[17],在左右两耳室内另放两个小棺,《烧沟》报告推测“似乎不是成年人的合葬,或是死者所属夭殇的子女附葬的”。又如烧沟M1034(图五,右),属于“单穹窿顶墓”,除了主室埋藏的一对男女可能是夫妇合葬以外,埋藏在侧室中的另一对男女也可能是一对夫妇。相对于主室夫妇来说,埋葬在侧室中的如果是晚辈,就形成两代人两对夫妇合葬,当然也不排除属于其它情况的可能性。另外,三人葬中亦偶见主室之中并列三棺的情况,如烧沟M632所见,若是同辈人,是否与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有关呢?如果不是,为什么该墓有足够的空间而三棺却要挤在一起?尽管目前还难以对这样的疑问给予满意的解释,但有一点却是相对比较明确的,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那样,即如果在同一墓葬中实施“多代合葬”的过程中有一代是夫妇合葬的话,那么满足其基本条件的人数应不少于4人[18]。准此,前述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中埋藏有2代人以上的墓葬,恐怕就只有学者们常引用的烧沟M1035一座有此可能。然据《烧沟》报告,M1035为横前堂双后室砖券墓,通常情况下此类墓葬中的棺柩应安置在双后室中,但该墓除双后室以外,横前堂的一侧也发现有棺痕,显示出某种特殊性。
分析汉代多人葬出现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在将多人葬与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变化以及相应的家庭(或家族)关系的强化联系起来的同时,往往很少考虑到汉代多人葬的具体人数差异以及不同人数的多人葬各自出现的频率等问题。通过对洛阳烧沟和西郊两处汉墓群的考察,所谓“多人葬”应是以夭殇的(未成年)子女附葬于父母墓的情况为主。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中原北方地区对于未成年人的埋葬曾一度流行瓮棺葬或瓦棺葬之类,往往位于父母墓葬的附近或房屋周围[19]。多人葬的出现则表明,对于夭殇的(未成年)子女的安葬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强化家庭观念这一出发点来看,或许将子女纳入父母的墓葬之中是与之相应的一种表现方式,但从数量上是否已构成一种制度化的表现或流行的丧葬习俗,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至于在这些多人葬中是否存在所谓“多代合葬”,从前述的统计数据看其可能性应该很小,即使有,其出现频率也应该是极低的[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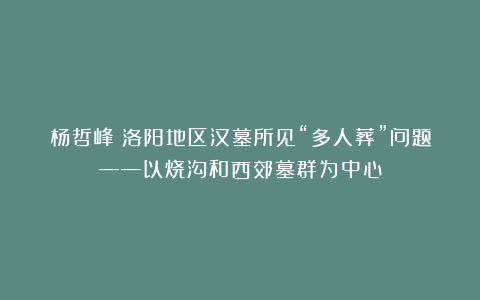
事实上,也有学者在将汉代的多人葬上升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在墓葬制度上的表现”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导致多人葬的情形,即《后汉书》所载“收葬”灵帝宋皇后及其父亲和兄弟,“归宋氏旧茔皋门亭”[21]的特殊历史事件,认为“合葬一室的可能性极大”[22]。从另外两座常被引用的晚于汉代的墓葬实例即洛阳周公庙西晋裴祗墓(葬于293年)[23]和洛阳西晋士孙松墓(葬于302年)[24]来看,前者是裴祗夫妇与其母亲和女儿惠庄的合葬墓,后者是傅宣之妻士孙松与其夭殇二子的合葬墓,两墓中均存在将子女与父母(或父母之一)共葬一墓的情形。两墓的埋葬时间上距东汉灭亡不足百年,墓志所载墓葬中的人物关系为我们理解当地汉代的多人葬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裴祗墓的埋葬背景,黄明兰先生曾指出:“从此墓结构看,确系一次建造,也当是一次下葬,一家三代老少四口同时同墓而葬尚不多见。据墓志,裴祗死于晋惠帝元康三年(293)七月,时八王之乱初起,裴祗一家之死是否与此有关,尚待考”[25]。由此可见,作为丧葬结果的多人葬,其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以前在讨论汉代的多代合葬时,学者们还常以四川地区东汉崖墓的埋葬情况作为例证。从大家常引用的宋代洪适《隶释》著录的所谓“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26]来看,张伟伯与其少子叔元既然在“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俱下世”,本身就暗示了其死亡背景的特殊性。至于1991年在偃师发现的东汉“肥致墓”出土的碑文,也为我们探讨东汉时期的多人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碑文看,该墓有可能是一群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方术之士或道教信徒的多人合葬墓[27]。
除了前述政治或宗教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一种因素也值得重视――即汉代多人葬数量最集中的东汉中晚期,既是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出现动荡、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乘机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汉代疫病盛行时期。作为东汉都城所在的洛阳地区便是当时疫病流行地区之一,史载有“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28];“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29],等等。由于瘟疫所导致的“民多病死,死有灭户”[30],以及“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31],或许也能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该地区东汉中晚期多人葬墓葬数量增加、以及个别墓葬中埋葬人数增加的原因。事实上,早在西汉末期,汉朝廷对于因疾疫而亡故人数较多的家庭还赐“葬钱”以助安葬,其“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32]的记载,也为我们正确理解汉代多人葬的埋葬人数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总之,通过对洛阳烧沟和西郊汉墓群所揭示的“多人葬”的统计分析,本文试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即多人葬在汉代当地的丧葬习俗中并不居于主流,而且从多人葬单座墓葬的埋藏人数上讲,总体上仍可能是以夫妇合葬为基础但又有别于单纯的一夫一妻合葬,推测其主体仍应该是以最基本的家庭结构为单位,但也不排除会有少数的例外。由于汉代的家庭结构本身复杂多样,多人葬的表现方式也可能不尽相同。对于其出现与流行的原因,除了学者们论及的土地所有制变革导致的丧葬制度或风俗的变化(如对核心家庭观念的强化)等原因以外,本文认为对因疾疫或其它原因导致的非正常死亡者的丧葬安排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某些多人葬中埋葬人数及其布局与墓葬形制之间的明显不协调或许更有助于说明墓中埋葬人数的增加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或偶然性。更何况,汉代墓葬中出现的埋葬人数的差别,并不一定都是制度化的结果。某些现象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新的丧葬习俗或丧葬制度的反映,还要看其普及或流行程度如何。因此,对于汉代丧葬制度或丧葬习俗的研究,还应该注意不同现象的量的变化以及在等级、地域、时代等方面的差异,尤其不应该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相混淆。对于某些特殊现象,应该放到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方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根本出发点。借此希望将来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汉代多人葬墓中各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死亡原因等进行鉴定和分析研究,也希望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对有关现象的记录能够更为细致、更为精确,为相关的研究保存更为翔实的资料――相信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揭开汉代多人葬的面纱。
2003年8月28日初稿
2007年11月二稿
2008年1月三稿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例如: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韩国河《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10期;齐东方《袝葬墓与古代家庭》,《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5期;等。
[2]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历史特征》,均见《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7月。
[3] 《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12月。
[4] 《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
[5] 《烧沟》报告对于部分墓葬采用了A、B式编号,并且在墓葬形制划分上有的还归入了不同的型式,因理解不同可能会造成统计结果略有出入,但这类墓的数量较少,对于总体上把握《烧沟》所报道的埋葬人数情况影响不大。本文暂以报告的墓葬总表所列229座作为总数。
[6] 事实上,即便是《烧沟》报道的可以统计人骨数量的171座墓中,人骨的保存状况均极差,绝大多数墓葬的埋葬人数主要是依据痕迹所作的推断,加上盗扰的影响,有的统计数据未必准确,故在报告中还出现了统计数字前后矛盾的现象。本文中所列的相关数据基本上都是以报告的墓葬总表为依据,其结果也只是作为一种参照,目的在于通过类似的统计分析,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也希望将来的考古报告能够对类似的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
[7] 韩国河认为该墓“合葬7人”(《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10期),推测可能是出于对该墓之“后二室”(主室?)埋葬人数不止一人的考虑。从砖棺垫的位置推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该墓被盗扰,情况可能已发生变化,难以确知。故本文仍按报告所述统计为6人。
[8] 洛阳地区已报道的西汉早期墓葬资料相对较少,可参见《洛阳邙山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99年1期)、《洛阳北郊C8M574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5期)、《洛阳北邙45号空心砖墓》(《文物》1994年7期)、《洛阳市文管会配合防洪工程清理出二千七百余件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等。
[9] 距离洛阳不远的陕县刘家渠墓地,在1956年曾发掘46座汉墓。据报告《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1期)的统计,人骨不明者18座,骨架明确的28座墓中,单人葬6例、双人葬11例、3人葬8例、4人葬2例、6人葬1例。按照本文对“多人葬”的界定,刘家渠汉墓群的多人葬也是包括三人葬、四人葬和六人葬这3种情形。多人葬的数量在人骨明确的墓葬中所占比例约为39%,占墓葬总数的23.9%。这一比例略高的情况,可能是与该墓群的绝大多数墓葬年代均属于东汉时期有关。若就三人葬而言,其所占多人葬总数的比例72.7%仍和洛阳烧沟和西郊墓群接近。顺带说明的是:俞伟超先生在《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一文曾引用刘家渠汉墓群的M3,认为是“四对夫妇葬于四室”,以此作为汉代“多代合葬”的例证。然查检原报告,M3虽为多室墓,但被盗扰,人骨数量不明。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报道两汉时期墓葬94座,据统计,“除人骨无存者外,能够辨别为单人葬者有53座,双人葬者9座,三人葬者6座,四人葬者1座、六人葬者1座”。如此,则人骨不明者应为24座,但据报告附录三《墓葬登记表》,人骨不明者有28例,相应地单人葬降为49例,其余17例合葬墓则相同,只是在原报告页253列举合葬墓时误作15座。按照本文对“多人葬”的界定,这批墓葬中多人葬共计8例,在人骨明确的墓葬中所占比例约为11.4%(单人葬按53座计算),占墓葬总数的8.5%。单就多人葬而言,同样也是以3人葬为主,占多人葬总数的75%。
[11] 对于这种现象,齐东方先生曾指出“汉代的袝葬墓一般不改变流行的墓葬形制,而是改变某些空间的功能”。参见齐东方:《袝葬墓与古代家庭》,《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5期。
[12] 就《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报道的94座两汉时期墓葬来看,所谓“同穴合葬墓”中,属于西汉者仅见双人葬,而多人葬主要出现于东汉时期,尤其是2例四人葬和六人葬的墓葬年代均在东汉晚期。关中地区西汉时期罕见多人葬的情况,还可从《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该报告公布的139座西汉中晚期墓葬中,除1座人骨不详外,“双人合葬墓30座,单人葬墓108座”,也没有1例多人葬。目前所知,年代大致在西汉末至王莽时期的西安净水厂M36中葬有3人(《西安净水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是关中地区东汉以前较为少见的多人葬例证。
[13] 《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1期。
[14] 例如,韩国河在《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10期)一文中还指出,除了四川境内的崖墓以外,东汉至魏晋时期“在黄河流域乃至辽河都可见到多人的合葬”。
[15] 《汉书·哀帝纪》、《汉书·外戚传下·定陶丁姬传》。
[16] 《后汉书·列女传·阴瑜妻传》。
[17] 关于该墓主室中安葬的人数,《烧沟》的描述前后自相矛盾,本文暂以双棺计算。
[18] 如西晋裴祗墓便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参见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
[19] 参见白云翔:《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3期。
[20] 学者们在讨论汉代多人葬时经常引用的另一个例证,即西安净水厂M18(《西安净水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埋葬人数达到8人,报告认为“至少是两代人的合葬”,但也只是一种推测。至于“侍妾”、“家庭内部侍仆人”加入合葬的说法,也需要进一步证明。据墓葬平面图,在该墓北侧室的东北角还有“殉人骨骸”,其真实性亦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类似净水厂M18这样的多人葬出现在东汉中晚期,的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21] 《后汉书·皇后纪》。
[22] 韩国河《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99年10期。
[23] 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
[24] 《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5] 《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
[26] 参见齐东方:《袝葬墓与古代家庭》,《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5期。
[27] 《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9期。
[28] 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
[29] 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
[30] 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张衡语。
[31] 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曹植语。
[32] 《汉书·平帝纪》。
本文原载《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引述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