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还原电位(Eh)与 pH 作为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的驱动因子:指向农学整合机遇的跨学科综述
奥利维耶胡松(Olivier Husson)
收稿日期:2012 年 5 月 25 日 / 录用日期:2012 年 8 月 16 日 / 在线发表日期:2012 年 9 月 8 日
作者(2012)。本文已在Springerlink.com平台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
期刊信息
《植物与土壤》(Plant Soil),2013 年,第 362 卷,第 389-417 页
DOI:10.1007/s11104-012-1429-7
责任编辑:汉斯兰伯斯(Hans Lambers)
作者单位
奥利维耶胡松(*)
法国农业国际合作发展中心(CIRAD),农业系统与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室(UPR SIA)
法国蒙彼利埃,阿格罗波利斯大道,TA B01/07 号,邮编 34398
电子邮箱:olivier.husson@
网址:http://www./ur/couverts_permanents
摘要
研究背景
氧化还原反应与酸碱反应是维持所有生物生存的关键过程。然而,与被视为 “主导变量” 的 pH 值不同,氧化还原电位(Eh)在农学领域尚未受到足够关注。农学家可能遗漏了作物与土壤科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该因素本可成为实用的整合工具。
研究范围
本文综述了农学相关各学科中与 Eh 相关的现有文献(无论是否涉及 pH 值),并将这些知识整合到一个综合框架中。
研究结论
本跨学科综述证实,Eh 与 pH 值分别且共同构成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的主要驱动因子。关于 Eh 与 pH 值在植物和微生物生理学、土壤发生过程中作用的研究成果,共同形成了一个可用于深入研究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功能的实用框架。该框架基于以下假设:植物在特定的体内 Eh-pH 范围内实现生理功能;植物会与微生物共同改变根际环境的 Eh 与 pH 值,以维持细胞水平的稳态。这一新视角有助于连接农学相关的多个学科,打通微观与宏观尺度,进而为常规农业、有机农业及保护性农业的种植系统设计与管理提供优化思路。
关键词
细胞稳态;“理想” 土壤;养分;根际;土壤电阻率
引言
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阿尔伯特森特 – 哲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在 1960 年曾有一句精辟总结:“生命的驱动力是由阳光维持的微弱电流”。事实上,电子是无机反应、有机反应及生化反应中的关键反应物(Bohn,1971)。与更关注质子转移的酸碱反应相比,生物体的化学过程更依赖于氧化还原反应(即电子转移)(Clark,1960;Dietz,2003;Falkowski 等,2008;Greenberg,1998)。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体的主要组成成分(尤其是蛋白质)仅由六种元素构成:(1)氧 —— 最强氧化剂;(2)氢 —— 最强还原剂;(3)四种氧化还原价态跨度最大的元素:碳(在甲烷中为 -Ⅳ 价,在二氧化碳中为 +Ⅳ 价)、氮(在铵根中为 -Ⅲ 价,在硝酸根中为 +Ⅴ 价)、磷(在磷化氢中为 -Ⅲ 价,在磷酸根中为 +Ⅴ 价)、硫(在硫化氢中为 -Ⅱ 价,在硫酸根中为 +Ⅵ 价)。
氧化还原状态通常通过测量氧化还原电位(Eh)来评估,单位为伏特(V)。Eh 值的基准点由标准氢电极(SHE)确定,以 H⁺/H₂ redox 电对为参照。Eh 值被广泛应用于多个与生物相关的学科,包括微生物生态学(Alexander,1964)、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湖沼学(Bohn,1971;Falkowski 等,2008;Reddy 与 DeLaune,2008)、生物能学(Guérin,2004;Mathis,1995;Szent-Gyorgyi,1957)、水生生物学与海洋生态系统研究(Meadows 等,1994)、土壤科学(Chadwick 与 Chorover,2001),以及生理学与生理生态学(De Gara 等,2010;Dessaux 等,2009;Dietz,2003;Foyer 与 Noctor,2005;Lambers 等,2008)。
不同学科会在不同尺度、针对不同基质测量 Eh 与 pH 值,涉及的对象包括细胞器、细胞、植物、根际、土体土壤、沉积物、土壤溶液及水体等。然而,在许多学科中,氧化还原状态与电子通量并未获得与 pH 值及质子通量同等的关注。例如,在土壤科学领域,尽管 Eh 的重要性已得到认可,但 pH 值仍常被视为 “主导变量”(Brady 与 Weil,2010;Simek 与 Cooper,2002);植物生理学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Rengel,2002)。
令人意外的是,与 pH 值不同,Eh 在农学领域的核心地位远未确立。多数关于土壤 Eh 的研究局限于导致厌氧环境的极端场景,如稻田与淹水土壤(Bartlett 与 James,1993;De Mars 与 Wassen,1999;Gotoh 与 Yamashita,1966;Kludze 与 DeLaune,1999;Kogel-Knabner 等,2010;Ponnamperuma,1965、1972;Stepniewski 与 Stepniewska,2009;Yoshida,1981)。而作为多数耕作土壤类型的好氧土壤,其 Eh 值在农学领域却鲜有研究。
文献中相关研究较少的现象,可能源于三个方法学层面的原因:(1)与 pH 值相比,Eh 值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异性更高;(2)好氧土壤中 Eh 值的测量难度较大;(3)Eh 与 pH 值存在关联性。这导致 Eh 值的测量结果难以重复与解读,不同研究者的成果也难以比较(Snakin 等,2001)。
尽管农学领域(尤其是针对好氧土壤)关于氧化还原电位(Eh)的研究较少,但这一关键参数不应因测量或解读难度而被忽视。好氧土壤 Eh 研究的缺乏,可能导致人们先验性地低估高 Eh 水平对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功能、植物健康及产量的影响。农学家或许遗漏了植物与土壤科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 若将其与 pH 值系统结合,有望推动可持续农业领域的农学知识发展。
本文旨在完成两项工作:(1)综述农学相关各学科中与 Eh 相关的现有文献(无论是否涉及 pH 值);(2)整合这些知识,构建一个实用视角,以连接农学相关学科、打通微观与宏观尺度(从植物细胞到田间尺度的植物、根系及土壤)。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并强调 Eh 在细胞与植物生理层面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探讨 Eh 与 pH 值分别及共同对微生物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在田间尺度上依次分析以下内容:(1)Eh 与 pH 值的范围及变异性;(2)Eh 与 pH 值对植物生长的影响;(3)土壤 Eh-pH 值与植物养分有效性的关系;(4)植物对土壤 Eh 与 pH 值的影响;(5)Eh-pH 值与土壤有机质的相互作用;(6)Eh-pH 值与土壤发生的关系;(7)Eh 与 pH 值对温室气体排放、土壤污染及生物修复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农业措施对土壤 Eh 与 pH 值的影响;第五部分整合上述知识,提出假设 —— 植物会与微生物共同改变根际环境的 Eh 与 pH 值,以调整至最适生理水平,从而实现正常功能。
本文还将探讨这一综合视角为农学领域带来的问题,并提出:该视角有助于评估农业措施,为常规农业、有机农业及保护性农业的种植系统设计与管理工具开发提供理论框架。
细胞与植物生理学中的氧化与还原
氧化还原反应与能量
在植物界,光合作用利用光子的光能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还原,并与从水中获取的氢结合(Govindjee 与 Krogmann,2004;Wurmser,1921)。该反应生成葡萄糖并释放氧气,反应式如下:
6CO₂(气态)+ 12H₂O(液态)+ hν(光能)= C₆H₁₂O₆(水溶液)+ 6O₂(气态)+ 6H₂O(液态)
这一反应为吸热反应,在 25℃条件下,每摩尔 CO₂的焓变 ΔH⁰为 + 470 千焦(Bisio 与 Bisio,1998)。
固氮作用同样是吸热反应,需将大气中的氮还原(Eagleson,1993),其能量来源于光合作用储存于葡萄糖中的能量(Atkins 与 Jones,1997)。葡萄糖还原氮的总反应式(Bayliss,1956)如下:
C₆H₁₂O₆(水溶液)+ 4N₂(气态)+ 6H₂O(液态)= 6CO₂(气态)+ 8NH₃(水溶液)
此外,植物体内的蛋白质合成与脂肪合成均属于还原反应,化学能会在合成的分子中积累。在含氧环境中,这些不同还原态化合物氧化释放的能量会被细胞利用(Lambers 等,2008)。细胞的能量代谢依赖于线粒体中的三羧酸循环(Krebs cycle):进入线粒体基质的底物通过循环过程被氧化,产生还原力(Lambers 等,2008)。
氧化还原反应的催化作用会改变反应动力学,但不会影响其热力学条件。在热力学上可行的反应中,主导反应由其氧化还原动力学决定。因此,氧化还原反应的热力学与动力学是理解细胞及生物体生化功能的关键。
区室化与氧化还原状态
“细胞氧化还原状态” 这一概念,概括了氧化还原活性化合物之间的大量相互作用,以及环境参数对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Potters 等,2010)。细胞氧化还原状态被定义为细胞内还原性与氧化性氧化还原活性分子的总和(Potters 等,2010)。由此衍生出细胞器氧化还原状态(如线粒体氧化还原状态)、组织氧化还原状态乃至器官氧化还原状态(Potters 等,2010)。
细胞内的不同细胞器需在特定氧化还原状态下才能正常运作。例如,维持细胞核处于还原状态,对转录因子结合及转录激活至关重要(Hansen 等,2006)。在无功能叶绿体的细胞或处于黑暗环境的光合细胞中,各细胞器按 Eh 值由低到高排序为:线粒体、细胞核、细胞质、内质网、细胞外空间(Hansen 等,2006)。
植物体内高度活跃的光合代谢,进一步增加了氧化还原状态的复杂性(Dietz,2003)。光合作用会产生氧化还原电位极低的中间产物:光驱动的电子传递过程,会将电子从光系统 Ⅰ 的受体位点(中点电位 <−900 毫伏)传递至包括氧气在内的多种受体(Baier 与 Dietz,2005;Blankenship,2002)。
此外,叶绿体中的光合作用涉及膜结合的光合电子传递,这意味着 Eh 与 pH 值存在差异:(1)类囊体膜两侧(类囊体腔与基质)的 Eh 与 pH 值不同;(2)膜表面不同区域的 Eh 与 pH 值也存在差异(Lambers 等,2008)。线粒体中的三羧酸循环也存在类似过程。因此,区室化与氧化还原电位的合理平衡不仅在许多情况下对电子传递动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也对维持电子传递途径相关电位梯度中固有的能量至关重要(Chang 与 Swenson,1997)。
综上,氧化还原状态是细胞功能的关键决定因素,任何严重失衡都可能导致细胞严重损伤甚至死亡(Dietz 与 Scheibe,2004)。以烟草(Nicotiana sylvestris)为例,其叶片线粒体可调节整个细胞的氧化还原稳态,并决定细胞的抗氧化能力(Dutilleul 等,2003)。
过氧化作用
过氧化作用对细胞具有显著危害,具体表现为:破坏细胞膜、氧化巯基、抑制含巯基酶的活性、造成 DNA 链断裂(Ahmad,1992)。线粒体谷胱甘肽的氧化会破坏线粒体完整性,导致吡啶核苷酸氧化,最终影响能量产生;膜脂的过氧化会导致细胞功能异常,甚至引发细胞死亡(Ahmad,1992)。
植物细胞中活性氧(ROS)与活性氮(RNS)的产生,会通过氧化氨基酸侧链改变蛋白质结构(Foyer 与 Noctor,2005)。过氧化作用还会抑制多种酶的活性,因为这些酶的功能受氧化还原状态调控(Ahmad,1992;Chang 与 Swenson,1997;Ding 等,1996;Ghezzi,2005)。严重的蛋白质氧化对细胞而言代价高昂,因为氧化损伤的蛋白质需通过特定蛋白酶降解(Sweetlove 等,2009)。相反,为避免细胞氧化还原状态过度还原造成的有害影响,细胞还需具备耗散途径(Scheibe 等,2005)。
氧化还原稳态
植物的光合作用与同化过程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环境条件的剧烈波动会对生物体产生显著胁迫,尤其是当波动超出正常生理耐受阈值时(DeAngelis 等,2010)。为防止这些剧烈变化导致灾难性氧化损伤,细胞拥有复杂的补偿性缓冲机制网络(Dietz,2003;Hanke 等,2009;Hansen 等,2006;Kandlbinder 等,2003;Lambers 等,2008;Noctor 等,2000)。
含氧光合作用过程中同时存在强氧化剂与强还原剂,这是调控机制的基础(Scheibe 等,2005)。谷胱甘肽、谷氧还蛋白与抗坏血酸参与多种细胞过程,在应对氧化胁迫及调控活性氧(ROS)方面发挥关键作用(Foyer 与 Noctor,2003;Mullineaux 与 Rausch,2005;Noctor 与 Foyer,1998;Sanchez-Fernandez 等,1997;Xing 等,2006)。此外,蛋白质表面可能富集易氧化氨基酸(如半胱氨酸、酪氨酸、色氨酸),这些氨基酸可作为 “诱饵” 或 “牺牲性残基”,从而保护对蛋白质功能更重要的残基免受氧化或延缓其氧化(Saurina 等,2000;Sweetlove 等,2009)。
这些缓冲机制需与更大的氧化还原网络中的信号级联整合,以确保短期响应的有效性;同时,当缓冲能力不足时,细胞需在转录水平启动响应(Hanke 等,2009)。短期与长期机制会根据胁迫强度与类型灵活互动(Scheibe 等,2005)。只要适应机制的能力足够强,细胞稳态就能维持;若胁迫变化过快,基因表达层面的适应无法及时启动,则会引发细胞损伤与死亡(Scheibe 等,2005)。
在含有共生根瘤菌的根瘤中,豆科植物为细菌提供能量,并创造适合固氮酶活性的微氧环境(Marino 等,2009)。对于具备有氧分解代谢能力的生物而言,氧气对固氮作用既有利也有害:它能为固氮酶提供底物(ATP),但也会抑制该酶的活性并阻遏其合成(Hill,1988)。
在共生关系的各个阶段(共生建立、固氮过程、根瘤衰老),均会产生活性氧(ROS)。为应对活性氧的产生,根瘤具备多种酶促与非酶促抗氧化机制(Marino 等,2009)。
氧化还原调节、氧化还原信号传导、植物物候学与全球环境感知
氧化还原区室化还可作为氧化还原信号传导特异性的作用机制(Hansen 等,2006)。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转运活动、植物发育及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氧化还原调节与信号传导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氧化还原相互作用参与质子泵运、膜 energization(膜能量化)、离子通道调节、铁还原、养分吸收、信号转导及生长调节等过程(Dietz,2003;Dietz 和 Pfannschmidt,2011;Kandlbinder 等,2004;Luthje 等,1997;Noctor,2006;Pfannschmidt,2003)。
氧化还原信号还能调节蛋白质与 DNA 的相互作用,并在基因表达、DNA 复制及基因组稳定性中发挥关键作用(Shlomai,2010;Turpaev 和 Litvinov,2004)。从基因转录到翻译、组装与周转,再到通过状态转换和酶活性实现的短期适应,光合作用在几乎所有层面上均受氧化还原作用调控(Dietz,2003)。
许多酶的氧化还原调节对植物发育有显著影响。早在 1949 年,Stout 就发现甜菜生殖发育的诱导与其植株特定部位的氧化还原平衡变化相关(Stout,1949)。根生长、开花、花器官发育、叶片分区及光周期现象均受氧化还原电位调节(Becker 等,2006;Foreman 等,2003;Rosso 等,2009;Sanchez-Fernandez 等,1997;Xing 等,2006)。活性氧(ROS)是调节植物休眠与萌发的关键因子(Bailly 等,2008)。细胞抗氧化剂通过调控从有丝分裂、细胞伸长到衰老与死亡的一系列过程,影响植物生长发育(Foyer 和 Noctor,2005)。
目前已明确,氧化还原调节是植物根据当前环境条件调整代谢与发育的核心要素(Dietz,2003)。氧化还原感知 / 信号传导机制可能是环境变化的主要感知器,并且通常是感知非生物胁迫的重要组成部分(Huner 等,1996)。例如,与冷胁迫感知相关的细胞氧化还原状态,可激活氧化还原响应蛋白,并可能作为信号调控基因表达重构(Yadav,2010)。叶绿体氧化还原感知不仅能响应光照强度,还能应对多种非生物胁迫,进而影响叶绿体和细胞核的基因表达(Baier 和 Dietz,2005;Wilson 等,2006)。
最后,植物的营养状况会影响其氧化还原状态。氮、磷或硫营养缺乏会引发明显的氧化还原变化,并在营养特异性代谢改变的背景下,以特定模式诱导氧化胁迫。例如,氮缺乏会使拟南芥叶片中的抗坏血酸含量增加 5 倍(Kandlbinder 等,2004);磷缺乏会导致抗坏血酸和谷胱甘肽水平升高;而硫缺乏则会使谷胱甘肽水平降至对照水平的 25% 以下(Kandlbinder 等,2004)。
氧化还原信号、植物对生物胁迫的响应及抗病性
氧化还原活性在植物病原菌的生物防治中具有一定作用(Altomare 等,1999)。已知在生物胁迫下,植物体内会积累活性氧(ROS),且不同细胞区室会通过特定的抗氧化系统对其作出响应(Kuzniak,2010)。一种广泛存在的局部防御机制是:植物对病原菌产生 hypersensitive response( hypersensitive response, hypersensitive response,过敏反应),生成活性氧,进而对定殖微生物或邻近根系产生胁迫(Blokhina 等,2003;Bolwell 等,1995;Hartmann 等,2009;Lamb 和 Dixon,1997;Mori 和 Schroeder,2004)。病害抗性的增强很可能是由水杨酸、过氧化氢、谷胱甘肽以及其他潜在未鉴定化合物触发的氧化还原信号共同作用的结果(Mateo 等,2006)。抗坏血酸 – 谷胱甘肽(AsA – GSH)循环是植物细胞中的主要抗氧化途径,它将活性氧防御与氧化还原调控的植物防御机制联系起来(Kuzniak,2010)。基于此,过氧化氢可被视为细胞的 “进攻性武器”,而过氧化氢酶则是 “防御性武器”,因为该酶能将过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气(Voisin,1959)。
氧化还原过程还参与植食性昆虫与植物的相互作用。植物会产生促氧化化合物作为化感防御物质,加剧所有需氧生物的内源性氧化胁迫(Ahmad,1992)。例如,寄主植物中的酚类物质对舞毒蛾(Lymantria dispar)的有害影响已得到广泛认可(Meyer 和 Montgomery,1987;Rossiter 等,1988;Roth 等,1994)。有研究认为,酚类物质在昆虫中肠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有毒的醌类物质,从而降低食物的消化率(Appel 和 Maines,1995)。植食性昆虫通过对促氧化物质或抗氧化物质进行直接解毒,以及利用抗氧化酶等方式应对这种胁迫(Ahmad,1992;Appel,1993;Roth 等,1997)。然而,植物叶片中高含量的化感物质可能会超出昆虫的解毒能力(Lindroth 和 Hemming,1990)。
氧化还原电位、化感作用与寄生植物的识别
在已鉴定的 20000 种化感物质中,许多具有促氧化性并能引发氧化胁迫(Ahmad,1992;Downum,1986;Downum 和 Rodriguez,1986)。例如,万寿菊(Tagetes minuta)的植物毒性作用主要源于其能提高脂质过氧化速率,其精油在此过程中充当 “氧化剂” 角色(Scrivanti 等,2003)。
化感现象与寄生植物对寄主植物的识别过程存在相似之处(Tomilov 等,2006)。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寄生植物(如独脚金属植物 Striga sp.)对寄主因子的感知,是通过氧化还原相关机制实现的(Yoder,2001)。
植物细胞与生理过程中的氧化还原电位和 pH:被忽视的 Eh – pH 相互作用
pH 被视为植物生理学中的关键变量,相关研究和综述已有很多(Kurkdjian 和 Guern,1989;Rengel,2002;Smith 和 Raven,1979),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综述。与氧化还原电位(Eh)和电子传递类似,pH 和质子传递对细胞的能量代谢至关重要,且对植物的物质代谢和分解代谢有显著影响,例如胚胎发生过程中的细胞分裂(Pasternak 等,2002)。水作为细胞生物学中的活性成分,以网络形式存在,这种结构不仅便于蛋白质与其他生物分子之间的电子传递,还能实现质子的快速扩散(Ball,2008)。与氧化还原电位相同,区室化和细胞内 pH 调节也是细胞生理学的关键特征。细胞质中的反应对 pH 变化极为敏感(Taiz,1992)。pH 调节涉及多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Felle,1988;Rengel,2002;Sakano,1998;Smith 和 Raven,1979)。细胞质 pH 可通过将大量质子从细胞质泵入液泡腔来调节,且不同植物物种的液泡 pH 存在差异(Smith 和 Raven,1979;Taiz,1992)。在 pH 调节过程中,Smith 和 Raven(1979)强调,植物会将过量的质子或羟基离子释放到根际环境中。
与氧化还原电位类似,pH 依赖性信号也能调节生理过程,例如缺氧胁迫下的根系水分运输(Tournaire – Roux 等,2003)。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对氧化还原电位(Eh)的研究与对 pH 的研究通常是相互独立的,且 Eh – pH 相互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忽视。这显然是多数研究的局限性,因为 Eh 和 pH 并非相互独立的影响因素:其一,氧化还原反应可能涉及质子转移,尤其是涉及铁、锰、氮等元素氧化态变化的主要化学反应,这些反应还会伴随氢离子(H⁺)的消耗或生成,从而使 Eh 与 pH 相互关联(Hinsinger 等,2003);其二,植物细胞质膜上的氧化还原系统对细胞质 pH 调节具有重要意义(Rengel,2002);其三,在根际环境中,氧化还原过程与 pH 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要理解根系诱导 pH 变化的所有机制,就必须考虑这些氧化还原过程(Hinsinger 等,2003)。因此,对 Eh 和 pH 的分析最好结合两者的相互作用同时进行。
氧化还原电位(Eh)、pH 与微生物
环境中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 pH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环境中细菌群落的代谢类型,因此它们是影响生物活性的重要参数(Billen,1973;Stumm,1966)。例如,固氮螺菌属(Azospirillum spp.)的固氮作用受土壤氧化还原波动、pH 及有机质含量调控(Charyulu 和 Rao,1980)。
氧化还原电位(Eh)对微生物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早在 1934 年,Heintze 就提出可通过土壤 Eh 的变化来区分不同类群的微生物(Heintze,1934)。细菌生长与 Eh 变化直接相关(Kimbrough 等,2006)。在厌氧土壤中,微生物活性和酶活性与 Eh 呈负相关(Brzezinska,2004;Kralova 等,1992;Snakin 和 Dubinin,1980)。此外,根瘤的氧化还原状态被视为豆科植物 – 根瘤菌共生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Marino 等,2009)。
每种微生物都适应特定的 Eh 条件,其特征表现为能在较宽或较窄的 Eh 范围内生长。例如,厌氧细菌只能在极低 Eh 值的狭窄范围内生长;而放线菌属(Actinomyces sp.)、固氮菌属(Azotobacter sp.)等好氧微生物则需要较高的 Eh 值,但能在更宽的范围内生长(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在中度还原条件下(Eh > + 250 mV),真菌的生长量超过细菌;而在高度还原条件下(Eh < 0 mV),细菌的数量则多于真菌(Seo 和 DeLaune,2010)。
频繁且大幅度的氧化还原波动可能对土壤细菌群落的系统发育和生理组成产生强烈的选择压力,并可能促进代谢可塑性或氧化还原耐受机制的形成(Pett – Ridge 和 Firestone,2005)。例如,本土土壤细菌能很好地适应波动的氧化还原环境(Pett – Ridge 和 Firestone,2005)。反过来,微生物为生存而形成的适应或规避策略,会影响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DeAngelis 等,2010)。
尽管关于 Eh 对植物病原菌影响的研究较少,但现有研究均表明,多种植物病原菌的生长发育可能与高 Eh 相关。以下四个例子可印证这一假设:
1.向烟草植株施用过氧化氢,或通过施用羟胺抑制过氧化氢酶(这也会导致细胞内过氧化氢积累),均会诱导花叶病毒的发生(Yamafuji 和 Cho,1948;Yamafuji 和 Fujiki,1947);
2.氧化胁迫可诱导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等植物病原真菌的菌核分化(Patsoukis 和 Georgiou,2007a,c);
3.已知低 Eh 可抑制镰刀菌属(Fusarium sp.)、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等土传病原菌(Blok 等,2000;Shinmura,2004;Takehara 等,2004);
4.施用硝酸根(NO₃⁻,氮的氧化态形式)作为氮肥会引发严重的稻瘟病,而施用铵根(NH₄⁺,氮的还原态形式)则不会诱导稻瘟病发生(Osuna – Canizalez 等,1991)。
同样,每种微生物都适应特定的 pH 范围,超出该范围便无法生存。大多数土壤细菌能在 pH 4.5 – 10 之间生长(Baas Becking 等,1960)。中性土壤中微生物多样性最高,酸性土壤中多样性最低(Hinsinger 等,2009;Lauber 等,2009)。微生物的生态行为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它们适应较宽或较窄 pH 范围的能力,以及能够实现繁殖的 pH 范围上限和下限(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例如,硫细菌的潜在生存环境非常广泛,而藻类几乎遍布各处(Baas Becking 等,1960)。在土壤和水中广泛存在的腐生细菌,能在多种环境条件下生存(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在碱性土壤中,分布广泛的放线菌数量会增加(Roger 和 Garcia,2001),而木霉菌属(Trichoderma)则更偏好酸性环境(Steyaert 等,2010)。因此,有研究认为 pH 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的主要因素(Fierer 和 Jackson,2006;Lauber 等,2009)。
与病原菌类似,适应特定生境和特殊生态条件的微生物,其适宜的 pH 范围通常较窄(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许多病原真菌更倾向于在略低的 pH 条件下生长。例如,高 pH 会抑制瓜果腐霉(Aphanomyces cochlioides)和腐霉属(Pythium spp.)真菌的生长(Payne 等,1994);当土壤 pH 提高到 7 以上并添加黏土时,亚麻枯萎病(由镰刀菌引起)会受到抑制(Höper 等,1995);当 pH 高于 6 时,菊科扶郎花(Gerbera)的镰刀菌病害会减轻(Minuto 等,2008)。
相反,多项研究表明,低 pH 会抑制病毒的增殖。在水中,当 pH 低于某个临界值时,病毒几乎能被完全去除(Guan 等,2003)。在沉积物中,病毒丰度与 pH 呈显著相关性,这表明病毒对低 pH 较为敏感(Kyle 等,2008)。然而,有些病毒与古菌(生活在酸性热泉等极端环境中的生物)相关联(Happonen 等,2010)。
在植物中,番茄斑萎病毒和烟草花叶病毒等病毒的活性会随 pH 变化(Best 和 Samuel,1936)。关于低 pH 影响病毒增殖的机制,已有多种解释:其一,番茄斑萎病毒表面有一种糖蛋白,它对病毒结合敏感细胞的能力至关重要,而在低 pH 条件下,这种糖蛋白会发生 pH 依赖性构象变化(Pekosz 和 Gonzalez – Scarano,1996;Whitfield 等,2005);其二,如在南方豇豆花叶病毒中观察到的那样,pH 会改变离子通道的电导率(Helrich 等,2001);其三,对于芜菁黄花叶病毒,pH 会诱导其 RNA 解聚和降解(Sam 等,1991)。
同时,已知微生物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改变周围环境的 Eh 和 pH,且其改变能力远强于其他生物(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Potter(1911)可能是最早注意到微生物培养会导致 Eh 降低这一现象的学者。在土壤中,广泛分布的腐生菌和厌氧病原菌会使 Eh 降低(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在好氧土壤中,微生物消耗氧气,进而导致 Eh 下降(Bohrerova 等,2004;Kralova 等,1992)。当土壤含水量增加时,Eh 会降低,由于微生物快速消耗氧气,导致氧气部分或完全流失,最终形成厌氧土壤环境(Savant 和 Ellis,1964)。
在培养基中,初始 pH 会因微生物的代谢活动而发生改变并受到调控(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真菌能够改变其菌丝周围微环境的土壤条件,如 pH(Garrett,1963;Twining 等,2004)。微生物活动通常会导致环境酸化(Rabotnova 和 Schwartz,1962)。在土壤中,这种酸化可通过吸附复合体的缓冲能力得到补偿(Roger 和 Garcia,2001)。
田间尺度下的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与 pH 值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与 pH 值的变异性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的正常波动范围为 – 300 至 + 900 毫伏(mV)。不同学者研究表明,渍水土壤的 Eh 值低于 + 350 至 + 250 毫伏,干旱土壤的 Eh 值则高于 + 380 至 + 400 毫伏(Pearsall & Mortimer,1939;Pezeshki,2001)。
根据 Kaurichev 与 Shishova(1967)的研究,可依据 Eh 值将土壤条件划分为四个主要类别:
·通气性土壤:Eh 值高于 + 400 毫伏;
·中度还原土壤:Eh 值介于 + 100 至 + 400 毫伏之间;
·还原土壤:Eh 值介于 – 100 至 + 100 毫伏之间;
·强还原土壤:Eh 值介于 – 100 至 – 300 毫伏之间。
在好氧条件下,耕作土壤的 Eh 值多处于 + 300 至 + 500 毫伏范围内(Macías & Camps Arbestain,2010)。而在灰化土中,Eh 值可高达 + 750 毫伏(Kaurichev & Shishova,1967)。
多数耕作土壤的 pH 值介于 4 至 9 之间,但在酸性硫酸盐土壤中可测得低于 3 的 pH 值,在碱土中可测得高于 10 的 pH 值(Brady & Weil,2010)。值得注意的是,土壤中 pH 值与 Eh 值呈负相关关系(Bohrerova 等,2004;Van Breemen,1987)。
空间变异性
即使在极短距离内,土壤 Eh 值与 pH 值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Hinsinger 等,2009;Yang 等,2006)。例如,直径为 6-7 毫米的湿润土壤团聚体,其中心的氧化还原电位比表面低 100 至 200 毫伏(Kaurichev & Tararina,1972)。
众多学者还发现,Eh 值与 pH 值会随土壤深度发生明显变化(Bohrerova 等,2004;Mansfeldt,2003;Rousseau,1959;Snakin 等,2001)。以俄罗斯的灰色森林土为例,深度为 7 厘米的 A 层土壤,其 Eh 值比深度为 116 厘米的 C 层低 80 毫伏,pH 值则高 0.9 个单位(Snakin 等,2001)。此外,土壤中的生物还会导致特定土层内 Eh 值与 pH 值出现显著异质性(Snakin 等,2001)。
时间变异性
土壤 Eh 值与 pH 值还具有较高的时间变异性,存在日变化周期,且受季节影响显著(Mansfeldt,2003;Snakin 等,2001)。Sabiene 等(2010)的研究还记录了其随气候条件和土壤湿度变化的年际差异。
淹水会对 Eh 值和 pH 值产生显著影响,在有机土壤中尤为明显(Kashem & Singh,2001)。Balakhnina 等(2010)发现,淹水后几小时内,土壤 Eh 值便从 + 543 毫伏骤降至 + 70 毫伏;而排水后几天内,Eh 值又会恢复至初始水平。
氧化还原动力学的影响因素
土壤氧化还原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微生物催化作用调控,因为土壤微生物会产生催化酶(Fenchel 等,1998)。微生物活性本身也受 Eh 值和 pH 值影响,同时还会因黏土的存在而增强,黏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充当表面催化剂(Filip,1973;Theng & Orchard,1995);
2.吸附微生物所需的有机质(Wardle,1992);
3.为微生物提供保护性微生境(Heijnen & van Veen,1991)。
Davet(1996)的研究显示,向砂质土壤中添加黏土后,土壤中的微生物生物量(细菌和真菌)会显著增加。
土壤的缓冲能力
面对如此高的时间变异性,多位学者认为土壤对 Eh 值和 pH 值的缓冲能力是一项重要参数。Eh 缓冲能力决定了土壤氧化还原条件的变化趋势,尤其影响土壤对电子输入的响应速度和幅度(Von de Kammer 等,2000)。
上述学者提出了 “总还原能力(TRC)” 这一参数的计算方法,即某一环境中还原态组分可提供的电子数量。与之类似,Heron 等(1994)考虑了氧气、硝酸盐、铁、锰和硫酸盐等主要电子受体,计算出 “氧化能力(OXC)”,该能力代表某一环境可接受的电子数量。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pH 值与植物生长
除了淹水土壤中极低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外,在全植物研究范畴中,Eh 值的受关注度较低。植物生长的 Eh 值适宜范围为 + 300 至 + 700 毫伏(Volk,1993),还原条件(<+350 毫伏)对多数植物生长具有显著限制作用。
相关研究实例如下:
·Dwire 等(2006)发现,河岸植物物种丰富度和总植被覆盖度与 10 厘米和 25 厘米深度土壤的 Eh 值呈正相关;
·Pennington 与 Walters(2006)研究表明,在 Eh 值介于 + 400 至 + 450 毫伏的过渡带,5 年生树木的纵向生长量更大、存活率更高,而在 Eh 值介于 + 250 至 + 380 毫伏的低地,树木生长和存活表现较差;
·Carter(1980)发现,当 Eh 值低于 332 毫伏时,甘蔗的年产量每天会减少 0.2 至 0.3 吨 / 公顷;
·Husson 等(2001;2000b)在越南酸性硫酸盐土壤中的研究显示,在还原条件下,Eh 值升高会使水稻产量大幅增加;而在氧化条件下,Eh 值升高则会导致水稻产量下降。当水稻根系周围土壤形成黄钾铁矾时(表明局部 Eh 值约为 + 400 毫伏),水稻产量达到最高。
植物对氧化还原条件的耐受性
不同植物对氧化还原条件变化的耐受性差异显著。对河岸草甸的研究表明,观测到的生物多样性与水文和土壤 Eh 值形成的剧烈环境梯度密切相关(Dwire 等,2006)。
同样,在人工湿地中,不同植物群落带与 Eh 值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表明在广泛的湿地生态系统中,可利用自然植物群落来表征土壤的氧化状态(Pennington & Walters,2006)。
土壤 pH 值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土壤溶液的 pH 值也是影响植物生长的关键环境因素(Brady & Weil,2010)。与氧化还原条件类似,不同植物对酸性和(或)碱性条件的耐受性差异较大,但所有植物都有一个相对较窄的最适 pH 值范围。
多数耕作作物在微酸性至近中性的土壤中生长良好,仅有少数物种能在 pH 值低于 4.5 或高于 9 的土壤中生长(Brady & Weil,2010)。一些植物如甘薯(Ipomea batatas)、木薯(Manihot esculenta)和茶树(Camellia sinensis),具有在酸性土壤中生长的能力。
强酸性或强碱性条件会影响植物生长,主要原因在于 pH 值会显著影响养分的有效性和离子毒性风险(Brady & Weil,2010;Marschner,1991)。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pH 值、养分溶解度及植物吸收
在复杂的化学和生物环境中,Eh 值与 pH 值是影响多种养分迁移能力的重要因素(Gambrell & Patrick,1978;Laanbroek,1990)。
基于热力学定律,Eh-pH 图(即 Pourbaix 图,Pourbaix,1945)可展示溶液中某一元素不同化学形态的稳定区域,该区域是 Eh 值与 pH 值的复合函数。在热力学上可能发生的反应中,特定时间点占主导地位的反应由氧化还原动力学决定(Chadwick & Chorover,2001)。因此,需谨慎考虑异质且动态变化的土壤中氧化还原过程的复杂动力学(Sparks,2001)。
同时,Eh 值与 pH 值也会影响这些动力学过程,因为它们会作用于微生物活性,而微生物活性又会催化相关反应(Fenchel 等,1998)。反过来,土壤中的各种元素也会影响 Eh 值与 pH 值,尤其是氧化还原价态变幅大的元素(如氮、磷、硫)和高浓度元素(如铁)。
图 1 氮(N)的普尔拜克斯图(Pourbaix diagram),该图展示了在 25°C、浓度为 100 微摩尔(μM)的溶液中,氮的不同存在形态随氧化还原电位(Eh,单位为伏特 V)和 pH 值变化的关系。此图改编自 MEDUSA 软件,来源为 Puigdomenech 2009–2011 年的研究成果。
注:Pourbaix diagram 是电化学领域常用图表,标准中文译名为 “普尔拜克斯图”,也常被称为 “电位 – pH 图”,用于直观呈现物质在不同电位和 pH 条件下的稳定存在形态。
氮(N)
如图 1 所示,Pourbaix 图展示了水溶液中不同形态氮在特定 Eh 值和 pH 值下的优势存在区域,由此可见氮循环与 Eh 值、pH 值密切相关。在氧化条件下(pH 值为 7 时,Eh>500 毫伏),氮在热力学上的稳定形态为硝酸根离子(NO₃⁻);而在还原或中度氧化条件下(pH 值为 7 时,Eh<400 毫伏)且 pH 值低于 9.2 时,铵根离子(NH₄⁺)则占主导地位。
由于硝酸根离子和铵根离子均具有可溶性,Eh 值与 pH 值主要影响植物吸收氮的形态。植物吸收氮的形态还会对细胞 pH 值调节产生显著影响(Marschner,1995)。此外,植物利用铵根离子合成蛋白质,而吸收硝酸根态氮(NO₃⁻-N)时,需消耗大量能量将其还原为铵根态氮(NH₄⁺-N)(Marschner,1995)。同时,硝酸根离子溶解度高,存在流失和污染的风险。最后,植物吸收氮的形态还会对根际 pH 值以及植物对其他阳离子和阴离子的吸收产生显著影响(Hinsinger 等,2003;Marschner,1995)。
磷(P)
在田间条件下,植物根系吸收的是土壤溶液中溶解的无机磷,主要形态为一价磷酸根离子(H₂PO₄⁻)。相较于二价磷酸根离子(HPO₄²⁻),一价磷酸根离子更容易通过细胞质膜(Hinsinger 等,2003)。
在酸性土壤中,一价磷酸根离子占主导地位;而在碱性土壤中,二价磷酸根离子则是绝对优势形态。但根质外体的 pH 值通常低于 6,因此即使在高 pH 值土壤中,植物通过细胞膜吸收的磷仍以一价磷酸根离子为主(Hinsinger 等,2003)。此外,已知许多植物在磷缺乏时,会通过根系分泌质子来酸化根际,以应对磷胁迫(Hinsinger 等,2009)。
Eh 值与 pH 值还会通过影响金属离子(如锰、铝、铁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或碳酸钙的溶解度,间接影响磷的有效性。这些物质会与磷酸根离子结合或吸附磷酸根离子,导致其无法被植物吸收(Brady & Weil,2010;Kemmou 等,2006;Phillips,1998;Sallade & Sims,1997;Vadas & Sims,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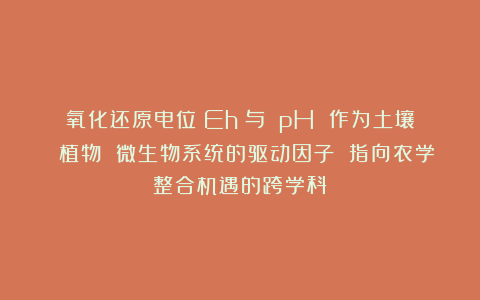
另外,一价磷酸根离子 / 二价磷酸根离子(H₂PO₄⁻/HPO₄²⁻)体系在细胞质 pH 值缓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erendas & Schurr,1999;Hinsinger 等,2003)。
图 2 硫(S)的普尔拜克斯图(Pourbaix diagram),该图展示了在 25°C、浓度为 100 微摩尔(μM)的溶液中,硫的各种存在形态随氧化还原电位(Eh,单位为伏特 V)和 pH 值变化的关系。此图改编自 MEDUSA 软件,来源为 Puigdomenech 2009–2011 年的研究成果。
硫(S)
在农业生产中,硫缺乏现象较为少见,尤其在好氧条件下。在正常的田间 Eh-pH 条件下,硫在热力学上的稳定形态为硫酸根离子(SO₄²⁻)(图 2),该形态可被植物运输并轻易吸收。
由于硫酸根离子还原为硫化氢(H₂S)仅在低 Eh 值和特定 pH 值条件下发生(pH 值为 6 时,Eh 约为 – 100 毫伏),因此 Eh-pH 值对硫溶解度的直接影响仅限于渍水或淹水田间。在这类田间,尤其是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土壤中,极低的 Eh 值会导致硫酸根离子还原为硫化氢,而硫化氢对植物具有强毒性(Ponnamperuma,1972)。
在较高的 Eh 值和 pH 值条件下,硫的有效性也会受到间接影响,因为 Eh 值和 pH 值会改变土壤对硫酸根离子的吸附能力(Lefroy 等,1993)。相反,在自然环境中,硫是决定 Eh-pH 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Baas Becking 等,1960)。此外,还原态硫(硫化氢或二硫化亚铁)的氧化(多数情况下由自养细菌如硫杆菌属完成)会产生硫酸,进而导致土壤酸化(Dent,1993)。
铁(Fe)
Eh 值和 pH 值均会对铁的溶解度产生显著影响。植物吸收的是可溶性的二价铁离子(Fe²⁺)。在低 Eh 值条件下,土壤溶液中二价铁离子浓度较高;当 Eh 值升高至 + 350 毫伏以上(pH 值为 5 时),由于铁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形成,二价铁离子浓度会迅速下降(Frohne 等,2011)。
在低 Eh 值和特定 pH 值条件下,二价铁离子毒性现象较为常见;反之,在高 Eh 值和特定 pH 值条件下,植物可能出现缺铁症状(Tanaka 等,1966)。在自然环境中,铁对土壤的 Eh-pH 特征具有重要影响(Baas Becking 等,1960),且铁的还原 – 氧化过程是土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氧化还原阈值(Chadwick & Chorover,2001)。
钾(K)、钠(Na)与铝(Al)
钾、钠、铝的溶解度不受 Eh 值直接影响,因为这些元素仅有唯一的氧化还原价态:钾离子(K⁺)和钠离子(Na⁺)为 + I 价,铝离子(Al³⁺)为 + III 价,它们无法进行电子交换。
钾
钾的有效性主要与土壤 pH 值、黏土含量及黏土类型相关。pH 值升高会增强钾的固定作用,因为这会使钾离子更容易向胶体表面移动;而钾离子越靠近胶体表面,就越容易被 2:1 型黏土固定,这类黏土对钾的固定能力强且固定量较大(Brady & Weil,2010)。
钠
碱土的 pH 值较高,原因是氢离子(H⁺)会取代黏土胶粒上吸附的钠离子(Na⁺),导致氢氧根离子(OH⁻)浓度升高。钠交换百分比(SEP)的定义为交换性钠与阳离子交换量的比值,该指标与土壤 pH 值呈正相关(Abrol 等,1988)。
碱土中过量的交换性钠会对土壤物理性质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破坏土壤团聚体结构、降低土壤对空气和水的渗透性(Abrol 等,1988),并改变土壤的 Eh 值。此外,交换性钠过量导致的高 pH 值还会间接影响其他养分(如磷、钙、镁、锰、锌)的浓度(Abrol 等,1988)。
铝
铝的溶解度主要由土壤 pH 值决定,同时也受土壤有机质和黏土含量影响。当 pH(KCl)值降至 4.3 以下时,交换性铝含量会迅速增加。铝是导致土壤酸性的主要因素:水分子与铝离子结合形成六水合铝离子(Al (OH₂)₆³⁺),该过程会促进水的解离并产生质子(Manahan,2001)。一个铝离子(Al³⁺)最多可释放出三个氢离子(H⁺)(Brady & Weil,2010)。
图 3 锰(Mn)的 Pourbaix 图(电位 – pH 图),展示了在 25°C、浓度为 100 微摩尔 / 升(μM)的溶液中,锰的不同存在形态随氧化还原电位 Eh(单位:伏特,V)和 pH 值变化的关系。该图改编自 MEDUSA 软件,来源为 Puigdomenech(2009–2011)。
微量营养素
多种微量营养素(如锰、铜、锌)的有效性受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的强烈影响。
有研究表明,生物活动会对锰、锌、铜、钼、钴、硅、镍及其他多种微量营养素的有效性、溶解度或氧化还原状态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Reddy 等人,1986)。例如,锰的普尔拜克斯图(图 3)显示,二价锰离子(Mn²⁺)的溶解程度是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碱性土壤中,好氧条件下可能出现锰缺乏的情况。氧化还原电位(Eh)降低会提高锰的生物有效性(Schwab 和 Lindsay,1982),而土壤酸碱度(pH)较低时,锰毒害现象则十分常见(Brady 和 Weil,2010)。
同样,多种微量营养素的普尔拜克斯图(未展示)表明,以下情况更可能导致微量营养素缺乏:(1)铜缺乏多见于高 pH 值和 / 或低 Eh 值环境;(2)锌缺乏多见于高 pH 值环境;(3)镍缺乏多见于极低 Eh 值或高 pH 值环境;(4)钼缺乏多见于低 Eh 值和低 pH 值环境。土壤溶液中铜和镍的浓度会随氧化还原电位(Eh)升高而增加,这一田间观测结果证实了上述结论(Frohne 等人,2011)。
植物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的影响
植物能显著改变其根际环境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Hartmann 等人,2009)。植物根系创造的条件可促进根际独特微生物群落的形成,且这种影响程度极深 —— 进化过程已促使土壤生物适应了这一特定生态位(Hartmann 等人,2009;Lambers 等人,2009;Sanon 等人,2009)。
这种改变可能来自两个途径:一是根系分泌物的直接作用;二是特定微生物优先繁殖后的间接作用,这些微生物同样会改变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
适应高还原环境的植物根系,会通过充满空气的细胞间隙系统获取必需的氧气(Flessa 和 Fischer,1992a)。水稻等湿地植物能够提高根际环境的氧化还原电位(Eh),其主要方式是通过通气组织运输氧气(Evans,2004;Gilbert 和 Frenzel,1998;Gotoh 和 Tai,1957)。这种提高根际氧化还原电位(Eh)的能力,可保护植物免受还原性物质的毒害,且该能力与植物的营养状况相关。例如,在缺钾的稻田土壤中施用钾元素,可提高水稻根系的氧化能力、升高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减少活性还原性物质和二价铁的含量,并降低耗氧微生物的数量(Chen 等人,1997)。
在好氧条件下,多种双子叶栽培植物(如豌豆、箭筈豌豆、向日葵)的根际环境中,根尖附近的氧化还原电位(Eh)会降低,这可能是由于根系释放了还原性分泌物(Flessa 和 Fischer,1992b)。
根际环境的酸碱度(pH)也会被植物根系和土壤微生物改变。有研究指出,根际 pH 值可能比土体土壤 pH 值高 1-2 个单位或低 1-2 个单位,且在距离根系表面 2-3 毫米的范围内,就能检测到这种差异(Chaignon 等人,2002;Hinsinger 等人,2009;Hinsinger 等人,2003;Youssef 和 Chino,1989)。Miller 等人(1991a)对大麦和白三叶草的研究显示,根尖处根际环境的酸碱度(pH)高于远离根尖的区域。
植物吸收营养元素的形态会显著影响根际酸碱度(pH),其中氮元素的影响尤为突出 —— 铵根离子(NH₄⁺)和硝酸根离子(NO₃⁻)占植物吸收的阴阳离子总量的 80%(Marschner,1995)。微生物介导的氮氧化过程会导致酸碱度(pH)发生显著变化(Hinsinger 等人,2009),具体原因如下:(1)植物根系吸收铵根离子(NH₄⁺)时,需释放氢离子(H⁺)以平衡多余的正电荷(Hinsinger 等人,2003;Raven 和 Smith,1976);(2)相反,植物吸收硝酸根离子(NO₃⁻)时,会释放氢氧根离子(OH⁻)以平衡多余的负电荷,而多余的氢氧根离子(OH⁻)部分会被 “生化 pH 缓冲系统” 中和(Raven,1986;Raven 和 Smith,1976)。
除根系外,许多土壤微生物(如外生菌根真菌、腐生真菌或病原真菌)也能产生有机酸,使根际环境酸化(Hinsinger 等人,2009)。但改变根际环境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需要植物消耗能量。在一年生植物中,30%-60% 的光合固定碳会被转运到根系,其中很大一部分(高达 70%)会释放到根际环境中(Neumann 和 Römheld,2000)。例如,小麦、大麦等谷物会将 20%-30% 的总同化碳转移到土壤中,而牧草则会将 30%-50% 的同化产物转运到地下部分(Kuzyakov 和 Domanski,2000)。因此,植物根系以多种形式释放的有机化合物(即根际沉积),占总光合产物的 20%-50%,最高可达 80%(Gobat 等人,1998)。
除对根际环境产生短期影响外,植物还会长期影响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因为它们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来源。植物生物量是否归还土壤,会对土壤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大且长期的影响。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酸碱度(pH)与土壤有机质
有机质是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的主要因素之一(Oglesby,1997)。生物可利用的有机质作为电子库,构成了土壤还原能力的主体(Chadwick 和 Chorover,2001;Lovley 等人,1998)。微生物可对有机质进行部分可逆的还原,而有机质在此过程中起到电子穿梭体的作用,即作为可移动的电子载体(Lovley 等人,1998)。有机质是土壤中最丰富的电子来源,在分解过程中可视为 “电子泵”,为土壤中氧化性更强的物质提供电子(Chesworth,2004)。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会导致氧化还原电位(Eh)降低:在易分解有机质丰富的土壤中,氧化过程会消耗大量氧气,进而形成具有还原性的有机化合物(Lovley 等人,1998)。新鲜有机质是土壤中还原性最强的组分,因此热力学稳定性最低;其次是死亡生物量和大部分土壤有机质;而有机醌类分子的抗氧化性最强(Macías 和 Camps Arbestain,2010)。
有研究显示,新鲜秸秆的氧化还原电位(Eh)约为 + 150 毫伏(pH 值 5.5-6)。在堆肥过程中,氧化还原电位(Eh)会从初期的 0 毫伏(pH 值 7.7)变化到堆肥结束时的 + 300-+400 毫伏(Miller 等人,1991b)。综上,有机质的质量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Eh)及其缓冲能力。
有机质也是缓冲土壤酸碱度(pH)的主要因素之一(Magdoff 和 Bartlett,1984),有助于将土壤 pH 值维持在中性至微酸性范围(Brady 和 Weil,2010)。在低 pH 值环境中,土壤有机质会与铝形成络合物,这是土壤中重要的 pH 缓冲过程(Skyllberg 等人,2001)。在高 pH 值环境中,有机质会与钙、镁等非酸性阳离子形成可溶性络合物,这些络合物易随淋溶作用流失,从而导致土壤酸化(Brady 和 Weil,2010)。
另一方面,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是调控腐殖化过程速度和强度的主要因素(Reddy 等人,1986;Rusanov 和 Anilova,2009)。在游离氧(O₂)存在的氧化条件下,有机质的分解速率最快(Macías 和 Camps Arbestain,2010)。当缺乏游离氧(O₂)或硝酸根(NO₃⁻)、四价锰(Mn⁴⁺)、三价铁(Fe³⁺)、硫酸根(SO₄²⁻)等无机氧化剂时,会发生发酵过程,此时有机分子会作为电子受体被利用(Reddy 等人,1986;Ugwuegbu 等人,2001)。
在全球碳循环中,碳以固体有机质形式存在于土壤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氧化还原电位(Eh)。在氧化性土壤中,有机质中碳的留存时间可短至 1 年;而在高度还原的环境中,这一留存时间可长达数千年(Chesworth,2004)。有机质的分解速率还受三个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相关的参数影响:(1)微生物代谢类型;(2)细菌活性效率;(3)土壤系统提供电子受体的能力(Reddy 等人,1986)。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酸碱度(pH)与土壤发生
土壤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是影响土壤发生方向的关键因素(Chadwick 和 Chorover,2001;Chesworth,2004;Chesworth 等人,2006;Chesworth 和 Macias,2004)。这种发生方向可通过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Eh-pH)图(图 4)来呈现。土壤的化学演化本质上由质子和电子的迁移所决定,其中电子迁移发生在以有机质为主要来源、以大气氧为主要受体的体系中(Chesworth 和 Macias,2004)。
质子和电子迁移的共同作用,使大多数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且该范围包含三个特征维度:酸性、碱性和水成作用(即土壤中水分的永久或临时饱和状态)。其中,酸性维度涵盖三种主要土壤发生过程的演化路径:灰化过程、铁铝化过程和火山灰土化过程(Chesworth 和 Macias,2004);钙质土、钠质土和盐土沿碱性维度演化;泥炭土则沿水成作用维度演化 —— 过量水分会抑制土壤形成过程中的好氧因素。
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Eh-pH)图对于研究酸性硫酸盐土尤为重要。这类土壤含有黄铁矿(FeS₂),氧化还原电位(Eh)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其酸碱度(pH),因为黄铁矿氧化会产生大量硫酸。含有黄铁矿的潜在酸性硫酸盐土处于还原状态,当发生氧化(pH 值 4 时,Eh>50 毫伏)时,黄铁矿氧化会导致土壤强烈酸化,进而形成实际酸性硫酸盐土(Dent,1993;Husson 等人,2000b)。
图 4 展示土壤类型分布随 pH 值和 Eh 值变化的 Pourbaix 图。改编自 Chesworth 等人(2004)、Snakin 等人(2001)、Dent(1993)、Husson 等人(2000b)以及 Macias 和 Camps Arbestain(2010)的研究。
氧化还原电位(Eh)、酸碱度(pH)与环境问题
通常情况下,土壤溶液中重金属和类金属污染物的浓度受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的共同影响。镉(Cd)和铅(Pb)的浓度在低 Eh 值环境中较低,随 Eh 值升高而增加,这与它们与溶解有机碳、锰的相互作用以及硫化物等沉淀物的形成有关(Frohne 等人,2011;Stepniewska 等人,2009)。添加有机质会降低镉(Cd)的溶解度,因为这会导致 Eh 值降低和 pH 值升高(Kashem 和 Singh,2001)。相反,砷(As)和锑(Sb)的各种形态浓度会随土壤 Eh 值升高而急剧下降,这表明低 Eh 值环境会促进这些化合物的迁移(Frohne 等人,2011)。
汞在氧化形态(Hg²⁺离子)下溶解度高,但易被有机质吸附。在有硫存在且 Eh 值较低(<−100 毫伏)的环境中,汞会以不溶性硫化汞(HgS)的形式沉淀。甲基汞形态的汞溶解度高且毒性强,其仅由甲基化微生物(尤其是梭菌属)产生,而这类微生物仅在特定的 Eh-pH 范围内(Eh 值介于−400 毫伏至 + 100 毫伏之间)繁殖(Billen,1973)。
此外,氧化还原反应会调控铁氧化物和锰氧化物的转化与活性,这类氧化物对重金属和类金属污染物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是这些污染物的主要汇(Huang 和 Germida,2002)。
氧化还原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生物修复过程。例如,腐殖酸可作为电子受体,促进氯乙烯和二氯乙烯的厌氧微生物氧化(Bradley 等人,1998)。阿特拉津的生物转化过程也属于氧化反应,该过程会被锰促进、被抗氧化剂抑制(Masaphy 等人,1996);在氧化性土壤中(Eh>392 毫伏),这种生物转化速度极快,而在还原环境中(Eh<169 毫伏,如湿地土壤),转化速度会大幅减慢,阿特拉津可在其中留存数月(DeLaune 等人,1997)。
在修复过程中,氧化还原电位(Eh)可作为土壤健康的指标,也可作为多环芳烃污染土壤修复速率的指标(Owabor 和 Obahiagbon,2009;Ugwuegbu 等人,2001)。此外,基于生物降解、扩散、稀释、吸附、蒸发以及污染物的化学和生化稳定等过程,氧化还原缓冲能力还可作为评估自然衰减 / 原位修复长期效果的工具(Von de Kammer 等人,2000)。
在大多数土壤中,氧化还原反应产生或消耗三种主要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 N₂O、甲烷 CH₄、二氧化碳 CO₂)的过程,受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碳源以及氧气(O₂)、四价锰(Mn⁴⁺)、三价铁(Fe³⁺)、硝酸根、硫酸根或氢等电子受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调控(Li,2007)。温度、湿度、酸碱度(pH)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与土壤一氧化二氮(N₂O)、甲烷(CH₄)或二氧化碳(CO₂)排放相关的生化或地球化学反应(Li,2007)。
甲烷(CH₄)的生成与排放过程受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调控(Wang 等人,1993)。一氧化二氮(N₂O)的排放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相关(Kralova 等人,1992;Masscheleyn 等人,1993;Wlodarczyk 等人,2003;Yu 和 Patrick,2003),也与土壤酸碱度(pH)相关 —— 因为 pH 值会影响产生一氧化二氮(N₂O)和氮气(N₂)的三个关键过程: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以及硝酸根异化还原为铵根的过程(Simek 和 Cooper,2002)。
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还会共同影响一氧化二氮(N₂O)和甲烷(CH₄)的排放:当 pH 值升高时,一氧化二氮(N₂O)和甲烷(CH₄)生成量最低的 Eh 值范围会向氧化还原电位(Eh)刻度的更低端移动(Yu 和 Patrick,2003)。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与农学
氧化还原电位与酸碱度的测定
在农学领域应用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时,主要难点之一在于这两个参数的测定,尤其是好氧土壤中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观点有时存在争议,多篇综述文献均体现了这一点(Bartlett & James, 1993;De Mars & Wassen, 1999;Fiedler 等,2007;Gantimurov, 1969;Greenland & Hayes, 1981;Kaurichev & Orlov, 1982;Kovda, 1973;Rabenhorst 等,2009;Snakin 等,2001;Unger 等,2008;Zakharievsky, 1967)。
这些综述指出了两个主要问题:
1.仪器的质量与可靠性,氧化还原电位测定仪器尤为突出。目前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电极,但电极可能出现渗漏或极化现象,从而干扰测定结果。
2.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变异性较强,这导致取样和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受限,需要重点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制定相应规程,确保在合适的尺度下,测定结果可靠且解读合理。自 1929 年雷梅佐夫(Remezov)首次测定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以来,该类电极的研发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已有关于氧化还原电位电极选择与使用的建议(Fiedler 等,2007;Snakin 等,2001)。但仍需密切关注,最大程度降低测定结果的干扰风险;同时,还需准确界定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的变异性,以便在不同尺度上实现取样和测定方法的标准化。
图 5 基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的农艺限制因素综合分析及植物生长最适条件估算。其中,“Eh” 是土壤学专业术语 “氧化还原电位” 的英文缩写,全称为 “Oxidation-Reduction Potential”;“pH” 为表示溶液酸碱度的通用符号。
此外,氧化还原电位与酸碱度并非相互独立。例如,在厌氧土壤中,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会随酸化过程升高,随碱化过程降低(Van Breemen, 1987)。基于此,测定氧化还原电位时的酸碱度数值应系统记录。
对氧化还原电位相关文献的综述发现,研究中仅偶尔将氧化还原电位与酸碱度关联,且在研究过程中,很少关注二者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下,不同研究之间难以进行对比,这也是氧化还原电位在农学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部分原因。
最后,氧化还原电位并非唯一反映电子活性的指标,它还与质子活性相关(Fougerousse, 1996;Orszagh, 1992)。为更有效地界定氧化还原状态,在与生命体相关的多个学科中,包括生物物理学,均采用了 rH₂这一化学概念(Deribere, 1949;Fougerousse, 1996;Huybrechts, 1939;Orszagh, 1992;Rabotnova & Schwartz, 1962;Vincent, 1956;Vlès, 1927, 1929)。rH₂的定义类比于 pH,表达式为–log [H₂],其中 [H₂] 是水分子与溶质物种间发生电子交换后,可能形成的分子氢的热力学活性(Orszagh, 1992)。
在农学领域,部分学者提出采用 pe 值(电子电位),其定义为–log [e⁻],其中 [e⁻] 是假设的电子活性(Lindsay, 1979;Sillen & Martell, 1964;Sposito, 1989;Stumm & Morgan, 1981;Truesdell, 1969)。也有学者提出将 pe+pH 作为土壤的氧化还原参数(Lindsay, 1983)。目前,如何最恰当地界定氧化还原状态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图的应用
自克鲁姆拜因(Krumbein)和加勒尔斯(Garrels)于 1952 年首次将普尔拜克斯图(Pourbaix diagrams,即电位 – pH 图)应用于地球科学领域后,该图已被应用于土壤化学、地球化学、水生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在地球化学领域,一项针对 6200 多组测定数据的研究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1.土壤、水体等环境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可从多方面用于界定该环境的特征。
2.自然环境的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特征主要由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铁和硫的氧化还原对决定(Baas Becking 等,1960)。
在农学领域,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图通常用于渍水土壤研究,稻田研究尤为常见。在这类变化迅速的环境中,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是关键参数,普尔拜克斯图是理解其化学过程的有效工具(Ponnamperuma, 1972)。相比之下,针对好氧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研究较少。
尽管好氧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研究数量有限,但现有研究表明,氧化还原电位可作为界定田间条件的有效农学工具。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斯纳金(Snakin)等人(2001)将土壤液相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作为生态指标。通过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图,这些学者能够将环境单元划分为不同类别,划分依据包括:
1.生态系统类型:农业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
2.植被类型:针叶林、阔叶林、草甸、草甸草原和草原植被。
3.土壤类型:灰化土、灰色森林土、黑钙土和栗钙土(农业群落和自然群落分别划分)。
他们还利用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图,通过向量表征农业土壤与原始未开垦环境之间的差异程度。
农业措施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与酸碱度的影响
有四类主要农业措施会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分别是土壤改良剂(有机或化学改良剂)施用、水分管理、土地整理和作物轮作。
施用石灰和 / 或有机质等改良剂是调节土壤酸碱度的常用方法(Brady & Weil, 2010;Whalen 等,2000)。目前已提出多种通过施用石灰调节土壤酸碱度的方法,尤其针对铝毒问题(Dietzel 等,2009)。赫贝尔(Herbel)等人(2007)提出使用硝酸钠(NaNO₃)或羟基氧化锰等化学物质来稳定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除了专门用于改善土壤不良化学特性的措施外,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也会对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产生影响。例如,过磷酸钙等肥料具有酸化作用,而托马斯炉渣等肥料则具有碱化作用。微生物对尿素或硫酸铵的氧化过程会产生强无机酸(Brady & Weil, 2010)。除草剂也会引发氧化胁迫(Blokhina 等,2003),例如百草枯(1,1′- 二甲基 – 4,4′- 联吡啶二氯化物)是一种氧化性除草剂,其作用机制是刺激生物体产生超氧化物(Cocheme & Murphy, 2009)。
灌溉和排水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影响显著。土壤饱和会阻碍氧气在土壤中的扩散,因为氧气在溶液中的扩散系数约为其在气相中扩散系数的 1/10000(Stolzy & Letey, 1964)。当微生物通过呼吸作用消耗氧气时,会导致土壤氧化还原电位迅速降低(Flessa & Fischer, 1992a;Lambers 等,2008)。在持续淹水条件下,土壤酸碱度会趋向中性:酸性土壤的 pH 值会升高,碱性土壤的 pH 值会降低(Glinski & Stepniewski, 1985;Ponnamperuma, 1972)。
土地整理也会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整理会改变土壤结构。土壤容重和团聚体大小对土壤水分脱附以及氧气可扩散至的土壤深度影响极大(Grable & Siemer, 1967)。土壤管理措施会影响孔隙连续性以及水分、气体和热量的流动(Horn & Peth, 2009)。传导性大孔隙数量减少会导致土壤处于缺氧状态(Horn & Peth, 2009)。
斯纳金(Snakin)等人(2001)发现,在自然森林中,灰色土壤不同土层间的氧化还原电位存在显著梯度,但耕作土壤中无此现象。通过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图,这些学者能够区分农业用地、草原和森林群落。齐兹(Czyz)(2004)对从砂土到壤土的四种土壤进行研究,发现土壤压实会降低土壤通气性,进而使氧化还原电位下降。土壤耕作会改变土壤通气性,影响表层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同时,在耕作层以下区域,土壤耕作与降雨的相互作用也会对氧化还原电位产生影响(Clay 等,1992;Olness 等,1989)。
种植的植物种类及其在轮作中的顺序会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原因有二:
1.植物及其伴生微生物在土壤形成和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Lambers 等,2009)。
2.植物生物量的产生和向土壤中的输入会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而有机质对整体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具有缓冲作用(Paustian 等,1997)。
博雷罗娃(Bohrerova)等人(2004)对好氧土壤表层(0-30 厘米)的研究发现,不同种植制度下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存在显著差异,苜蓿 / 小麦轮作模式下的土壤氧化还原电位高于甜菜 / 大麦轮作模式。此外,植物会使其叶片 pH 值不同于生长土壤的 pH 值;且绿叶 pH 值与落叶 pH 值存在跨物种相关性,基于此,植物种类能够改变其生长土壤的 pH 值(Cornelissen 等,2011)。
植物与微生物对根际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的调节作用(向最佳生理水平)
多年来,人们已认识到植物的能量利用和代谢过程有助于维持体内 pH 稳态(Kurkdjian & Guern, 1989;Rengel, 2002)。近期一项针对 23 种草本植物的生态学研究表明,叶片 pH 值与整体土壤 pH 值无关;该研究还指出,对于任一特定植物物种,其组织 pH 值受到严格调控,因为 pH 值对植物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功能作用(Cornelissen 等,2011)。
基于本综述的视角,可提出一个更广泛的假设:植物细胞的生理过程仅能在较窄且特定的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范围内正常进行,因此植物会进化出相应机制,将细胞的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稳态维持在最佳水平。改变植物周围环境(即根际)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是为维持植物体内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稳态(进而保障细胞生理过程正常进行)而进化出的复杂交互过程的一部分。
现有文献表明,根际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会向 “理想” 值趋近,在根尖周围尤为明显。例如,在还原条件下,水稻根系可将整体土壤中的氧化还原电位从 + 120 毫伏提升至根表面的 + 420 毫伏,且对根表面 4 毫米范围内的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均有影响(Flessa & Fischer, 1992a)。相反,在氧化条件下,生长在土壤中的蚕豆(Vicia faba L.)根尖接触到微电极时,可使氧化还原电位从 + 700 毫伏降至 + 380 毫伏(Fischer 等,1989)。
在酸碱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植物根系会主动避开周围土壤 pH 值过高或过低的区域(Hinsinger 等,2003)。在酸性土壤中,根际 pH 值较整体土壤 pH 值最高可升高 2 个单位(Hinsinger 等,2003)。相反,在碱性土壤中,沙尼翁(Chaignon)等人(2002)发现根际 pH 值可降至 6.9。
遗憾的是,目前极少有研究将氧化还原电位与酸碱度结合分析,且在根系分泌物和呼吸作用相关研究中,从未提及初始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数据。因此,现有文献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上述假设,该假设无疑需要进一步验证。
农学领域面临的问题
基于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界定 “理想” 土壤
本文提出,可将氧化还原电位与酸碱度结合,作为界定土壤特征的关键基础参数,并确定特定作物对应的 “理想” 土壤标准。
“理想” 土壤的概念并非新提出。在农学相关的多个学科中,已有关于 “理想” 土壤界定的提议,主要分为两类:
1.基于单一参数,如盐基饱和度(Kopittke & Menzies, 2007)、含水量(Keen, 1924)和毛管拉力(Hackett & Strettan, 1928)。
2.基于综合参数(De Orellana & Pilatti, 1999;Janssen & de Willigen, 2006;Pilatti & de Orellana, 2000)。
通过本综述,可估算出植物生长最佳条件对应的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范围(图 5)。大多数栽培植物的最适 pH 值为 6.5-7,而 5.5-8 的 pH 范围也较适合植物生长。植物生长的最适氧化还原电位可能在 + 400 至 + 450 毫伏之间。当氧化还原电位低于 + 350 毫伏时,植物生长会迅速减缓。
现有资料难以确定氧化还原电位的上限值,且上限值可能因植物物种、土壤 pH 值及其他特性而异。但本文认为,在 pH 值为 6.5-7 的条件下,氧化还原电位高于 + 450 至 + 500 毫伏时对植物生长不利,可能导致矿物质缺乏(如磷、锰、铁)、重金属毒性(如镉、铅)以及病原菌滋生等问题。
上述最佳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值对应土壤中两种主要氮形态(硝酸根离子 NO₃⁻和铵根离子 NH₄⁺)的转化临界点(图 1)。众所周知,对于大多数植物而言,同时供应硝酸根和铵态氮时,植物生长状况最佳(Marschner, 1995)。
该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范围还对应所有主要植物养分和微量养分(如氮、磷、镁、锰等)的高有效性状态,同时重金属、类金属、铝或铁的毒性风险最低。具有此类 “理想” 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特征的土壤,符合植物最佳生理条件需求,能以易吸收的形式为植物提供所有养分,且矿物质毒性风险较低。此外,这种 “理想” 土壤还能为有益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有利条件,同时抑制病原菌的生存。
在这类 “理想” 土壤中,能量利用效率达到最高,可保障细胞稳态。因此,大部分光合产物可用于植物及伴生微生物的代谢和生长。植物生产力达到最优水平后,高生物量的产生会促进土壤中碳的流动,增加腐殖质形成,并推动有益微生物的繁殖。这些物质流动和微生物活动有助于将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维持在有利水平,使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高效且稳定运行。
可推测,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与最佳生理水平的偏差越大,植物维持细胞稳态所需的能量成本就越高。当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与最佳生理水平偏差极大时,植物将难以维持土壤处于有利的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水平。
还原环境中植物的生理功能紊乱已得到广泛认可和研究,尤其是在水稻作物研究中(Ponnamperuma, 1972;Yoshida, 1981)。但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是,有两个过程会形成恶性循环,维持并加剧土壤的还原状态:
1.在缺氧环境以及矿化相关微生物生存的不利条件下,土壤矿化速度极慢。
2.厌氧微生物会将氧化还原电位稳定在较低水平,而这类微生物在还原环境中会大量繁殖。
同样,当氧化还原电位高于 + 450 至 + 500 毫伏的阈值时,四个过程会形成正反馈循环,维持并进一步提高氧化还原电位:
1.高氧化还原电位下能量利用效率低,导致植物生长缓慢,生物量产量下降。
2.随之而来的是叶面积减小,太阳能吸收受限,植物的还原能力也随之降低。
3.生物量产量低还会导致土壤有机质流失,且高度氧化环境会加速矿化过程,进一步加剧有机质减少(Chesworth, 2004;Macías & Camps Arbestain, 2010)。
4.最终,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会导致其缓冲能力下降,进而使氧化还原电位升高。
利用电阻率界定土壤特征
本综述明确了氧化还原电位(一种电极电位)在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中的重要性,这与圣捷尔吉(Szent-Gyorgyi)(1960)的观点一致,即 “生命的动力源于微弱的电流”。这表明,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的运行可视为一个电路系统。
在物理学中,仅通过电压(单位:伏特,V)无法描述电路的运行状态,还需考虑电阻(单位:欧姆,R)。根据欧姆定律(I=V/R),可计算电流强度(单位:安培,A)。电流强度是表征导体中电子流动或电解质中离子流动的关键参数。在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欧姆定律的类比应用广泛,例如菲克扩散定律(Fick’s law of diffusion)。
类比可知,在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中,电阻率可视为欧姆定律中的电阻。电导率(EC)是电阻率的倒数,可类比为菲克定律中的扩散系数。
一个多世纪以来,土壤电阻率一直被用于界定环境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后,其应用更为广泛。如今,在精准农业中,土壤电阻率已成为界定土壤特征的重要指标(Samouëlian 等,2005)。这种无创测定技术能帮助研究者界定土壤的多种特性,例如阳离子交换量(CEC)、盐度、养分含量、残余湿度、优势水流路径、土壤质地及相关特性(如砂层、不透水黏土层等)、容重、压实区域和有机质含量(Paillet 等,2010;Samouëlian 等,2005)。例如,土壤容重增加时,电阻率会降低,在土壤含水量较低时尤为明显(Richard 等,2006;Seladji 等,2010)。电阻率还可用于估算土壤风化程度(Son 等,2010)。
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 – 电阻率视角:农学研究的新见解
这表明,除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度(pH)外,结合土壤电阻率开展研究极具实用价值。通过计算强度等衍生参数,能够进一步完善对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运行机制的描述与认知。在畜牧业领域,研究人员通过类比电路原理,利用电阻率计算相关强度参数来分析畜禽生长状况,实践证明该方法切实可行(阿内尚斯利、戈雷维特,1991;里加尔马等,2009)。在水产养殖领域,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对鱼类、贝类及牡蛎养殖的重要影响已得到广泛认可。法国水产养殖创意公司研发的 “涡旋” 软件(2008 – 2011 年版本)已整合这三项参数,该软件目前被大规模应用于养殖池塘的调控管理。这引发了农学家的两大疑问:其一,此类类比方法是否适用于植物种植领域?其二,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能否精准捕捉表征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这一复杂系统所需的核心信息?
本综述整合了多学科研究成果,证实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是三大基础参数,将其纳入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运行机制的概念模型,可揭示该系统的内在规律。若该模型得到验证,且针对特定作物,学界能够通过这三项参数界定 “理想土壤” 的标准,那么这一分析视角将为相关研究开辟新方向,并推动农学及各交叉学科的科技创新。
例如,该研究框架可用于分析基因型、环境与管理措施的互作关系。基于此视角,可通过评估作物在最适生理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条件下的品种差异,同时结合作物在初始整体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环境中维持内稳态的能力及各类田间管理措施,来阐释三者的互作机制。
该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的概念模型,还为解释文献中根系分泌物的显著差异性提供了可靠依据。该模型推测,根系分泌物的分泌量与初始整体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及田间管理措施密切相关,而目前根系分泌物相关研究中尚未考虑这些因素。
此外,该概念模型对土壤有机质(尤其在旱地农业中)的作用与重要性提出了新见解:有机质可将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稳定在适宜水平,从而降低植物维持自身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内稳态所需的能量消耗。这一机制也能够解释肥料利用率存在差异的现象,以及土壤生产力恢复过程中的滞后效应(蒂托内尔等,2008)。当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时,土壤处于氧化状态,短期内肥料利用率会显著下降。这是因为植物需将大量光合产物转化为根系分泌物释放到根际环境中,以此调节根际的氧化还原电位,保障细胞内稳态。
这一聚焦氧化还原电位在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中核心作用的整合视角,还可解释以下两类现象。其一,亚洲绿色革命在淹水稻田的还原环境中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土地翻耕、土壤通气、矿物施肥及化学农药施用等氧化性管理措施,快速将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提升至适宜作物生长的水平;其二,长期定位试验中出现的作物减产趋势(拉达等,2003),这是由于长期持续的氧化性措施可能导致土壤过度氧化,进而造成产量下降。另外,水稻强化栽培技术之所以成效显著,也与该技术通过交替灌溉与排水,维持了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环境有关(斯图普等,2002)。
该新视角还能解释为何施用农药会增加真菌病害发生风险,例如有研究指出草甘膦的使用会加重镰孢菌病害(费尔南德斯等,2009)。农药施用会使植物产生氧化应激反应,而这种环境恰好有利于致病真菌繁殖。同时,该研究框架也印证了沙布苏提出的营养共生理论(1985),即水分胁迫或化学投入品施用引发的植物生理功能紊乱,易导致作物遭受虫害或病害侵袭。这是因为大多数化学肥料和农药均具有氧化性,这些胁迫本质上多与酸碱度异常或氧化应激相关(布雷西,1996)。
此外,该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搭建理化科学与生命科学的沟通桥梁,成为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实用工具,而学科融合正是农学领域开拓新方向的关键(琼斯等,2004)。例如,斯帕克斯(2001)指出,研究微生物驱动的氧化还原反应,以及碳、氮、磷、硫等元素在不同氧化还原阈值下的转化过程,是理化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的前沿方向。
同时,该框架也有助于突破尺度限制带来的研究瓶颈。尺度研究的割裂是当前科研领域的主要局限之一。若科研人员能够实现从单一根系根际到田间乃至更大尺度土壤的微观与宏观研究衔接,相关领域将取得突破性进展(欣辛格等,2009)。在系统研究法中,某一尺度下系统参数的平均值,是由更小尺度下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厘清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等核心参数的变异特征及成因,不仅有助于实现不同尺度研究的转化,还能加深对跨尺度过程的理解。例如,明确细胞分区中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的分布结构与功能,是揭示细胞生理基本过程的关键(汉森等,2006;沙伊贝等,2005)。而欣辛格等(2009)则提出,当前亟待改进微观尺度下根际物理结构的描述方法,并结合这些微观结构信息解读数据的功能意义。
在更大尺度的研究中,明确越南酸性硫酸盐土壤的变异特征、成因及其与氧化还原电位和酸碱度的关联,为构建高效种植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于松等,2000a;于松等,2000b)。此外,在环境生物技术领域,追踪电子在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路径,被视为将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相关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最可靠手段(里特曼,2006)。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及电阻率与生产潜力的关联研究
能否结合植物生理学特性,将土壤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这三项参数所反映的信息,转化为植物生产潜力的评估指标呢?作物的生产潜力主要由温度、水分、光照等气候因素以及土壤特性决定。笔者认为,这三项参数可显著提升生长环境表征的精准度,进而为土壤生产潜力评估提供可靠依据。但农学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确定不同气候条件下土壤的最佳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 – 电阻率组合,从而最大化作物的生产潜力。
目前,关于这三项参数与特定土壤生产潜力的关联,仍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有待解决。研究需深入评估气候与这些参数的相互作用,其中温度的影响尤为关键。温度不仅会改变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还会影响生化反应速率,同时极有可能对微生物生长繁殖产生重要作用。作物生长所需的最佳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 – 电阻率组合,很可能会随温度变化而改变,且受气候条件调控。例如降雨量不仅会影响土壤含水量,还会改变土壤中的氧气含量。
结论: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 —— 种植制度设计与管理的实用工具
该研究框架及其优化后的土壤表征方法,可用于构建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的互作模型。明确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 – 电阻率的适宜范围,将为种植制度的设计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届时,种植制度的构建可围绕这一最佳参数组合展开,筛选适配的作物品种和微生物,制定配套田间管理措施,从而营造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
这一分析视角的研究成果,对农业生态集约化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农业生态集约化是指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借助生物调控手段,在保障高粮食产量的同时,兼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尔等,2011)。例如,可基于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 – 电阻率参数,筛选根际优势微生物,以促进作物生长并提升作物抗病性。而这一方向也被视为未来可持续农业领域中,农学研究需攻克的核心难题(哈特曼等,2009)。
目前,农学家仅在少数场景中,且仅通过单一方式运用氧化还原电位调控技术改良土壤。例如,卡特(1980)通过监测氧化还原电位来调控甘蔗种植的排水系统;萨维奇等(1980)提出采用高锰酸钾、高氯酸钠或氧化铁等氧化剂调节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帕楚基斯与乔治乌(2007)利用亚硫酸盐和亚硝酸盐这类细胞毒性氧化剂,使真菌维持在未分化的菌丝阶段,此阶段的真菌更易被土壤微生物分解;布洛克等(2000)与新村(2004)通过添加易分解有机物、淹水处理或用密封塑料膜覆盖土壤等方式降低氧化还原电位,以此防控尖孢镰刀菌和立枯丝核菌;竹原等(2004)则利用化感植物降低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实现土传病害的防治。
若能整合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和电阻率三项参数,进一步优化土壤表征方法并确定最佳土壤条件,像水产养殖领域那样设立参数目标区间,上述土壤改良措施的效果将得到大幅提升。而这类技术的创新发展,需深入研究不同作物和微生物对应的土壤最佳氧化还原电位 – 酸碱度 – 电阻率参数,同时明确各类生物对这些参数的影响机制。若该土壤 – 植物 – 微生物系统框架获得验证,那么不同研究方向的农学家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农业技术方案。
致谢
在此,我衷心感谢阿兰卡皮永教授、诺曼厄普霍夫教授、法布里斯德雷弗斯以及塞西尔福韦 – 拉博,感谢他们为稿件完善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并给予的支持;同时感谢法国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研究室的同事们,容忍我长期围绕氧化还原电位相关问题展开反复探讨。此外,感谢彼得比金斯对英文稿件的校对润色,也向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的匿名评审专家们致以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