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
/2025年第1期
熔古铸今
守正出新
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文本删削问题再探
杨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历史文献与知识史,数字人文研究。
提要:由清人辑佚并收入《四库全书》的《中兴小纪》,在排除掉四库馆臣字句层面的改窜后,应当基本反映了《永乐大典》“宋高宗”条下整体引用的熊克《中兴小历》样貌。通过将之与《中兴纪事本末》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中兴小纪》中被删削的文本在形式上以事条或事条要件为核心,内容基本均能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找到对应的记载,且删削数量、形式等情况在不同卷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现象的成因,极可能是明人在将《中兴小历》收入《大典》“宋高宗”条下时,曾依据《永乐大典凡例》中提及的避免重复原则,比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其中事条进行删削。许多自《大典》中辑出的宋代文献如今的样貌,同《大典》的编纂实践有着密切关系,针对二者的研究应当彼此兼顾,以求相互发明。
关键词:《中兴小历》 《永乐大典》 《中兴纪事本末》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辑佚学
南宋人熊克所著《中兴小历》一书,是一部记载宋高宗一朝(1127—1162)史事的编年体史书。一向最为宋史学界所看重的高宗朝编年史,自然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但《中兴小历》记载时段与《要录》基本一致,且相较《要录》成书时间更早,内容也与之时有参差,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历史叙事,对于研究南宋前期历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兴小历》原本久佚,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有此书的两个“变体”:一是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并厘为四十卷的《中兴小纪》(为避乾隆帝讳而改名,以下简称《小纪》),二是题名“学士院上进”、今存七十六卷的《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图书馆所藏《纪事本末》抄本重新进入学术视野,学界针对今本《纪事本末》的作者、性质、形成过程等问题均有较为充分的讨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辛更儒《有关熊克及其〈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文史》2002年第1辑,第193—207页;王曾瑜《就整理和校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辛更儒先生商榷》,《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第25—27页;辛更儒《熊克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辑,2008年,第183—200页;周立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之关系》,《文献》2010年第3期,第104—112页;温志拔《再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55—158页;高纪春《关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十五辑,2022年,第72—91页;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文史》2022年第3辑,第177—204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纪》如今却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冷落。
实际上,《小纪》的重要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小纪》因被收入《四库全书》,在《纪事本末》得到重新发现以前,曾长期作为《中兴小历》的一个通行版本流传于世。其次,由于今本《纪事本末》阙失绍兴二十一年(1151)及以后的纪事,现存部分也存在一些残缺、改易之处,因此《纪事本末》不能完全替代《小纪》,我们仍需要将二者对勘,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兴小历》之旧貌。再次,《小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兴小历》在《大典》中的保存状态,这为我们观察《大典》收录宋代史书的情况,乃至《大典》编纂过程中处理史部文献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小纪》及其背后的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认识尚显不足,相关问题仍有剩义。
《小纪》是《中兴小历》的一个删削较多的节本,这一点如今已是学界的普遍认识。但我们对《小纪》的认识,不能止步于此。前人研究虽对《纪事本末》与《小纪》的文字差异有了一定的关注,但往往将之笼统视为对《中兴小历》原本的“删减”“改窜”,而较少深入追索这些文字差异的性质及其文献学意义。故而为了更充分地理解《小纪》的学术价值,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入追问:《中兴小历》为何遭到删削?这些被删削的文本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些删削工作是谁、在哪一个环节所为?在这些问题上,学界尚有诸多不同意见。辛更儒将《小纪》中对《中兴小历》文本的删削,归咎于四库馆臣出于政治目的的篡改;高纪春则认为,这些删削当是宋元书贾所为,《大典》所据底本原已如此。(辛更儒《熊克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考》,第186页;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79—184页。)此二说均不确。实际上,这些删削更有可能是明人在将此书收入《大典》时所为;《小纪》所依据的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样貌的形成,同《大典》的编纂体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即拟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以求更全面地呈现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的样貌与价值。
近年来学界对《大典》引用文献的情况进行了很多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由此我们对《大典》的编纂体例与征引文献的方式等问题有了更全面、清晰的认识。(相关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王云海《〈永乐大典〉本〈宋会要〉增入书籍考》,《文献》1980年第3期,第116—142页;陈智超《从〈宋会要辑稿〉出现明代地名看〈永乐大典〉对所收书的修改》,《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第31—33页;黄宽重《〈永乐大典〉中〈三朝北盟会编〉史料及其相关问题》,《文献》2003年第2期,第98—112页;钟仕伦《永乐大典本〈南北朝诗话〉论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第138—140页;瞿林江《新见〈永乐大典〉残卷引“礼记类”诸书及版本考》,《文献》2018年第1期,第78—86页;董岑仕《〈永乐大典〉之〈崇文总目〉、〈四库阙书〉考——兼论〈永乐大典〉中四十二卷书目汇编》,《古典文献研究》第21辑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73—203页;杜以恒《〈永乐大典〉引〈周易〉经注疏释文底本初探》,《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第77—87页;张良《〈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兼论〈永乐大典〉之修纂体例》,《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第199—232页;韩悦《〈永乐大典〉引录文献方法考略—以〈周礼〉为中心》,《文献》2022年第5期,第157—178页。另外,张升对《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诸问题的探讨,也对笔者的研究有很大启发,相关研究参见氏著《〈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这些研究无疑为我们理解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文本样貌的形成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同时,对《中兴小历》这一个案的考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大典凡例》在实际编纂工作中是如何落实的,从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大典》编纂体例、编纂方式的认识。
(南宋)熊克 著 中兴小纪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一、《小纪》《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的关系概述
本文主要探讨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对原本所作删削的文本特征及其成因,而展开这一讨论的主要方法,是将《中兴小历》现存的两种“变体”—即《小纪》与《纪事本末》—进行文本比对。本文的观点能够成立,首要的逻辑前提即在于这一方法的有效性。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首先阐明《小纪》《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三者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仍有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推敲。
(一)从《中兴小历》到《纪事本末》
熊克,字子复,建阳人,约出生于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高宗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后一度颇得孝宗赏识,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卒于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熊克主要的生平事迹,参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熊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43—13144页。辛更儒与高纪春亦对熊克生卒年、家世、经历等问题进行过考证,参见辛更儒《有关熊克及其〈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第193—198页;高纪春《熊克卒年新考》,《宋史研究论丛》第二十八辑,2021年,第341—346页。)熊克曾撰记载北宋历史的《九朝通略》,以及南宋高宗一朝“自建炎初元至绍兴之季年”的编年史《中兴小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嘉泰禁私史》,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0页。)后者似成书于孝宗淳熙(1174—1189)末,其后大概曾于绍熙年间刊刻。此书在南宋中后期一度流传较广,曾为诸多南宋著作所援引,亦是李心传编纂《要录》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的记载,宁宗时期“嘉泰禁私史”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即是当时有“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中兴小历》及《通略》等书欲渡淮”;此事被发觉并上报后,朝廷“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嘉泰禁私史》,第149—150页。)这一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兴小历》在当时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被现代学者视为《纪事本末》出现的契机。
自郑翼、王欣夫以来,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纪事本末》原本当脱胎自《中兴小历》;“中兴纪事本末”之名,当是嘉泰(1201—1204)以后书坊为避免政治上的麻烦所更,同时亦将作者改题为“学士院上进”。(参见郑翼《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跋文(载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该书宣统抄本后),及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73—1574页。高纪春亦赞同这一观点,参见氏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78页。辛更儒虽认同《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本为同书异名的观点,但认为此书初名乃是“中兴纪事本末”,后来才更名为“小历”,参见氏著《有关熊克及其〈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第210—212页。)宁宗朝以后特别是理宗朝成书的部分类书中,亦颇有引用“中兴本末”“中兴纪事”者,当即出自《纪事本末》。但此书在当时并未完全取代《中兴小历》,李心传、徐自明等人在理宗朝所著史书中仍然大量引用了后者。
仔细考察引用二书的宋人著作即可发现:相对而言,编辑更为严肃的史学著作,往往引用《中兴小历》;而引用《纪事本末》的,则多是福建书坊编纂或刊刻的史书、类书一类作品。而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一书的引用书目中,则同时分别著录了《中兴小历》与《纪事本末》两者—陈均作为陈俊卿之孙,其人其书既有一定的精英色彩,又与福建书坊有着密切关系。综上可见,《纪事本末》虽脱胎自《中兴小历》,但在南宋后期实与之并行于世,不过传播路径则更为大众化,而《中兴小历》的受众似乎更加精英化。至于王应麟在《玉海》中径称“《中兴纪事本末》一名《中兴小历》”,虽未正确解释二者渊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纪事本末》内容的实质。(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四十七《乾道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946页下。)
《纪事本末》一书今存三个清抄本,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据高纪春研究认定,此三本均以朱彝尊所曾见、宋筠所藏的七十六卷《纪事本末》刻本为祖本;而今本及其所据底本,并不能与南宋人所见的《纪事本末》等量齐观。(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93—203页。考虑到《纪事本末》与《小纪》现存各版本间的关系以及使用的便利程度,本文在具体讨论过程中,《纪事本末》将使用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小纪》则使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3册),特此说明。)
图一《纪事本末》卷十三与《小纪》卷八版面对比
(上: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纪事本末》卷十三叶11b至12a;
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小纪》卷八叶24a至25b)
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今本的残缺问题上。今存抄本《纪事本末》的内容仅有绍兴二十年以前的部分,并未完整覆盖高宗一朝,目录亦仅列现存的七十六卷,说明今本所据底本相较《中兴小历》原本应当已有缺卷。另据笔者观察,即便是今本现存的卷次,也存在一些缺叶的情况。例如,《纪事本末》卷十三建炎四年六月己丑条下,言“己丑无名之费不急之务皆所当去”云云,其事转折突然,殊无头尾;且“己丑”在叶11之末,而“无名之费”则在叶12之首,刚好跨越了版面。考之《小纪》,则其于“己丑”与“无名之费”之间较《纪事本末》多出自“上谓宰执曰”至“以节用爱人为先凡”等共计411字,其内容不仅包括《纪事本末》头尾两事的前因后果,中间还多出两条纪事(见图一)。今本《纪事本末》半叶11行、行22字,故其每一版面最多可刻484字,而考虑到《小纪》与《纪事本末》文字、排版方面的差异,以及《小纪》内容多有删削等情况,则今本《纪事本末》很可能在“己丑”与“无名之费”之间缺失了一叶。此外,今本《纪事本末》卷十四的叶6与叶7之间、卷三十二的叶10与叶11之间,亦当有缺叶,情况与前述卷十三类似。(温志拔已经注意到了这些脱漏的情况,但并未将这些文字脱漏的问题同《纪事本末》的版面情况联系起来,见氏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熊克〈小历〉”及其相关问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87—88页。)
另外,今本《纪事本末》页面中亦偶见空缺之处,如卷四十七叶4b的右下角“遂离间同列”等字下有三个空格,与后文“与之祸”文意中断;但此处前后文字实为叙述同一事件,故而此处并非标识不同事条的空格。据《小纪》所载,此处原文当为“遂离间同列卒成党与之祸”,《纪事本末》此处缺失“卒成党”三字(见图二)。今本《纪事本末》的事条中,时而会出现类似这样因缺字而留出的空格,且这些空格多出现在页面边角,说明很可能是今本所据底本的部分页面存在一定的破损。总之,今本系统在流传过程中保存状态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字残缺问题。
图二《纪事本末》卷四十七与《小纪》卷二十六版面对比
(上: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叶4b至5a;
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小纪》卷二十六叶5a至5b)
今本《纪事本末》与原本更大的差异,则在于前者掺入了少量出自《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下简称《续宋通鉴》)的文字。高纪春已经注意到,今本《纪事本末》中建炎元年六月壬戌条中自“纲又上三议”至“公之谤愈多矣”一节文字(计443字),不见于《小纪》,而应当是自《续宋通鉴》中窜入;而其后的“纲又言”至“树党邪正在都者曾无伏节死难”等文字,亦不见于《小纪》。(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87—193页。这段文字详见《纪事本末》卷一下,建炎元年六月壬戌条,叶1b至叶2b。)《小纪》中相应位置的文字以“纲又曰”起首,至“仕于中都者曾无伏节死难”止,内容与《纪事本末》迥异。据《要录》《宋宰辅编年录》等书所引《中兴小历》文字,此处《中兴小历》原文当同于《小纪》。可见,“纲又”及“都者曾无伏节死难”等字,《小纪》及原本《中兴小历》当有;故而《纪事本末》此处之异文,实自“上三议”起,止于“树党邪正在”,即此卷叶2之内容(见图三)。而且此叶中不止“公之谤愈多矣”出自《续宋通鉴》,其末行文字亦见于《续宋通鉴》所引“《中兴大事记》曰”,只是文字为适应《纪事本末》一书之行款而略有删润。(参见刘时举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遥上孝慈渊圣皇帝尊号”条所引“《中兴大事记》曰”,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页。)故而这一整叶内容,实际均是以《续宋通鉴》文字替换掉了原文。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今本《纪事本末》中有多处前后文字不甚通顺而又与《小纪》行文差异较大之处,均可在《续宋通鉴》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字。《续宋通鉴》一书虽题为宋人刘时举所撰,但实为书坊伪作,大约成书于宋末元初。这表明,今本《纪事本末》所据底本确当如高纪春所言,是一个形成于南宋末或元代的刻本。(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93页。)考虑到今本《纪事本末》所呈现的残损情况,很可能今本所据底本在编纂时,曾以《续宋通鉴》补入部分缺叶、残损之处,故而形成了原书文字与《续宋通鉴》文字交织的情况。
图三《纪事本末》卷一下所窜入的《续宋通鉴》文字(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二)《小纪》与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
而另一边,仍题名为《中兴小历》的著作,其原本今已不存,但此书曾为《大典》收录,后来四库馆臣又将之辑出,整理而为《小纪》。前辈学者已经指出,四库馆臣在将《小纪》辑出并收入《四库全书》时虽对原文有所改窜,但馆臣所做的工作集中于将原文中涉及民族问题的违碍字样加以订改,主要是遣词造句方面的改动,并没有整段整条地篡改原书内容。(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574页;王曾瑜《就整理和校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辛更儒先生商榷》,《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第26页;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82页。)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尽管现存《大典》残卷中,似已无直接引录《中兴小历》的内容,但是仍可以进一步通过《小纪》考察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的情况,这对我们认识其中文本删削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永乐大典本”,是在辑佚过程中产生的概念,其实质是被辑佚的文献在《大典》中最终呈现出的样貌。既有研究早已指出,《大典》的引书方式,分为“全录”与“节抄”两种:前者主要指的是整书或整篇成规模地整体抄录(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全文录入,但也存在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选择地录入的情况,这一点后文将详述),后者则是将书中内容分割成更小的段落零散征引。(王云海《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第60—63页;林鹄《〈永乐大典〉编纂流程琐议——以〈宋会要辑稿〉礼类群祀、大礼五使二门为中心》,《文史》2020年第1期,第279—288页。)需要注意的是,对文献采用“全录”还是“节抄”的方式,并非主要以文献类别来确定,而是根据条目等情况的不同加以区分。
以史书为例,根据《永乐大典凡例》及近人研究,《大典》会在各朝国号字韵下以历代君主为名的条目中,将记载相应时段的史著采取“全录”的形式征引,顺序是先正史本纪,次编年、纲目体史书,最后则收录一些杂史。(《永乐大典凡例》,见《永乐大典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叶5;张良《〈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兼论〈永乐大典〉之纂修体例》,第199—232页。)相关实例,如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至卷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一等《大典》残卷,均为“宋”字韵下的“宋宁宗”条,即以“全录”的形式征引了多部史书中的宋宁宗朝部分内容。其中,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至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四为《两朝纲目备要》(即佚名氏所作《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以下简称《两朝纲目》)的后半部分,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五为《宋史全文》,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六至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八为《通鉴续编》,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为《中兴大事记讲义》,卷一万二千九百七十至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一为《宋宰辅编年录》。“宋宁宗”条今存诸卷征引文献的方式,正可与《永乐大典凡例》相互印证。此外,据《永乐大典目录》,“宋宁宗”条起自卷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六,至卷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二止,共计17卷。(《永乐大典目录》卷三十五,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叶20b至22a。)根据《两朝纲目》与《宋史·宁宗本纪》的内容体量与《大典》每卷的容量估计,今已不存的“宋宁宗”条前四卷,当仅包含《宋史·宁宗本纪》与《两朝纲目》的前半部分两种文献(最可能是各占两卷),也与《凡例》相契合。
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出的很多宋代史书,应当都是利用了诸帝条目下这种以“全录”方式征引的文字。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四库馆臣即称“《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册,第63页。)。近来的研究指出,馆臣有这样的表述,正是因为《长编》在《大典》“宋”字韵下的“宋太祖”“宋太宗”以至于“宋哲宗”等七帝条目中被以“全录”方式征引;馆臣所辑出的七朝本《长编》,主要当即来自《大典》中这七处,而没有悉心搜讨以“节抄”方式被引用于其他条目下的《长编》文字。(张良《南宋官藏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传续考》,《文史》2021年第2辑,第143—164页。)又如《两朝纲目》,《四库全书》所收此书即为永乐大典本,其原因在于“其书世罕传本,惟见于《大典》者尚首尾完具”(《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册,第71页。)—前述的《大典》残卷显示,馆臣之所以称永乐大典本《两朝纲目》“尚首尾完具”,应当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大典》将此书以“全录”的方式于“宋光宗”与“宋宁宗”条下引用。
从《小纪》的情况来看,《大典》对《中兴小历》的征引,亦当属“全录”的范畴。《小纪》虽内容节略较多,但其中纪事的确是自建炎伊始至绍兴内禅不曾中断,可称首尾连贯,很难想象四库馆臣能够从零章断简的“节抄”条目中,辑出这样完整的内容来。四库馆臣为《小纪》所撰提要也称:
《宋史·艺文志》载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大典》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无端委,仅此书尚为完本。惟原书篇第为编纂者所合并,旧目已不可寻。(《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册,第62页。)
从“尚为完本”之语,可见四库馆臣对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的判断与《长编》《两朝纲目》类似—当然,从《小纪》实际呈现的情况来看,馆臣的这一看法其实是有误的。但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注意到,《大典》中《中兴小历》的文字遗存仍较为丰富,且涵盖了整个高宗一朝,至少看起来并非“首尾零落”;而《中兴小历》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应当是因为此书与《长编》《两朝纲目》类似,在《大典》中是在“全录”式征引文献的条目下集中出现。
按照《大典》的编纂体例,以“全录”方式征引《中兴小历》的,自然应当是“宋”字韵下的“宋高宗”条。根据《永乐大典目录》的记载,《大典》中的“宋高宗”这一条目自卷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起,至卷一万二千九百三十止,共占据172卷。(《永乐大典目录》卷三十五,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叶1a至18a。)这172卷中,今仅存最后两卷,内容是《中兴圣政草》等杂著;而前面的170卷,若按照《大典》的编纂体例,则应当首先收入《宋史·高宗本纪》,其后则可能分别征引了《要录》《中兴小历》等书——二者日后均为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出。考虑到《大典》行款为半叶8行,小字双行,行28字,故每叶最多容纳896字;而其每卷大约十余叶至四十多叶,即以其中位数计算,平均每卷亦有两万余字,则“宋高宗”条的前170卷共计可承载三四百万字——这样庞大的篇幅,自然是可以涵盖《宋史·高宗本纪》以及今本《要录》《小纪》全部内容的。而且从《大典》“宋太祖”至“宋哲宗”等条征引《长编》、“宋宁宗”条征引《两朝纲目》《宋史全文》等书的情况来看,“宋高宗”条会征引《要录》与《中兴小历》,也在情理之中——甚至可以认为,“宋高宗”条下征引的二书内容,很可能构成了今本《要录》与《小纪》的主体。(通过将七朝本《长编》与五朝本以及今存《大典》残卷中以“全录”和“节抄”方式被征引的《长编》文字进行比对,学者已经指出,四库馆臣在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长编》时,所做的工作基本只是整体抄出“宋”字韵下诸帝条目中“全录”的《长编》原文,而未能全面搜讨他韵下“节引”的《长编》佚文(参见张良《南宋官藏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传续考》,第155页)。四库馆臣在辑出《要录》《中兴小历》《两朝纲目》等宋代史书时,很可能也采取了同辑录《长编》类似的工作方式。)
图四《小纪》《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示意图
本节通过讨论《中兴小历》一书的发展演变历程,分析了其与今本《纪事本末》《小纪》的关系,结论大体如上图所示(见图四)。可以看到,《小纪》的内容编排,在排除掉四库馆臣的文字篡改后,应当基本反映了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的样貌;而所谓“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其实质应当主要是《大典》“宋高宗”条下整体引用的《中兴小历》文字。今本《纪事本末》虽然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字修订与讹变,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原本《中兴小历》中绍兴二十年及以前的内容,主要需要注意的是文本残缺问题,以及甄别后来窜入的《续宋通鉴》文字。建立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小纪》与《纪事本末》之间各类文本差异的成因—通过《小纪》与《纪事本末》的文本比对,同时再借助《要录》《宰辅编年录》《续宋通鉴》等其他宋代史籍作为旁证材料,来考察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删削原本的情况,这一方法也由此变得可行。下一节即通过这种比对,来分析《小纪》被删削文本的特征。
二、《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特征
尽管《小纪》与《纪事本末》皆是《中兴小历》的“变体”,但是一方面,《中兴小历》在成书后即广为流传,应当在南宋时已有一些不同版本,《大典》与《纪事本末》各自所本,或许已非此书的同一版本;另一方面,《小纪》与《纪事本末》的形成过程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二书之间异文颇多。这些异文可以按照其规模,分成三类:字词层面的差异、语句层面的差异与事条层面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异文,形成原因也不尽相同。
《小纪》与《纪事本末》中即便是同条纪事,也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文字讹变,这是书籍流传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自不在话下。另外,二者之间时常也有一些语句上的参差。如表一所示的两条记载,第一条《小纪》较《纪事本末》少“请于国”至“大鼐”等24字,第二条《小纪》则较《纪事本末》多“及漕司”至“二州守倅”等18字。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是翻刻、传抄过程中的脱漏。如《小纪》的第一条纪事文字全无当日事项内容,显有阙失,当是在流传的某个环节上,脱漏了此段文字中前后两个“大鼐”之间的文字;《纪事本末》在第二条纪事中两个“二州守倅”之间文字的遗漏,情况应当与之类似。这样一些语句的脱漏在两书中均可以见到,每处一般十几二十字,多者不过三五十字,且一般都在同一条纪事之内,前后文叙事有明显的割裂感,应当并非系统性的、有条理的删节,而是同字词层面的差异类似,属于流传过程中的讹变。除此之外,《小纪》中一些标注材料出处的小字注在《纪事本末》中则无,可能是在某一流传环节的编纂者有意为之,也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版本差异。
表一 《小纪》与《纪事本末》语句层面的差异示例
然而,《小纪》与《纪事本末》之间最显著也最重要的文字差异,还是在事条层面上。《小纪》中有而《纪事本末》无的纪事极少,仅有二三条而已;反过来,《纪事本末》中却有数百条纪事,是《小纪》所无的。《小纪》中阙失的这些事条,一方面体例、辞气与《小纪》中保存下来的事条基本一致,而且在《纪事本末》中上下行文通畅,不似《小纪》在相应位置时有文气中断、系时混乱等问题(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第182页。);另一方面,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其中有数十条曾为李心传在《要录》小字注中明确提及是《中兴小历》所有的内容,还有一些曾为《宰辅编年录》等南宋著作明确征引。(辛更儒《有关熊克及其〈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第180页。)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事条应当是《中兴小历》原本即有的,并非《纪事本末》后来增添,而是在《小纪》中遭到了删削。
前辈学者虽一再强调《小纪》文本遭到删削的问题,并曾反复统计其删削字数,但主要是借此凸显《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而对小纪中被删削事条的特点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也未能对这些事条层面的删削的成因给出合理的解释。以下我们就从形式与内容等角度出发,来归纳《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征,从而为理解这些删削的成因奠定基础。
(一)被删削文本的形式特征
《小纪》中被删削的文本,从形式上看,大体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
(1)基本类型:以事条为单位被整条删去
《纪事本末》中的很多纪事在《小纪》中是完全阙失的,因为这些文字被以事条为单位被整条删去了。如表二中,《小纪》此处阙失了癸未、庚寅及辛卯第一事共计三条纪事,以至于单看《小纪》的话,我们会以为“山东贼首郭仲威”一事发生于戊寅日,然而原本此事是被系于辛卯日下的。当然,《小纪》中阙失的不只有这种简单的事条,很多文字更多、内容更详细的事条也被整体删去。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认为,删去事条是《小纪》中删削文本的基本操作形式。但是,有时《小纪》在删削某些事条时,却并非将其中内容悉数删去,而仅仅删去了部分内容,由此产生了以下四种删削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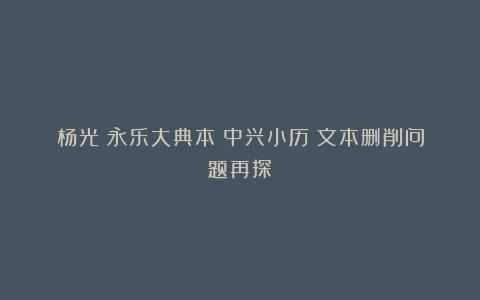
表二 《小纪》中被整体删去的条目示例
(2)上一日的事件本体与下一日中提示事件缘起的标识语皆被删去
这类删削是由第一种衍生出来的。自《左传》以来,在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书中,一条完整的纪事往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系时、事件缘起、事件本体。“系时”即此一纪事所系之月日,“事件本体”则是纪事的主体部分,“事件缘起”部分则追叙此日此事的缘起,往往以“先是”“初”“时”等标识过去时间的词语领起。当然,一部编年史内,并非所有事条的结构都会如此完整:很多纪事未必会追溯事件缘起,而被系于同一日下的多个事条一般也只会在首条标明系时。至于这三部分内容在一条纪事中如何排序,不同著作之间也有所不同。具体到《中兴小历》中的事条,三者的顺序一般为“事件缘起—系时—事件本体”,这样的形式也为今本《纪事本末》与《小纪》所继承。《小纪》中很多删削之处,虽非将一事条完整删去,但也显然是以事条三部件为单位进行删削的。
这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情况是,当某一事条遭到删削时,若其后的一条纪事为“事件缘起—系时—事件本体”结构完整的事条时,最后被删去的是前一事条的事件本体与后一事条中事件缘起部分的“先是”“时”“初”等标识语。其状态正如表三所示,由《纪事本末》与《小纪》的对比可见,四月甲辰条的事件本体在《小纪》中被整体删去,但其“夏四月甲辰朔”的系时却被保留了下来;而后一条即四月戊申条,是结构完整的一条纪事,其事件缘起部分的标识语“先是”,在《小纪》连同上一条的事件本体被一并删去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原本从属于下一事条的事件缘起内容,仿佛变成了甲辰条的事件本体。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而是在《小纪》中出现了不下数十次。
表三 《小纪》中事件缘起标识语被删去的情况示例
(《纪事本末》此处四月戊申条在“岁”字下原为两个空格(叶1a),当如前文所述,是今本所据底本页面有缺损而致,故此处可据《小纪》补出“计量”二字。)
(3)事件缘起得到保留,事件本体(有时也包括系时)则被删去
《小纪》中也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一原本结构完整的事条,事件本体部分被删去,事件缘起部分却还在,如表四所示。对比《纪事本末》可知,“参知政事王绹累章求退”与“初吕颐浩之长天官也”云云的两处记载,原本并非独立存在,而分别是二事条中的事件缘起,《小纪》却将二者所对应的事件本体删去,以致两处文字与上下文无法衔接,显得异常突兀。至于被删削事条中的系时是否会被保留,则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如表四中第一条的系时“乙卯”也随着事件本体被一部删去,第二条的系时则被保留,原因是第一条此日仅此一事,而第二条中“丁亥”日原有二纪事,而同日第二事即余深一事则在《小纪》中整体得以保留,故而此处的丁亥系时也随之得到保留。
表四 《小纪》中事件本体被删去的情况示例
(4)系时与事件本体得到保留,事件缘起被删去
《小纪》中也有一些事条,仅有事件缘起部分被整个删去。典例如表五所示,《小纪》中此条只有系时与事件本体,全无作为事件缘起的田如鳌、高宗与赵鼎之言论。总体来看,这种情况出现得不多,全书不过两三处而已。
表五 《小纪》中事件缘起被删去的情况示例
(5)事件本体中的部分文字被删节
《小纪》中也有一些事条并非全部或某一部件被整体删去,而是只有其内部某些内容被节略。如叙述李纲罢相之事时,《纪事本末》中有右正言邓肃维护李纲并因而被贬的一段情节,这部分文字在《小纪》中则被删去。(参见《纪事本末》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叶5a至b。)又如建炎二年七月己亥条关于程千秋的纪事中,关于程千秋守御公安县事迹的一节文字,也为《小纪》所删略。(参见《纪事本末》卷六,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叶2a。)这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叙述较详细、文字较多的事条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以上归纳了《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几种基本形式。从《纪事本末》与《小纪》的对比结果来看,(1)这种情况在《小纪》中最为普遍,(2)(3)两种情况也很常见,(4)(5)两种情况则比较少见。同时,《小纪》中常有连续几条纪事均被删去的情况,此时这几种删削形式也可能会叠加出现。
(二)被删削事条的内容特征
《小纪》中被删去的事条,在所记载的内容方面,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呢?辛更儒认为《小纪》中被删削的条目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触四库馆臣忌讳而遭到回避者,二是四库馆臣认为不值得抄录的日常政事,三是原文内容较为繁冗者。(辛更儒《熊克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考》,第191—192页。)这样的归纳,乃是建立在《小纪》中的文本删削是四库馆臣所为这一错误认识上的,自不足为据;而且辛氏所谓“日常政事”,包括了“如宰执拜罢、近臣任免、言官弹奏、朝廷礼仪、诏令颁布、君臣议论以及边防攻守、地方民事、金人动息等等”的内容,所涵盖不免芜杂。(辛更儒《熊克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考》,第191页。)但辛氏的看法确实揭示了一个问题:《小纪》中被删去的事条内容所涉甚广,不仅有很多记载的是各类较普通的政务,也有一些事关军国大政者。从总体上看,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在删削事条时,似乎在事项类型方面并没有非常一致的标准。
不过,《小纪》中被删去的事条在内容方面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方面,有几类内容在《小纪》中被删去得比较多。一是那些记载较为简略的事条。这些事条的内容,既可以是宰执拜罢、近臣任免、朝廷诏令等等朝廷政务,也可能是如表一中高宗驻跸地的变更等方面情况,其内容未必可以用“日常政务”完全概括—毕竟宰执拜罢等高层人事变动,乃是当时政治中的重要事务,并不能以寻常事务视之。但这些事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记载简略、文字较少,此外它们还经常是当日的第一条纪事。二是一些君臣议论。《中兴小历》中有很多可能出自起居注、时政记一类官方记载,包含了很多高宗君臣讨论政事的对话,特别是在绍兴八年秦桧专权以后的时段里,这类记载所占比重尤其高。但相应地,这类内容在《小纪》中遭到删削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三是一些整段引用其他材料(如《赵鼎事实》《秀水闲居录》等)文字的内容。《中兴小历》经常整段引用一些笔记材料的原文,这样的段落在《小纪》中也经常遭到删削。
另一方面,《小纪》中所有被删去的事条,基本上都能在《要录》中找到对应的内容。《纪事本末》与《小纪》均有且叙事大体一致的事条(即出自《中兴小历》而未经后人窜乱者),《要录》大多数时候也会记录相应的事项,甚至与二者文字保持一致,但也经常有记载与之差异颇大甚或完全阙失的情况。但那些《纪事本末》有而《小纪》无的事条,《要录》中一般必定有对相应事项的记载,且文字或与《纪事本末》基本一致,或较之更为详细。不过,《纪事本末》中的这些事条有时也包含着《要录》相应条目中所没有的信息;《要录》中的一部分相应纪事后,常见有小字注中提到“熊克《小历》”作如何的记载,这些记载也经常能够和《纪事本末》对应上。如表六这一条,根据《要录》小字注的描述,《中兴小历》原有此纪事,但今本《小纪》却无此条。而《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和《要录》大体类似,但在王时雍官职的记载上则和《要录》正文有差异,而同《要录》注所描述的《中兴小历》情形一致。这有力地说明,原本《中兴小历》当即有这一事条,且内容同《纪事本末》类似,但却在《小纪》中被删去了—《纪事本末》《小纪》《要录》之间类似这样情形的事条还有很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如此,那么为何这些在《小纪》中不见踪影的《中兴小历》事条,却都能够在《要录》中找到对应内容呢?考虑到今本《要录》也是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表六 《小纪》中事件缘起被删去的情况示例
(三)被删削文本在不同卷次之间的差异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小纪》中被删去的事条,在不同卷次之间或者说不同时段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小纪》不同部分被删去的事条多寡有所不同。如《小纪》卷二十一至二十四中所记绍兴七年正月至八年六月事,同《纪事本末》对应的内容相比,仅有极少的几条被删去。由于《小纪》经过严重删削,因此《小纪》一卷的纪事时段范围一般对应《纪事本末》的二卷,然而此四卷内容在《纪事本末》中对应的是卷四十至卷四十四等五卷,特别是绍兴七年的内容,近乎是1∶1被纳入《小纪》之中。此外,如记载绍兴三年事的《小纪》卷十五,较之《纪事本末》也删削极少,以至于《纪事本末》卷二十七的全部事条都被《小纪》收录,这是极为罕见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纪》卷三十一至三十四绍兴十三年至二十年间的纪事,《纪事本末》相应时段的内容为卷六十一至七十六,共计十六卷之多。《小纪》此四卷在保持内容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每卷的时间跨度都相当于《纪事本末》的四卷,其中缘由正是在于这部分事条被删去颇多。
不仅如此,被删削文本的形式、内容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卷间差异。如事件缘起保留、事件本体被删的第(3)类删削形式,在《小纪》中集中分布在卷十二(覆盖时段对应《纪事本末》卷二十至二十一)与卷十六(覆盖时段对应《纪事本末》卷二十八至二十九)。在内容方面,卷十五、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删削较少的卷次中,被删掉的事条内容也多是宰执拜罢等简单事项;而被压缩较多的卷三十一至三十四中,则有大量君臣对话、高宗“圣语”的内容遭到了删削。
今本《小纪》的分卷,应当并非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之原貌,更遑论原本《中兴小历》之形态。但是这种卷次差异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它反映出,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的不同部分之间,在删削去取的标准与具体操作方式上,既有内在的联系,又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四)小结
由于今本《纪事本末》纪事到绍兴二十年为止,我们比对二书的工作只能到覆盖《小纪》卷三十四及之前的部分,约占《小纪》全书的八分之七。但是从另一些宋人著作征引的《中兴小历》文字来看,对于绍兴二十一年以后的纪事,《小纪》应当也有删削。如《(嘉泰)会稽志》卷十三曾引用《中兴小历》所记载的绍兴二十九年高宗与王纶关于“沟洫利害”的一番对话,但《小纪》中却无此纪事;《要录》对此事亦有记载,但文字与之稍有差异(见表七)。可见,在事条层面对原本《中兴小历》进行的删削,是贯穿于《小纪》一书始终的。
表七 《(嘉泰)会稽志》所引《中兴小历》绍兴二十九年纪事
这些被删削文本在形式、内容、卷次差异等方面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删削之处,一般均涵盖完整的事条或事条三要件之一,“切口”相当齐整。这与《纪事本末》中脱漏、改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脱漏经常是从某一条的叙述中间忽然断掉,或被重新填充上《续宋通鉴》的文字,且填补的内容为了凑足字数,行文逻辑往往有不通之处。相比之下,《纪事本末》的脱漏与补充,更像是对一个书册残本的补救措施,而《小纪》的删削,则显然是一种有目的、有原则的系统性工程。
然而,一旦注意到《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这些特征,我们便也很难认为这些删削工作如高纪春所推测的那般,是宋元时期的书贾所为。《小纪》中的这些文本删削既有一定的规律性,又有极强的误导性,如果此书原本即以经过这般删削后的样貌作为一部独立著作存在,则这些删削工作实际造成了此书内容信息的极大变化,甚至是事件系时、前后叙述上的诸多差谬。即便是牟利的书贾,倘若以这样的方式编书,也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但如果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进行这般删削,本就不是为了以书册形式单独流传,而是要作为《大典》这样一部类书中的征引文献、依附于《大典》中的上下文而存在,那么一切都能得到完满的解释。要更充分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考察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所作删削与《大典》编纂之间的关系。
三、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所作删削的成因
《小纪》为何会呈现如今这样的状态?其中被删削的事条,是在哪一环节、出于怎样的目的被删去的?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近来,高纪春在驳斥了众多错误观点后,推测今本《小纪》中的这些删削工作乃是宋元时期书贾所为,在《大典》开始编制以前即已形成。其理由有三:一是《大典》编者没有四库馆臣一般需要篡改原书的政治理由;二是《大典》所载《长编》与《两朝纲目》均较为完备,没有经过系统性地删节,故而《中兴小历》也不应当独遭此厄;三是明正统六年(1441)编定的《文渊阁书目》中同时著录有“《宋中兴纪事本末》一部三十一册”和“《宋中兴小历》一部十册”,“从册数的绝对悬殊亦可想见,《本末》之内容卷数应远较《小历》为多”,故而高氏推测,明代内府所藏《纪事本末》“是内容完整、卷册繁多的全本”,《中兴小历》则已是如今这般的删节本,而《大典》所利用的则正是后一部。(高纪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关系再研究》,《文史》2022年第3辑,第182—183页。)
然而,从《大典》所引《长编》《两朝纲目》等他书情况来看,明廷所收藏并为《大典》所引据的宋史著作,大多应该还是一些比较完整的本子,很难想象唯独《中兴小历》是这样一个质量堪忧的删削本。高氏所举的三条理由看似合理,其实也均有值得商榷之处。以第三条理由来说,我们知道,古籍书册的装订变动往往较大,册数的多少并不能完全反映书籍内容的详略。同样以《文渊阁书目》为例,其中所载的“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就只有“一部二十册”,其册数比《纪事本末》还少(杨士奇等撰《文渊阁书目》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5册,第147页上。另,国家图书馆藏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所载“宋建炎系年录”册数亦同(见叶38b)。);但馆臣自《大典》中辑出的《要录》却有洋洋百余万言,其内容之丰富,与《纪事本末》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根据《文渊阁书目》所载《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二书的册数差异,即判断明代官方收藏的《中兴小历》是如今本《小纪》一般的删节本,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
而高氏的第一、二条理由之所以不能成立,则涉及《大典》的编纂体例问题,这也是本节的讨论重点。
《大典》编者确乎没有必须篡改所引之书的政治理由,但却有其他理由来删削引书文本—这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大典》自身的编纂体例。《大典》收录史书的体例,《永乐大典凡例》多所提及,近来学者已有过较为详细的阐发。(张良《〈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兼论〈永乐大典〉之修纂体例》,《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第199—232页。)其中与《中兴小历》文本删削问题密切相关的,主要是以下这一条:
若诸史中文有重复者,止存一家。或事文互有详略,则两存之。或事同而文有详略者,则存其详者。如外七史,南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之类。(《永乐大典凡例》,见《永乐大典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叶5。)
这条凡例说明,《大典》在编纂时会对所引诸史书文本有所去取;而其去取的主要原则,是避免重复。中国古代的史书往往辗转相抄,因而书写同一时代的史著之间内容重复者甚众。而《大典》本质上是一部类书,故而虽然征引文献,但其首要任务是记录文献中的知识,而非保存文献本身。因此,尽管《大典》中有很多“全录”条目,会不惜笔墨将一部分引书全文抄入,但当“诸史中文有重复”时,《大典》原则上会选择“止存一家”;如若诸史所记“事同而文有详略者”,《大典》则会只“存其详者”。这也就意味着,与所存的“一家”“详者”之言对应的“别家”“略者”之文字,将有可能不会被《大典》收录—由此,这种在“文同”或至少“事同”时避免重复的原则,成为了《大典》在一些“全录”条目中删削所引史书文本的基本理由。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最终呈现的样貌,很可能正是由此而来。
不过,《凡例》中对这一原则的实际操作方式语焉不详,要论证这条凡例如何在《大典》特别是赵宋诸帝条目中得到落实,我们还需结合《大典》残卷作进一步的考察。虽然这些条目的绝大多数内容均未能留存下来,但万幸的是,“宋宁宗”条下有前后连续的十余卷流传至今,其中所征引的《两朝纲目》和《宋史全文》二书,正好体现了对避免重复原则的实际运用方式。因此,以下我们即以《大典》此条对此二书的征引方式为例来加以说明。
《两朝纲目》,南宋佚名氏撰,其内容承续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以纲目体记载光、宁两朝史事。纲目与编年体例相近,且此书是现存的光、宁两朝编年史中内容较为详细的一种,在《大典》成书的时代应当也较受重视,故而在“宋宁宗”条下,此书在排序上仅次于《宋史·宁宗本纪》。而同条下紧随其后被征引的《宋史全文》,是元代书坊刊刻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含括整个宋代。此书的光宗、宁宗部分同《两朝纲目》在内容上颇多相似之处,很可能直接参考过后者,或与后者有着相同的史源。(对于二者文本源流关系的研究,参见梁太济《〈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李心传史学地位的侧面观察》,载《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91—521页;原载《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然而,《大典》编者在“宋宁宗”条中征引二书的方式,却有着天壤之别。在此条下,《两朝纲目》宁宗部分被全文照录,完全符合这类“全录”条目的一般做法;但是《宋史全文》在被征引时,却遭到严重删削,内容寥落。以至于今存“宋宁宗”条下所引的《两朝纲目》嘉泰三年以后的内容即占据五卷之多,若算上今佚部分,总共可能多达七卷左右;而原本与之体量不相上下的《宋史全文》宁宗部分,在同条下总共仅占一卷而已。
为何《大典》对待二书的方式如此不同?原因应即在于,《大典》编者在征引此二书时,遵循了《凡例》所提出的避免重复原则。这里以二书嘉泰三年三、四月间的纪事为例加以说明(见表八)。此二月间《两朝纲目》共六条纪事,而《宋史全文》则有十条,其中前八条与《两朝纲目》记载略同(“有司言”与四月丙午两条文字见于《两朝纲目》三月丙子条目文),只有四月辛酉、乙丑二条不见于前书。而《大典》在“宋宁宗”条下引用《宋史全文》时,嘉泰三年三月并无一事,四月亦仅录辛酉、乙丑二条—换言之,《大典》于此仅录用了《宋史全文》中不见于《两朝纲目》的事条,而删去了与之重复者。
表八 《两朝纲目》《宋史全文》原文及永乐大典本之文本比较
以上情况并非个例:实际上,《大典》“宋宁宗”条下于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五所保留的《宋史全文》纪事,绝大多数都是《两朝纲目》中未载之事条;而其所删去的,基本都是《两朝纲目》已有的事条。仅有极个别的例外不符合这一规律,如庆元元年正月丁亥条“蠲两淮租税”一事,《两朝纲目》有此记载,《大典》此处却未将之删去(参见佚名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四,汝企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9页;《永乐大典》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五,叶1b。);又如《宋史全文》庆元元年二月壬戌条原有“诏嗣秀王伯圭赞拜不名”一事,《两朝纲目》无此记载,但在《大典》中亦被删去。(参见《宋史全文》卷二十九,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叶1b。)考虑到《大典》体量浩大,又成于众人之手,难免会出现失误,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五中这些少量的例外情况,应可视为编者的遗漏与误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避免重复的原则在“宋宁宗”条下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此条处理《两朝纲目》与《宋史全文》的方式,似乎仅发生在这两种编年及纲目体史书之间,而不涉及最前面的“本纪”与后面的其他“杂史”。《宋史·宁宗本纪》与《两朝纲目》宁宗部分纪事亦多重复,然而《大典》残卷中所引《两朝纲目》中与《宋史·宁宗本纪》“文同”或“事同”的条目,皆未被删去。而《宋史·宁宗本纪》作为官修史书,是更权威的宁宗朝编年史,在此条下的次序亦在《两朝纲目》之前,《大典》当无删削前者而全录后者之理;且倘若《宋史·宁宗本纪》曾遭到如《宋史全文》一般的严重删削,则其同《两朝纲目》嘉泰三年之前部分相加,恐怕无法凑足《大典》中四卷的内容。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大典》“宋宁宗”条在征引《宋史·宁宗本纪》时,并未对其加以删削,也未曾借助其删削《两朝纲目》以降诸书。至于“宋宁宗”条下在《宋史全文》之后所引的《通鉴续编》《中兴大事记讲义》等书,虽然也有很多条目与《两朝纲目》内容重复,但《大典》的处理方式却与《宋史全文》不同。(关于永乐大典本《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删削问题,学界近来亦有关注,参见杨光《〈中兴大事记讲义〉在宋元时期的“再生产”—以版本比对为核心的考察》,《文献》2023年第2期,第79—96页;刘冲《〈中兴大事记讲义·宁宗朝〉永乐大典本考论》,《宋史研究论丛》2024年第2辑,第543—555页。相较而言,刘冲的观点似更为合理,但无论如何,《永乐大典》对《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处理方式都是与《宋史全文》不同的。)
因此,“宋宁宗”条征引《两朝纲目》与《宋史全文》的方式,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在编年(或纲目)体史书内部,将两种原本独立但内容重复较多的著作加以整合,以其中较重要的一种为基础,“全录”此书中相应时段内的文字,另一种则依据《凡例》所提出的避免重复原则,删去与前书“文同”或“事同而文略”的事条,仅保留前书未载或记载有较大出入的事条,附于前书之后。
“宋宁宗”条这种处理所引编年(或纲目)体史书的方式,很可能并非个案,而是《大典》中赵宋诸帝条目引书时的一种通例。《大典》北宋诸帝条目对李焘《长编》与熊克《九朝通略》的征引方式,或可作为旁证。前文已论及,《长编》在北宋前七帝条目之下,应当均是被全文征引的,恰如“宋宁宗”条下的《两朝纲目》;而《九朝通略》则没有那么幸运——据四库馆臣所见,这部原本一百六十八卷的著作,“今《大典》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无端委”。(《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册,第62页。)由于《大典》引书是打乱原书卷次的,《九朝通略》至清代亦无其他传本,因此四库馆臣所言的“仅存十有一卷”,当是指《九朝通略》一书在《大典》中占据了十一卷篇幅,就如《宋史全文》占据了一卷这般。因此,四库馆臣的记述提供了两方面信息:一方面,《九朝通略》在被《大典》征引时还是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有一些整卷录此书文字的情况出现,说明此书应当曾为《大典》的“全录”条目(按照《大典》的编纂体例,当即北宋诸帝条目)所征引;但另一方面,《九朝通略》即便在这些整卷引录的部分也是“首尾零落,已无端委”,说明此书在被“全录”条目征引时遭遇了相当程度的删削。种种迹象表明,《大典》北宋诸帝条目在征引《九朝通略》时,处理方式当一如“宋宁宗”条之于《宋史全文》——甚至很有可能,在北宋前七帝条目中,《大典》编者即是比照《长编》来对《九朝通略》进行删削的。
由此,我们可以反观《大典》“宋高宗”条下所引的《要录》与《中兴小历》二书。四库辑本中所见二者留存的状态,正与《大典》“宋宁宗条”下的《两朝纲目》与《宋史全文》、北宋诸帝条目下的《长编》与《九朝通略》略同:《要录》得到《大典》详尽的“全录”征引,《中兴小历》则遭到严重删削,且被删削的基本都是与《要录》重复的事条。通过这番类比可以看到,《要录》与《中兴小历》四库辑本的内容,在被收录在《大典》的“宋高宗”条下时,很可能是《要录》在前,《中兴小历》在后;由于《要录》的史学价值在各方面均胜《中兴小历》一筹,所以《大典》编者全录了《要录》,之后在抄入《中兴小历》时,也对照《要录》,删去了很多“文同”或“事同”的事条,又对二者皆曾引用的一些长篇奏疏进行了节略。高纪春引《长编》与《两朝纲目》二书为旁证以说明《小纪》中的文本删削不可能是《大典》所为,这一论证之所以不能成立,症结即在于找错了参照系——在《大典》“宋高宗”条下,地位与《长编》《两朝纲目》等同的其实是《要录》,而《中兴小历》则类似于《九朝通略》《宋史全文》。
一旦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特征,便都可以得到解释。《大典》“宋高宗”条下的《中兴小历》文本原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同条下的《要录》文本具有一定的共生关系,故而很多事条的删削只是为了避免二书之间的重复,却未考虑到若单独抽出《中兴小历》看会有叙述凌乱、系时倒错等问题。同时,《要录》与《中兴小历》这两部著作卷帙浩繁,文字冗杂,比对删削的难度较大;即便面对《两朝纲目》与《宋史全文》这样相对简单的文本时,《大典》编者尚且会出现漏删与误删的问题,因而他们在比照《要录》删削《中兴小历》时会留下大量的纰漏,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凡例》中对“事文互有详略”与“事同而文有详略者”的界定其实相对模糊,《大典》又成于众人之手,各人对编纂体例的执行标准乃至工作态度都有较大差异,因而最终造成了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中存在很多删削不尽、不当的问题。
表九 《小纪》事件本体被删去者与《纪事本末》《要录》之文本比较
(注:根据高纪春等人的研究,表中《小纪》第二条的小字注,当是四库馆臣辑出时所加)
不仅如此,《小纪》中很多事条只有系时以后的部分被删去,很可能是因为《大典》相应卷次的编辑者是以干支系日为基准来比对《要录》与《中兴小历》之事条的。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要录》中事条三要件的排列方式与《中兴小历》不同:前者每日的纪事绝大多数都是以系时开始,极少在当日系时前书写事件缘起;后者则是在系时之前书写事件缘起。故而尽管《中兴小历》中的很多事条,正如表九中所示一般,其全部信息均已被《要录》中的相应记载囊括,只是叙述顺序不同,照理应当被整条删去,但实际上只有系时以后的部分被《大典》编辑者找到并删去。出于类似的原因,《小纪》中也出现了如表十所示的情况。对比《纪事本末》可知,己亥条纪事在《要录》中并无相应记载,但其事件缘起部分(“吏部奏大小使臣差遣事”)在《小纪》中却被无缘无故地删去。究其原因,应当是《大典》编者以为己亥条是从系时处开始的,而“吏部奏大小使臣差遣事”这几个字是戊戌条的一部分,故而在比对《要录》发现相同位置已有类似记载后,一并予以删去。
表十 《小纪》戊戌条被删削的状况
至于《小纪》中那些纪事简略的事条更多地被删去,则很可能是因为《大典》编者更容易在《要录》中锁定与之内容重复的条目;当某一日有多条纪事时,其中第一条更容易被删去,原因应与此相同。而《小纪》不同卷次之间在事条去取标准上有一定差异,也可能是因为《大典》编纂时,编辑《中兴小历》这几卷的人不止一个。这些人彼此之间有所分工,又对凡例的理解、去取的标准乃至工作态度都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今本《小纪》与《要录》仍多有“文同”“事同”之处,这表明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中也有很多与《要录》重复的事条并未遭到删除,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总而言之,综合考虑《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特征,《大典》的编纂体例及其在赵宋诸帝条目中的实际操作方式,以及其他诸多旁证,《小纪》中被删削的文本,最有可能是在《大典》的编纂过程之中被删去的,而非之前或之后;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最终形态的形成,当同《大典》赵宋诸帝条目对避免重复原则的运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小纪》中被删削文本的特征及其成因。今本《纪事本末》在掺入了少量《续宋通鉴》文字之外,应当仍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原本《中兴小历》中绍兴二十年及以前的内容;而《小纪》在排除掉四库馆臣于字词层面的篡改之后,应当基本反映了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即《大典》“宋高宗”条下整体引用的《中兴小历》文字之样貌。通过《小纪》与《纪事本末》的文本比对,本文揭示出《大典》删削原本《中兴小历》的具体情形,包括被删削文本在形式、内容等方面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不同时段之间的差异性。永乐大典本《中兴小历》的形态,是由《大典》的编纂体例与编纂实践所造就;其中被删削的文本,应当是在《大典》的编纂过程之中被删去的。
本文的讨论,虽然看似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案研究,但它背后实际牵涉到另一些更深层的问题。首先,《中兴小历》一书如今虽仅有《纪事本末》与《小纪》两种“变体”传世,但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二者的流传演变过程,将二者同其他宋代材料所征引的《中兴小历》文字综合加以利用,是能够在现有条件下尽量恢复《中兴小历》原本状态的。这对于我们利用这部著作研究高宗朝政治史乃至南宋史学史,都将大有裨益。而理解《小纪》的样貌与《大典》的编纂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合理利用这一史料的重要前提。
由此,本文的研究也提示我们,对《大典》编纂方式的探究,对宋史研究的开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明清以降,《大典》成为学者辑佚文献的重要对象。从《大典》中所辑出的古代文献多达千种,其中尤以宋代文献数量最多、史料价值最大。《长编》《要录》《宋会要辑稿》等等极为重要的宋代史料,均是因有《大典》辑本传世,才得以为今人所用。因此,宋史研究者在充分利用《大典》进行辑佚、借助《大典》辑本文献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应当充分注意《大典》的编纂活动、后人的辑佚活动本身可能对史料文本、体例造成的扰动。对《大典》编纂的实际操作方式展开进一步研究,将能够使我们对《大典》宋代辑佚文献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帮助我们剥离出这些辑本文献生成的不同层次,从而也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些文献所载史实的理解。前辈学者针对《宋会要辑稿》等书的研究已经开此先河,本文的讨论则提醒我们关注《大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更具体的操作方式—受这些操作方式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兴小历》,也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宋代史料文献。
而如果我们着眼于《大典》的编纂方式,则本文的讨论又会引发另外一些思考。最直接的一个便是:赵宋诸帝条目处理《宋史全文》《中兴小历》等编年史的方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朝代诸帝条目之中?就笔者所见《大典》残卷来看,赵宋以前的诸帝条目在引用诸史时,似乎并未着力于删削史书。如留存至今的《大典》卷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九至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六乃“宋文帝”条下之部分内容,其中先后征引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与朱熹《通鉴纲目》,但二者皆为全文照录,并未见到哪一方曾因二书内容重复而被删削。另外,尽管《凡例》在揭橥避免重复原则之时,是以“外七史,南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等为例,但实际上,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一些人物、名物条目对这些史书之志、传的引用上,如“陈”字韵下的“陈叔达”“陈君宾”等条,只选用了《旧唐书》本传,而未取较为简略的《新唐书》本传(陈叔达在《陈书》中亦有传,但极简略,《大典》亦未用);与此同时,在现存的“唐宣宗”条下,两唐书的《宣宗本纪》却均被全文录入,并未因事有重复而遭到删节。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不同时代史料留存情况的差异有关:五代以前的史书,在《大典》成书之时留存已不算多,且多为正史、《资治通鉴》或《通鉴纲目》等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著作,诸书又有各自独特的笔法与体例考量,因而这些引书在诸帝条目中得到了较全面的保存;而宋元时期成书的宋史著作,在明初之时数量仍很可观,而且泥沙俱下,很多著作并不具备经典性、权威性,内容重复之处又极多,故而有部分著作即便在赵宋诸帝条目这样的“全录”条目下,却仍然遭到了严重的删削。
这些情况表明,《大典》的实际编纂方式非常复杂,《凡例》同《大典》的编纂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追索。目前针对《大典》引书的研究,多是在《大典》与某一文献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考察《大典》征引此书时使用的版本、引用此书的方式等问题。这些个案研究无疑为我们理解《大典》的编纂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但《大典》的编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窥一斑有时未必能知全豹。因此,即便是为了理解《大典》与某一所引文献的关系,我们也不能仅仅着眼于《大典》征引此文献的情况,而是需要转换思路,以《大典》为中心,对其中某类条目编排内容的方式进行整体考察,才能对很多现象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