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的官僚体系中,有一个特殊群体,那就是言官。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刚愎雄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在废除中书省后,又在六部之中设置了都给事中和左右给事中,品级正七品,掌封驳诏令、稽查六部;同时又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共同构成了明王朝“科道并行”的言官体系。
明王朝言官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小治大”,这里的“以小治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言官们对于皇帝的旨意有“封驳”之权,其次则是品级只有七品的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们有权力监察朝廷二品大员。
当然作为明王朝言官体系的创立者的朱元璋而言,言官体系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监察百官,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还赋予了言官们“风闻奏事”的特权,也就是说在言官弹劾朝廷大臣,不需要实际证据。
洪熙元年,言官体系正式形成“科参制度,”明朝言官体系的职能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分别是言官体系的官僚纠劾权和对皇帝旨意和六部奏章的封驳权;宣德十年,都察院御史按照十三布政司形成固定监察区域,覆盖了整个大明帝国十五省中的十三省,其中南直隶和北直隶由都察院直辖。
至此,明王朝言官体系行政框架和运行制度真正成型。
不可否认,在明王朝前期,言官体系的存在,大大增强了明帝国决策的容错率,言官们封驳权力为明帝国的决策运转起到了“安全阀门”的作用,这种制度设计让明朝的决策更加谨慎,同时言官们还负责监督百官,对维护官场风气、保证政府正常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整个封建帝国的吏治清明和健康运行起到了监督作用。
但文管体系的这种监督权力,在随着明王朝权力的失衡逐渐失去了原本客观的监察立场,异化为明帝国政治势力之间博弈的工具,是明王朝中后期党争的主要政治武器。
言官体系的异化,主要是开始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战”,由于英宗对于宦官王振的盲目信任,形成皇权和宦官势力的结合:皇帝绕过言官监督机制乾纲独断,宦官凭借皇帝的信任把控军政大权,言官们的“封驳权”彻底瘫痪。
当然其中也有言官们不知兵的原因,导致言官体系的监察权在战时彻底失效。
事实上在土木堡之后,文官集团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明王朝中后期的一元化文官政治,皇帝为了对抗文官集团对于皇权的压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对文官集团进行打压:一条途径是皇帝联合宦官势力,比如武宗时期的皇帝借助巨宦刘谨来对抗文官集团;另一个途径则类似于暴力镇压,比如嘉靖皇帝炮制的“左顺门流血事件”。
同样,文官们同样以言官的“纠劾权”形成祖制,道德的牢笼,把皇权逐步困在宫廷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万历皇帝时期的“国本之争”,文官们以言官的“封驳权”把皇帝的旨意困在宫禁之中,对于六部奏章则进行筛选,然后把符合文官阵营利益的奏章送入宫廷。
如果皇帝批准,就会增强文官集团的力量,如果皇帝留中不发,就会背上拖延国政,昏庸无能的黑锅。
原本作为国家决策“安全阀”的言官体系,在这个时候变成了隔离带,把皇帝与朝廷大臣隔离开来,内廷与外朝的沟通渠道被割断,皇帝成为了文官集团摆在龙椅上的吉祥物。
天启帝时期,文官集团内部分裂成了东林党,楚党,浙东党,还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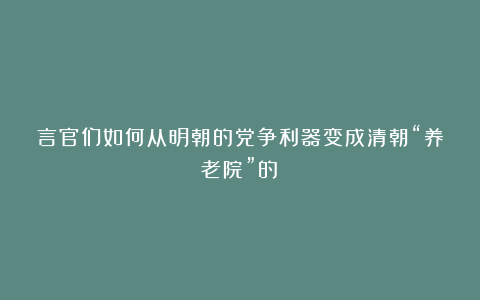
言官“以下制上”的特殊职能,迅速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言官群体随之分裂为‘清流派‘与‘阉党派‘,形成‘每疏必争,每争必讼‘的恶性循环,监察重点转向双方的礼仪琐事,以至于明王朝末代帝王崇祯帝在面临国家危亡时,却仍然“忙于琐事而无瑕大政。”
言官体系的建立,原本是为了监察百官,形成皇帝耳目,最终却走向了其创立初衷的反面,言官们从‘天子耳目‘沦为党争工具,从‘风宪之臣‘变成政治打手,最终沦为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角斗场。
崇祯末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言官们仍在为繁琐礼仪喋喋不休,这种制度性失灵最终与明王朝一同走向了终结。
公元1644年,当清军铁蹄驰骋在中原腹地的时候,一个崭新的王朝被重新建设。
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政治框架进行的继承和扬弃,言官体系就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清王朝虽然表面上保留了六科给事中的编制,依旧拥有“封驳”之权,但实际上仅能针对文书技术性错误提出修正,无权质疑皇帝核心决策,明代给事中可驳回皇帝敕令的“以小制大”权力被废除,比如顺治朝明确规定,“凡内阁票拟本章,六科仅得稽核显谬。”
康熙皇帝时,对于言官的原本的“纠劾权”进行了修改,言官体系的监察方向由原本的“议论国政”转向具体吏治问题,尤其强化了对钱粮亏空、刑狱冤案等实务的稽查力度,这种转变既规避了明代言官空谈误国,又使监察力量聚焦于维持官僚体系的健康运转。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为了避免言官体系再一次从国家决策的“安全阀”演化为围困皇权的“隔离带”,他补充了“密折制度”,密折制度下,皇帝任意选择心腹大臣,可以绕过科道监察体系,直接向皇帝汇报各地事务。
“密折制度”有效避免了科道监察体系把皇帝和朝廷隔开的困局,是清朝统治者对言官体系的补充。
雍正时期,六科并入都察院,形成“科道合一”的新架构,结束明代以来科、道分立的双轨制,合并后六科长官改称“掌印给事中”,改革后的六科给事中品级从正七品降至从七品,沦为都察院下属官员
这种情况下,原本属于六科的封驳职能被转移至都察院,而都察院完全听命于皇帝,意味着封驳权从“制约皇权”变为“皇权工具”。
同时,雍正帝大幅度扩大了康熙帝时期的密折制度,打造了直达皇帝的信息网络,科道言官体系事权大幅度缩水。
乾隆皇帝在康熙帝和雍正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密折制度,科道言官体系逐步沦为“闲散机构”,朝廷事务的处置,大部分都是经过密折制度的信息网来完成,特别是对于地方贪腐各种案件;相比于科道言官体系的冗长程序,密折制度显得高效务实,更得清朝统治者的青睐。
科道言官体系的衰落,是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冗长的监察流程,以及“风闻奏事”带来的公共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其“封驳权”有掣肘皇权的可能,这些都成为清朝统治者眼中的隐患。
当密折制度将信息权、监督权、决策权全部收归皇帝一人,传统言官‘以制度制约权力‘的功能自然瓦解,但是同样,失去制度保障的密折体系,最终因过度依赖皇权个人能力,反而最终成为清王朝晚期的衰落的沉重枷锁。
从封建社会角度来说,清王朝对科道言官体系的改革,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完美规避了科道言官体系对皇权的制约,维护了封建帝国条件下皇权的至高无上。
当然,如果站在历史大角度看,清王朝对于前朝的制度改革,就如同在修补一件破屋子,但不论修补得如何完美,这座房子的地基却已经在时代洪流中塌陷。这座被修补好的屋子,反而成了清王朝最后的棺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