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全国名为“香山”的地方不胜枚举,而苏州吴中香山,却因2500年前吴王种香、西施采香于此而得名。千百年来,悠悠太湖水涵养了香山人包容开放、勇于探索的艺术情怀。而香山的山水,也催生出了别有的人文。
《木渎小志》
据《越绝书》记载:“葛山者,句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去县七里”同一件事,《吴越春秋》中也有类似记载:“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欲献之。” 其大意是越王勾践在败于吴国后,为了麻痹吴王夫差,命令越国的男女入山采葛,让越国女子织造成黄丝葛布献给夫差。夫差因葛布“弱于罗兮轻靡靡”,便命在太湖沿岸(包括香山)大规模种植葛草,作为纺织原料基地。葛布在春秋时期是重要的纺织原料,吴国通过控制葛草种植和纺织技术,巩固了经济实力,香山也因此成为吴国手工业的重要基地。而香山后来闻名的 “香山帮” 建筑技艺,其工匠传统或许与早期葛草种植、纺织业积累的手工艺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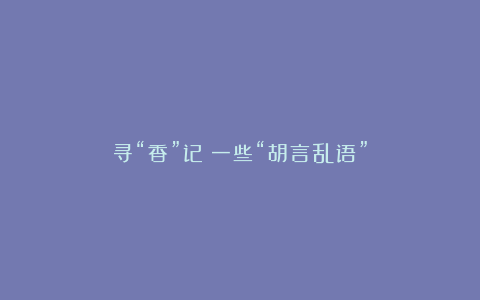
1972年,在距今六千多年的苏州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三块炭化葛布罗纹织物,它们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手工织花葛布实物,也是最早的纺织实物之一。同时出土有陶制纺轮、骨制梭形器、木制绞纱棒等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说明先民们早在六千多年前,就掌握了纺织的专业技术。在中华书局注音版《说文解字》中,“葛”标注读音为gé,其解释为“絺綌艸也”。古人依据纱线的粗细为葛布划分了等级,类似于现代衣服水洗标上对面料的分类:最高端的葛布名为“绉(zhòu)”,细薄的葛布称为“絺(chī)”,而粗厚的葛布则叫“绤(xì)”。这表明当时葛布的纺织技术已经相当高超。此外,《周礼·地官》中还专门设有“掌葛”之官,由此可见葛布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古代,人们消夏避暑的智慧别具一格,而轻薄的衣物则是抵御酷暑的必备之选,其中细葛布尤为突出。细葛布洁白亮泽,织就的葛衣轻薄透气、吸湿散汗,深受贵族统治阶层的钟爱,象征着统治阶级的身份与地位。魏文帝在《说诸物》中赞誉道:“江东葛为可,宁比总绢之繐辈,其白如雪华,轻譬蝉翼。”《遵生八笺》中还详细记载了葛衣的洗涤方法:“洗葛衣,用梅叶揉碎洗之,经夏不脆。忌用木盆,否则黑,当以磁器洗之。”具体而言,轻薄的葛衣需置于瓦盆中,以梅叶泡水,借助梅叶的酸性去污,再轻轻揉搓洗净并阴干,如此方能保持其洁白轻柔的特性。
foto by:织绣染
香山曾经可能拥有着深厚的葛草文化,其发展历程或许折射出古代手工艺的进步,也承载着先辈们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然而,时至今日,制作与使用“葛”已十分罕见,像哈尼族手工编织的葛包,虽很貌美但数量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