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列游记第207&208合篇:河南光山邓颖超祖居&永济桥
题记:女杰无缘归祖宅,古桥流水逝繁花
寻访时间:2025年10月17日
本文系静思斋·于岳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这几年每到秋季,我总会策划一次为期三日左右的“别致”秋游。所谓别致,是指行程主旨与我的某件藏品深度相关,或是对我所关注的某历史事件的实地走访。此前两年皆赴陕南之汉中,今年则为豫南的信阳一带。
在大城市的钢铁水泥森林中待久了,有些厌倦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气息,高速的生活节奏亦时常让人感到焦躁。近年若是自己一个人独行,我则格外热衷于“走县”——深入到一些冷门的县城甚至乡村,去品味一些与大城市有别的气韵和慢时光。坐绿皮车到信阳那天,预报下午将有大雨,恐不适合爬鸡公山,我遂改变了原案,在信阳站“无缝换乘”先去县城。此行的核心目的地是潢川县(原委下篇再说),但我在盘点信阳的文保名单时发现,潢川旁边不远的光山县(只需多坐十几分钟火车)有国保两处,乃决定先至光山一游。
光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角、大别山北麓,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经济似乎稍欠发达(2018年才摘帽)。老县城东门外有一座紫水塔,塔建成于康熙初年,因矗立于紫水河畔而得名。乾隆年间塔毁,直到光绪年间才由知县王玉山(河北冀州人)主持重修并亲题门额,但因资金短缺,当时只修复到第五、六层,第七层及塔刹直到解放后才得复原完整,这也是光山城区范围最拿得出手的一处古迹(现为省保)。我在火车站乘7路公交至此,从紫水塔开始了光山之旅。
光山在古代与近代分别出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古代的是司马光,司马光是“土生土长”的光山人,其父当时在光山当县官,据说司马光是因出生地而得名,此“光”正是光山县的“光”,而如果“司马缸砸光”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它正是发生在这里。后来司马光名垂青史,成为光山人的骄傲,现代为发展文旅专门开辟了一个“司马光故居”(原为宋代官廨,明清时改作学宫,现为市级文保),成为当地名胜。故居旁建有司马光宾馆,我因对先贤在史学上的成就深表景仰,差点就在“他家”下榻一宿。
近代的那位则是邓颖超。邓家的宅院就在“司马光故居”西南不远,一路上走过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或许还保留着清、民时的格局。来此参观后我才知道,原来邓颖超的家世颇为了得,其父邓廷忠是光绪时期的武进士,被皇帝钦点为御前侍卫,三年后获派外任,起步就是从三品的游击。邓廷忠骁勇善战,在广西抗击法军时曾以铁旗杆格毙法军少校,庚子年间回京护驾有功,被擢升为总兵(武职正二品),惜后来与广西提督有隙,被诬革职充军新疆,最终客死他乡。但即便如此,邓家在光山也堪称头等门第了。
不过邓颖超可谓一位“非典型”光山人。她生在南宁(其母为续弦),长在天津,唯在8岁其父去世那年,其母带着她打算回光山祖籍省亲。但因当时通讯极不发达,她们乘坐的火车晚点,来信阳迎接的家人苦等未见人,只好先回光山,待母女二人到了信阳,不见有人接站,又人生地不熟不知光山何在,只好转车回湖南娘家去了。邓颖超后来四海为家,却从未回过光山,幼年的失之交臂最终成为历史遗憾。
邓颖超的丰功伟绩这里不再赘述,邓家老宅应该也正是因为这个从没回来过的女儿得以保存下来,且挺早就被列入国保(否则寻常清代宅院当然很难成为国保)。国保项定名为“祖居”而非“故居”,是非常贴切的,其中的玄机正如上面所述,而且可能另外还有一重考虑:邓颖超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她与周总理住过的房舍“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而此处虽搞成了纪念馆,但毕竟不是故居,且宅院以前也是邓家私产,既尊重了遗嘱的精神,也收得纪念缅怀之效,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我在司马光、邓颖超两家的宅院中大略转了一圈,并未停留太多时间。说实话,名人故居在我寻访国保的经历中,属于我不太喜欢逛的四类之一(除了那些富丽堂皇、能让我对“美好生活”产生向往的),颇有鸡肋之感。毕竟它们的文物属性普遍偏低,拍照也不好看,而我对那种提纲挈领式的陈展需求又属实不高。
光山的另一处国保永济桥,远在县城南边五十里的泼陂河镇。但光山的城乡公交搞得相当不错,从县城到镇上很方便(我事先打电话给公交公司专门咨询过),只需3元,近乎直达。而桥则是我特别喜欢的四类古迹之一(墓、塔、桥、寺,排名分先后),可以去永济桥其实才是我此番决定来光山的最主要原因。
泼陂河这个地名挺有意思,又被“简称”为泼河,我想这可能与第二个字的读音比较复杂、难以被人读对有关。“陂”字有四个读音(bēi、pō、pí、bì),此前我只知pí(好像只用在湖北黄陂这个地名上)和bēi(池塘,如芍陂),《信阳河湖大典》中对泼陂河的英文注释为(Popi river),故我一度将这里戏称为“泼皮河”,但又觉得bēi音的应用似乎更为广泛。刚在网上查,又有一道“真题”说这里应读pō音(读pō时,字意为不平坦),所以泼陂河到底应该肿么读,我现在还真不是很确定,可惜当时没有和老乡尬聊几句求证,是我疏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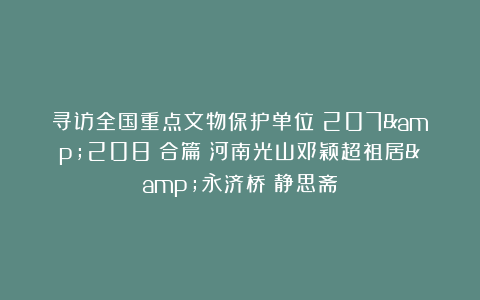
这里大概在元代即已成市镇,泼陂河则是在清代正式定名。这条淮河支流的支流,水面实则颇为宽广,旧时逢雨季常有洪涝灾害。明万历末年,当地士绅集资建桥,不久后由致仕还乡的御史毕佐周主持修建,由于工程难度很高,一直修了七八年,方于天启七年(1627年)落成,桥名永济,又因集各家之财力建成之故而称“万金桥”。
永济桥微呈“八”字形,长百米有余(著名的赵州桥只有60多米),据说是河南全省最长的古代石桥,远远观之,但觉稳固坚实,根骨不凡,实为古桥中之杰作。自桥建成,当地水陆交通日渐便利,清、民时期的泼陂河发展成一个热闹的集镇,“南北两街,商旅辏集”,大概到了抗战时期,才逐渐没落下去。再后来这里成为“老区”,在著名的“中原突围”中,“我军”王树声部就是从泼陂河镇踏上征途的,他们的脚步想必也曾经过永济桥。
在现代行政区划逐渐定型、现代交通蓬勃发展之后,泼陂河则愈发边缘化,以我今时所见,除国道两侧之商铺略有活力之外,往深处走则人烟稀少,只碰到一些“留守老人”在屋里打牌消磨时光。便是当年那条繁华的“明清老街”,如今门户大半紧闭,细雨之中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面上,唯闻自己的脚步橐橐回荡,更添萧条冷肃之气。当然了,我平生素来厌恶人多嘈杂,在眼前这般氛围中怀古,高兴还来不及呢!更何况,若非是以国保为纽带,我又怎会有机会千里迢迢与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地方产生奇缘呢?除了少数发烧友,大概也很少有人会以“旅游”为目的来到这里吧。
永济桥就在明桥老街北口的不远处,国保碑被桥头护栏挡得严严实实,无法拍摄正面,我这可是从各角度拍全后请高手PS修复的,目前网上大概唯此一张靓图。四百岁高龄的永济桥虽已贵为国保,但仍然切实肩负着沟通两岸之责,甚至小型汽车亦可畅行,绝不似许多古桥已成为温室中被人百般呵护的花朵那般娇柔不堪,而这种“活着的”的古桥尤为我所喜爱。
信步走到桥上,脚下砂石(这大概是近代修缮所致,据说抗战时期永济桥曾被国军103师炸毁两孔,但具体时间和原委有待考证)发出细腻的咯吱声。桥板之上,滑腻的青苔好似一层温润的“包浆”;石缝之间,则生满了各种草本植物,岁岁轮回。流淌的河水带走了世事变迁与人生百态,唯有脚下的古石桥岿然不动,这种厚重的沧桑感,大约也只有身临此境,才能在刹那间有所感悟。远眺着更为源远流长的泼陂河,不禁幽幽一叹。
解放后在永济桥上游不远处兴建了泼河水库,如今河面风平浪静,大约已鲜有洪水之患,生态环境看似也尚可,空中有鸿雁,水中有游鱼。岸边坐了些悠闲的垂钓叟,甚至还有放梯子下到桥东面分水尖上的,这是又一个领域的发烧友。间或有鱼儿上钩,在水中挣扎的扑通声便打破了时空的宁静感,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被拉出水面,嗬,好大一条肥鱼,可怜就要成为人家的盘中餐了。
这别有一番画意的乡间惬意时光弹指而逝,忽而天色渐沉,雨势渐起,我复撑起伞来,就此默然别过。从泼河坐城乡公交终点便是光山汽车站,我心想已然没有必要再走回司马光宾馆住上一宿,不妨直接去潢川便了,于是取消了预定房间,在汽车站又一次“无缝换乘”。待到夜幕快降临时,我已抵达潢川,站在心心念着的潢河岸边了。
其实泼陂河正是潢河的支流,假如那条鱼没有被人捉到,我想它大概也有机会能游到这里吧……
静思斋 于岳
2025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