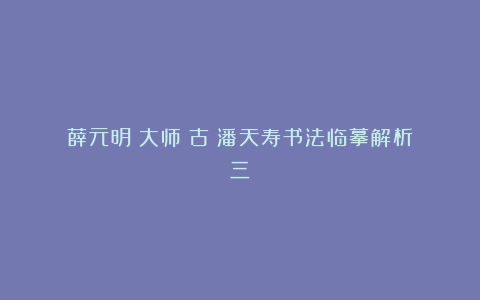为了不错过每篇推送,请将“牛墨王说书”设为星标 ☆
大师橅古:潘天寿书法临摹解析(三)
▲潘天寿
行(草)书是潘天寿存世最多的书体,最见性情变化,也最能代表个人成就,贯穿其一生。行书的积累毕生以黄道周为根基,但发展、融合脉络最为复杂,可谓是千头万绪。如前所述,好在潘天寿有一个特别的习惯,留存于世的很多作品,有具体时间,这就使得其风格锤炼和变化脉络虽然略显纷繁,依然可以梳理出明确的脉络。
▲私塾匾额“率真处世”,取法柳公权
▲早年所书“五叶流芳”匾,23岁
▲崇德,取法颜真卿
▲《埋头子》诗四条屏,取法颜真卿
先看几件早期风格尚未定型的作品,在锁定黄道周之前,即便是大师,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喜好不定。“一师”前后的书迹不多见,大字残匾“率真处世”和“五叶流芳”,主要取法柳公权,尤其是“率真处世”匾额,更为明显。“五叶流芳”能够看到具体的时间,时23岁,乃是为冠庄“都总庙”旁的“清莲寺”书题,可以看出气格不俗,丝毫不拘谨。“崇德”有非常明显的颜体风格,但已经有一种不安分的气质。很多人学书印持有一种观点,认为颜柳书俗,易刻板,而学印则认为吴齐“有毒”。不知道这些观点出自何人之口,其实任何经典作品,既有启发性,也有限制性,事在人为,个人必须是“善学者”,知其长,更知其是否适合自己。以颜柳为启蒙根基,几乎是中国人学习书法,特别是自唐之后,普遍存在一种选择倾向,尤其是书家在幼年时期,多半是大人做出的选择,根本不是自主意识。这种“第一口奶”是好是坏,仍然取决于个人。到了明清之际,更是异常普及,令人讨厌的“馆阁”,被视作颜柳的“异化”。有一件内容为《埋头子》自作诗四条屏根基仍在颜,但个人风格已初见端倪,特别之处在于有翁同龢书风的影子。翁同龢本身也是学颜的,可谓是顺受其正。有一种可能性,某次见到翁的作品之后很激动,一时技痒而挥毫。这和今日到了博物馆看到一块古砖或残瓦之后忍不住以指代笔划来划去,道理是一样的。分析大家的取法,应该考虑到一些偶然性。
▲赠赵平福册,拟康有为笔意,24岁
▲《沪杭车中偶成》诗札,取法沈曾植
▲集“零石天花”联,拟《石门铭》笔意
同样的“小概率”,也体现在早期的“灵石天花”联中,潘氏个人特有的霸气基本上一览无余。这件对联风格竟然与民国的庄蕴宽书法极为神似,庄也是写《石门铭》的。这说明,潘天寿宗法北碑,最初是时代大潮的作用,而后就受到个人心目的偶像如康有为和沈曾植等人的强烈影响,《赠赵平福册》就是典型的“康体”,但又避免了“像翻滚的烂草绳”的不足,用笔起收刚劲利落,从23岁的“五叶流芳”到24岁的《赠赵平福册》,风格跨度实在太大了,难怪吴昌硕见他之后担心“行太速”。大家并非都是到了风格完全成熟之际才有不凡气象,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赠赵平福册》尚可见《瘗鹤铭》笔意,最典型的如第二列的“相”字极其明显。《沪杭车中偶成》诗札乃典型的沈曾植笔法,字字独立,有浓重的章草意趣,又有《宝子碑》的恣肆。这并不奇怪,沈曾植本身也是写《宝子碑》的,外加上又是乡贤,晚清遗老,海上名宿,其时与康、吴并列,自然会对潘天寿有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明白一点,这也可能是一种“暗合”,因为书法存在“共性”的成份,但在分析思考的过程中,需要左顾右盼,方能有所悟、有所得。
▲《秃头僧图》,26岁
▲左图,《墨荷图》,26岁;中图,录苏轼《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句题款,38岁;右图,录李贺《蝴蝶飞》诗,45岁
徐渭是另一位对潘天寿影响巨大的乡贤。作于26岁的《秃头僧图》和《墨荷图》款字,先声夺人,飞扬跋扈,有不可羁勒之气,特别是《秃头僧图》款字,与青藤笔意特别接近。徐渭故居的“青藤书屋”四字,便出自潘天寿手笔,评徐渭乃潘天寿的精神偶像,所言不虚。有意思的是,人到中年之后,徐渭的笔意仍偶尔会显山露水,可以称之为“艺术反刍”现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轮“反刍”,食物虽磨细研碎,但所获能量并未增加。但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大有不同。借助“反刍”,引导并给与一定时间让自己形成内化和反思,使得不能理解之际再次返回原点,如此循环往复,促进肌肉记忆、知识积累和深入思考,从而提高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艺术家只有具备蕴含灵智特性的反刍功能,可以凭借助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这种超时空的体验和感悟,可以给予艺术家的无穷灵感,经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这样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
▲《暗香冷梅图》,29岁
▲《秋华垂湿露》,28岁
1923年,从一师毕业三年后,潘天寿由褚闻韵引见,拜访年逾八旬的吴昌硕,两人结成忘年交。同样又是一位乡贤!其后,潘天寿老老实实收敛了自己早年粗阔雄肆的画风,而从吴的画法入手,从笔墨、构图、意境等各方面加以揣摩。这种深入传统的努力,为他几年后最终跳脱吴风影响,寻找并确立自身艺术面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上海追随吴昌硕期间,潘天寿的诗文书画印无不受其影响,持续了数年时间,尤其是在最初的两年间,其行草书题款与吴昌硕极为相似,得其笔法、体势和神采,模拟地惟妙惟肖,入之甚深。从作品持续时间来看,吴昌硕对潘天寿影响巨大,膜拜服膺之情常溢于言表,亦可见看出潘天寿的模仿能力。潘天寿的艺术个性很强,不想一味的摹仿。这就是大师的特质。缶庐曾对友人说:“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多半年,可得皮毛也。”潘天寿更是谨记吴昌硕的教诲——“化我者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必须另辟蹊径,跳出吴门。吴昌硕的行草书参以篆隶楷多体,潘天寿为了能写出不同面目,尝试融入北碑的奇肆,汉隶偏方结构和方折用笔,打破了吴书的耸肩体势,虽保留了吴书苍茫古厚的气息,但整体上拉开了距离。第二次登门时,吴昌硕即书赠潘天寿“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的集古诗联,给予潘天寿的书法和诗文很高的评价。“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吴昌硕评“阿寿的画有自家面目,这就好……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潘天寿师从吴昌硕而不泯于吴,苦心探索独运机杼,始终保持自身的艺术气质,极为高明。在吴门弟子中,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自立门户的,也仅仅只有潘天寿等极少数人,所以有人评述“吴派中,只跳出一个潘天寿”。对比来看,吴昌硕是“诗书画印”四绝,潘天寿诗歌创作颇丰,书画同修,唯独印章创作较少。
▲左图,《萝卜》,28岁;中图,《秋菊图》,30岁;右图,《晓霞凝练艳繁枝》,35岁
两人是师徒,更是知音。“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当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年龄相差,有前辈后辈之别,谈诗论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目前,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言语形容之概。”“缶翁晚年画竹好野战,如老将搴旗,颐指气使,无不如意,在梅道人瞎尊者以后又开一蹊径矣。”“颐指气使,无不如意”亦可视为潘天寿的创作宗旨。与传统花鸟画的路数不同,潘天寿的画给人一种霸气侧露感觉,吴昌硕一句“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给了他以最高的赞美。同样是以碑学金石笔法入画的潘天寿,与吴昌硕的做法全然不同,不特别在意追求笔墨上的霸悍和强其骨的风格,给人在画面构图上形成了自我个性。除有石涛的痕迹,亦有对李瑞清的借鉴。李瑞清把石涛画中复杂的层次简化了,将柔性线质转化为刚劲有力的线形,潘天寿在花鸟画外,兼长山水,进而创造了一种花鸟和山水相结合的体裁。潘天寿最终以雄强、霸悍、狂肆的美学范式,成为近代花鸟画坛中代表性的高峰人物。
在早期书法创作方面,影响潘天寿的尚有八大、石涛和郑板桥三人,可以找到笔意相近的作品。
▲《八哥顽石》,69岁
▲《湖石栖禽》
▲《枯石寒鸦图》,66岁
▲《拟个山僧墨鸟》
▲《拟雪个栖禽图》,56岁
▲《双吉图》
有资料记载,潘天寿背临八大几可乱真,甚至在潘天寿的传记里面讲,“有人说八大山人比不上他,他说:’哪里哪里,哪里比得上八大呢!’’画不过他,画不过他!八大山人表现事物深刻之极,以虚求实,古无二得,妙处难及,画不过他。’’落落疏疏’,很潇洒”。在潘天寿的笔下,继承和发扬了石涛与八大的艺术精神。他的革新之处决非随随便便从西画中搬来一些“热门”的技能方法或形式语言,而是从徐渭、石涛和八大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笔墨精神”,重新强化和提炼。潘天寿善于博采众长、取精用宏,不仅笔墨苍古、凝炼老辣,而且大气磅礴,雄浑奇崛,具有慑人心魄的审美张力。
▲《水仙图》
▲《颐者所喜》,62岁
▲《竹菊石图》,68岁
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充分利用了书画同源的优势;从小的方面来看,是基于对八大个人的崇拜与借鉴。八大对潘天寿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两人的画面布局奇特而又严谨和谐,笔墨简练然神完气足,甚至在取材方面,也有较多效仿承袭之意,皆喜画荷、松、鸟、石,但潘的天赋极高,并不完全止步于八大,不以简单的形似为满足,从“八大之奇”而济之以“石溪之繁”和“石涛之变”,再加上自己的独到理解,用高度凝练的多变手法强化形象,以精到的笔墨,真实而鲜明地表现出气韵的生动,乃至全新的画面,境界之高妙,气势之雄强,气格之霸悍,体现出不同寻常的阳刚之美,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人面目。八大的造型以圆为主,意象流动,但在运笔中侧锋兼用,侧峰与卧笔居多,下笔利落流畅,潘天寿则以方为主,寓动于静,造景布置颇具匠心,古松主干与危石重心向右,颇具动势,但主干上部一枝突兀转向的枝干又使逸出画外的动势折回画内,并使整个画面形成微妙的平衡。行笔多用硬毫中峰——尤其以山马笔和狼毫笔居多,笔画偏于滞重,墨色生涩苍老,体现了“强其骨”的用笔法则。潘天寿的山水借鉴八大的孤高冷峻,彻底改变了文人画末流的轻薄柔弱与玩世不恭的靡靡之风,在精神层面上与峥嵘壮阔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如前所述,有人说,潘天寿基本上得力于李瑞清,这话对也不对,不错也错,但凡大家,必定有共同的特质:其一,必定是博涉多家而集众人之长;其二,必定不甘居于人后,一定要有自我表现;其三,基于这两点,作品必定存在鲜明的风格,且有诸多的不同侧面。也许在某一阶段,会有模仿的经历,但最终必定会自成一家。六件绘画中,前五件题材相近,八哥或老鹰之类,从款字来看,异曲同工,可以看出心态的起伏变化。有的只是简单地写“拟个山僧”,多数是“拟个山僧而未似”,也有“拟个山僧未似,奈何”的感慨,单独有一件比较特别,题“偶然作画,似个山僧矣,一笑”,说明心有戚戚。有意思的是,绘画风格完全拟八大,款字却是自抒胸臆。留心不难发现,潘天寿拟八大书法笔意的款字,如《水仙图》《颐者所喜》《竹菊石图》,可谓形神兼得。潘天寿取法黄道周一路,注重虚灵之变,八大以篆书笔意写行楷,笔笔中实,通过字内空间和字与字的关系来调整行气,形成错落变化,此三桢款字皆得其要旨,神韵自显。《竹菊石图》稍变八大之法,“篱”字“隹”部的使转,乃八大标志性的夸张笔法,可见潘天寿临摹时观察体验极为细致深邃!
▲为顾坤伯《仿沈石田灵隐山图卷》题跋,30岁
▲左图,《赠中望诗轴》,31岁;右图,《山水图》,37岁
▲《普陀写景图》,3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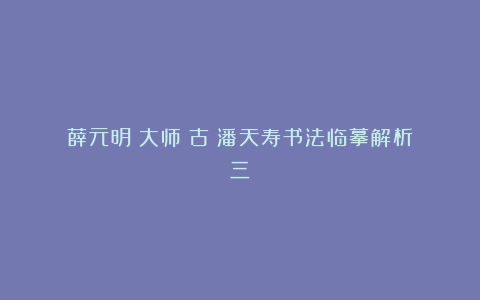 石涛和八大都是皇室后裔,前者为嫡系,后者乃旁支,相同的是,两人皆以出世避祸,佯狂为僧,在书画创作方面成就非凡,独步千古,各有千秋。石涛书法最主要的特点,一是摹古而入古,二是面目多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亦正亦奇,小楷直入钟王之室,但有些题款夹杂篆隶,又有奇古之气,故而笔意不可端倪。然而这些“野怪”路数,正对潘天寿的胃口,所选四则题款,风格跨度极大,然气息相似,否则几乎无法判断是否出自一人之手,然而却实实在在出自潘天寿笔下,可见潘天寿对于“野怪”的特殊嗜好。为顾坤伯《仿沈石田灵隐山图卷》题跋字形似颜,然用笔有米芾和徐渭的影子,但透露出来的却是北碑意趣,尤其是后半段的枯笔,几乎是“钉头”排布,可能是写生途中,笔墨无法像书斋中那样讲究,在最后一句点出“学术原贵在自见面目也”,总体上来看,心中虽有大痴,笔下却是自己的笔意。要知道,在清初画坛趋向复古,出现“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时候,正是石涛挺身而出,贬斥时弊,力求师法自然、师法古人,强调创新,对清初画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不正是潘天寿的真实写照吗?《赠中望》诗轴不见“书家笔法”,而全是书家笔意,不在意笔画精到与否,只注重自抒胸臆,故不能以寻常规矩视之,而此等意境,只有在石涛书画中可见。《山水图》题款隐约有颜真卿。米芾和黄道周笔意,就像款字中所说的“泼墨岂曾徒草草,谁知难画米家山。”可谓信手拈来,不考虑每个字笔画的精美与否,在乎的是整体感觉,不能不说,此时还是“画家意识”占主导地位。所谓“木樨开侯”,大致是在九、十月份,《普陀写景图》时间在四月十五,相距半年左右的时间,逸笔草草,洒脱之极,此时刚刚涉猎黄道周,之前所学尚未摆脱,尤其是吴昌硕的行草书影响依然很大,但大家就是大家,一时心性不同,善用短笔,依势而生,字形大小疏密一任自然,书画融为一体,而且字数很多,得力于石涛。由此可见,书家临摹的广泛性,包括读帖等等在内,拓宽眼界,提高应变能力。对于潘天寿来说,这既是书家的本领,又得力于画家的优势,但绝非仅仅只是简单的“画家字”所能概括的,潘天寿有明确而强烈的“书法意识”。
石涛和八大都是皇室后裔,前者为嫡系,后者乃旁支,相同的是,两人皆以出世避祸,佯狂为僧,在书画创作方面成就非凡,独步千古,各有千秋。石涛书法最主要的特点,一是摹古而入古,二是面目多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亦正亦奇,小楷直入钟王之室,但有些题款夹杂篆隶,又有奇古之气,故而笔意不可端倪。然而这些“野怪”路数,正对潘天寿的胃口,所选四则题款,风格跨度极大,然气息相似,否则几乎无法判断是否出自一人之手,然而却实实在在出自潘天寿笔下,可见潘天寿对于“野怪”的特殊嗜好。为顾坤伯《仿沈石田灵隐山图卷》题跋字形似颜,然用笔有米芾和徐渭的影子,但透露出来的却是北碑意趣,尤其是后半段的枯笔,几乎是“钉头”排布,可能是写生途中,笔墨无法像书斋中那样讲究,在最后一句点出“学术原贵在自见面目也”,总体上来看,心中虽有大痴,笔下却是自己的笔意。要知道,在清初画坛趋向复古,出现“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时候,正是石涛挺身而出,贬斥时弊,力求师法自然、师法古人,强调创新,对清初画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不正是潘天寿的真实写照吗?《赠中望》诗轴不见“书家笔法”,而全是书家笔意,不在意笔画精到与否,只注重自抒胸臆,故不能以寻常规矩视之,而此等意境,只有在石涛书画中可见。《山水图》题款隐约有颜真卿。米芾和黄道周笔意,就像款字中所说的“泼墨岂曾徒草草,谁知难画米家山。”可谓信手拈来,不考虑每个字笔画的精美与否,在乎的是整体感觉,不能不说,此时还是“画家意识”占主导地位。所谓“木樨开侯”,大致是在九、十月份,《普陀写景图》时间在四月十五,相距半年左右的时间,逸笔草草,洒脱之极,此时刚刚涉猎黄道周,之前所学尚未摆脱,尤其是吴昌硕的行草书影响依然很大,但大家就是大家,一时心性不同,善用短笔,依势而生,字形大小疏密一任自然,书画融为一体,而且字数很多,得力于石涛。由此可见,书家临摹的广泛性,包括读帖等等在内,拓宽眼界,提高应变能力。对于潘天寿来说,这既是书家的本领,又得力于画家的优势,但绝非仅仅只是简单的“画家字”所能概括的,潘天寿有明确而强烈的“书法意识”。
▲《兰》
▲左图,《插了梅花便过年》,45岁;右图,《墨荷》,45岁
▲《竹·其四》
▲《抱吉图》,67岁
▲《荫山阁看云》
郑板桥的书画乃至蕴藏其间的个性精神,与八大、石涛一脉相承。但凡极有个性的大家,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方能有一席之地。郑板桥以“六分半书”名世,说白了,就是篆隶行楷草的“乱炖”,褒之者谓“乱世铺街”,贬之者“四不像”、“夹生饭”。从技法方面来说,郑板桥将多体的融合明面化甚至可以说表面化,可惜未能臻于圆融之境,反观八大、石涛,哪个不是多体兼擅?八大以行书写《石鼓文》册页,以篆写行楷的高妙表现,韵味更丰。郑板桥的书法,识者深知,可观而不可学,可读而不可临,体悟其趣味可以,不易上手之外,也很容易变油。这六件款字,皆为板桥笔意,有早年之作,如《兰》有“乱石铺街”的特点,几笔兰草叶子,穿插在字里行间,更有助于形成“乱世铺街”的效果。潘天寿45岁当年的作品,如《插了梅花便过年》和《墨荷》款字,及自作诗《竹·其四》中“模糊”二字,与郑板桥的代表作“难得糊涂”对比,以及《抱吉图》末的“秋”字,笔法如出一辙,令人惊奇。《荫山阁看云》是晚年作品,除了字势的欹侧险峻之外,有几个字特别变大,无疑是郑板桥书法重要特征之一。潘天寿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心有所系,再次看到潘天寿在书法上的“反刍”现象。不难看出,学郑板桥确实容易变油,有太多的“信笔”成份。也有资料说,潘氏的早年行书,吸收了高凤翰左笔书之意趣,很可能是某种“暗合”,或者说,潘天寿对于“八怪”书风,存在一种默契之情。
如果只限于款字分析而言,那潘天寿的书法只能被称为“画家字”。书家必定要有专门的“代表作”。“扬州八怪”当中,有些人只是以画名世,书法只能见到题字,真正见书法功夫的当数金农、郑板桥和高凤翰,黄慎稍少一些。归根结底以作品说话。潘天寿专门的行书作品从35岁到70岁,时间跨度近三十五年。被再三强调的是,诸多作品有明确的时间款,可以清晰地看出变化脉络,实践了“一家为主,多家为辅”的宗旨,其中,“一家”就是黄道周,“多家”则需要结合具体的作品来探讨。
▲“懒秃寿者草草”款,笔法毛糙
▲录《清平乐·六盘山》
▲录汤显祖《暮江图》
潘天寿行书的个性,主要来自黄道周。黄道周书法既有晋人书法的气度和韵味,又蕴藏汉隶奇逸雄迈的特点,笔法方圆並用,自成一家。黄道周自谓:“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厚,不坠佻靡,便足上流。”潘天寿青年时期就致力学黄道周书法,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心契神会,志趣相投。潘天寿最为看重人品,一贯认为“人品不高,落墨无法”,由此可知,潘天寿长期取法黄道周,特别喜欢《榕坛问业》,反复临写,爱不释手,不仅在于学其书法,更是学其为人。取法黄道周不仅是潘天寿立基之功,也是行草变化之关键,以隶写行,正如张怀瓘评黄道周书法:“或寄以骋纵横之态,或托以散抑结之怀;虽至贵不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尽其力。”除了黄道周,明末书家中潘天寿还倾心于倪元璐、张瑞图等。潘天寿书法走得是险峭劲厉的路数,崇尚阳刚气与金石气。笔画多为方笔,结体上学倪黄,再进一步融入小爨笔意,形成了险峻高冷的面目。因为书法特殊的个性,他的画给人以霸气之感。
▲临黄道周《登岱诗》手札等
▲临黄道周《榕坛问业》
先看对临黄道周的作品。这是潘天寿目前所见仅有的对临之作,可见潘天寿对黄道周书法的重视。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还认真地一字一字地临摹黄道周的字帖。所临《登岱诗》等四页呈现了完整的临摹过程,涵盖黄道周自作诗和手札若干,没有遵从原有的章法样式,完全是从节约纸张等实用态度出发,内容很难释读,原因在于一些字的“重复”——在临习过程中,写的不满意的字,觉得没到位的,就重新写,极为严谨。有时一个字连续写几遍,最多达到七遍,直到写好为止,再换另外的字。潘天寿虽然“自以为天分不差”,但一直牢记了吴昌硕对他的劝勉,功力积累必须到位。直至暮年,还对八大的花鸟、黄宾虹的山水临写不辍。临《榕坛问业》虽未见时间,依据风格和笔力来看,应该是中年之后作品,笔断意连,起收干净利落。此时虽然风格已经成熟,但仍然忠实于原帖。潘天寿虽受黄道周影响很深,重在取其精神,并不以成法自囿。黄书圆笔多于方笔,潘书则方笔多于圆笔,侧锋为主,黄书字势一致,行距疏阔,行气整齐,潘书则字形大小变化错落,往往随势倾侧左右,趋紧凑以侧取势,行距时疏时密,追求“险绝为奇”。
▲“娴将会心”对联
▲《雁荡纪游诗》
再来看拟黄道周笔意作品,可以更加立体、清晰地感受潘天寿的化合功夫。“娴将会心”对联堪称潘氏的经典代表作,结字有黄道周的欹险生姿之变,笔画则有北碑的凝重遒厚之意,隐约可以看到徐生翁的痕迹——也许这是一种“暗合”。不过,这种“联想”在临摹过程中非常重要,可以打开思路。虽然是对联,不以字形等大和对称均衡为要旨,如“落墨”二字的挤压,“会、居”二字的撇捺画极力舒展,上联末“鱼”字欹斜生势,动感十足,下联末“诗”字复归平正,既对应了“平仄”音韵,字形安排上也形成强烈对比。《雁荡记游诗》长卷有数稿传世,既有草稿,亦有抄录稿,此作当为后者。可见潘天寿对黄道周乃至整个晚明书风的钟情,即便到了晚年,仍有回归,原汁原味地用黄道周的笔法来创作,少了凌冽之风,气息平淡古雅,准确来说,是黄道周、倪元璐和张瑞图的“合体”,对晚明书风有准确地演绎。潘天寿书法筑基于黄道周、张瑞图、小爨,多见险峭劲厉之气,与他崇尚阳刚、金石气的审美倾向一致。但与一般取法黄道周、张瑞图者注重书法本身完整有序的“相似”大不同,潘天寿有时会站在绘画的空间设计和视觉立场来把握和取法。在保持黄道周、张瑞图紧峭幽折、方笔翻绞特点的同时,笔法更趋铦利、破碎、断裂,一如其山水画的大斧劈,具有画法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章法上的不断造险、破险,则使他的书法具有一定的空间紧致感。潘天寿改变了黄道周书法纵向的空间节奏构成,一变为“散点式”的绘画视觉空间节奏,结字服从章法要求,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起初会关注整体感,其次才会考虑释读内容。
潘天寿的人生历程如果从艺术求索的角度加以归纳,最主要的时间短划分有:14岁—19岁,高小读书阶段;19岁—24岁,师范学习阶段;24岁—26岁,执教小学阶段;27岁—31岁,上海历练阶段;32岁—52岁,风格形成阶段;53岁—60岁,成熟融合阶段;61岁—69岁,成就辉煌阶段;70岁—75岁,蒙难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自1928年起,潘天寿定居杭州近十年间,主要受到黄道周、倪元璐、八大山人、石涛、沈曾植等人书风启发,系统性地兼取碑帖之长而变法成功,形成雄强恣肆、奇倔刚劲的独特书法风格。而立之年是一个起点。综合来看其行书创作作品的分期,大致有35-40岁,41-50岁,51-60岁,61-70岁等四个基本阶段,可以与前面的一些题款作品可以结合起来看,“书法意识”此后日渐明确,最终也改变并塑造了款字风格。
▲左图,《观濮水亭厂》,35岁;右图,《立春偶成》,36岁
▲苏轼诗三首,36岁
▲《雪中三首·其一》,36岁
▲《书旂仁兄以近作画册属题》,36岁
▲《夜归竹口四首·其二莫干山》,38岁
35岁所书《观濮水亭厂》自作诗较特殊,明确取法黄庭坚的影子,如“水”字极其明显,底子则是颜字。从36岁的作品开始,黄道周书法的因子就占主导地位了,自此相伴终生,而且这一年的作品很多,颇有说服力。字形开始变得跌宕,但刻意夸张之笔很少,实笔居多。《立春偶成》与黄道周书法最似,《苏轼诗三首》有沈曾植笔意,《雪中三首·其一》有徐生翁笔意,《书旂仁兄以近作画册属题》手札纯用方笔,提按减少,连笔仍较少,到了38岁时《夜归竹口四首·其二莫干山》斗方,风格已然有了变化,连笔增多,有个别字形开始有意夸张放大,且上下字形有时不在一条轴线上,而是左右摆动,已经出现了后来的成熟特征。
▲左图,录黄景仁《山馆夜作·其一》,41岁;右图,《秋夜》,42岁
▲左图,《秋意》,44岁;右图,《登燕子矶感怀·其一》,45岁
41-50岁这一阶段,风格有了突变,黄庭坚书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黄庭坚和黄道周有一定的共同点,就是字形的处理跌宕多变,个别笔画开始着意延展拉长,如41岁书黄景仁《山馆夜作·其一》,有时也会有所回归,如42岁《秋夜》就展现了融合起伏的过程。到了44-45岁期间,笔画的收放对比更加强烈,如“天”字的处理,两横画几乎等长,一同缩短,撇捺画极力夸张。《登燕子矶感怀》中“无”字的夸大,使左右两列形成有效的“联结”,既有纵向上的气势和对比,又有横向上的关联和默契。这显然是从题款中借鉴来的,不仅书法对绘画产生影响,尤其是篆隶书,绘画也对书法产生了影响,书画同修的优势显现出来了。
▲左图,《论画绝句·其三》,45岁;右图,《夜宿普陀息耒禅院南楼·其二》,45岁
▲左图,《听天阁画谈随笔》,47岁;中图,《过桃源车中口占》,48岁;右图,录弘一法师语,50岁
但凡有技法的人都知道,字幅中夸张的笔画,易于让人关注,但如果因此造成局部影响到整体,显然是失败的,必须有整体感。得益于多方探索,避免形成习气。47岁所作《听天阁画谈随笔》用的都是短笔,令人耳目一新。大家必然有多种尝试,深得“计白当黑”之妙。48岁《过桃源车中口占》和50岁录弘一法师语,不仅考虑字形上下之间有左右腾挪的关系,也考虑到左右结构字形的错落关系,使得整体上更加跌宕多变,但一定要避免过于支离破碎,以及人工安排痕迹太重。
▲左图,《春雨》,52岁;右图,《盘龙寺看梅·其二》句,52岁
▲左图,录韩偓《春尽》句,55岁;右图,《咏兰·其四》,55岁
▲左图,《雁荡杂詠》,59岁;右图,《为显道上人作》,59岁
五十岁之后的字迹,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字形内部的疏密,字与字之间,整体的协调观感都是综合考虑的,这是个人对书法的要求。作为一个大家,各方面的修养火候基本到了,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必要的支撑力和内驱力,眼高手低必然达不到想要的境界,必须“眼高手高”方能如意。比如52岁《春雨》款字位置,就非常讲究,也是作为一个有强烈个性的画家区别与单纯的书家之处。从52到57岁这一阶段中的作品,字形之间的连带减少了,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左右结构的左高右低或右高左低,或者将字形压扁,独体字则瘦长处理,有时更为开张,完全是一种感觉和意念,借助熟练的经验,达到一种和谐,即便某个字突然夸大,也不觉得突兀,反而成为作品之“眼”。其实无论书法还是篆刻,营造出独特的风格和韵味是一个目标,但前提是,不能以损伤文字本身的美为代价,否则将适得其反。前文曾经提到过郑板桥的“油”,以及一些“信笔”,就是犹不及如果控制在一定的尺度之内,就是“随意自然”。
▲《十六字令》,64岁
▲“天飞雨过”,66岁
▲左图,录韩偓《已凉》句,66岁;右图,录陆游《书愤五首·其一》句,66岁
▲左图,《清平乐·六盘山》句,67岁;右图,《十六字令》,70岁
过了花甲之年的潘天寿,作品一一不同,可以捕获不同创作状态中微妙心理的起伏变化,最典型的如“天飞雨过”对联,既有碑学的厚重,又有黄庭坚的开张,兼有米芾的“刷”的韵味,还有一些徐渭的“奇崛”,有如此“张扬”的个性,但看上去特别“随意”。虽然是笔笔夸张,字字变形,但感觉愈加新鲜,做到了“入古出新”。款字安排是典型的绘画题款手法,形成妙趣横生的疏密对比,随心所欲,字形大小磊落,夸张对比强烈。此时在书写内容上有明显的变化,除了抄录古典诗词外,毛泽东诗词内容增多,成为特殊时代的“护身符”,“何时缚住苍龙”的“何”特别大,凸显了内容主旨。《十六字》三首,64岁写了一首,70岁写了两首,内容不同,风格拉开了距离,显然是有意的。第三件有了王铎风韵,最典型的就是“字团”的出现,很多字形紧缩夸张,截然不同于原来的以笔画伸展来夸张,形成别致的“疏密”对比。“字团”形成了块面效果,同样是对绘画技法的有效“化”用。王铎是通过“涨墨法”来实现“块面”的经营,也是出自画家的技法,使得书法在点线之外又有了“面”的对比,从而深化了韵味。用笔在画面上所表现的形式,不外乎点、线、面三者,“点”比如短笔和粗笔,“线”是笔画的延展,“面”是字形紧缩,形成“团”,也就是“块面”。“画事用笔,不外点、线、面三者,然线实由点连接而成,面亦由点扩大而得,所谓积点成线,扩点成面是也。苦瓜和尚云:’画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一笔也。即万有之笔,始于一笔也,盖吾国绘画,以线为基础,故画法以一画为始也,然而点却系最原始之一笔,因线与面实由点扩积而得也。故点为一画一面之母。”在书写节奏上的把控,古法就是最好的导向。潘天寿行草多为侧锋方切和侧带中或中带侧的用笔,大多是侧锋起笔,增加了用笔的灵活和字势的飞动。除了少数笔画被夸张拉长,或辅以牵丝连带外,点画皆短促斩截,随着起笔转锋动作顺势而过,或收锋或出锋,或折锋转入下笔,极少藏头逆锋和圆转形态。
▲《十六字令》,70岁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提倡原创,转发即鼓励
|